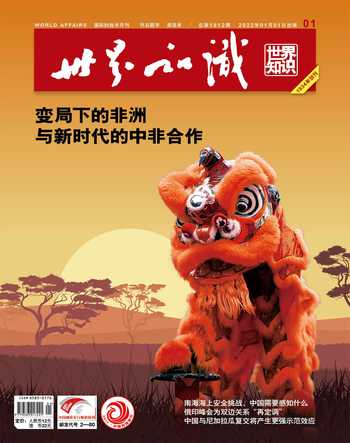在低谷中徘徊的世界經濟(上)

江瑞平
身處百年大變局中的世界經濟,在2008年遭遇金融危機后,已被推到了十字路口,且始終未能重回正常軌道,而到2020年遭受新冠疫災沖擊后,更是被推到了戰后最嚴重的衰退之中,目前雖已顯現“補償式”反彈態勢,但因面對諸多“兩難選擇”,只能在低谷中徘徊不前、搖擺不定。
防控疫情還是恢復經濟 時至今日,疫情仍在世界各地肆意蔓延,一些國家甚至到了近乎失控的狀態。防控疫情依然是全球面臨的首要任務,為此只能減少人員流動,這樣物流也會受到阻礙,由此導致生產鏈條斷裂,引發嚴重經濟衰退。2020年全球經濟增長率驟降至-3.1%,創下戰后最嚴重衰退紀錄。其中發達經濟體更降至-4.5%,最嚴重的歐洲國家如西班牙和英國,更分別達到-10.8%和-9.8%。經濟衰退導致失業劇增、收入驟減、貧困加重,引發諸多社會問題,甚至導致社會動亂,因此人們期待能盡快恢復經濟。于是就在防控疫情與恢復經濟之間,形成了顧此失彼的兩難選擇。許多國家都深受其苦:一會兒優先防控疫情,不得不先把經濟問題放在一邊;一會兒優先恢復經濟,又導致疫情反彈。如此在“收緊”與“放松”之間反反復復、搖擺不定的直接后果,是“兩難選擇”造成的“雙重苦難”,許多國家深陷其中難以自拔。
促進增長還是健全財政 世界經濟走出金融危機、步入回升不久,就遭遇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沖擊,陷入金融危機與財政危機的惡性循環之中,這也成為回歸正常增長軌道的最大阻礙,從而導致與金融危機前的增長水平漸行漸遠。疫情暴發后,在紓困政策耗費大量財力、經濟萎縮導致稅收銳減的同時,不得不采取緊急對策以刺激經濟復蘇,由此導致本已十分嚴峻的財政狀況進一步惡化,既將以往健全財政的努力付諸東流,又使未來健全財政的路途更加艱難。由此形成促進增長抑或健全財政的“兩難選擇”。2020年美國、日本、歐元區和英國的財政赤字與GDP之比,分別攀升至15.8%、10.1%、7.2%和12.4%,遠遠超出國際公認警戒線(3%)。另一警戒線——累計公共債務余額與GDP之比也達到60%,超出一倍以上,發達經濟體更是平均達到126%。財政危機進一步深化,成為后疫情時代世界經濟穩定發展面臨的重大問題。
增加就業還是抑制通脹 疫情導致社會經濟活動全面停擺,引發嚴重失業問題。2020年第二季度,美國的失業率攀升至兩位數,4月份竟高達14.8%。為刺激增長、增加就業,不得不連續推出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且規模空前。但由此又引發了日趨嚴重的通貨膨脹。如美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2021年5月攀升至5%以上,歐盟正逼近4%,俄羅斯已突破7%,巴西更是逼近兩位數。更加嚴重的是,此次通脹的產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疫情導致供應鏈斷裂所致,加重了市場供求錯配,而恢復供給能力則需更長時日。這意味著世界經濟在走向“補償式”回升的進程中,宏觀政策正面臨“菲利普斯式”兩難困境——增加就業需要擴張而抑制通脹則該緊縮,運作空間受到嚴重擠壓。
回歸實體還是數字轉型 數字轉型是世界經濟在百年大變局中的重要變化趨向,勢不可擋且不可逆轉。目前無論是疫情防控,還是經濟復蘇,數字治理都功不可沒。但數字經濟又往往與虛擬經濟結伴而行,過度虛擬化極有可能誘發嚴重泡沫化,損害經濟有機體健康循環和穩定運行,甚至有觀點認為,2008/09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就是其直接后果之一。于是,回歸實體又被提上了各國經濟發展與產業優化的重要議程。正確選擇應該是努力形成強化實體與數字轉型的相互支撐、良性互動,但現實中又常常會面臨著相互脫節甚至背離的風險,由此也加大了世界經濟在回升進程中的不確定性和政策選擇的難度。
專注回升還是綠色發展 全力防控疫情,盡快恢復經濟,無疑是全球面臨的當務之急。但疫情造成的深重生命健康危機,也再一次警示人類,必須更加關注經濟社會發展與自然環境保護的和諧共進,應對氣候變化也變得越來越刻不容緩。但氣候行動是需要成本和代價的,包括在一定程度上犧牲經濟增長,尤其是那些對自然環境破壞嚴重的產業發展。于是,在優先復蘇經濟與注重綠色發展之間,一定程度上也是“兩難”。正確選項顯然是兼顧經濟復蘇與綠色發展,這本身也是全球性議題,更是大國不可推卸的責任。令人欣慰的是,在剛剛結束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格拉斯哥大會(COP26)上,《中美關于在21世紀20年代強化氣候行動的格拉斯哥聯合宣言》正式發布,給刻不容緩的綠色復蘇帶來一抹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