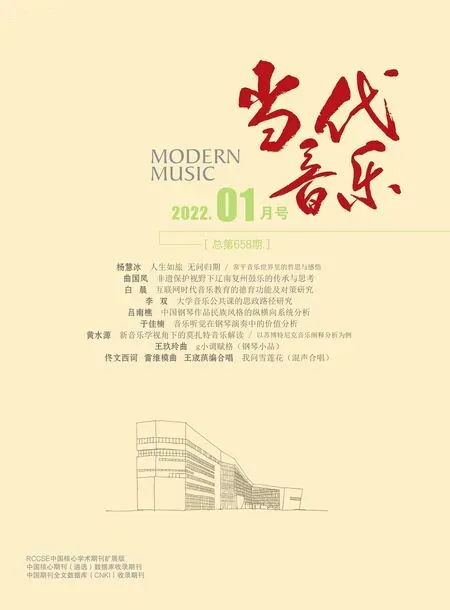音樂劇《國之當歌》戲劇情節(jié)結構的審美特征
楊亞冬
《國之當歌》是上海歌劇院推出的一部以人民音樂家聶耳藝術經歷和《義勇軍進行曲》的產生過程作為題材的音樂劇,旨在從人物性格展現和形象塑造的角度出發(fā),彰顯聶耳為國而歌、為民呼吁的時代精神。[1]此劇構思于2009年,并于2011年與觀眾見面,在接下來十年的時光中公演100余場,其間在音樂、情節(jié)、舞美、舞蹈等方面歷經數次雕琢,成為當代音樂舞臺劇的精品之作。由于此劇在思想性、藝術性、教育性方面均取得了高度的成就,于2018年獲得國家藝術基金滾動資助,得以廣泛推廣。[2]本文以此劇的戲劇情節(jié)結構作為探討對象,著意從結構特點、敘事筋脈、思想深度、沖突特點、懸念設計技巧五個方面談談審美特征,以便能夠對此劇在情節(jié)結構方面的藝術個性有一個充分的認識。
一、傳統(tǒng)戲劇情節(jié)結構的二重性
音樂劇作為一種舞臺藝術形式,戲劇在其中占有很大的分量,尤其是在情節(jié)安排和結構的處理上是否得當,對作品主題的呈現和人物性格、形象的塑造起著關鍵性作用。通過對許多經典的音樂劇作品分析可以看出,諸如《悲慘世界》《日落大道》等作品均在戲劇情節(jié)結構方面有著精巧的布局、明朗的情節(jié)線條,這也是它們能夠成為經典音樂劇作品的重要原因。《國之當歌》作為一部主旋律式的時代作品,劇中人物以及人物所處時代的歷史背景均為人們所熟知,編導正是根據這一特點,[3]在情節(jié)結構的安排上遵循了歷史和社會的發(fā)展規(guī)律,運用了傳統(tǒng)戲劇情節(jié)結構將人物特點、人物關系和典型事件進行了綜合性呈現,總結其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開放漸進式結構特點。作品由序場、七個主場構成。其中序場情節(jié)表現的是聶耳去世五年后田漢和黎錦暉對昔日朋友兼同事的追憶,七個主場的標題分別為“海上明月”“市井歌聲”“浦江風暴”“街頭怒火”“劇社風波”“風云兒女”“血肉長城”。除了序場之外,七個主場均采用了時間過程和事件發(fā)展的線條式結構手法,在兩者的漸進式進行中突出了聶耳的思想進階歷程。在空間結構的設置上,宏觀上呈現出內外轉換的特點,從明月劇社到滬上街頭、從市井家院到港灣碼頭,在空間場景的自由化轉換中使不同的情節(jié)環(huán)環(huán)相扣,引人入勝;二是網絡化編織結構特點。主要體現在人物形象塑造、人物關系和情節(jié)設計的關系方面。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作品主要是突出聶耳愛國憂民的情懷,在情節(jié)設計上則表現為對底層人民的人文關懷和在民族遭受危難時的英雄情緒展現。如他對長庚一家的同情、對民眾遭受日寇欺辱時的那種義憤填膺的精神等均是通過細致的情節(jié)描寫進行塑造。在人物關系上,聶耳與田漢之間的合作關系、與黎錦暉之間的師生關系以及與小莉之間的愛情關系等均建構在以國家、民族為重的基礎上,正是這一“基礎”的存在,成為整個作品情節(jié)網絡的中心點,各個情節(jié)均是圍繞這一“基礎”而形成結構的向心力。

二、主題統(tǒng)一性的多元敘事筋脈
敘事筋脈是形成情節(jié)結構的基礎,也是情節(jié)安排的具體化、針對化,它直指在情節(jié)中所體現出的思想,并以藝術化的表現手段作為前提。《國之當歌》雖然在主題思想的表達上具有唯一性和獨立性,但是在整體的敘事過程中則具有多元復合型的特征。縱觀作品的敘事筋脈,則著重體現在人物關系敘事、人物情感敘事和音樂背景敘事三個方面,正是因為這三個方面的存在,使得作品具有史實可信性、情感真摯性、角色塑造藝術性的特質。
首先,在人物關系敘事方面,作品中出現的諸多配角均與聶耳有著直接或者間接的關系,如聶耳與黎錦暉之間的關系則屬于直接關系,他們在藝術上為師生、同事關系,然而在大時代背景下為了實現民族救亡的理想又間接形成了志同道合的關系,他們之間數種關系的現實存在融入于不同的情節(jié)之中,為主題思想的呈現構成了第一道敘事筋脈;其次在人物情感敘事方面,作品通過對聶耳與不同人物角色的接觸和相互之間所發(fā)生的故事,使作品的主題表達更加的深刻和有力度。如聶耳與小莉之間的愛情敘寫,就是一名無產階級文藝戰(zhàn)士和社會底層舞臺演員在抗日救亡背景下的真情流露,這種真情既是不屈不撓的個人愛情,更是一種相互扶持、共赴國難的階級情誼,因此作品中情感敘事筋脈使主題思想鑄就的有深度、有濃度。再次,在音樂背景敘事方面,音樂劇創(chuàng)作者有意識的采用原創(chuàng)、移植、改編等手法增強了情節(jié)的真實性和藝術性。此劇在性質上屬于音樂劇,同時又是一部以人民音樂家藝術經歷和思想經歷為題材的作品,所以對于創(chuàng)作者來說,如何使劇中的音樂具有史實特點和藝術特點,則體現出了創(chuàng)作者對歷史、對人物、對藝術的敬重和真知灼見。在原創(chuàng)作品方面,《天才的隕落》(田漢與黎錦暉的二重唱)、《愛的漣漪》(聶耳與小莉的二重唱)、《我能做什么》(聶耳的詠嘆調)等歌曲具有西方古典主義時期意大利正歌劇的表現特點;《上海是個夢工廠》《踏浪飛揚》這兩首合唱歌曲則運用了爵士音樂、探戈舞曲元素,表現出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滬上風情。其它改編、移植的作品如《毛毛雨》《賣報歌》《畢業(yè)歌》等不僅是劇中人物的代表作品,象征性的闡釋了聶耳、黎錦暉在音樂史上的貢獻,并通過對這些歌曲創(chuàng)作背景的敘寫和音響展示,為最后《義勇軍進行曲》的出現和主題的點名做好了深厚的鋪墊。
三、人物性格展現的思想深度
戲劇表現的目的是在特定環(huán)境背景下通過對典型人物的性格塑造而達到主題的烘托與呈現,因此如何在情節(jié)結構中去突出人物的性格,應當是戲劇的主要人物。一般而言,音樂劇不同于場面宏大、劇情起伏復雜的大歌劇、正歌劇,也不同于話劇那種純語言化和純動作化的塑造。所以用音樂劇的方式去突出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具有一定的挑戰(zhàn)性。在這部作品中,聶耳性格的塑造和展現過程可以說是圍繞主題思想生成而展開的。通過不同場景的敘述和情節(jié)的貫穿讓我們認識到了一個有志青年的形象。
筆者認為,在聶耳性格展現的思想深度上,有兩個方面可圈可點。一是為了藝術追求而不懈怠的性格。在第一場中,聶耳還是一個來自云南偏遠農村、初出茅廬的音樂工作者,他一邊在明月劇社擔任作曲工作,一邊又不斷加強自己的業(yè)務學習。如他為了能夠使歌唱演員充分地發(fā)揮出自身的歌唱優(yōu)勢和表演特點,在未經黎錦暉的同意下擅自改動了樂譜,他的這一行為正體現出了他對藝術負責的態(tài)度,雖然在劇中聶耳和黎錦暉之間是師生關系,但是為了藝術他始終堅持著自己的觀點。在業(yè)務上,他為了能夠提升自己的演奏和作曲水平,不惜當掉大衣的代價購置了一把小提琴,并堅持每天練習,由此呈現在人們面前的是一個積極向上的時代青年形象。二是為了民眾疾苦而創(chuàng)作的性格。聶耳之所以能夠創(chuàng)作出諸多反映民眾疾苦和呼吁人們敢于斗爭的作品,這與他能夠深入到人民群眾中間汲取創(chuàng)作素材有著很大的關系。在第二場《市井歌聲》中,當報童毛娣的報紙被小混混搶去之后而無法交付房租受到家人的斥責時,聶耳雖然不能從物質上去幫助毛娣,但義憤填膺為其創(chuàng)作出了《賣報歌》,以一己之力幫助她渡過難關,撫平心靈上的創(chuàng)傷;在第三場《浦江風暴》中,聶耳為長庚伸張正義,斥責包工頭,在與廣大底層勞工的接觸中了解到人民的生活現狀,為此他創(chuàng)作了《碼頭工人歌》。正是由于聶耳這種深入人民生活的采風活動,才能創(chuàng)作出反映時代的歌唱,也筑就起了一座座藝術高峰。從以上的論述中可以看出,《國之當歌》之所以在思想性方面能夠取得很高的成就,主要原因在于對人物性格思想深度的挖掘和探索。當然這種思想的深刻性則具體的融入于各個情節(jié)之中,而各個情節(jié)之間的貫穿、結合與有機聯(lián)系則是作品思想性形成的關鍵。
四、矛盾沖突的連續(xù)性和節(jié)奏性
矛盾沖突作為戲劇情節(jié)的核心內容,對于推動情節(jié)發(fā)展和完善戲劇結構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特別是對具有史實性、主旋律式的戲劇作品,觀眾對其情節(jié)矛盾沖突的展現有著很強的期待。《國之當歌》中的時代背景、人物背景可以說是形成矛盾沖突的根本所在。[4]從時代背景看,此時正處于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和中華民族頑強反抗、為爭取自由而努力的時代,而發(fā)生地上海則又是當時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重點覬覦區(qū)域,所以這為矛盾沖突的產生奠定了現實基礎。從人物背景看,無論是作為主角的聶耳還是劇中以田漢、黎錦暉、小莉為代表的文藝工作者,或者以長庚、毛娣為代表的勞苦大眾,他們心中都對現實的疾苦有著深刻的體會,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更是充滿了仇恨,由此而形成了戲劇矛盾沖突的社會基礎。
在此部作品的情節(jié)結構中,矛盾沖突的特點主要表現在連續(xù)性和節(jié)奏性兩個方面。從連續(xù)性上看,音樂劇中的每一場雖然建構于同一個標題下,但是在情節(jié)發(fā)展和相互的聯(lián)系中卻處處存在沖突。如在第四場《街頭怒火》中,作品通過多媒體視頻展示和LED燈光、舞美的輔助下展現出了日寇侵略上海的場面,以此激發(fā)出了民族的仇恨,接下來賣唱女的內心抒發(fā)、遭受侵略后民眾的動作和情緒展現以及聶耳的伸張正義依次在舞臺上呈現,使矛盾沖突在角色表演中層層推進。在矛盾沖突的節(jié)奏性上,作品則遵循了戲劇節(jié)奏松緊有序、強弱有致的結構布局原則,對人物性格與形象塑造、情感的起伏變化起到了很好的襯托和發(fā)展作用。如在第五場《劇社風波》中,開場曲《桃花江》在風格上輕柔、曼妙,當舞臺上的人們沉浸其中時,聶耳的出現和對創(chuàng)作、表演人員的強烈職責將矛盾沖突推向了高潮,也使情節(jié)氣氛達到了緊張的制高點上,這種一松一緊的節(jié)奏對比有效地推動了情節(jié)的發(fā)展。在第七場《血肉長城》中,通過《戰(zhàn)爭必將終結》《搖籃曲》《血肉長城》《振奮中華的歌》等不同體裁、風格歌曲的層層鋪墊,最終引出《義勇軍進行曲》,這種“由弱漸強”的情節(jié)沖突安排對于主題曲的出現和主題思想的升華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意義。
五、結構安排中“懸念”出現的技巧性
在現實生活中,群眾對聶耳和《義勇軍進行曲》的產生背景可以說十分熟悉,但是對聶耳本人的藝術經歷、性格特點、愛恨情仇以及《義勇軍進行曲》的創(chuàng)作細節(jié)可以說不能娓娓道來。音樂劇《國之當歌》可以說在情節(jié)設計上正是從群眾渴望的心理角度出發(fā),以細節(jié)描述的途徑向人們對聶耳和《義勇軍進行曲》進行了介紹。在戲劇創(chuàng)作情節(jié)結構安排方面,創(chuàng)作者對“懸念”的設計和出現可以說有著很強的技巧性。戲劇懸念是創(chuàng)作者在編劇過程中從觀眾心理期待角度而進行的一種對情節(jié)結局難料的安排,起著吸引觀眾興趣的作用。在此部作品中,創(chuàng)作者主要運用了期望式懸念設計和突發(fā)式懸念設計兩種技巧。

期望式懸念指的是觀眾對戲劇人物的角色定位和人生經歷已經有了初步的了解,但是對于具體人物角色應該如何表現和經歷細節(jié)還并不熟悉。創(chuàng)作者從觀眾的心理期待出發(fā),設計了聶耳與黎錦暉、聶耳與小莉兩對人物關系,通過他們之間的關系對情節(jié)進行了期望式的設計。如聶耳與黎錦暉的關系具有史實性,但是并不知道在他們身上有哪些故事發(fā)生,于是在第一場《海上明月》和第五場《劇場風波》中通過兩人的矛盾沖突發(fā)展讓觀眾對他們的性格特點有了充分了解。在劇中,聶耳與小莉之間為愛情關系,雖然部分情節(jié)為虛構,但正是通過兩個人的關系才有力地說明了聶耳憂國憂民、為民而歌的情懷,使觀眾對聶耳的個性精神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突發(fā)式懸念指的是在對情節(jié)發(fā)展保密的情況下讓觀眾為之驚奇的戲劇效果,這種懸念的設計不僅可以更為有效地增強戲劇張力,而且也是矛盾沖突發(fā)展至高潮的動力。如第四場《街頭怒火》中聶耳與日寇之間的沖突、第五場《劇場風波》中聶耳與小莉、黎錦暉之間的沖突等均是突發(fā)式懸念的情節(jié)設計,無論是對于戲劇發(fā)展和滿足觀眾心理期待都具有積極的意義。
結 語
音樂劇《國之當歌》在戲劇情節(jié)結構審美特征表現方面可以說是全面性的,同時也具有個性。它的全面性主要是遵循了戲劇結構布局的原則和規(guī)律,符合戲劇藝術性創(chuàng)作和表演的要求。在個性方面,其戲劇情節(jié)結構主要是建立在主題思想的基礎上,從當下音樂劇創(chuàng)作現狀看,以主旋律作為題材的作品可謂不多,然而能夠體現出深刻思想性和高度藝術性的作品更是鳳毛麟角。此劇在尊重史實性的基礎上,通過情節(jié)結構的合理安排和有機貫穿讓人們認識到了一位人民音樂家的心路歷程和藝術追求,以及他那不斷開拓進取、銳意創(chuàng)新的時代精神和人格特質。因此,《國之當歌》的出世,可以說對當代中國風格音樂劇的創(chuàng)作具有引領性的意義。
注釋:
[1]徐文正.國之當歌 浩氣長存——音樂劇《國之當歌》評析[J].人民音樂,2018(11):24—28.
[2]董 芳.原創(chuàng)音樂劇的演唱分析與指導 以《國之當歌》為例[J].音樂愛好者,2020(10):45—50.
[3]孫 磊.精益求精,力爭打造中國原創(chuàng)音樂劇精品——國家藝術基金專家為《國之當歌》把脈[J].歌劇,2018(08):68—70.
[4]《歌劇》編輯部.“人民需要這樣的藝術”——音樂劇《國之當歌》晉京獻演綜述[J].歌劇,2014(1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