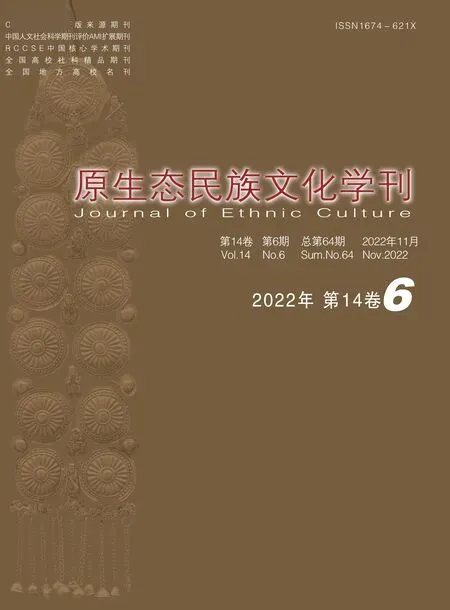從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視域看非漢民族祖源英雄
——評秋陽先生的《蚩尤與中國文化》
張中奎,吉力使呷
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而這樣一個由多民族共同組成的大家庭中,每一個民族都有著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在不同民族的文化記憶中,人們往往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來獲得成員之間的身份認同。除了我們所熟知的諸如共同的地域、共同經濟生活、共同的語言等因素外,追憶共同的祖先也是增強各民族成員之間的認同感與凝聚力的重要方式。當然,各民族的認同與中華民族的認同是不同層次的認同,兩者之間并不矛盾,甚至可能出現重合。誠如費孝通先生所言:“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1]1
秋陽先生2015 年出版的《蚩尤與中國文化》(以下簡稱“秋著”)是研究蚩尤與中國文化的杰作,分為上編“蚩尤新論”與下編“苗族文化及其他”兩部分。秋著上編“蚩尤新論”收錄了11 篇論文,下編“苗族文化及其他”收錄了12 篇論文。本研究主要聚焦于上編“蚩尤新論”,與秋氏展開學術對話。秋氏數十年在研究蚩尤與中國文化關系中發表的多篇文章,論述了華夏創世之謎、早期華夏文明的多元性、蚩尤與良渚文化、黃帝與紅山文化、夷夏之間的競爭互補以及蚩尤在中華文化發展史的重要地位,匯集了秋氏對于蚩尤與中國文化的學術創見。
蚩尤為上古時期九黎部族的首領,與炎帝、黃帝處于同一個歷史時期,率領其部族在黃河中下游與長江中下游一帶活動,創造了璀璨的良渚文化,秋著將其與炎帝、黃帝同稱為“中華三祖”。在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的背景下,我國作為一個文化多樣的中華民族大家庭,秋著恰好為我們再現了蚩尤這個代表了少數民族祖源的中華民族精神共祖形象,論證了中華文化與中華文明的多元性。秋著非漢民族從祖源英雄蚩尤入手,論證了中華民族的發源地并不是單一的,而是由多個作為文化單元的支流交融匯合,最終形成了“有容乃大”的中華文化與文明。就《蚩尤與中國文化》這本專著而言,目前與其展開學術對話主要有石朝江、陳曉軍等。石朝江的《讀秋陽先生〈蚩尤與中國文化〉》一文認為,這部著作在蚩尤與中國文化研究方面,具有三方面的亮點和創新:一是研究論證中華文明中華文化的多元性;二是研究論證中華文明的兩大源頭文化;三是研究論證蚩尤對早期中華文化的卓越貢獻[2]。陳曉軍的《從秋陽先生的〈蚩尤與中國文化〉看“中國故事”的當代表述》一文認為,對“黃帝戰蚩尤”的表述實際上是一個對歷史遺產的繼承問題,事關多民族國家族群關系的整合,值得我們檢討與思考。《蚩尤與中國文化》在表述“中國故事”中體現出的地理生態的多樣互補、文明發生的多源交匯、族群種類的多元交往、歷史沿革的交錯連續等視角,對我們深化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認識,促進中國各民族和諧共處,以增強多民族國家的凝聚力不無啟發[3]。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作了以“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推動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講話,闡明了在國家復興強盛、中華民族文化日漸繁榮的新時代背景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必要性。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必須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的主線,推動各民族堅定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高度認同,不斷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4]為進一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升各族人民的中華民族自豪感,我們要通過樹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民族文化符號和中華民族祖源英雄形象,不斷夯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思想基礎。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基礎,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文化是人類行為的意義編碼體系,是社會運行的“軟件”,給一個群體以身份認同和歸屬感[5]。秋氏認為:“中華民族及其文化的發祥地,不止是黃河流域,甚至遍及長城內外、大江南北,東起大海之濱,西迄青藏高原,整個中華大地幾乎都有中華先民活動的遺跡及其所創造的文化。……時至今日,仍有固執一端的偏頗者。有的學者將其歸納為‘幾偏’,即‘重血緣的狹隘觀念’‘成王敗寇的正統觀念’‘天朝自居的漢族中心觀念’‘忽視國內外交融的保守觀念’,等等。……華夏族形成的時間以及作為族征的華夏文化,已經是眾源融合的‘流’,而不再是原始的某個族體(如黃帝)單元了。”[6]1筆者認為,秋著以蚩尤為例,充分肯定非漢民族祖源英雄的歷史貢獻與地位,恰好為當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有力的學術依據,將其作為中華民族的文化符號之一,將大大增強各族人民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認同。
一、蚩尤文化與早期華夏文化的多元性
秋著在《序論·中國文化的源流》中討論了中國文化的源流問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在華夏正統觀念的影響下,中國文化的源頭被自然而然地與“黃河母親搖籃”“炎黃始祖”聯系起來進行一元化的祖源敘事,但中國作為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各民族及其文化的發祥地卻不只是黃河流域,而是隨著先民活動的遺跡遍布在中華大地的各處。他們共同創造的文化才構成了中華民族燦爛的文化。歷史上的“夷夏之辨”(或稱“華夷之辨”)盡管有偏頗之處,但說明除了中原的華夏之外,還有“四夷”(即東夷、西戎、南蠻、北狄),這樣的以華夏為中心的論述才是反映中華大地多民族的存在及各民族之間錯綜復雜的歷史關系。
(一)文化同出一脈的關系:蚩尤文化與良渚文化
一個民族的形成除了共同的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等因素的影響之外,不同的地理環境及相應的生產生計方式也會塑造其獨特的民族文化。如在古代中國的中原地區,形成以種粟為主的旱地農耕文化;長江中下游及以南的濕潤氣候形成以種水稻為主的稻作農業文化;北方的草原地區形成以放牧、采集和狩獵為主的游牧文化,這些都是塑造不同民族文化多樣性的重要因素。
2014 年5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明確提出:“推動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鞏固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7]從中華民族發展史來看,古代中國各民族之間早就存在交往交流交融,即中華大地每一塊區域都可能曾經有其他民族活動的痕跡,并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關系。蚩尤為上古時代九黎部落聯盟的首領,驍勇善戰,被尊稱為“戰神”,同時也是苗族世代相傳的遠祖之一。據王桐齡的《中國民族史》所敘,就移入中國內地的先后次序而言,苗族在漢族之先。當4000年前漢族占領黃河流域,而揚子江中流,現在的湖北、湖南、江西等地,已經由苗族占領;此族之國名為九黎,君主名蚩尤,蚩尤與炎帝起沖突,擊敗炎帝,追至逐鹿。有熊國君主公孫軒轅(即黃帝)迎擊蚩尤,敗其兵,殺之。后來苗族子孫,有一大部分完全同化于漢族;其不肯同化之一小部分,逐漸遷到西南各省深山中[8]5。良渚文化,因首先在浙江良渚地方發現而得名。考古發掘表明,今天的良渚文化覆蓋面已經擴大到了除浙江以外的江蘇、上海以及安徽和山東等周邊地區,占據了長江中下游的廣大區域,被歷史學家稱為“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新石器時代”,處于由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過渡的階段,因其發達程度與黃河流域不相上下,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源頭[6]52。據考證,良渚文化距今4 000~5 000年,處于新石器時代的晚期,良渚人以稻作農業為主,同時飼養家畜,加之狩獵捕魚,作為長江中下游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良渚文化已經呈現出高度發達的文明。有學者認為:“良渚文化的生產力水平較前一階段有很大的提高,農業生產工具的改進,精美玉器的制作、嵌玉漆器的出現,都表明當時的手工業技術已相當發達,具有一定的專業水平。石鉞既是一種工具,亦是一種武器,而精美的玉鉞則是威嚴與權力的象征。玉琮、玉璧既是財富,又是某種權力的象征。擁有這類精美玉器的人,意味著有不同于普通氏族成員的特殊身份與地位。他們很可能是氏族貴族。這些都表明良渚文化已處于原始社會末期,并已接近文明社會的門檻。”[6]56在原始社會末期,主導生產活動的是由父系氏族組成的部落聯盟,部落聯盟作為部族最高的權力機構,那么這個部落聯盟中居于領先地位的族群會不會與蚩尤統領的九黎部族有關呢?秋氏通過查閱史料,參閱其他學者的相關著述,結合考古發現的良渚文物,從代表良渚文化品類多樣,制作精美的良渚玉器入手,為我們論證了良渚文化與蚩尤部族之間的從屬關系。秋氏通過《中華文明史》對浙江余杭反山12 號墓出土的標志性玉琮——“琮王”上精美的人像圖案的描述認為,這樣精美的玉器乃是首領及權威人物才可以擁有的貴重物品,是權威與權力的象征。“琮王”上面的人像圖案被稱為“神人獸面紋”,很可能就是部族首領蚩尤的象征。
秋氏通過對《古玉之美》一書中描述出土的玉臂環分析中發現:“有的臂環在外壁表面雕琢出四組獸面紋。過去有人把這種類型的臂環稱作‘蚩尤環’,據說有辟邪作用。傳說黃帝戰敗蚩尤,把蚩尤的人首像琢在臂環上作為紀念,看來不是空穴來風。”[6]116并在其所列臂環圖的說明文“蚩尤環”前冠以“良渚文化”四字。另外,秋氏還從多學科角度上對該圖案進行了分析,如從美學角度說明“琮王”上圖案也可能是巫師佩戴作法的面具圖徽[6]59。總之,秋氏認為不管哪種說法,都可以肯定“琮王”是最高權威與權力的象征,只有部落聯盟的最高統帥才能擁有,而作為九黎部族首領的蚩尤很可能就是“琮王”所要表達的象征。秋氏強調,蚩尤統領的九黎部族在長江中下游區域活動,其活動的地域恰好與良渚文化的覆蓋面相吻合,說明蚩尤文化與良渚文化有密切的關系。
(二)族群競爭互補的關系:蚩尤與炎黃的涿鹿之戰
距今大約4 600 年前炎帝、黃帝的部族相聯合,為了共同對抗蚩尤部族而進行的一場戰爭,因戰爭地點發生在涿鹿,史稱“涿鹿之戰”。涿鹿之戰的發生地點位于今天的河北省涿鹿縣及周邊地區,在當時是土地肥沃的富饒之地,戰爭的雙方為了各自部族的利益而戰,最后以蚩尤部族戰敗而告終。秋氏指出,此次大戰關系到中華民族的生存與發展,也是華夏部族壯大繁盛的重要原因。關于這次大戰的經過,原先多見于神話與野史的敘述。司馬遷在《史記·黃帝本紀》中將神話寫入“正史”:“蚩尤作亂,不用帝命。于是黃帝乃征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9]秋氏認為,司馬遷把涿鹿之戰的起因歸結為“蚩尤作亂,不用帝命”,蚩尤順理成章地成了黃帝率領各部落征討的對象,黃帝戰勝蚩尤也就名正言順地被擁戴為“天子”。
由于《史記》作為“正史”第一部的巨大影響,以致晚到民國時期出版的歷史教科書都承續其說法把蚩尤描寫成“亂德”的形象:“古時苗黎族散處江湖間,先于吾族,不知幾何年。至黃帝時,生齒日繁,民族競爭之禍,乃不能不起,遂有炎帝、黃帝、蚩尤之戰事。”[10]13司馬遷作為漢王朝的太史令,在撰寫《史記》時也是參照了許多古籍和經過了多方的實地考察,才說“遂擇其言之尤雅者,故著為本紀之首”,即將《五帝本紀》列為卷首。秋氏參考了自然史學家“夏禹宇宙期”的說法,即發生在4 000 年前的神州大地上的一個洪水泛濫、天塌地陷的自然災害時期,在太湖地區留下了自然災害的痕跡,“良渚晚期遺址的遺物大部分出自潛水面以下的淤泥層和大型的遺跡單位”[11]45。此時期與涿鹿之戰發生的時間段是一致的,也就是說,長期活動在長江中下游的蚩尤率領的九黎部族因受到自然災害的侵襲,不得已向北尋求發展,在涿鹿與南下擴張的炎黃部族相遇,為爭奪生存之地才引發了這場對華夏文明乃至中華民族都具有重要意義的戰爭,秋著使讀者對涿鹿之戰有著更全面、更深層次的了解。
秋氏指出,“涿鹿之戰”最終以炎黃部族的完勝而蚩尤部族大部傷亡慘敗結束,蚩尤部族的一部分歸降了炎黃部族,一部分則散至各處,成為少數民族的先民。“涿鹿之戰”促成了族群大融合,為后來的華夏族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秋氏認為,作為中華文明源頭之一起源于長江、黃河中下游蚩尤部族的“良渚文化”,在經過“涿鹿之戰”及后來大大小小的部族文化融合之后,才最終造就了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歷史及豐富燦爛的文化。今天,人們為了紀念“涿鹿之戰”的重要意義,在河北省涿鹿縣境內原黃帝祠的基礎上擴張設立了“中華三祖堂”,這是對包括蚩尤在內的中華文明三祖——炎帝、黃帝和蚩尤對中華文明所作的巨大貢獻的肯定[6]41-51。
二、非漢民族祖源英雄蚩尤與民族的雙重層級認同
秋著開篇即圍繞著蚩尤及其為中華文明所做的巨大貢獻充分的肯定,對“炎黃始祖”敘事的不足之處作了有力的辯駁。他說:“炎黃是華夏的始祖,漢族尊崇之,無可非議,可是中國是個多民族國家,幾十個民族獨尊炎黃,不是有失偏頗么?”[6]13毋庸置疑,炎帝、黃帝對早期華夏族的形成功不可沒,但人們漸漸淡忘了蚩尤在中華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是需要給予矯正和重新強調的。作為非漢民族祖源英雄的蚩尤,在涿鹿之戰中戰敗了,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對蚩尤的描寫“蚩尤最為暴,莫能伐”[9]影響深遠,繼之被歷代的史書“層累”地描寫為“殘暴”“無德”的暴君形象以區別于黃帝的“正統”形象。今天,普遍認為自己是蚩尤后裔的苗族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秋氏對民國時期夏曾佑編寫歷史教科書中把炎黃部族與蚩尤的九黎部族表達為“吾族”與“土族”的二元對立敘事給予激烈的批評,認為這是典型的“大漢族主義思想”的產物[6]89-91。蚩尤率領的九黎部族生活在黃河與長江中下游地區,是不同于發源于黃河中上游的炎黃部族,但在“涿鹿之戰”中,蚩尤部族的戰敗使其余部的一部分與炎黃部族融合形成了早期華夏族的雛形。秋氏認為,蚩尤雖然戰敗了,但其歷史影響與相關的傳說故事在后世仍然不絕于耳,其族屬并沒有因此而滅絕,而是繼續在中華大地上繁衍生息,一部分歸入炎黃部族,與之融合成為華夏族的基礎,另一部分則散至各處,世代居于中華大地上。蚩尤應該與炎帝、黃帝同稱為中華文明的三大先祖[6]89-91。
(一)蚩尤與苗族認同
我們常說的“黎民百姓”,指代的是普通的人民大眾,“黎民”便是源自蚩尤率領的九黎部族。無論是古時候的南蠻族、九黎族,還是今天的苗族都共同將蚩尤奉為自己的始祖。另外,蚩尤在“涿鹿之戰”之前就大造兵器,作戰勇猛而被稱作“兵主”和“戰神”,被認為是最早金屬冶煉方法的發明者,是創造“五兵”之人,《世本·作篇》說:“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12]781-784《山海經》中記載,由于蚩尤驍勇善戰,在與炎黃部族的作戰當中,多次取勝,炎黃最后借助外力的幫助才得以在“涿鹿之戰”中戰勝蚩尤[13]。黃帝深知蚩尤的作戰能力,通過畫蚩尤的肖像,借用其軍事威望和文化影響來鎮撫四方。秋氏引用了史料證明,《史記·高祖本紀》記載劉邦興師起兵之時都會“祠黃帝、蚩尤于沛庭”。《史記·封禪記》記載齊國人祭祀八神,其中之三就是蚩尤:“三曰兵主,祀蚩尤。”[6]39民間亦有為了紀念戰神功績而創作的蚩尤戲,對他在戰斗中的英勇形象進行模仿。據《述異記》記載:“秦漢間說,蚩尤氏耳鬢如劍戟,頭有角,與軒轅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樂,名‘蚩尤戲’,其民三三兩兩,頭戴牛角而相抵。又漢造角抵戲,蓋其遺制也。”[14]而蚩尤作為我國苗族等民族的祖源英雄,民間也會舉行紀念蚩尤的祭奠活動[6]39。
蚩尤作為苗族的遠古先祖,已經得到多方面的驗證,苗族民間傳說與民俗習慣中長期留存著蚩尤的印跡。在苗族古歌中,傳頌著蚩尤統領的九黎部族遷徙歷史,《蚩尤與苗族遷徙歌》中記載了九黎部族的一支南遷的歷史:“古時苗族住在直米力,建筑城垣九十九座,城內鋪墊青石板,城外粉刷青石灰,城里住著格蚩尤老、格婁尤老。直米力城建,直力城啊直力城,平又平來寬又寬,欣賞城內好風光,房屋成排起在平原上……”[15]276-283“直米力”為苗語音譯,相傳是地處今河北一帶的地名,古歌中提到的“直米力城”用漢語音譯則是“黎城”即是蚩尤所率領的九黎部族建立的,苗族民間還流傳著祭奠蚩尤的習俗。據田玉隆研究,蚩尤的傳說在苗族民眾中廣為流傳,從服飾中可以看到:“黔西北等地苗族服飾圖案,既美麗,又是歷史記錄。裙腳三條橫線,表示祖先曾經‘生活在黃河、長江和大平原里’;‘星宿花’,表示蚩尤與黃帝打仗,晚上行軍,靠星星指引方向;‘蜘蛛花’,表示祖先受困時戰斗精神;‘九曲江河花’,表示蚩尤被打敗后,祖先從黃河南遷中渡過許多河流;‘虎爪花’,敘述遷到深山林箐打虎故事。”[16]蚩尤與苗族的關系不僅僅體現在民間傳說與服飾文化中,更多的是文獻的記載,《尚書·呂刑》就把蚩尤和苗人聯系了起來:“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17]519-520因此,我們不能忽略苗族把蚩尤當作祖先來崇拜這一民俗,說明蚩尤與苗族關系密切的,秋著對于蚩尤這一被認為是非漢民族祖源英雄形象的研究也為中華民族是個多民族組成的大家庭增添另一證據。
秋著對中華文明中早期的華夏文明的代表性文化作了充分的說明,他介紹了作為中華文明源頭的兩大文化——紅山文化與良渚文化,為讀者再現了豐富多彩、琳瑯滿目的文化內容。秋著對蚩尤的地位給予充分肯定,書中引經據典,引用了大量蚩尤的史料,又以紅山文化與良渚文化等具有代表性的中華文明遺址作為輔證,說明了蚩尤作為中華三祖之一的原因。
秋著充分肯定蚩尤的貢獻和歷史地位,主要是受了20 世紀90 年代中后期中國文化界掀起的一股研究蚩尤文化熱的感召。1994年,河北省涿鹿縣政府利用涿鹿縣作為黃帝與蚩尤作戰地的神話和歷史傳說,計劃在該縣修建“炎黃城”,樹立“炎黃像”以回應“愛國主義運動”熱潮和中國百姓對同為“炎黃子孫”的普遍認同。當地政府希望通過這樣的方式增強民族凝聚力,同時吸引游客以增加財政收入。這一文化創意無論是政治上、文化上,還是經濟上都是利國利民的大好事,但策劃方卻忽視了堪與炎黃二帝比肩的蚩尤的位置。因此,該提議隨即引起了以苗族學者為代表的不滿與聲討,部分代表直接向中央領導申訴,論證了蚩尤與九黎、三苗及現在苗族的淵源關系,從漢民族的形成歷史過程等方面要求重視且恢復蚩尤在中華民族史上的地位[18]。他們的訴求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視,從民族團結的大局意識出發,認可并尊重苗族等少數民族群體作為中華民族成員爭取自己地位的訴求。最后的結果是在有關學者專家的建議下,確定了建設“中華始祖文化村”的設想,在黃帝祠的基礎上擴建設立“中華三祖堂”將炎帝、黃帝、蚩尤的塑像立于堂中供游客瞻仰與祭奠,并成立了“涿鹿縣三祖文化研究會”。通過“中華三祖堂”事件,從苗族知識分子到普通苗族群眾更加深刻地認識到自己與蚩尤的淵源關系,也通過蚩尤這一祖源英雄增強了彼此之間的文化認同和族群凝聚力。
(二)蚩尤與中華民族認同
秋著提到,從涿鹿縣“中華文化三祖堂”成功落成的背后,蚩尤被作為中華文化的三祖之一得到了官方的承認,同炎帝、黃帝一樣,受到百姓的瞻仰與祭拜。這已不僅是把蚩尤作為苗族或其他民族的先祖來崇拜,更是把他當作是中華民族的先祖來崇拜,恰恰說明了蚩尤的歷史是與中華民族的歷史緊緊聯系在一起的。從史料中我們可以發現,蚩尤的形象與地位是一直處于變動之中的。作為“兵主”與“戰神”的存在,在《史記·封禪書》中記載秦始皇出游東海祭祀的八神中,就有被作為“兵主”的蚩尤,漢朝的開國之君劉邦在戰前也會祭拜蚩尤,希求“戰神”賜予力量。在民間也有蚩尤崇拜的諸多祭奠活動。蚩尤的形象在《史記》等文獻中是一個“不用帝命”的反叛者,是黃帝帶領各部族討伐的對象。到了清末民初面臨著亡國滅種危機之際,一些學者本著愛國救國的初衷,極力強化同為“炎黃子孫”的民族認同,以達到推翻清政府統治的目的。“隨著‘民族’這一概念經由日本傳入,‘種族’與‘民族’說開始大行其道。種族言說成了革命派詆毀滿清政權合法性的最為銳利武器之一。”[19]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蚩尤就被主流話語遮蔽,處于邊緣位置,進而與非漢民族的“異族”首領聯系起來。
今天,蚩尤作為中國部分少數民族的先祖一說似乎已變成大眾的普遍認識,但中華民族從來都是一個大家庭,把蚩尤與中華民族大家庭聯系起來也不無道理。1990 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同志就曾經說過:“我們都是中華民族的子孫,我感到‘中華民族’這個詞,相較于過去我們所常講的‘炎黃子孫’概括性更強,因為它包含了我們中國的各個民族。”[20]在新時代背景下,“中華民族共同體”相比于“炎黃子孫”具有更廣泛的內涵,我們應該更加重視培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強調:“要正確把握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各民族意識的關系,引導各民族始終把中華民族利益放在首位,本民族意識要服從和服務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同時要在實現好中華民族共同體整體利益進程中實現好各民族具體利益,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都不利于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4]中華民族是一個不能分割的民族共同體,這是不爭的事實。中國各民族世代生活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從歷史神話傳說中的蚩尤與炎帝、黃帝的“涿鹿之戰”形成華夏族的早期融合起,各民族通過幾千年來的交互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借用費孝通先生的話來說:“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通過發揮各民族團結互助的精神達到共同繁榮的目的,繼續在多元一體的格局中發展到更高的層次。在這層次里,用個比喻來說,中華民族將是一個百花爭艷的大園圃。”[1]37-38筆者認為,這也是秋著想要為蚩尤正名分,進入“中華三祖堂”后提供更多學理依據的動機所在,也是秋著的上編“蚩尤新論”的主旨所在。
三、結語
秋著對包括蚩尤文化在內的中國文化的精彩論述,剛好契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作的“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推動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高質量發展”的講話精神。今后,我們需要更加重視蚩尤文化作為中華文明三祖之一的文化象征符號。蚩尤文化符號將進一步增進中華民族內部各民族成員之間的團結和睦與文化、情感認同,每一個重要的中華文化象征符號都不應該被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中,也不應該局限于單一民族的祖源英雄認同,而應該重新引起重視,并將其歸屬于最高的民族認同,即作為在中華大地上勤勞勇敢、生生不息的偉大的中華民族。
蚩尤作為中華民族的先祖之一,在中華民族各兄弟民族攜手走入現代化的背景下,不僅是非漢民族的祖源英雄,更是中華民族祖源英雄的重要文化象征符號。秋氏梳理的一系列蚩尤與中國文化的證據,諸如“紅山文化”“良渚文化”等作為早期造就華夏文明的重要源流,其各自文化里所產的玉器與彩陶等內容豐富的文化遺產,都向我們表明了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的多元一體中華文明。秋著給我們的啟示是:我們需要在現有文化認同的基礎上,盡可能地尊重并吸收各民族的祖源英雄認同,充分肯定他們作為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對其相應的文化傳統和習俗給予充分的發展空間,承認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格局,從而更好地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秋陽先生所著的《蚩尤與中國文化》是一本針對蚩尤文化與中國文化討論的論文合集,在章節中難免存在觀點的反復強調與內容的重復敘述,但每篇論文都言語懇切,行文優美,援引了大量史料和文物作為證據,在關于中華文明源頭的討論中,秋著多次提及蚩尤這一形象,并多層次、多維度地論證了這位非漢民族祖源英雄與中華文化的密切聯系,論證了蚩尤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不爭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