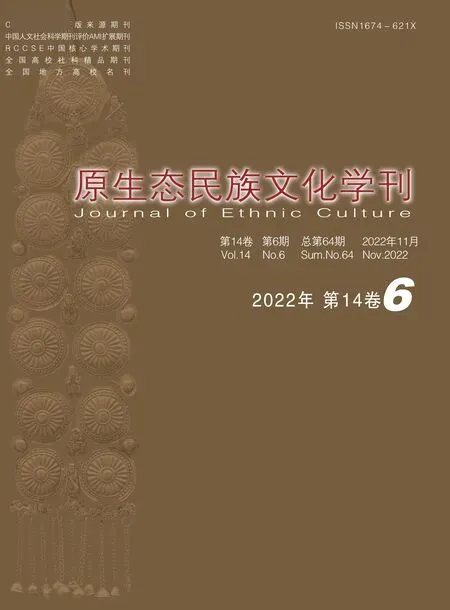二十世紀(jì)上半葉苗族知識(shí)分子關(guān)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探索與實(shí)踐
王金元,彭 婧
自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會(huì)議召開(kāi)以來(lái),共同體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成為社會(huì)各界關(guān)注的議題。既有研究在概念來(lái)源、理論內(nèi)涵、性質(zhì)特點(diǎn)等方面已取得十分有價(jià)值的思考,但在如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上則呈現(xiàn)多種討論。沈桂萍[1]、范君[2]、馬英杰[3]等提出文化是培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重要路徑;張立輝[4]、趙剛[5]、高承海[6]等強(qiáng)調(diào)政治制度可以解決中華民族共同體內(nèi)部凝聚的實(shí)際問(wèn)題;尤金菊[7]、麻國(guó)慶[8]等則認(rèn)為民族心態(tài)和族群記憶對(duì)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具有重要理論意義;楊鹍飛[9]、彭謙[10]等則主張綜合政治、經(jīng)濟(jì)和文化要素可以增強(qiáng)中華民族共同體認(rèn)同意識(shí)。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從政治整合、文化凝聚、經(jīng)濟(jì)共享、心理認(rèn)同等宏觀方面對(duì)如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進(jìn)行認(rèn)識(shí)論范疇的探討,但對(duì)鑄牢過(guò)程中的行動(dòng)主體缺乏微觀分析。這種將共同體意識(shí)形成路徑置于整體視角來(lái)討論的研究范式,往往容易遮蔽日常生活中的個(gè)體及其實(shí)踐,從而給人以行動(dòng)主體“缺席”的假象。青覺(jué)、徐欣順結(jié)合馬克思主義學(xué)說(shuō)指出:“共同體存在決定共同體意識(shí),共同體意識(shí)反映共同體存在;共同體意識(shí)除了具備成員的主觀反應(yīng)和認(rèn)識(shí)特性,還具有主觀能動(dòng)和反思特性。”[11]也就是說(shuō),共同體成員是共同體意識(shí)的主體,而作為共同體成員的民族知識(shí)分子,其意識(shí)受到共同體存在的影響;反之,民族知識(shí)分子的主觀能動(dòng)性也作用于共同體存在,在共同體意識(shí)形成過(guò)程中發(fā)揮著巨大作用。因此,要理清“作為共同體本體的中華民族與反映共同體本體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12]之間的生成關(guān)系,不同族類(lèi)共同體成員及其能動(dòng)性是理解共同體意識(shí)形成的關(guān)鍵。
本文旨在關(guān)注民族知識(shí)分子的共同體意識(shí)及其實(shí)踐過(guò)程,從更為微觀和鮮活的個(gè)體生命歷程探尋他們關(guān)于共同體意識(shí)的不同論述,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路徑提供參考。具體選取苗族三大方言區(qū)知識(shí)分子梁聚五(中部方言區(qū))、石啟貴(東部方言區(qū))和楊漢先(西部方言區(qū))為研究對(duì)象,在爬梳這些知識(shí)分子撰寫(xiě)的文獻(xiàn)資料基礎(chǔ)上,將他們的身份轉(zhuǎn)換及認(rèn)同選擇置放于近現(xiàn)代社會(huì)轉(zhuǎn)型的歷史場(chǎng)景,探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多重面向及路徑邏輯。
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中的知識(shí)精英及其可能性
毋庸置疑,民族知識(shí)分子深諳民族文化精神,擁有社會(huì)資源,在很大程度上支配著民族政治體系的運(yùn)作,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整個(gè)民族的生存與發(fā)展[13]104。尤其是近代社會(huì)轉(zhuǎn)型中的少數(shù)民族知識(shí)分子,是理解中國(guó)從“天下帝國(guó)”到“民族國(guó)家”進(jìn)程的鑰匙[14],他們的認(rèn)同觀念變遷對(duì)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形成以及構(gòu)建新時(shí)代和諧民族關(guān)系有重要影響。
首先,作為本體或意識(shí)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概念一直為知識(shí)精英所培育。從“中華民族”概念提出到“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生成,可以看到知識(shí)精英“在場(chǎng)”及其主觀能動(dòng)的作用,并以其智識(shí)不斷豐富共同體本體和共同體意識(shí)的概念內(nèi)涵。近代歐洲民族主義、西方列強(qiáng)侵華以及“西學(xué)東漸”的多重刺激,迫使中國(guó)知識(shí)精英“開(kāi)眼看世界”,以康有為、梁?jiǎn)⒊热藶榇淼闹R(shí)分子群體將“民族”概念引入中國(guó),并主張中華版圖內(nèi)所有人都可使用“民族”一詞來(lái)實(shí)現(xiàn)“合群”,進(jìn)而達(dá)到“愛(ài)國(guó)保種”。梁?jiǎn)⒊?899 年始,先后在《東籍月旦》《論民族競(jìng)爭(zhēng)之大勢(shì)》《論國(guó)民與民族之差別及其關(guān)系》等文試圖厘清西方的民族概念,并對(duì)布倫奇里的民族“八要素”學(xué)說(shuō)予以注解。1905年,他在《歷史上中國(guó)民族之觀察》中明確闡釋“中華民族”的概念:“今日之中華民族,即普通所謂漢族者,自初本為一民族乎?一由多數(shù)民族混合而成乎?”[15]1678梁氏將“中華民族”等同于“漢族”的做法,顯然是“驅(qū)除韃虜,恢復(fù)中華”歷史語(yǔ)境的需要。此后,梁氏在《中國(guó)歷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對(duì)“中華民族”予以修改,“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國(guó)人也’之一觀念限于腦際者,此人即是中華民族一員也”[15]3221。他試圖通過(guò)共同體概念內(nèi)涵擴(kuò)展,解決清末民初被種族主義充盈的社會(huì)境況。與此同時(shí),孫中山則以民族概念來(lái)武裝革命,通過(guò)“國(guó)族計(jì)劃”逐步實(shí)現(xiàn)政治理想。之后,中國(guó)國(guó)民黨繼續(xù)堅(jiān)持“國(guó)族”概念,強(qiáng)調(diào)同化和融合,認(rèn)為中國(guó)境內(nèi)各人群應(yīng)組成強(qiáng)有力的“國(guó)族”;共產(chǎn)黨則大量使用“民族”“少數(shù)民族”“弱小民族”“中華民族”等概念,根據(jù)國(guó)內(nèi)外局勢(shì)變化策略性地提出“民族平等”“民族團(tuán)結(jié)”和“民族自治”等概念[16]222-249。正是國(guó)共兩黨對(duì)共同體概念的認(rèn)知差異,加上抗日時(shí)期國(guó)家處于危難的嚴(yán)峻形勢(shì),引發(fā)學(xué)界關(guān)于“中華民族是一個(gè)還是多個(gè)”的激烈討論。
顧頡剛主張凡是中國(guó)人都是中華民族,在中華民族之內(nèi)絕不該再析出什么民族。“中華民族是一個(gè)”,這是信念,也是事實(shí)。他還呼吁:“我們對(duì)內(nèi)沒(méi)有什么民族之分,對(duì)外只有一個(gè)中華民族。”[17]“中華民族是一個(gè)”形成于日本假借“民族自決”口號(hào)來(lái)分裂中國(guó)的歷史背景,有其特定的用意,旨在“團(tuán)結(jié)國(guó)內(nèi)各種各族,使他們貫徹‘中華民族是一個(gè)’的意識(shí),實(shí)為建國(guó)的先決條件”[18]785。“中華民族是一個(gè)”被提出以后,引起學(xué)界熱烈反響。費(fèi)孝通對(duì)此觀點(diǎn)持反對(duì)意見(jiàn),他贊同中國(guó)人在文化、體質(zhì)、語(yǔ)言等方面確實(shí)存在分歧,且這些經(jīng)常導(dǎo)致社會(huì)分化,但沒(méi)有必要去回避和否定國(guó)內(nèi)不同“民族”的事實(shí),要使文化、體質(zhì)、語(yǔ)言各異的群體在政治上合作,共謀安全與強(qiáng)盛,維護(hù)國(guó)家團(tuán)結(jié),絕不是取消幾個(gè)指稱(chēng)就能達(dá)到的,而應(yīng)消除各種界限所引起的政治上的不平等[19]67-68。為進(jìn)一步探索中華民族的理論意義,費(fèi)孝通在1988年的演講中提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理論,就中華民族的概念及形成過(guò)程予以深入闡釋?zhuān)?0]3-38。循此宏論,費(fèi)先生在“民族走廊”“人口較少民族”等方面做出了許多富有開(kāi)創(chuàng)性的研究,并身體力行地將自身及研究投入到“邁向人民”的民族研究行列當(dāng)中。
其次,知識(shí)精英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形成的重要載體和形塑主體,他們的身份轉(zhuǎn)換與認(rèn)同選擇直接影響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形成。沈松橋曾指出“民族英雄”概念及系譜建構(gòu)是各派知識(shí)分子關(guān)于國(guó)族史學(xué)論述的重要產(chǎn)物,是近代中國(guó)國(guó)族主義文化政治的具體展演,是對(duì)抗、爭(zhēng)持和協(xié)商的權(quán)力場(chǎng)域[21]。黃興濤以民族知識(shí)分子自覺(jué)為突破口,考察中華民族的形成過(guò)程并從學(xué)理剖析中華民族的深層結(jié)構(gòu)[22]1-8。與此相類(lèi)似,高翠蓮也從“民族實(shí)體”和“精英主觀建構(gòu)”兩個(gè)層面討論清末民國(guó)時(shí)期中華民族的自覺(jué)進(jìn)程,并從橫縱兩個(gè)維度闡釋中華民族從自在到自覺(jué)的進(jìn)程以及伸縮的軌跡,指出中華民族共同體自覺(jué)進(jìn)程的曲折性、復(fù)雜性和獨(dú)特性[23]。顯然,在上述學(xué)者看來(lái),知識(shí)精英及其主觀能動(dòng)性成為構(gòu)建共同體意識(shí)的重要基點(diǎn)。那么,如何形塑和鑄牢共同體意識(shí)?張淑娟[24]、納日碧力戈[25]等研究者認(rèn)為民族知識(shí)分子在多民族國(guó)家中應(yīng)承擔(dān)雙重建構(gòu)使命,既要澄清國(guó)情基礎(chǔ)上單元民族與中華民族兩種內(nèi)涵迥異的“民族”的關(guān)系,又要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過(guò)程中尋求與高層、中層和基層民眾相通與互聯(lián)。哈正利和張福強(qiáng)則以《中國(guó)回教救國(guó)協(xié)會(huì)會(huì)刊》為中心,指出抗戰(zhàn)時(shí)期回族精英通過(guò)“回族與中華民族”“回族文化與中華文化”“回與漢”等關(guān)系的闡釋和“舊話題”的強(qiáng)調(diào)來(lái)構(gòu)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26]。可見(jiàn),民族知識(shí)分子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過(guò)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以致有學(xué)者斷言“民族知識(shí)分子可以消解近代民族主義造成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建構(gòu)的內(nèi)在緊張”[24]。
不論在相關(guān)概念內(nèi)涵的提煉和闡釋方面,還是在共同體培育和形塑的實(shí)踐過(guò)程中,民族知識(shí)分子都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梁聚五、石啟貴和楊漢先等人作為苗族知識(shí)分子的代表,其在個(gè)人生命歷程中不斷踐行著對(duì)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認(rèn)知、闡釋與實(shí)踐。這些苗族知識(shí)分子生活跨越清末民國(guó)和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等不同社會(huì)體制時(shí)期,面臨身份轉(zhuǎn)換和認(rèn)同選擇的困境,他們變動(dòng)的身份認(rèn)同恰是微觀角度下共同體意識(shí)形成的縮影,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不可或缺的單元要素。
二、苗族知識(shí)分子關(guān)于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探索與實(shí)踐
(一)梁聚五“邊民-夷-苗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建構(gòu)與轉(zhuǎn)換
梁聚五(1892-1977),貴州雷山人,年輕時(shí)曾在外地求學(xué)、從軍,活躍于川、湘、黔等城市,接受過(guò)民主思想,曾任貴州民意社社長(zhǎng),擔(dān)任過(guò)西南軍政委員會(huì)委員、西南民族事務(wù)委員會(huì)副主任、四川省政協(xié)委員等,一直關(guān)注民族平等,為民主政治建設(shè)做過(guò)巨大貢獻(xiàn)。梁聚五是著名苗族歷史文化研究者,先后著有《苗夷民族發(fā)展史》等十多部作品,他的人生軌跡及其關(guān)于“近代中國(guó)邊緣族群以漢語(yǔ)文表述我族身份認(rèn)同的文本書(shū)寫(xiě)與政治實(shí)踐”[27]189-202,可為我們理解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鑄牢問(wèn)題提供個(gè)案參考。
19 世紀(jì)末,在梁聚五的出生地曾爆發(fā)過(guò)多次苗民起義運(yùn)動(dòng),當(dāng)?shù)亓鱾鞯姆纯骨逭缆竞蛪浩鹊墓适掠|發(fā)了梁聚五的民族意識(shí),尤其是看到“聚殲叛苗碑”之后,梁聚五踏上了為少數(shù)民族政治權(quán)利和平等地位而奔走呼號(hào)的人生之路。對(duì)于當(dāng)時(shí)民族歧視問(wèn)題,梁聚五認(rèn)為有必要“把貴州各民族實(shí)際生活公開(kāi)展覽、鋪敘出來(lái)”[28]414,以較為客觀地觀察貴州各民族,“指出過(guò)去對(duì)于貴州各民族觀察的錯(cuò)誤,使今后不致再以盲導(dǎo)盲,重演不幸的慘劇”[28]414。為尋找各民族間的共通點(diǎn)和聯(lián)結(jié)紐帶,消除民族仇恨和成見(jiàn),提高各民族權(quán)利地位,梁聚五提出廢除侮辱性的民族稱(chēng)謂和字樣,將黔南地區(qū)的少數(shù)民族群體分“苗”“夷”兩個(gè)系統(tǒng),并試圖用“邊民”“邊地”等概念來(lái)表述族群類(lèi)別。他還強(qiáng)調(diào)用“苗夷民族”取代“邊疆民族”作為西南邊緣族群的指稱(chēng),借此抗拒民國(guó)政府邊緣化西南邊疆族群的行動(dòng)[29]21-25。梁聚五鼓勵(lì)通過(guò)通婚來(lái)戳開(kāi)種族壁壘,構(gòu)建“新的國(guó)族陣線”,以促進(jìn)民族融合。但他強(qiáng)調(diào)民族融合不等于民族同化,認(rèn)為“同化主義”違背了“國(guó)內(nèi)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精義,也違背“扶持國(guó)內(nèi)弱小民族,使之自決自治”原則。他指出:“以不同而強(qiáng)同,是不啻以帝國(guó)主義自居,而把國(guó)內(nèi)各弱小民族當(dāng)作殖民地來(lái)看待,如此只能分割中國(guó)民族的團(tuán)結(jié)力。”[29]78若說(shuō)反對(duì)“五族共和”和“民族同化”政策是梁聚五身份認(rèn)同的自覺(jué)陳述,那么,爭(zhēng)取“國(guó)大代表席位”則是他尋求政治承認(rèn)的精英實(shí)踐。1945年,一群“夷苗精英”聯(lián)名提議梁聚五作為第一屆國(guó)民大會(huì)的“邊疆民族代表”遭拒,梁聚五借用孫中山“國(guó)民大會(huì)”和“國(guó)民會(huì)議”概念質(zhì)疑此次大會(huì)的合法性,提出以“全民公開(kāi)選舉”代替“委任”來(lái)決定大會(huì)代表。
1949年以后,新中國(guó)實(shí)行民族平等政策。“苗族”身份被確認(rèn)后,梁聚五把參加第一屆全國(guó)政協(xié)會(huì)議二次會(huì)議視為“我們苗族一件光榮的事”[29]26,還向大會(huì)提交一份名為“建議推行中國(guó)少數(shù)民族文字拉丁化運(yùn)動(dòng)案”[29]28的提案,并通過(guò)書(shū)信、言傳身教等鼓勵(lì)青年保護(hù)和發(fā)展苗族語(yǔ)言文字。回到苗族地區(qū)后,梁先生積極開(kāi)展土地改革,親自深入鄉(xiāng)村調(diào)研,撰寫(xiě)大量土改工作的總結(jié)報(bào)告。
此外,梁聚五也在不斷修正自身的民族史觀,他早期的作品把漢族及大漢族主義作為少數(shù)民族的敵人,之后他把對(duì)象縮小為滿清及民國(guó)政府,尤其是當(dāng)政推行“五族共和”與“民族同化”政策后,他指出“中國(guó)民族”除了“漢滿蒙回藏”之外,還有一位長(zhǎng)兄“苗族”,他們之間“親如兄弟,本是一家”,只是為爭(zhēng)奪沃土繁衍下一代而已[28]415,借此強(qiáng)調(diào)要正視苗漢之間的民族關(guān)系。1949年后,梁聚五遵從和采納唯物史學(xué)觀的敘事方式,將書(shū)稿中所有的“苗夷民族”改為“苗族”,使之符合國(guó)家標(biāo)準(zhǔn)稱(chēng)謂。同時(shí),他號(hào)召?gòu)V大苗族同胞分清階級(jí)特征與民族特征的區(qū)別,積極參與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
以上體現(xiàn)了梁聚五不同時(shí)期的身份建構(gòu)與認(rèn)同選擇:從苗夷民族身份認(rèn)同到苗族認(rèn)同和中華民族認(rèn)同,這種認(rèn)同差異及主體轉(zhuǎn)向絕非知識(shí)精英的個(gè)人式獨(dú)白,而是社會(huì)政治背景下知識(shí)精英與邊界他者之間的互動(dòng)。清末民初年間,包括苗族在內(nèi)的少數(shù)民族是地理上和政治上“邊緣體”,不僅是遠(yuǎn)離帝國(guó)庇佑的“邊胞”或“邊民”,還是“五族共和”之外的他者;1949 年以后,由邊緣人群轉(zhuǎn)變成為“國(guó)家主人”。因此,是邊緣還是中心的社會(huì)處境成為梁先生調(diào)整共同體意識(shí)的決定性變量[30]。
(二)石啟貴“湘西苗族”身份的自我表述及文本實(shí)踐
石啟貴(1896-1959),湖南吉首人,近代知名苗族學(xué)者,在教育和學(xué)術(shù)研究方面頗有建樹(shù),曾受聘擔(dān)任湘西苗族補(bǔ)充調(diào)查員、湘西苗族教育勸導(dǎo)員[31]。一生致力于教育、經(jīng)濟(jì)和文化發(fā)展,爭(zhēng)取少數(shù)民族政治權(quán)利地位,對(duì)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探索與實(shí)踐主要體現(xiàn)在對(duì)湘西苗族的身份認(rèn)同。
首先,通過(guò)對(duì)“湘西苗族”歷史書(shū)寫(xiě),從學(xué)理上消除畛域隔閡,促進(jìn)民族團(tuán)結(jié)。早在1933年,石啟貴承邀協(xié)助“中央研究院”在湘西開(kāi)展調(diào)查工作后,就產(chǎn)出大量湘西苗族文化研究成果[31]。當(dāng)時(shí)的苗族“地多崖,巖多田少,地瘠民貧”[32]80,經(jīng)濟(jì)、教育、文化等方面發(fā)展明顯不如中原漢族地區(qū),民族間歧視極為嚴(yán)重,“凡見(jiàn)丑陋之物件,動(dòng)輒以‘苗’來(lái)比擬。如粗碗粗筷,漢人謂之‘苗碗苗筷’;品貌不美,漢人謂之‘苗相苗形’”[32]210。為打破“苗漢畛域隔閡,力矯過(guò)去錯(cuò)誤思想”,石啟貴回到漢文獻(xiàn)典籍的敘事脈絡(luò)中,梳理這冠之以“苗”的人群的歷史,以糾正此種民族歧視。他提出“苗民乃中國(guó)之主人公,古老之民族也”[32]665,是最早與漢族發(fā)生互動(dòng)的民族。后又從“族源”“語(yǔ)言”“名稱(chēng)”“醫(yī)藥及干支”“姓名”“宗教習(xí)俗”等六個(gè)方面論證“苗漢同源論”,這是符合當(dāng)時(shí)主流社會(huì)的話語(yǔ)。此外,他認(rèn)為歷史上的“苗亂”不能歸咎于苗人,而是被侵犯、壓迫、剝削以及專(zhuān)制政策所致,若以德化之則無(wú)亂。顯然,石啟貴所述的苗族及其悠久歷史與漢族之間的密切關(guān)聯(lián),一方面是為了闡明苗族在中國(guó)歷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增強(qiáng)民族自信與認(rèn)同,更是不惜以夸張的反知識(shí)的知識(shí)生產(chǎn)(同源論)去拉近苗漢關(guān)系以消除民族畛域隔閡。該書(shū)寫(xiě)方式即便超乎學(xué)術(shù)的科學(xué)與嚴(yán)謹(jǐn),卻在社會(huì)上激起了浪花,具有較為深刻的社會(huì)意義。
當(dāng)然,石啟貴對(duì)民族問(wèn)題的探索并不停留在民族史書(shū)寫(xiě)上,還體現(xiàn)在復(fù)興本民族的教育、經(jīng)濟(jì)和文化等事業(yè)中。早在1926年,石啟貴積極組織乾城苗民文化經(jīng)濟(jì)改進(jìn)委員會(huì),帶領(lǐng)苗家開(kāi)發(fā)山區(qū)。1936年,他同其他有識(shí)之士向湖南省府提交《湘西苗民文化經(jīng)濟(jì)建設(shè)方案》,建議政府“對(duì)湘西苗疆要穩(wěn)定治安、注重建設(shè)、改良待遇、推廣教育”[32]216,按“開(kāi)導(dǎo)”“開(kāi)誠(chéng)”“開(kāi)化”“開(kāi)發(fā)”四大步驟來(lái)進(jìn)行。同年,他被委任為“湘西苗族教育勸導(dǎo)員”,恐“有障礙情形,難收效益”,便親力親為,因材施教編寫(xiě)鄉(xiāng)土教材。1946 年,他作為“土著民族”代表在南京國(guó)民大會(huì)上提交“民族平等、教育開(kāi)化邊胞,發(fā)展苗區(qū)經(jīng)濟(jì)建設(shè)”等提案。1951 年,他請(qǐng)求“中央劃撥巨款,惠濟(jì)苗胞,早為設(shè)法發(fā)展農(nóng)村生產(chǎn)力量,建立地方公益事業(yè)。其余文化設(shè)施,每縣請(qǐng)建立苗民完全高級(jí)小學(xué),充實(shí)鞏固基層教育。切實(shí)清理原有村校,啟迪民智,掃除文盲,提高苗民子弟之文化。生聚教養(yǎng),造福將來(lái)。如此,苗民發(fā)展前途遠(yuǎn)大,當(dāng)有無(wú)限之光明也”[32]80。總之,湘西苗族的教育、經(jīng)濟(jì)和文化等事業(yè)的發(fā)展占據(jù)了石啟貴的大部分生命,體現(xiàn)他作為現(xiàn)代公共知識(shí)分子的使命與職責(zé),這種強(qiáng)烈的民生意識(shí)與他作為“湘西苗族”的身份以及秉持“事關(guān)吾族,責(zé)豈旁貸”的人生理念有很大關(guān)聯(lián)。
此外,石啟貴還致力于爭(zhēng)取少數(shù)民族的權(quán)利地位。明清時(shí)期,湘西苗民身處化外之地,是帝國(guó)重點(diǎn)教化的對(duì)象。1911年以后,“民國(guó)肇興,力謀解放,盛倡平等,號(hào)稱(chēng)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并不惠及苗族等其他少數(shù)民族,反置苗族于化外民族,國(guó)民大會(huì)設(shè)定的額定代表更是缺“土著民族”名額[32]206。為此,他向國(guó)民政府上書(shū)指出“苗民歷受政治壓迫,五千年來(lái)不堪言狀,以無(wú)人代表參政之原因”并詳列五條理由呈之,爭(zhēng)取全國(guó)土著民族額定代表10名,其中湖南1名[31]。針對(duì)國(guó)民政府把湘西苗族聚居區(qū)排除在“土著區(qū)域”之外且“停止特區(qū)教育補(bǔ)助費(fèi)”的行徑,石啟貴除了將《湘西土著民族考察報(bào)告書(shū)》部分章節(jié)上報(bào)外,還請(qǐng)求“中央研究院”的凌純聲、芮逸夫兩位民族學(xué)家提供證詞,詳細(xì)列舉其事實(shí),指出“湘西苗區(qū)就是土著區(qū)域”的三大理由。1946年2月,石啟貴以湖南“土著民族”代表身份出席國(guó)民黨在南京召開(kāi)的國(guó)民大會(huì),向大會(huì)提案40余條,建議開(kāi)化邊胞,加強(qiáng)邊疆經(jīng)濟(jì)文化建設(shè)等。
可見(jiàn),石啟貴關(guān)于湘西苗族及其爭(zhēng)取少數(shù)民族權(quán)利地位的實(shí)踐,顯然是以消解民族畛域隔閡為前提,在很大程度上回應(yīng)“他者描寫(xiě)”的話語(yǔ)及文本,體現(xiàn)本土知識(shí)精英“自我表述”的路徑以及對(duì)于少數(shù)民族在民國(guó)時(shí)期國(guó)族結(jié)構(gòu)中所處地位的定位和再思考[33]。
(三)楊漢先“教民-花苗”身份的并置、游移與認(rèn)同
楊漢先(1913-1998),貴州威寧人,先后就讀于石門(mén)坎光華小學(xué)、云南昭通宣道中學(xué)、華西高中和華西協(xié)和大學(xué)等教會(huì)學(xué)校。楊漢先出生的石門(mén)坎地區(qū),歷史上曾歸屬于黑彝“諾蘇”的統(tǒng)治范圍,花苗群眾曾遭受殘酷壓迫與剝削。“改土歸流”后,中央王朝開(kāi)始委派流官接管該地區(qū),但花苗群體的命運(yùn)并未得到改變。20 世紀(jì)初,隨著基督教及教會(huì)力量的介入和干預(yù),尤其是伯格理(Samuel Pollard)率領(lǐng)苗族教眾抵抗暴行以及在石門(mén)坎開(kāi)辦教育以后,該區(qū)社會(huì)文化發(fā)生巨變,先后涌現(xiàn)出一批優(yōu)秀的花苗知識(shí)分子。其中,一名叫楊雅各的花苗精英投入到傳教活動(dòng)中,并協(xié)助伯格理創(chuàng)建苗族文字、翻譯和編印苗文《圣經(jīng)》,此人正是楊漢先的父親。正是幼時(shí)家庭教育的熏陶、依托基督教力量才得以到縣建設(shè)局謀職以及返回教會(huì)學(xué)校繼續(xù)深造的人生經(jīng)歷,使得楊漢先對(duì)基督教有著較為特殊的情感[34]。
最初,楊漢先通過(guò)教會(huì)興辦教育的方式來(lái)“救苗”,經(jīng)常利用“做禮拜”等人員較為集中的時(shí)機(jī)和苗族青年討論“苗族如何能夠團(tuán)結(jié)起來(lái)”以及“應(yīng)如何提高苗族文化教育水準(zhǔn)”等問(wèn)題。1938年,楊漢先返回華西協(xié)和大學(xué)繼續(xù)學(xué)業(yè)后,向家鄉(xiāng)父老發(fā)出一份《告石川聯(lián)區(qū)同胞書(shū)》,號(hào)召苗族教民們起來(lái)抵制外來(lái)勢(shì)力欺壓,并倡議在石門(mén)坎開(kāi)會(huì)檢討過(guò)去和規(guī)劃未來(lái),但以失敗告終。事敗后,楊漢先對(duì)教會(huì)淪為國(guó)民黨地方政府的工具以及教會(huì)領(lǐng)導(dǎo)人采取妥協(xié)方式與黨政勢(shì)力合作,甚至狼狽為奸的態(tài)度更是極為不滿。由于基督教本身的局限性以及國(guó)民黨黨政勢(shì)力漸次滲入花苗地區(qū),此種“土著主義”[35]的方式難免失敗的命運(yùn),楊漢先最終與基督教決裂,再也不參加任何宗教活動(dòng)[34]。此后,在應(yīng)對(duì)近代國(guó)族建構(gòu)過(guò)程中,由于他選擇的是學(xué)術(shù)政治的道路,使得他關(guān)于花苗身份認(rèn)同的書(shū)寫(xiě)呈現(xiàn)出一種“較為安靜的自我表述”的文本。1939年,楊漢先在貴州方言講習(xí)所任教期間,接觸到兩位有共產(chǎn)黨背景的青年知識(shí)分子,通過(guò)閱讀《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wèn)題》,了解到蘇共的民族自治等政策,終促使其與國(guó)民黨決裂,并于1949 年加入中國(guó)民主同盟。1950 年以后,他先后擔(dān)任貴州省民族事務(wù)委員會(huì)副主任、貴州民族學(xué)院院長(zhǎng)、貴州省民族研究所所長(zhǎng)等職務(wù),多次被選為省人大代表和全國(guó)人大代表。
當(dāng)然,這種身份認(rèn)同不僅體現(xiàn)在楊漢先謀求民族出路的政治生活中,更是凸顯在其從事的學(xué)術(shù)研究。楊漢先早期發(fā)表的《苗族述略》是其關(guān)于花苗身份認(rèn)同研究的開(kāi)篇之作,主要對(duì)苗族的族源、支系、服飾、口述傳統(tǒng)、藝術(shù)等方面進(jìn)行考述[36]132-142。 1940 年,楊漢先在大夏大學(xué)社會(huì)研究部從事“苗夷社會(huì)研究”工作時(shí),發(fā)表《威寧花苗歌樂(lè)雜談》等多篇苗族研究文章,后被收錄于吳澤霖、陳國(guó)鈞主編的《貴州苗夷社會(huì)研究》中。楊漢先在《大花苗名稱(chēng)來(lái)源》一文中提出“大花苗”是傳教士根據(jù)民間稱(chēng)謂記錄支系名稱(chēng)而開(kāi)始被運(yùn)用,批評(píng)學(xué)界濫用“大花苗”的做法。1941 年4 月,楊漢先到華西協(xié)和大學(xué)中國(guó)文化研究所工作,《大花苗移入烏撒傳說(shuō)考》和《大花苗的氏族》,兩篇文章都是運(yùn)用口述史資料寫(xiě)作而成,彰顯本土民族學(xué)者家園研究的優(yōu)勢(shì)和特點(diǎn)[34]。1948年,楊漢先與鮑克蘭(Inez de Beauclair)共同完成了《黔西苗族調(diào)查報(bào)告》的書(shū)稿。綜觀他的著述及學(xué)術(shù)經(jīng)歷,不難看出楊漢先在定義“苗族”時(shí)對(duì)土著經(jīng)驗(yàn)和口述資料的偏愛(ài),導(dǎo)致他在借用近代民族研究論述中的“民族”概念來(lái)應(yīng)對(duì)現(xiàn)代國(guó)族建構(gòu)工程時(shí),又往往從“主位觀”[34]出發(fā)并呈現(xiàn)出一種“自我表述”[35]的文本。
楊漢先關(guān)于“教民-花苗-苗族”等身份的并置、游移與多重認(rèn)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jié)果。一方面石門(mén)坎花苗地區(qū)特殊的社會(huì)政治環(huán)境和基督教彌漫的文化氛圍,深刻地影響著他的族群觀以及相關(guān)文本的生產(chǎn);另一方面隨著教育層次的不斷提高,以楊漢先為代表的花苗知識(shí)分子被卷入近代國(guó)家的社會(huì)生活中,原有的社會(huì)、文化和族群的邊界被打破,在與這些邊界他者的接觸中增強(qiáng)了楊漢先的族群意識(shí),促使他自覺(jué)地從其所屬的“土著族群”的社會(huì)、歷史和文化研究中抽取有價(jià)值的資源以形成“自我表述”的文本,進(jìn)而在族群、區(qū)域和民族國(guó)家的政治脈絡(luò)中重新定義自我的身份認(rèn)同。
梁聚五、石啟貴和楊漢先等苗族知識(shí)分子的個(gè)案顯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正是由無(wú)數(shù)知識(shí)精英關(guān)于單元民族的認(rèn)同以及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不同層次認(rèn)同意識(shí)逐漸構(gòu)筑而形成的,而非如既有研究假定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作為最高準(zhǔn)則去調(diào)整某種民族認(rèn)同形式,進(jìn)而劃清其與不同層次族群認(rèn)同的界限。誠(chéng)如麻國(guó)慶教授所言,建設(shè)適應(yīng)新時(shí)代需求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需從民族現(xiàn)象的基本維度出發(fā),突破現(xiàn)有民族單位的限制。同時(shí),又要把中華民族共同體置放到民族社會(huì)以及不同層次的社會(huì)結(jié)構(gòu)中予以考察[37]。
三、苗族知識(shí)分子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多重面向及實(shí)踐邏輯
(一)苗族知識(shí)分子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多重面向
“中華民族共同體是歷史形成的命運(yùn)、政治、社會(huì)、文化的共同體”已達(dá)成共識(shí)。在探索鑄牢共同體意識(shí)的路徑策略時(shí),若遮蔽多民族國(guó)家培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多重面向和不同層次,將中華民族共同體視為固化的實(shí)體范疇,乃至與單元民族的身份認(rèn)同對(duì)立,既無(wú)視“多民族國(guó)家的家底”,又有悖于費(fèi)孝通關(guān)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理論主張[37]。民族知識(shí)分子鑄牢共同體意識(shí)的多重面向反映了單元民族建設(shè)共同體意識(shí)的層次性問(wèn)題。
首先,求發(fā)展,謀共生共榮,致力少數(shù)民族教育、經(jīng)濟(jì)、文化等事業(yè)建設(shè)。梁聚五一生輾轉(zhuǎn)于苗族地區(qū),為發(fā)展其交通、學(xué)校和語(yǔ)言文字和衛(wèi)生保健等事業(yè)而奮斗。石啟貴幾乎所有的人生活動(dòng)都與湘西苗族的經(jīng)濟(jì)、教育和文化建設(shè)相關(guān)聯(lián),“事關(guān)吾族,責(zé)豈旁貸”是他生命歷程的寫(xiě)照和最好詮釋。楊漢先所在花苗地區(qū)的特殊歷史遭遇及其本人的坎坷求學(xué)經(jīng)歷,使得他的民生意識(shí)多聚焦于教育方面,試圖以“立智”來(lái)改變民族命運(yùn)達(dá)成“教育救苗”的理想。可見(jiàn),民族間發(fā)展機(jī)會(huì)不均的社會(huì)事實(shí),促使不同地區(qū)的苗族知識(shí)分子把目光聚焦到民生問(wèn)題,并秉承共生共榮理念致力于民族地區(qū)發(fā)展。
其次,以史“立志”,書(shū)寫(xiě)我族歷史,爭(zhēng)取政治平等。苗族知識(shí)分子意識(shí)到僅謀求民族事業(yè)發(fā)展是遠(yuǎn)遠(yuǎn)不夠的,爭(zhēng)取有尊嚴(yán)地立足于多民族社會(huì)才是發(fā)展的前提。針對(duì)民國(guó)國(guó)族建構(gòu)將夷苗等少數(shù)民族排除在“五族共和”之外的做法,梁聚五先后撰寫(xiě)了《苗夷民族發(fā)展史》等多部著作并發(fā)表政論性文章抨擊民族同化政策,試圖通過(guò)對(duì)話主流社會(huì)來(lái)爭(zhēng)取少數(shù)民族平等的權(quán)利地位。石啟貴通過(guò)漢文書(shū)寫(xiě)我族歷史來(lái)化解民族間的“畛域隔閡”,作為“土著民族”代表身份參與到國(guó)民黨的政治事務(wù)。楊漢先則試圖用教會(huì)興辦教育的方式來(lái)“救苗”,失敗后又選擇學(xué)術(shù)政治道路。可見(jiàn),尋求政治承認(rèn)與認(rèn)同是苗族知識(shí)分子書(shū)寫(xiě)我族歷史的根本動(dòng)力,其行動(dòng)邏輯應(yīng)置放于近代國(guó)族建構(gòu)的歷史時(shí)代背景中去理解。
再次,尋求各民族間的聯(lián)結(jié)點(diǎn)和共通點(diǎn),促進(jìn)民族團(tuán)結(jié)與民族融合。梁聚五從實(shí)際生活出發(fā)找出“苗”“夷”或“邊民”“邊胞”等民族之間及其與漢族之間的共通點(diǎn)和聯(lián)結(jié)紐帶,鼓勵(lì)通婚,戳開(kāi)種族壁壘,構(gòu)建新的國(guó)族陣容[28]415。石啟貴通過(guò)“苗漢同源論”論證苗漢間的連結(jié)與共通,二者的共同點(diǎn)在于從“自省”與“他觀”中建立聯(lián)系,雖因不同文化間存在結(jié)構(gòu)性偏見(jiàn)和無(wú)法修正的刻板印象以致不能如愿,他們的不懈努力卻極大促進(jìn)了外界對(duì)苗族文化的了解,有利于加強(qiáng)各民族的團(tuán)結(jié)。
最后,在不同社會(huì)體制下轉(zhuǎn)換自我身份認(rèn)同,消解單元族群認(rèn)同與民族共同體認(rèn)同間的潛在張力。民國(guó)時(shí)期,梁聚五和石啟貴通過(guò)強(qiáng)調(diào)“苗夷”“湘西苗民”和“土著民族”的身份來(lái)回應(yīng)民國(guó)政府強(qiáng)制推行的國(guó)族計(jì)劃工程。新中國(guó)成立后,他們轉(zhuǎn)換原有的族群身份而認(rèn)同中華民族。不同社會(huì)體制轉(zhuǎn)變過(guò)程中,楊漢先也從教民、花苗等身份的并置和游移切換到苗族認(rèn)同。可見(jiàn),共同體意識(shí)的形成是動(dòng)態(tài)過(guò)程,是民族知識(shí)分子在特定社會(huì)歷史背景下發(fā)揮主觀能動(dòng)性的體現(xiàn),是他們?cè)诓煌瑢哟握J(rèn)同中尋找到出路并通過(guò)自我身份認(rèn)同的轉(zhuǎn)換來(lái)消解單元民族認(rèn)同與共同體認(rèn)同之間潛在張力的結(jié)果。
不難看出,苗族知識(shí)分子關(guān)于鑄牢共同體意識(shí)時(shí)呈現(xiàn)出“基于民族并超越民族”的生成路徑,處于不同歷史時(shí)代背景下的知識(shí)分子總是根據(jù)社會(huì)情勢(shì)變化來(lái)調(diào)整自我的身份認(rèn)同,并最終與民族國(guó)家達(dá)成共識(shí)。然而,有研究者把這種努力和實(shí)踐視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民族主義傾向”,認(rèn)為“近代民族知識(shí)分子無(wú)論是對(duì)民族主義理論本身的理解還是隨后內(nèi)涵的建構(gòu)都不穩(wěn)定,實(shí)用主義色彩鮮明,缺乏符合現(xiàn)代民族國(guó)家要求的健康內(nèi)容”[38]。這種認(rèn)知顯然囿于社會(huì)沖突的視角,忽略特定社會(huì)背景及不同行動(dòng)主體的能動(dòng)性。
(二)苗族知識(shí)分子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實(shí)踐邏輯
苗族知識(shí)分子關(guān)于身份認(rèn)同的探索和實(shí)踐與西方民族主義、近現(xiàn)代中國(guó)社會(huì)轉(zhuǎn)型以及族群歷史遭遇等因素交織在一起。在政治經(jīng)濟(jì)權(quán)益競(jìng)爭(zhēng)中,苗族知識(shí)分子根據(jù)當(dāng)下情勢(shì)做出選擇,認(rèn)同民族還是認(rèn)同國(guó)家成為他們轉(zhuǎn)換身份以及優(yōu)化生存環(huán)境常用的策略。這種主體轉(zhuǎn)向和認(rèn)同差異的實(shí)踐邏輯與其社會(huì)位置、邊界他者、承認(rèn)政治和主體能動(dòng)性關(guān)聯(lián)在一起。
第一,社會(huì)位置。這種認(rèn)同差異及主體轉(zhuǎn)向絕非梁聚五、石啟貴和楊漢先等苗族知識(shí)分子的個(gè)人式獨(dú)白,很大程度取決于他們所處的社會(huì)位置以及此位置確立的角色與行動(dòng)。不管是“苗夷民族”“湘西苗民”還是“花苗”,在清末民國(guó)時(shí)期都是政治上和地理上的“邊緣”,不僅是遠(yuǎn)離帝國(guó)庇佑的“邊胞”或“邊民”,還是“五族共和”之外的他者。1949 年以后,民族平等政策推行,他們當(dāng)家做主,從邊緣人群轉(zhuǎn)變?yōu)椤皣?guó)家的主人”。因此,是邊緣還是中心的社會(huì)位置成為苗族知識(shí)分子調(diào)整自我認(rèn)同意識(shí)的重要參照系[30]。
第二,邊界他者。人是社會(huì)性動(dòng)物,民族知識(shí)分子不可能局限于特定的社會(huì)空間,來(lái)自政治經(jīng)濟(jì)權(quán)益以及文化自覺(jué)等多方面的影響,尤其是新舊社會(huì)體制之間的更替,迫使民族知識(shí)分子從原來(lái)的社會(huì)空間轉(zhuǎn)入新的社會(huì)空間。隨著生存空間的轉(zhuǎn)變以及社會(huì)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擴(kuò)大,這些民族知識(shí)分子必然在新生活環(huán)境中遭遇到更多“意義他者”(significant others),比如,不同的黨政勢(shì)力、儒家傳統(tǒng)、民族學(xué)家、基督教會(huì)等。苗族知識(shí)分子在與這些他者的互動(dòng)中自覺(jué)為我,促使他們?cè)谛碌纳鐣?huì)空間通過(guò)歷史書(shū)寫(xiě)等方式來(lái)重新定義“我群”,并試圖消解因空間流動(dòng)和社會(huì)互動(dòng)所造成的身份認(rèn)同迷思。可見(jiàn),在新的社會(huì)文化環(huán)境里,苗族知識(shí)分子關(guān)于身份認(rèn)同的探索與實(shí)踐,顯然是不完全忠于自我的“本真性”(authenticity),而是通過(guò)與自身相關(guān)的他者展開(kāi)互動(dòng)并獲得他者承認(rèn)之后,苗族知識(shí)分子的身份認(rèn)同才得以擺脫個(gè)體性獨(dú)白,在不斷協(xié)商和對(duì)話的族群互動(dòng)中形成新的認(rèn)同意識(shí)。
第三,承認(rèn)政治。與他者遭遇所形成的邊界在某種程度造成不同行動(dòng)主體重新確認(rèn)自我的身份認(rèn)同,導(dǎo)致民族知識(shí)分子在民族認(rèn)同與國(guó)家認(rèn)同之間的游移和轉(zhuǎn)換。然而,這種認(rèn)同差異及主體轉(zhuǎn)向的關(guān)鍵不在于各群體間存在何種具體文化差異以及選擇何種身份認(rèn)同,而在于其關(guān)于身份的認(rèn)知類(lèi)別與差異,“人們強(qiáng)調(diào)差異僅是為了使這些差異具有關(guān)聯(lián)性,認(rèn)同需要的不是實(shí)際差異,而是差異的合法性”[39]175-176。因此,苗族知識(shí)分子努力通過(guò)漢語(yǔ)文書(shū)寫(xiě)我群歷史文化的文本實(shí)踐,意圖顯然不是突顯苗族歷史久遠(yuǎn)與文化特殊性,而是試圖表明它與“五族”一樣具有同樣的歷史貢獻(xiàn),進(jìn)而尋求他者的承認(rèn)與認(rèn)同。可見(jiàn),這種為爭(zhēng)取少數(shù)民族權(quán)利地位的文化自覺(jué)行為,不是知識(shí)精英自我孤立狀態(tài)下炮制出來(lái)的結(jié)果,而是通過(guò)與他者互動(dòng)并得到他者承認(rèn)才獲得的。誠(chéng)如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言:“我們的認(rèn)同部分地是由他人的承認(rèn)構(gòu)成的;同樣地,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認(rèn)的,或者只是得到他人扭曲的承認(rèn),也會(huì)對(duì)我們的認(rèn)同構(gòu)成顯著的影響。所以,一個(gè)人或一個(gè)群體會(huì)遭受到實(shí)實(shí)在在的傷害和歪曲,如果圍繞著他們的人群和社會(huì)向他們反射出來(lái)的是一副表現(xiàn)他們自身的狹隘、卑下和令人蔑視的圖像。這就是說(shuō),得不到他人的承認(rèn)或只是得到扭曲的承認(rèn)能夠?qū)θ嗽斐蓚Γ蔀橐环N壓迫形式,它能夠把人囚禁在虛假的、被扭曲和被貶損的存在方式之中。”[40]由此,梁聚五、石啟貴和楊漢先等知識(shí)分子最終走向“為承認(rèn)而斗爭(zhēng)”的道路。
第四,主體性。民族知識(shí)分子在身份認(rèn)同轉(zhuǎn)換和建構(gòu)中受到國(guó)家體制、邊界他者、自身社會(huì)處境等多種因素影響,導(dǎo)致他們具有多重認(rèn)同并搖擺于民族認(rèn)同與國(guó)家認(rèn)同之間,以致有研究者認(rèn)為其身份認(rèn)同是官方主導(dǎo)的國(guó)家話語(yǔ)工程。這種觀點(diǎn)完全忽略了知識(shí)分子在社會(huì)變遷中的主體性及其對(duì)身份認(rèn)同的影響。事實(shí)上,不同族類(lèi)共同體成員絕非消極地“被安排”“被定義”“被建構(gòu)”,無(wú)意識(shí)地接受?chē)?guó)家主導(dǎo)性的話語(yǔ)敘事。苗族知識(shí)分子在國(guó)家不同社會(huì)體制更替轉(zhuǎn)換自我身份認(rèn)同以及后來(lái)以不同方式參與到民族事務(wù)的政治實(shí)踐均表明這一點(diǎn)。換言之,苗族知識(shí)分子具有強(qiáng)烈的主觀能動(dòng)性,可以利用特定情勢(shì)來(lái)調(diào)整和構(gòu)建自我的身份,從而游移于“苗夷民族”“土著民族”“教民”“花苗”和“苗族”之間。總之,主體性是認(rèn)同建構(gòu)的源泉,只有認(rèn)同主體的訴求得到認(rèn)同客體的承認(rèn)和滿足,才能建構(gòu)起有效的認(rèn)同。多民族國(guó)家需從單元民族的主體性出發(fā),充分尊重單元民族并使之共享繁榮發(fā)展,才能有效化解認(rèn)同間的張力,進(jìn)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凝聚力[41]。
四、結(jié)論
福柯曾指出:“歷史不是崇高進(jìn)步的神話,而歷史為話語(yǔ)建構(gòu)的結(jié)果;因此,了解歷史便需要從主體的角度,探討其建構(gòu)歷史空隙(rupture)間的不同論述(narratives)。”[42]這表明了歷史主體對(duì)于話語(yǔ)建構(gòu)或敘述的重要性。歷史的主體是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主體也是人,民族知識(shí)分子作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倡導(dǎo)者和構(gòu)建者,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得以生成的重要載體。
苗族知識(shí)分子的個(gè)案顯示:(1)多民族國(guó)家中不同族類(lèi)共同體成員具有多種認(rèn)同,單元民族的認(rèn)同來(lái)源于特定的社會(huì)生活實(shí)踐,具有強(qiáng)烈的民生傾向,他們側(cè)重尋求各民族共享發(fā)展、共生共榮,致力于教育、經(jīng)濟(jì)、文化等事業(yè)發(fā)展,而非尋求政治或民族獨(dú)立,與國(guó)家認(rèn)同無(wú)矛盾沖突;(2)族群成員在社會(huì)轉(zhuǎn)型和跨界流動(dòng)過(guò)程中遭遇他者而引發(fā)身份認(rèn)同的游移,促使族群成員在新的社會(huì)環(huán)境中重新定義自我并搖擺于民族認(rèn)同與國(guó)家認(rèn)同之間。然而,這種主體轉(zhuǎn)向及認(rèn)同差異絕不是知識(shí)分子個(gè)人式獨(dú)白,很大程度取決于他們所處的社會(huì)位置以及由此位置確立的社會(huì)角色。為獲得應(yīng)有權(quán)益,民族知識(shí)分子通過(guò)書(shū)寫(xiě)“我群”歷史及諸社會(huì)實(shí)踐,致力于尋求他者認(rèn)同與承認(rèn),彰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過(guò)程中的主體性及他者性;(3)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rèn)同問(wèn)題不在于共同體成員擁有多種形式的認(rèn)同意識(shí),而在于不同族類(lèi)共同體成員在其認(rèn)同結(jié)構(gòu)中把“民族認(rèn)同”和“國(guó)家認(rèn)同”置放于何種級(jí)序以及民族國(guó)家在多大程度尊重并賦予公民平等的權(quán)利地位。
總之,民族知識(shí)分子的認(rèn)同意識(shí)及行動(dòng)實(shí)踐深刻地影響著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建設(shè)。一方面,民族知識(shí)分子是共同體意識(shí)的生產(chǎn)者,又是共同體意識(shí)的消費(fèi)者;另一方面,民族知識(shí)分子可以根據(jù)社會(huì)情勢(shì)轉(zhuǎn)換自身的身份認(rèn)同,從而彰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層次性問(wèn)題。我們不能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簡(jiǎn)化為國(guó)家認(rèn)同意識(shí),它基于民族而又超越民族,應(yīng)回到“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理論內(nèi)涵來(lái)厘清“多”與“一”的關(guān)系[43],應(yīng)從特定的民族社會(huì)及不同族類(lèi)共同體成員的認(rèn)同出發(fā),來(lái)理解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生成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