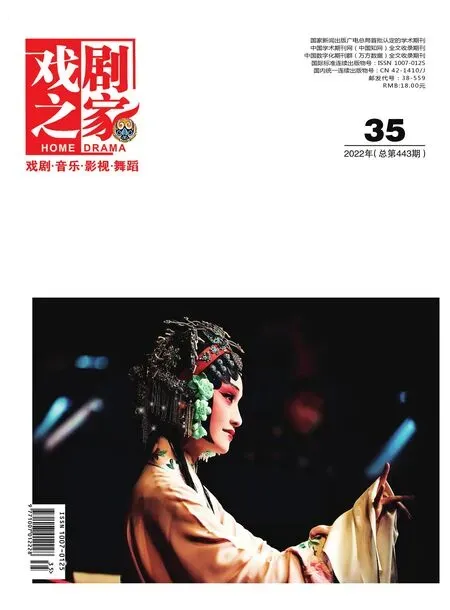我國民族風格賦格曲音程與和弦教學難點淺析
隋 星
(中國礦業大學 人文與藝術學院,江蘇 徐州 221116)
賦格曲來源于西方,是復調樂曲的一種形式。雖然當今世界作曲家的主要創作目標已經不是賦格曲,但是賦格曲的影響仍非常深入且廣泛。眾所周知,賦格曲除了要充分展現縱向聲部外,音程與和弦是其中兩個關鍵要素。在西方賦格曲法則里,關于音程與和弦的運用有著嚴格要求,這種要求在嚴格對位法體系里面體現得淋漓盡致。從中央音樂學院的段平泰先生和于蘇賢先生、上海音樂學院的陳銘志先生,到現階段各大音樂學院的復調教授,無不為建立我國民族風格賦格曲教學體系嘔心瀝血。但是從整體來看,有關民族風格賦格曲的專著以及論文的數量還遠遠不夠,需要更多年輕人投入其中。那么本文就圍繞一些經典的民族風格賦格曲作品,針對音程與和弦的寫作方法進行闡述。由于調式、音階、旋法等眾多因素的差異,我國民族風格賦格曲的寫作方法一直因為缺少操作性較強的理論坐標而成為一個教學難點。其中的音程以及和弦在繼承西方傳統的基礎上又衍生出了一些民族性特征,使得規范性更加難以被確認。本文試圖解開民族風格音程與和弦寫作的技術密碼,為賦格曲教學與實踐打好堅實的理論基礎。
一、音程的運用方法
音程法則的運用主要體現在二聲部對位。并非三聲部以上的對位中沒有音程,只是此時的音程都融入了和弦中,很多行為已經不受音程法則的限制,因此此處僅以二聲部為例。
在西方對位法中,強拍上以三、六度音程為主,五度與八度這種空洞音程在音樂進行中比較少見,二度與七度根本不協和,純四度更是被明令禁止。而我國民族風格賦格曲作者雖然在基礎訓練過程中仍然遵循西方傳統原則,但在實際創作中卻顯示了靈活運用的特點,比如二度、七度、五度、八度甚至四度都在一些作品中頻頻出現。我們在汪培元先生的《小賦格》開始處的主題與對題中可以看出,這七個小節的強拍音程分別是純四度、純五度、純四度、純八度、小六度、大二度、純四度、純八度;次強拍音程分別是純四度、小七度、大二度、純四度、純四度、大六度、純五度。雖然開頭音程是純四度到小三度的解決,但在總體音樂背景下,純四度的感覺非常明顯。在于蘇賢先生的《d 羽小賦格》開始處的主題與對題中,五個強拍依次是純四度、純八度、純八度、小六度、純八度。在段平泰先生的《三聲部賦格》第三小節的答題與對題結合中,強拍音程依次是純八度、小三度、純八度、純八度、純八度、純五度。在陳銘志先生的《山歌村舞》的開始部分,其依次是純五度、大七度、大二度、小三度,并且在《山歌村舞》最后的密接和應中,第二小節強拍是純四度,第三小節則是三聲部組成的純五度。
這些現象不是巧合,也不是例外。也許當它們剛剛出現的時候,確實會被稱為例外,但如今這種“例外”的情況已經太多,若我們再稱之為例外,恐有不妥。它們在當今中國復調音樂界頂級的三位大師的作品中頻頻出現,不能不讓人深思。
(一)純四度音程的運用
在基礎訓練中我們可以遵守傳統處理純四度的方法,比如作為和弦外音、放在弱拍、放在隱伏和聲中等等。但是筆者認為在創作中不能完全封殺關于純四度的自由運用。正如劉福安先生所說,在實際音樂作品中,有時和聲上比較自由,個別地方可以出現純四度或純四度平行,甚至純八度平行等。關于純四度的運用,筆者進行了如下思考。
西方不用純四度,不是因為它不協和,而是因為它不穩定,并且大家總會把純四度與四六和弦聯系起來。的確,西方音樂的骨架就是三度疊置的和弦,那么以和聲為基礎的西方音樂自然把每一個強拍都看作是自身的關節,既然是關節就必須穩定,又因為同樣穩定的五度與八度此時顯得過于空洞,于是所有的重擔就壓在了既穩定,又不空洞,還能明確調性的三、六度的身上。而在我國民族五聲調式中,如果按照西方的疊置原則,我們的和聲根本不完全,只有兩個完整三和弦,即宮和弦、羽和弦,僅靠這兩個和弦無法形成功能意義上的和聲連接。因此筆者認為,在五聲調式中,所有和音在調式中的“功能”性都沒有西方和聲那樣明顯,并不承擔逐次解決主和弦的義務,所以民族五聲調式中便沒有終止四六和弦,而四度音程也不會因為與終止四六和弦的血緣關系而受到排斥。經筆者計算,在我國的傳統五聲音階中,大二度音程的數目是三,小七度音程的數目是三,大三度音程的數目是二,小六度音程的數目是二。純四度音程的數目是四,純五度音程的數目是四,大六度音程的數目是一,小三度音程的數目是一。因為純四度和純五度互為轉位,所以我們可以將二者并為一類。四、五度音程在我國傳統五聲音階中占有絕對地位,四度音程的數目在五聲音階中超過了其他所有音程,所以它被用到的機會就更大。
(二)八、五度音程的運用
在我國的賦格作品(特別是原始型賦格曲)中,由于主題自身完整性的原因,樂曲內部存在大量的終止。在西方,中間部分用三、六度音程終止不但可以明確調性,而且還可以與最后的終止有所區別,但我國的賦格曲很難以三、六度音程為終止。原因之一是我們的終止音一般都是主音;原因之二是在五聲調式中不是所有的調式都有三音;原因之三是只有結束在八度才能讓我們真切感受到穩定的調性。比如G 六聲調式的終止,如果結束在三度或六度,結束音程就成了G、B 或B、G,感覺上不如八度聽起來更加穩定、明確。因此,純八度音程在民族賦格作品中運用的次數也就相對較多。
純五度音程在民族風格賦格曲的內部也有一定運用,但在強拍時出現的次數不多。在五聲調式中,一般情況下其由八度音程向內反向級進或二度音程向外反向級進產生,地位僅次于三、六度,卻增添了一些平穩的效果。
(三)二、七度音程的運用
從賀綠汀的《牧童短笛》到現代高難度的賦格曲,二、七度音程的運用在我國復調音樂作品中隨處可見。它們存在的理由與純四度存在的理由相似,其相關運用是突破了西方傳統三度疊置的和聲的結果,使這種特殊的色彩為我國復調音樂的民族化進程添上了濃濃的一筆。筆者認為,三、六度音程固然是好的,可是其他音程也不能被我們拒之門外,要知道只有它們才能讓我國作品與西方作品之間產生沖突,進而由沖突變成對峙,由對峙變成區別,由區別變成特點。
二、和弦的運用方法
民族性和弦自黎英海先生的“三度間音”開始至今仍是理論家研究的焦點,在賦格曲音樂創作領域,和弦問題更是關鍵。縱觀現存的賦格曲作品,關于和弦的選擇及其連接問題,筆者認為其中有三種現象比較普遍。
(一)和弦的多樣化特征
在西方,傳統和弦都是三度疊置。而在我國,由于五聲調式在主音階上存在的某種局限,使得能夠以三度疊置的和弦非常少。所以,某些中國作曲家為了適應民族風格的要求,在復調樂曲中采用非三度疊置的和弦,甚至借鑒印象派、現代派和聲中的某些手法,這些都是被允許的。為了豐富五聲調式和弦,黎英海先生提出了“三度間音理論”,試圖把調式中沒有的F 與B 加入和聲。這樣做固然豐富了民族和聲,但是也遭到了一部分學者的質疑:調式中都沒有的音,如何用得?于是一大批愛國音樂家投身于五聲調式民族音樂創作中,試圖通過創作來總結新的理論,進而創建民族和聲體系。集體的智慧是無窮的,在越來越多的作品出現后,我國獨特的民族和聲體系初見端倪。這些和聲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都把五聲音階看作級進,也就是暫時把調式中五個音之間的度數視為相同的,并以三個音疊置為基礎。此處以C 宮調式為例,具體類別如下:
和弦音之間相隔一個音(音符從左到右即從低到高排列,以下情況同理),如:136、251 等。
此類中有四度疊置的和弦,但并不都如此,與西方近現代的完全四度疊置和弦有所區別。另外,在一些賦格作品中我們會經常看到一些“四六和弦”出現,其實正來源于此。
在陳銘志先生的《新春》的第9 小節,次強拍上是一個明顯的四六和弦,這種情況如果在西方傳統的對位法則下應該是錯誤的,但是在民族風格和聲色彩里面就顯得非常有味道。
和弦音之間相差兩個音,如:152、315 等。
和弦音之間相差三個音,如:165、216 等。在多數情況下,此類和弦的應用一般要轉化為下面的形式,如561、612 等。
純四度與純五度的疊置,如:252、363 等。純四度與純五度音程的數目在五聲調式中占有壓倒性優勢,二者的完美結合成為民族和聲的代表性音色。
在第三類的中間附上一個二度,如:2562、3673等。此類和弦的音響更為豐富,比較接近西方的七和弦。當然七和弦的組合更加復雜多樣,但與三和弦同理,此處不再詳述。作曲家還可以根據以上幾類進行各種轉位處理,所以民族和聲其實是非常豐富多彩的。當然,現如今的民族音樂(特別是七聲調式)不會拒絕三度疊置的西方傳統和聲,而是與之結合起來,共同構建現代民族風格的新篇章。
(二)和弦的功能傾向性
在西方,每一個和弦都有自己的位置和作用,都具備直接或間接傾向主和弦的功能,而這種互相依賴的傾向性正是它們支撐作品完整性的法寶。在一個簡練的和聲連接中,任意一個和弦如果被抽調,都會導致整體性的殘缺。而我國的部分民族風格賦格曲卻與之有著相當大的區別,作曲家可以控制整體調性布局,但是同一調性下的和弦連接卻不像西方那樣一環扣一環。比如陳銘志先生的《新春》主題的第三次進入,如果我們把非和弦音全部去掉,再把和弦還原成三度疊置,就得到了這樣一組連接:135、613、357、135、613、616、357。這組和弦幾乎沒有什么傾向性,連接方面非常自由。再比如饒余燕先生的《賦格》中主題的第三次進入,如果我們把所有的外音都去掉,還原成最原始的和弦后形成了這樣一組連接:572、72 升4、572、625、246、575。從這個和弦連接中我們可以看出,雖然其有一定的傾向性,但不夠明顯,而且和弦之間的連接也沒有形成規范,仍比較自由。但是,民族和弦的連接也并非無章可循,總會通過一些和弦直接或間接結束主和弦。也就是說,在民族風格賦格曲里,和弦最終進入主和弦的方式不僅僅局限于屬和弦到主和弦,方式多種多樣。
(三)和弦的世界性特征
隨著創作與教學的進一步發展,我們逐漸會發現一些問題:是不是為了保證我們的民族性,就要在和弦運用上與西方和弦進行區別?是不是一定要在調式與和弦的各種法則上以我們的五聲音階為基礎?其實這個問題在我國老一輩作曲家的作品里面已經有了答案。比如桑桐先生的鋼琴作品《在那遙遠的地方》,在堅持民族化特征的同時引入大量西方作曲思維,甚至出現大量不協和和弦。因此,在當今賦格曲教學中,我們不應該完全限制學生對和弦的使用,要引導學生打破和弦界限,真正實現民族與世界的融合。
三、結語
民族風格賦格曲中的音程與和弦教學不是一件輕松的事,因為我們必須進行各種分類才能夠使之清晰。在西方對位法中,強拍上以三、六度音程為主,五度與八度這種空洞音程在音樂進行中比較少見,二度與七度根本不協和,純四度更是被明令禁止。而我國民族風格賦格曲作者雖然在基礎訓練過程中仍然遵循西方傳統原則,但在實際創作中卻顯示出靈活運用的特點,比如二度、七度、五度、八度甚至四度都在一些作品中頻頻出現。筆者希望通過文本能夠為民族風格賦格曲教學體系添磚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