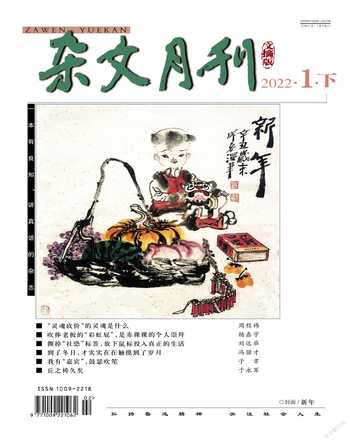讀《崇明老人記》想到的
沈棲
閑來無事翻閑書。《續古文觀止》收錄的康熙時代進士陸隴其的《崇明老人記》一文吸引了我。
該文稱:崇明有位吳姓老人,年已99歲,其妻也有97歲了。膝下四子,壯年家貧,鬻子以自給,四子相繼成了富人的家奴。后來,四子自立,贖身且娶妻,還各自經商,或開布店,或賣雜貨,或售腌臘,家境日隆。值得稱道的是,他們對年邁無業的父母孝敬備至,恪守“為人之子”的道德。
小輩孝敬老人,首先要解決老人吃住問題,使其老有所歸,延年益壽。崇明吳老的四子主動提出老人用膳“每月一輪,周而復始”,媳婦認為還不夠盡孝,“乃以一餐為率”。每回用膳,“稱觴獻壽,率以為常”。這般誠心侍奉老人,令老人笑口常開。相較時下某些年輕人,差焉!我曾看到一幅題為《最佳方案》的漫畫:四個兒子圍著一只轉盤,轉盤上寫著老大、老二、老三、老四,穿著寒磣的老人危坐在轉針上,四子唯恐轉針停留在自己的名下,其惶然之狀可掬。四子都不情愿承擔老人的生活,只得用“賭”的方式決之。如此道德水準和思想境界與《崇明老人記》中的四子比,宛如霄壤。老人倘若連吃住問題也無著落,遑論“安度晚年”!
對老人的生活習慣要以寬容的態度順從之,這也是小輩孝心的一個表征。兩代人不止是年齡反差,在生活習慣上也多有異趣,作為小輩理應“遷就”老人,而不是相反。吳姓老人喜歡與友人以弈棋賭博(純屬“小來來”),四子并不反對,在經常勸告老人注意起居的同時,還“遣人密持錢三百文”給友人,“囑其佯輸錢于老人”,以博得老人的歡心。四子唯一的心愿就是讓老人在有生之年盡享人間歡樂和溫馨。記得魯迅對老母也有一段軼聞:其母喜歡讀《啼笑因緣》之類的鴛鴦蝴蝶派作品,她寫信給蟄居在上海的魯迅,要兒子多買幾部這類作品。魯迅雖對鴛鴦蝴蝶派頗有微詞,但他卻以寬容的態度順從老母,相繼四次寄上這類書籍,并將此事一一錄于日記。小輩何必以自己的愛憎、興趣、是非標準來衡量老人呢?
給無業老人以經濟上的救濟,也應是小輩盡孝的題中之義。《崇明老人記》云:“老人飲食之所,后置一櫥,櫥中每家各置錢一串,每串五十文,櫥中錢缺,則其子潛補之,不令老人知也。”雖說四子從商,家境富裕,但主要還是他們有一顆孝敬老人之心。時下,不是亦有不孝之子虐待老人的事例見諸報端嗎?這些“逆子”未必都是“赤貧如洗”的窮漢,有些還是“大款”哩!孝敬老人,與其說是經濟因素,不如說是道德的緣故。孝敬老人是“為人之子”的必備道德,在文明國度里,它又是“文明”的一個重要內容,切莫等閑視之呵!
摘自《長寧時報》2021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