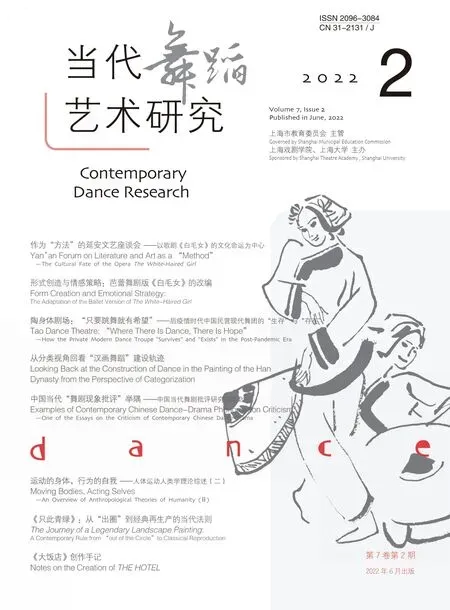綜藝舞蹈的影像感知與舞蹈—影像的技術“靈韻”
陳琰嬌
舞蹈影像的誕生與電影藝術的發展幾乎同步,無論是路易斯· 盧米埃爾(Louis Lumière)對本土各式舞蹈表演的拍攝,還是喬治· 梅里愛(Georges Méliès)將舞蹈作為“幻想電影”(fantasy films)的重要表現形式,都向我們展示了早期影像中舞蹈的重要性。從默片轉入有聲電影之后,完整的舞蹈電影類型出現,早期好萊塢歌舞片被視為其代表。此后,從舞臺音樂劇的電影改編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周六夜狂熱》(Saturday Night Fever,1977)、《閃電舞》(Flashdance,1983)為代表的青春舞蹈片,影像中的舞蹈也從具體的影像類別發展為表現社會身份與浪漫想象的文化隱喻。
舞蹈與影像的密切關系不僅體現在舞蹈影像的發展史中,舞蹈影像更成為大眾了解、欣賞舞蹈的最重要媒介:對非藝術院校的舞蹈教育而言,舞蹈鑒賞課程大多只能通過觀影方式完成;對劇場觀眾而言,促成《只此青綠》《醒獅》等作品“出圈”的,首先也是屏幕上的舞蹈表演與在線傳播;對電視觀眾而言,真正擔負起舞蹈藝術拓荒者角色的,并不是劇場中的舞蹈作品,而是屏幕上的舞蹈表演,這當中又尤以舞蹈綜藝為代表。換句話說,對今天的大眾而言,舞蹈幾乎等同于影像中的舞蹈。以此為背景,本文以舞蹈綜藝為研究對象,探討舞蹈—影像背后的藝術感知及技術“靈韻”問題。
一、 舞蹈綜藝:知識型與“視覺快感”
國內的電視舞蹈節目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歷了較大的發展變化,既有研究從不同路徑切入,對這一發展歷程進行了不同類別的歸納,總體來看都以時間為分期①對國內舞蹈綜藝的回顧研究,參見:楊越明.舞蹈類電視欄目現狀及前景分析[J].北京舞蹈學院學報,2005(2):74—77;董爽.中國電視舞蹈綜藝的他鑒與本土化(2006—2020)[D].北京:中國藝術研究院,2021。。本文嘗試僅將其劃分為電視綜藝、網絡綜藝兩個階段,在以總體時間線索為背景的基礎上,強調舞蹈節目形態演變背后的“知識型”(épistémè)問題:不同舞蹈節目的知識型對應著不同的舞蹈影像實踐、舞蹈影像感知與舞蹈影像再現。
中央電視臺綜藝頻道播出的《舞蹈世界》(1999)是較為典型的早期文化型舞蹈綜藝。節目由場內和場外兩部分內容構成,場內為晚會節目視角,由三個方向的機位組成,場外為電視紀錄片視角,由采訪、解說構成。這一時期的電視綜藝,重在文化知識的介紹,以《正大綜藝》為典型代表。無論是《正大綜藝》的“世界真奇妙”板塊,還是《舞蹈世界》對全球舞蹈的介紹,都可看作文化地理空間的建構和拓展。到了《舞林大會》(2006)和《舞動奇跡》(2007)階段,由于加入了比賽環節,觀眾明顯感受到了節目內容的更新。與這一時期典型綜藝《超級女聲》(2004)的素人選秀相比,舞蹈綜藝的策略是演員跨界競演,以明星的號召力吸引觀眾。但值得注意的是,從影像語言來看,此時的舞臺拍攝手法并沒有太大不同,更顯著的變化來自內容調整背后的知識話語變更:從強調(集體)地理空間的知識建構開始轉變為強調(個體)身體經驗的技術展示,從文化型舞蹈綜藝轉變為技術型舞蹈綜藝。網絡綜藝興起之后,舞蹈綜藝迎來了真正的變化。一方面,這一階段的節目充分吸納了前兩個階段的長處,如通過嘉賓、舞者講解舞蹈知識,通過字幕標注技術動作,競演形式也更新穎;另一方面,與以往舞臺空間的影像轉化不同,這一階段的舞臺開始向劇場空間融合,舞臺邊界越來越模糊,舞者留給觀眾的不再是舞蹈表演而是舞蹈作品。無論是充分展現街頭文化的《這!就是街舞》(2018),還是包羅各個舞種的《舞蹈風暴》(2019),舞者都不再是明星的搭檔,而是通過綜藝成了明星。
理解網絡綜藝有兩點不可忽視:一是有別于傳統電視節目更凸顯“網感”的綜藝制作,二是有別于電視媒介的移動設備端觀看。前者聚焦于網絡觀眾的觀看需求,后者使主動反復觀看成為可能,兩者都暗中指向觀眾位置的變化。理解了這一背景,也就能理解舞蹈綜藝知識型的再次調整,當如何編排作品更能“打動”(affect)評委/觀眾成為舞者創作的重要考量時②技術媒介對舞者身體與感知行為的影響,參見:宋啟明,董媛媛.技術哲學視閾下綜藝《舞蹈風暴》對媒介技術隱喻的解構[J].當代電視,2021(6):22—28,32.,個人技術展示就開始讓位于技術之上的情感召喚,舞蹈綜藝也就從技術型最終走向了情感型。
2021年,由嗶哩嗶哩與河南衛視聯合出品的《舞千年》成為年度評分最高的舞蹈綜藝,其獨特的情景綜藝形式廣受好評。《舞千年》將各具特色的中國舞蹈融入歷史情境,在情景劇中呈現舞蹈,的確與前面提到的各階段舞蹈綜藝都不相同。但從知識型來看,強調“概念化情感模式”的《舞千年》仍然屬于情感型③閆楨楨.創造“感受”還是加固“經驗”?:從《舞千年》大型文化劇情舞蹈節目談起[J].北京舞蹈學院學報,2022(3):1—7.。到這里我們可以說,舞蹈綜藝自身形態的變化并不等同于舞蹈綜藝知識型的變化。
節目制作技術的進步給觀眾帶來的最直接感受是看的方式發生了變化,更高清的節目效果,更極致的視聽語言,更便捷的觀看渠道,在這一背景下,對舞蹈綜藝的思考自然指向“如何觀看”,即影像技術、觀看媒介的變化如何直接影響舞蹈節目的呈現和觀眾的視覺體驗。但通過前文的梳理還可以觀察到,舞蹈綜藝并不只是影像化舞蹈的媒介載體,其發展也體現了大眾所面對的舞蹈知識型變化,正是這種知識型的變化給我們帶來了觀看舞蹈綜藝的真正難題—當我們通過綜藝來觀看舞蹈時,究竟應該將其放置在什么語境中來探討?這種變化要求我們重新審視的是舞蹈自身,還是觀看舞蹈的方式?
如果說技術變化首先指向觀看方式的變化,那么知識型的調整則提醒我們注意觀看內容的變更。以此為背景,文本提出“綜藝舞蹈”的概念,舞蹈綜藝指的是綜藝節目的具體類別,綜藝舞蹈則強調舞蹈在綜藝節目中呈現為獨特的“舞蹈—影像”形態,觀眾通過這種有別于傳統舞臺的場景(scene)被感召。相比于前者,后者可將非舞蹈綜藝中的舞蹈也納入討論范圍,如在《乘風破浪的姐姐》(第三季更名為《乘風破浪》)、《偶像練習生》《創造101》等綜藝節目中,舞蹈始終是競演的重要項目。綜藝舞蹈的提出正是為了回應舞蹈綜藝面臨的根本問題:經過鏡頭和屏幕中介的“舞蹈—影像”如何激發觀眾的“視覺快感”(visual pleasure),從而最終完成情感召喚。
所謂“舞蹈影像”,最廣泛的意義上可以看作關于舞蹈的影像,已有學者從媒介角度對舞蹈影像展開了基于圖像發展視野(從繪畫、攝影到視頻、電影)的哲學溯源①李洋.舞蹈影像的哲學問題:從舞蹈繪畫到舞蹈視頻[J].北京舞蹈學院學報,2021(5):1—7.。“舞蹈—影像”的提法則進一步強調了舞蹈和電影的交互,“影像元素投入舞蹈表演中,實現了舞蹈在電影發明之前不存在的身體,使舞蹈藝術的內容和表現形式都發生了變化”,其類別的劃分也是基于不同的交互訴求②程思.“舞蹈—影像”的研究路徑與類型建構[J].北京舞蹈學院學報,2021(5):32—38.。舞蹈影像不僅涉及最基本的舞臺舞蹈和銀幕舞蹈的區別,還包含不同影像形式的區別,指向不同的視聽語言規則。正是舞蹈影像的混雜性和流動性要求建立有別于傳統舞蹈的評價標準,以進一步分析“屏幕身體”(screen body)和“現場身體”(live body)的不同③DODDS S. Dance on Screen:Genres and Media from Hollywood to Experimental Art[M]. Houndmills, Basingstoke,Hampshire:Palgrave,2001:68.。
從形式上來看,應該說舞蹈影像至少包括這樣兩類:一類是現場舞蹈的影像轉化,也就是對舞臺進行忠實的影像改編,讓影像為現場舞蹈服務;另一類是專為影像而設計的舞蹈,在這一類作品里媒介創造性地參與到舞蹈編排中,舞蹈反過來成了影像的調動元素之一。前者更在意舞蹈影像的“現實感”,這類作品也是一般意義上的“舞蹈影像”,后者則更強調舞蹈影像的“設計感”,這類只能通過影像來觀看的舞蹈作品通常被稱為“視頻舞蹈”或“影像舞蹈”。但問題在于,媒介技術越發展,兩者的界限也就越模糊,比如綜藝舞蹈實際上就可以看作兩者的融合。
本文的“舞蹈—影像”首先認同于前文所梳理的舞蹈影像概念以及舞蹈與影像的關系,在此基礎上借助德勒茲的“生成”理論,探討綜藝舞蹈所觸發的舞蹈感知及其變化。與傳統的電視舞蹈相比,綜藝舞蹈的觀看視角更加突出,觀眾感受到的與舞者之間的距離也更加貼近。如果說傳統的電視舞蹈仍然是“過去”的影像化,那么面向“未來”的綜藝舞蹈則不存在這樣一個現場轉錄,現場只在觀看中生成。在從技術型向情感型的轉變中,這一點尤為重要。
這使得特寫、回放、停頓等具有“放大”功能的普通影像語言在綜藝舞蹈中獲得了新的意義:一方面,它們凸顯了視覺快感的集中投射,讓觀眾面對舞蹈也收獲了如同“游客凝視”的體驗,將所見之景影像化、景觀化;另一方面,這些技術手段也讓觀眾在感知中重塑了舞蹈,典型代表如《舞蹈風暴》中的“風暴時刻”,360度的照片顛覆了觀眾的傳統舞蹈感知,它給觀眾帶來的震驚不只是流動的身體被靜止了,更在于生命的強度被放大了,此時舞蹈是作為過程中的行動來把握的。接下來以“風暴時刻”為代表,進一步探討綜藝舞蹈的影像感知問題。
二、 舞蹈的影像感知:從“柯達瞬間”到“風暴時刻”
《舞蹈風暴》自2019年開播以來,取得了收視、口碑雙豐收④《舞蹈風暴》第一季芒果TV累計播放量8.32億,豆瓣評分9.1分(40 431人參與評分),第二季芒果TV累計播放量8.44億,豆瓣評分9.0分(17 019人參與評分)。數據檢索時間為2022年10月10日。。在2020年8月舉辦的第26屆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獎評選中,《舞蹈風暴》還獲得了“最佳電視綜藝節目”獎。該節目最亮眼的環節是“風暴時刻”的設置。所謂“風暴時刻”,指的是通過環繞圓形舞臺的128臺相機將舞者們的高光時刻合成為一張360度的照片—仿佛《黑客帝國》中“子彈時間”的舞臺再現。
“風暴時刻”并非《舞蹈風暴》首創,2018年由加拿大TVA電視臺播出的《舞蹈革命》(Dance Revolution)就設置了這一環節。同期的其他國內舞蹈綜藝,如《起舞吧!齊舞》(2019)《舞者》(2020)等,也采取了相似的技術手段—128機位加360度環形拍攝加“4K超高清”—呈現舞者在流動中的靜止。更值得關注的是,這一技術理念正在從綜藝舞臺進入劇場演出,如在中國歌劇舞劇院舞劇團業務考核展示項目《舞上春》(2021)的云演播中,“引入自由視角、多視角技術形成藝術畫面的視頻互動”①劉玉娟,張弘馳.藝術“破圈”之思:中國歌劇舞劇院《舞上春》云演播項目深度剖析[J].當代舞蹈藝術研究,2021(3):23.,高清全景捕捉技術的運用清晰地展示了中國古典舞的高水準技術,以互動為訴求的“時空凝結”和“動態流屏幕分享”更能讓觀眾以“編導”身份自主決定如何觀看,以便于深度觀賞和分析舞者的身體技術。
在此之前,舞蹈與攝影圖像之間的關系往往被看作充滿張力與沖突的。從藝術哲學的層面來看,舞蹈的運動與力總是和“拍攝”的靜止相反,舞者的“表演”和攝影師的“拍攝”事實上處于兩個不同的理論序列②李洋.舞蹈影像的哲學問題:從舞蹈繪畫到舞蹈視頻[J].北京舞蹈學院學報,2021(5):1—7.。“風暴時刻”對動作的瞬間凍結首先動搖了觀眾的時間觀念,同時也挑戰了舞蹈影像必然完美這一觀念,這一時刻的失誤將會被定格,而不是抹去。也就是說,對觀眾而言,舞蹈攝影事實上已經從表演與拍攝轉化為了表演與展示,即通過拍攝或觀看這樣的影像,來確認舞蹈與情境。
柯達呼拉秀(Kodak Hula Shows)③柯達呼拉秀是免費的露天表演,于1937年至2002年在美國夏威夷威基基的卡皮歐拉尼公園(Waikiki’s Kapiolani Park)舉行,借由傳統舞蹈和當地音樂在表演中呈現群島的歷史風貌。由于缺少贊助,演出于2002年結束。就是這樣一個拍攝和觀看舞蹈的典例。柯達公司從1937年開始出資贊助夏威夷呼拉秀,為了便于游客拍照,舞臺呈現與肢體動作都經過精心設計:表演場地設在戶外,觀眾面向中央舞臺,陽光要灑在舞者臉上而不是直射游客,以確保現場光線條件適合拍照;編舞時動作不能太快,舞者要偶爾停頓,以方便游客抓拍。在這樣的精心設計之下“呼拉秀宛如一場由柯達瞬間(Kodak moments)串接而成的表演”④厄里,拉森.游客的凝視[M].黃宛瑜,譯.上海:格致出版社,2020:198.。
如果我們將由柯達膠卷拍攝的柯達瞬間⑤在《游客的凝視》中,作者詳細回顧了旅游的“柯達化”。早在1890年,柯達相機就成為到埃及游玩的歐洲游客的普遍旅游配備,到1910年,全美1/3家庭都擁有一臺柯達相機。柯達公司鎖定新興中產階級家庭與旅游產業,“柯達瞬間”(Kodak moments)和“柯達家庭”(Kodak families)所體現的正是柯達的權力知識關系的制造,一如柯達經典廣告詞:“你只要按個鈕,其余交給我們。”(You press the button,we do the rest.)用戶可以通過“柯達瞬間”的網頁(https://www.kodakmoments.com/)上傳自己的照片或瀏覽別人的照片。與“柯達瞬間”的日常性不同,由華為提供技術支持的“風暴時刻”所代表的則是另一種攝影能力,超高清放大。華為手機近年最重要的技術革新之一就是其攝像頭可以提供50倍超級變焦,讓用戶清晰地拍攝月亮。看作“風暴時刻”的前身,那么兩個瞬間的對比的確展示了舞蹈與攝影關系的飛躍。最直觀的改變首先是攝影器材的變化,機器之眼的升級讓舞蹈攝影曾經面臨的爭論迎刃而解,360度立體照片也讓舞者擺脫了拍攝速度與影像質感的困擾,舞者不必為了觀看速度而改變動作速度。如果說“柯達瞬間”所代表的是將現場觀看定格的愿望,那么“風暴時刻”則恰恰相反,這是一種即使你身在現場,也不可能獲得的觀看視角。

圖1 柯達呼拉秀(美國夏威夷威基基,1937)⑥ 圖片來源: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ānoa Library. Kodak Hula Show[EB/OL]. [2022—05—07]. https://airandspace.si.edu/explore-andlearn/multimedia/detail.cfm?id=7073.
這就指向了技術之上的感知變化。“風暴時刻”由舞者提前自行選定,被選中的通常是具有極強技術性的展示性動作。更重要的是,360度的瞬間影像帶來的震撼不只是這一動作的具體停頓,更在于一種普遍意義上的停頓,在這里觀眾得以感受時間如何空間化。這種飽含生命沖動的停滯對觀眾而言近似于一種奇跡的顯現。只有理解了這一點才能理解“風暴時刻”何以能沒有分歧地同時被舞者、評委和觀眾接受。如果說“柯達瞬間”確認的是空間的文化想象,是對日常經驗和文化地理學的復述,那么“風暴時刻”確認的則是感知瞬間,是對抽象感知的具體展示,是日常經驗之外的震驚時刻。
當然,反對意見也可以說,在今天這樣的“總體屏幕”時代,我們的觀看視角早已被充分電影化,對于所有的綜藝節目來說皆是如此。如果不同類別的綜藝都以“情感客體化”為共同訴求,區別只在于差異化的實現方式,那么舞蹈就并不特殊,這仍然是“如何觀看”的問題。但值得注意的變化恰恰在這里,正是對這一瞬間的“自然”接納向我們宣告了綜藝舞蹈的實質:綜藝舞蹈只能通過影像和界面觀看。
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綜藝節目中的舞蹈競演環節往往容易引發爭議。例如在《乘風破浪的姐姐》(第一季)中,多輪投票環節都出現了現場觀眾的選擇和節目播出后網絡觀眾的反饋完全相反的情況,于是網絡觀眾將現場投票觀眾戲稱為“小聾瞎”,以調侃她們不懂欣賞,也由此質疑現場觀眾身份的合理性、質疑結果的公平性。這里不對節目內容做進一步分析,而是嘗試提供另一種理解分歧的思路。
表面上看,現場觀眾和網絡觀眾觀看的是同一個作品,區別只在于觀看視角不同:現場觀眾被固定在座位上,因此獲得了以特定角度融入此時此地的具身經驗;網絡觀眾則被機器之眼賦予了全能視角,以彈幕的形式表達網絡空間中的持續“在場”。但實際上兩者調動的已經是截然不同的舞蹈感知經驗,他們觀看的既是同一支舞蹈又是不同的作品,如果說現場觀眾觀看的是“現實”(the actual)的節目舞蹈,那么網絡觀眾觀看的則是“潛在”(the virtual)的綜藝舞蹈,綜藝舞蹈的舞蹈影像不是現實舞蹈的副本,而是對超越現場的感知的確認,在這里,現實等待著與感知相遇。從這個意義上說,兩者的分歧幾乎無法避免。
于是,新的問題也隨之而來,如果我們接受綜藝舞蹈是一種有別于現場副本的舞蹈—影像,那么它是否創造了一種新的舞蹈感知?如果不是,該如何理解這種感覺上的分歧?如果是,又該如何處理其與傳統感知之間的關系?如果綜藝舞蹈必然指向超越現場的感知,那么應該是把它當作一種概念來理解,還是把它當作一種感受來把握?而這種種問題都指向對舞蹈—影像技術“靈韻”的重新審視。
三、 綜藝舞蹈:“生成—可感知物”與技術“靈韻”的可能性
前文提到,由于在綜藝節目的舞蹈競演中比賽成員不得不首先考慮現場反饋,因此律動性和感召性更強的勁歌熱舞就成了首選。但節目上線之后,這樣的作品又未必能有預期中的流傳度。相反,節奏較慢的歌舞雖然往往意味著現場投票不占優勢,但其中的優秀舞臺作品卻能在網絡上廣為流傳。仍以《乘風破浪的姐姐》為例,在第二輪公演中張含韻、金晨、孟佳三人組“不幸”被分到了來自臺灣樂隊Tizzy Bac的歌曲《這是因為我們能感到疼痛》:一方面這首歌本身在節奏上不占優勢;另一方面其現代舞的舞種要求在選秀競演的舞臺上也難有較好的觀眾緣。
意外的是,節目播出之后,這首歌的演出迅速成為該輪比賽最受好評的作品之一。從專業角度來看,幾位表演者并非現代舞職業舞者,所謂現代舞的舞種要求也只是展現了現代舞的形式和概念。同時,作為競演選秀比賽中的唱演舞臺,舞蹈實際上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表演,從這個角度來說,這一舞臺作品似乎并不適合作為真正的舞蹈將其納入討論范圍。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恰恰是這種唱演結合的表演形式、表演不夠“專業”但作品卻出圈的強烈對比,向我們展示了綜藝舞蹈是如何被觀眾感知的。
開場三人躺在地上的俯拍鏡頭已經表明,這樣的動作編排是為鏡頭/節目觀眾設計的,是典型的“屏幕編舞”(screen choreography),而節目觀眾也清晰地理解了這一設計的目的。在一篇極具代表性的觀后感中我們看到,在觀眾眼中,一方面舞蹈被拆解了,動作、音樂與表演者互相增值;另一方面,舞蹈被重組為新的文本,正是這個新的文本讓觀眾感受到了“疼痛”,這種對舞蹈文本性的細致解讀也映證了舞蹈—影像的生成路徑①《 乘風破浪的姐姐》(第一季)以初舞臺的全開麥表演出圈,但在后期節目中又再次回到錄唱對口型。不少批評意見認為后期“假唱”的表演方式是一種欺騙,同時也導致節目水準下降。但實際上就綜藝舞蹈的訴求來說,這些問題其實并不重要。參見:我所感到的《疼痛》[EB/OL](.2020—10—09)[2022—05—07]. https://www.douban.com/note/780197792/?dt_dapp=1&_i=5490237HDz9NYJ.。也就是說,如果勁歌熱舞強調的是律動強度,那么綜藝舞蹈追求的則是情感強度,兩者之間的區別并不是節奏,而是喚起觀眾內在經驗的方式在這里發生了變化。
當觀眾在彈幕和評論中反復強調感受到“疼痛”時,這種體驗或許與德勒茲所說的藝術的呈現是“生成—不可感知物”恰恰相反,綜藝節目之所以呈現出“情感客體化”的共性正是為了“生成—可感知物”。“潛在”真實和“生成—可感知物”既是綜藝舞蹈的重要面向,也是觀看綜藝舞蹈時不得不面對的真正難題。在這里,首先值得探討的與其說是分析“可感知物”具體為何,不如更準確地說,是要理解“可感知物”是作為什么被觀眾接受的。即如果存在一種新的舞蹈感知,那么是否意味著也存在一種新的舞蹈“靈韻”?
技術復制取消了藝術的“靈韻”(auro),同時也改變了大眾和藝術之間的關系,這是本雅明在20世紀30年代寫作《可技術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Das Kunstwerk im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it)時的看法,彼時技術復制或者說藝術的媒介化才剛剛起步,其為影像藝術辯護也是以傳統藝術及其傳播形式為比較對象。對于今天的大眾來說,藝術與媒介的關系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尤其是近幾年來,“線上”(online)不僅成為工作空間受限時的替代選擇,更全面接入了藝術欣賞和知識教育體系。這讓人不得不思考,如果經由界面/影像感知藝術正在成為一種“自然”視角,即從一開始就將機器之眼等同于自己的觀看,那么“觀看即屏幕”將帶來什么樣的感知結構變化?如果傳統觀看方式對應的是舞蹈自身的“靈韻”,那么朝向“可感知物”的綜藝舞蹈又是否正在創造一種技術“靈韻”?
靈韻無法復制,因其與“當時”關聯,這種“此時此地性”(das Hier and Jetzt)構成了藝術品的原真性,這是靈韻之辯的關鍵。但綜藝舞蹈的“此時此地性”并不為物理空間打造,觀看者的內在經驗被放到了首要位置,“潛在”意味著只有在與觀眾經驗關聯的那一刻,綜藝舞蹈的作品概念才能回溯性地生成,這是傳統舞蹈未曾設想過的處境,也是綜藝舞蹈的真正不同之處。本雅明觀察到的補足電影靈韻的方式是以資本塑造明星人設(personality),即由外部浸入內部,現實滋養影像。綜藝舞蹈所提示的卻是另一種路徑,“生成—可感知物”的過程才是生成明星的過程,綜藝舞蹈的技術“靈韻”不僅不需要補足,反過來還會外溢。以《舞蹈風暴》合作賽中的作品《惑· 心》為例,不少觀眾在彈幕和評論中表示,舞者“比演員演得還好”,因為喜歡這個舞蹈作品,于是又去看了電影《畫皮》。
正是這種潛在性讓我們得以重新審視“靈韻”的生成:“本雅明從獨特性和永久性的角度界定‘原作’,從短暫性和可復制性的角度界定‘復制品’。就舞蹈而言,現場表演可能是獨特的,但卻不持久,而視頻舞蹈則相反。雖然電視以短暫性著稱,但就其大量輸出的轉瞬即逝的圖像而言,視頻舞蹈的表演卻被永久地記錄在了‘母帶’上,又由于錄像機是常見的家用設備,因此電視觀眾可以便捷錄制,可以一次又一次地觀看。”①DODDS S. Dance on Screen: Genres and Media from Hollywood to Experimental Art[M].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Palgrave, 2001:154.在這里,舞蹈—影像不再只是物質身體的冗余,而是重申了影像副本的“原作性”,因為“即使是復制品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具有膜拜的價值”②DODDS S. Dance on Screen: Genres and Media from Hollywood to Experimental Art[M].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Palgrave, 2001:156.,綜藝舞蹈追求的正是這種轉瞬即逝的永恒,這種必須依托技術與媒介才能被看見的“靈韻”。
贊美舞者“比演員演得還好”,以“再來億遍”的狀態反復觀看,或可看作綜藝觀眾的留戀與膜拜。若本雅明尚在,多半會對此感到震驚。盡管他為電影辯護,但他也認為,“電影觀眾與演員沒有了直面交流,于是,面對電影就采取了一種不受如此接觸影響的鑒賞者的態度。電影觀眾對演員的視覺感知只是通過置身于攝影機角度才發生。因此,他又采取了攝影機的態度:對演員進行著檢測。這不是一種能產生膜拜價值的態度”③本雅明.藝術社會學三論.[M].王涌,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66.。換句話說,與其說觀眾是在和演員共情,不如說是在和鏡頭共情。那么,綜藝舞蹈作為一種已經被“電影化”了的舞蹈,能豁免于此嗎?
但這樣的問題可能仍舊是在傳統藝術“靈韻”的框架下展開的思考,其對綜藝舞蹈的審視也仍然傾向于將舞蹈從影像中提取出來,而本文寫作的真正目的,正是要通過綜藝舞蹈的舞蹈—影像來探討影像生成舞蹈的可能性。綜藝舞蹈與劇場舞蹈最大的不同,不在于舞者自身,而在于其與觀眾相遇的瞬間是如何與個人經驗連接的。界面與影像對舞蹈生命強度的放大,強力塑造了觀眾的舞蹈感知,綜藝舞蹈也因此大受歡迎。但與此同時也要看到,這種強力塑造也提示了綜藝舞蹈的另一面,那就是“可感知物”的內向性與封閉性,這也是綜藝舞蹈的最大爭議所在。更何況,即使技術“靈韻”之說能夠成立,也并非沒有代價,如果我們欣賞舞蹈的方式正在被徹底界面化,那么生成—舞蹈又真的可能嗎?當然,這又是另一個話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