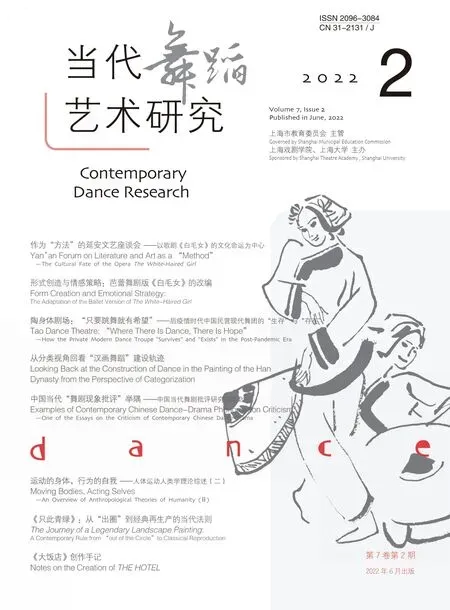拉班—芭特妮芙動作分析視角下京西太平鼓動作形態特征的主題二元性
莎日娜
拉班—芭特妮芙動作分析是由魯道夫· 拉班(Rudolf Laban)創立,英格尼特· 芭特妮芙(Irmgard Batenieff)、沃倫· 蘭博(Warrn Lamb)等人繼承和發展的,用于觀察、識別和描述如何組織人體動作的理論體系,被廣泛應用于舞蹈訓練、編創教育、人類學研究、身心療愈、體育訓練和人工智能等領域。通過提供動作描述的方法和研究框架,拉班—芭特妮芙動作分析為破譯復雜多變的人類動作提供了一個強大的工具。這一體系將人體動作區分為身體、力效、空間和形體形式,簡稱BESS①GROFF E. Laban Movement Analysis:Charting the Ineffable Domain of Human Movement[J].Journal of Physical Education,Recreation & Dance,1995,66(2):27—30.,這四個元素在動作過程中交融共生卻又重點顯現。基于這一微觀觀察分析的基礎,在更為宏觀的層面上,該理論將人體動作視為一種內在意圖的外在表達,是身體和心理交互的整體過程②周宇,凱倫· 布拉德利,廖彬彬.拉班—芭特妮芙動作研究體系綜述[J].北京舞蹈學院學報,2017(3):21—28.。這種整體性往往存在于動作中對立兩極的平衡和整合的關系中,即主題二元性(Themes Duality)。拉班最初識別了蘊含于動作中的“內在與外在(Inner and Outer)”“功能與表達(Function and Expression)”“部分與整體(Part and Whole)”和“穩定與移動(Stability and Mobility)”四類主題二元性,每個主題都包含兩個相互對立的動作概念,這兩類相反的極性在動作中交替反復,共同指向了動作的目的和作用。③Themes are main subjects and ideas that recur regulaty in a body of work as you study movement through the LBMA lens;themes emerge through repeated ideas and motif. each organizing Theme composes two ideas about movement that at first appear to be opposites of each other. 參見:WAHL C. Laban/Bartenieff Movement Studies:Contemporary Applications[M].Champaign,IL:Human Kinetics,2019:21—26.隨著拉班—芭特妮芙動作分析理論在當代被廣泛運用于跨文化動作研究,動作的主題二元性內涵不斷被拓展。從主題二元性出發,以平衡和整合的視角對動作開展分析研究,可以更為全面深刻地理解動作。
京西太平鼓歷史傳承悠久、群體參與廣泛,至今仍活躍于北京地區的節日慶典及廣場舞活動中,是非遺舞蹈活態傳承的典型。運用拉班—芭特妮芙動作分析這一科學理論的主題二元性整體觀和BEES工具,可以發現京西太平鼓因代際傳承過程中的變異、反映群體心理意圖和價值取向等的特殊表達方式,呈現出同一動作主題在“身體形態”“空間張力”和“力效”三個層面二元并存的特殊舞蹈形態。
一、 限制與釋放并存的身體形態
京西太平鼓身體形態層面上的主題二元性主要體現在限制與釋放的對立統一,在拉班—芭特妮芙理論指導下需要從識別動作的“身體啟動部位”“身體參與部位”“軀干的使用”“重力攜帶”“腳對地面的關系”“身體連接”④身體連接是表演者如何處理、支持和整合身體動作,這一理論由芭特妮芙及其學生佩吉· 哈克尼(Peggy Hackney)發展。這六個模式包含:呼吸連接(Breath)、核心末端連接(Core-Distal)、頭尾連接(Head-Tail)、上下半身連接(Upper-lower)、左右半身連接(Body-Half)、對側交叉連接(Cross-Lateral)。參見:美國加州大學歐文分校2016年春期學期拉班動作分析(Laban Movement Analysis)課程筆記,洛麗塔· 利文斯頓(Loretta Livingston)授課。等,這些被認為是反映特定舞蹈種類的典型性、具有特定的傾向性的身體形態特征的層面來開展分析。
舞蹈表演者下半身步伐以一種非穩定性支撐全身動作、個人空間移動范圍較小、使用道具太平鼓引領全身動作,呈現出限制性的動作連接形態,這與女性表演者裹腳有關。京西太平鼓于肇始之時是由裹腳女性為表演主體的舞蹈⑤高洪偉,張冠玉.北京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口述史:京西太平鼓[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8:iii.,表演者雙腳重心在前半腳掌,“顫”“拐”“挪”的動律明顯。腿部和腳部與地面關系的形態明顯是受到舊時裹腳女性舞蹈“非穩定性”的功能特征影響,在代際傳承中仍有所遺存,并成為特有的身體表現被存續。表演者軀干以向前微傾為主,頭部參與較少。向后甩頭、向前低頭、抬頭看等動作往往會在擊鼓后,或向后揮臂,或跳躍這樣動作的銜接之處瞬間發生,繼而停止,形成一種稍縱即逝的狀態,從而形成京西太平鼓特殊的舞蹈韻味。例如“大搧鼓”和“小搧鼓”套路動作對比可以發現,一旦在跳躍的過程中加入頭部的后仰,配合張開的手臂、繼而含胸低頭,會使“大搧鼓”動作幅度陡然增大,舞蹈的造型感也隨之增強。表演者在同一單位時間內,完成雙手擊鼓、揮臂、軀干前傾后仰、跳躍、踏步等動作,同時還要協調對方表演者的節奏,并通過步伐的流動完成隊形變化,這種高度的同步身體部位的動作序列模式,使得表演者的空間移動也受到了限制性的影響。
釋放的身體形態特征表現在動作“向外放射和向內聚合”的有規律的重復狀態。根據拉班—芭特妮芙動作分析方法,京西太平鼓表演者采用以身體部位對側交叉、結合核心末端連接的模式—即身體上下部位沿著對角線、交叉象限劃分,從身體一側的上象限通過軀干中心和身體另一側的下象限整合,即右上半身—左下半身或左下半身—右上半身,同時以擊鼓動作為始發,使得全身的力量由核心隨之傳導至四肢,從而支持完成在個人空間中的復雜動作組合。以“小搧鼓”動作為例:表演者以鼓點引領步伐、軀干前傾并滯后腳步動作,左腳向左后方撤步、雙手從左髖關節處啟動繼而向右前方擊鼓同時雙腿邁步。軀干和手臂向前高方向,繼而雙臂收縮、軀干前傾,回到聚合狀態,由此完成一套動作。太平鼓作為控制舞蹈的主導因素,在運動過程中表演者不得不放棄就近原則,在動作結束后不惜運用雙手臂完成最遠的交叉路線,回到起始點擊鼓開始下一個動作,從而使得京西太平鼓表演呈現出“艮勁十足”的限制與“大開大合”的釋放并行不悖的矛盾美感。
京西太平鼓限制與釋放的身體形態特征,直接促成了表演者的身體在三維空間中復雜的反向運動、梯度螺旋旋轉和貫穿機體的深度對角線連接支撐,從而使其身體形態也具備拉班—芭特妮芙動作分析體系空間及空間張力(Space Tensions)的典型特征。
二、 讓渡與守護共生的空間及張力
已有文獻資料將京西太平鼓舞最為典型的表演風格總結為“人舞鼓、鼓纏人”①高洪偉,張冠玉.北京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口述史:京西太平鼓[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8:iii.,這一表述立足傳統舞蹈研究視角,區分和整合了表演者主體與表演道具太平鼓的關系,而拉班—芭特妮芙動作分析理論作為方法,卻可以得到“表演者個人空間中的空間張力構成,以及個人空間與一般空間的交疊共生”的另一維度的二元性考察。
首先,“人舞鼓”呈現出表演者使用道具劃定出個體空間和一般空間的邊界。表演者手持鼓,在上半身個人球體空間(kinesphere)②個人球體空間(kinesphere)是圍繞著每個人的個人空間,是不需要邁步就可以接觸到的空間,它可以向任何方向延伸。當移動時,個人球體空間圍繞著動作者并跟隨移動,個人球體空間是拉班“空間和諧”理論的概念之一,個人球體空間之外是一般空間。參見:NEWLOVE J,DALBY J. Laban for All[M].London:Routledge,2004:17.的遠端邊緣作出各個定向方位上的連貫動作,以鼓呈現動作軌跡,塑造空間。例如“圓鼓”套路:表演者手持鼓和藤條,從身體右上部空間開始—經過后方繞到左旁—再回到身體中線附近。鼓的運動為表演者劃定了一個邊界清晰的封閉空間,使其他的表演者沒有機會進入這樣的一個被營造出的空間中。根據表演者性別、身體構造及個體表現風格的差異,舞鼓動作塑造的個人空間范圍也不盡相同。在“拉抽屜”“追鼓”等套路中,表演者在用鼓完成個體空間塑造的同時,通過隊形的移動變化完成一般空間的塑造。然而頗有意味的是,在這樣一來一去的追趕和搶占的過程中,在雙方距離較近的情況下,表演者保持著個人空間的封閉性,同時通過“閃”“躲”“跳”等動作讓渡出一部分空間給對方。
從觀者的角度來看,這樣的動作形態呈現出雙方表演者既親密又保持個人空間的邊界不被打破的狀態,沒有出現個體空間的重疊,而是在這樣一種讓渡與守護并存的空間移動中完成表演。一般空間組織了個人空間,包括身體如何在空間中移動,以及他們如何與周圍的環境進行互動。交疊或遠離是一般空間中群體文化的顯現,最能夠體現群體舞蹈的社會性互動,揭示舞蹈文化實質。③參見:BARTENIEFF I,LEWIS D. Body Movement[M/OL].Routledge,2013:129[2022—03—29].https://www.taylorfrancis.com/books/9781136758379.京西太平鼓發生于北京西部門頭溝地區,該地區是傳統的北方古文化村落聚集區,具有濃郁的北方人文傳統和建筑風貌,是以中街為軸,左右對稱的院落群格局,主要空間形態以線性空間為主的居住街區。這樣的村落生活和院落格局形態,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太平鼓表演的套路,例如“四方斗”套路的對稱交叉、用4人或者8人隊形的調度表現日常生活中抽屜拉開、關上的行為—“拉抽屜”;用對稱的環形路線,表現出走街串巷拉家常的“串胡同”套路;用頭部向前頓點的動作,模仿農家常見的“斗公雞”套路等,通過輻狀的定向性動作,完成個體空間在一般空間中的存在形式。這些當地民眾文化生活的形態,抽象形塑出京西太平鼓的獨特表演套路和空間呈現,經過200余年的傳承,在今天仍然保有鮮活的生活氣息。
其次,“鼓纏人”表現為道具的使用外化了表演者個人空間充盈著的復雜空間張力(Spatial Tensions)。拉班—芭特妮芙動作分析理論中,空間張力被定義為“人體如何投入空間、如何釋放緊張感,由此穩定和調動人體在空間中的質量”①Spatial tensions are the investments of the body. Movement is a continuous gradual shifting of spatial tensions. You invest in and release spatial tensions to experience the stabilizing and mobilizing quality of space that“guarantees upright stability as well as continuous readiness to move into space.參見:WAHL C. Laban/Bartenieff Movement Studies:Contemporary Applications[M].Champaign,IL:Human Kinetics,2019:129—131.,分為上下的垂直張力、左右兩側的水平張力和前后形成的矢狀張力等。空間張力不是孤立存在,需要有一組對應的反張力(Countertensions)與之共存,維系平衡。與特定身體表現模式匹配的空間張力,作用于動作力量的聚集或釋放、恢復或過渡,從而凸顯了動作的流動性。京西太平鼓動作形態中鼓的運動軌跡,標記了京西太平鼓表演者個人球體空間中的各個方向,從而為觀察這些空間張力變化提供有效支持。上文論述的身體姿勢姿態、身體連接模式的使用,可以較為清晰地觀察到京西太平鼓表演中空間張力呈現出多樣交錯的矩陣狀態,而這就是呈現“鼓纏人”特征的原因。
第一,“鼓纏人”表現在表演者身體垂直維度上的向上張力與向下反張力的對抗中。北京西部,尤其是門頭溝地區地處京西古道,是華北平原向蒙古高原延伸的腹地,這里永定河水系發達、商賈云集、文化多元開放。這里世代生活的鄉民經濟富足、生活舒適,性格豪爽、積極樂觀,有較多的閑暇時光開展休閑娛樂活動。這樣的群體心理映射在京西太平鼓舞蹈形態中呈現上升的形體品質(Rise Shape Quality)。“大搧鼓”“小搧鼓”“圓鼓”等套路中,鼓、手臂、軀干等大部分身體部位盡力擺脫地心引力,向上動作,但相反的“屈膝而行的步伐”卻著意降低重心、順從地心引力,形成向下的反張力。而偶爾爆發力量的跳躍,在瞬間投入全身的參與,則更加強化了垂直向上的空間張力占有主導地位的觀察者視角感受。第二,“鼓纏人”也表現在“從身體中心線向外輻射和向內聚集”的空間張力對抗中。京西太平鼓每一個套路的起始動作是擊鼓,藤條和鼓點接觸的瞬間將身體能量聚集于軀干中心,伴隨著藤條和鼓分離的手臂動作,表演者將聚合的能量從中心向個人球體空間中的垂直維度、水平維度以及矢狀維度發散,到達的每一個方向都會與身體核心形成緊張感,從而塑造向外輻射的空間拉力。在經過數個動作的力量釋放之后,隨著擊鼓的需要,再一次向內聚合收縮至軀干中心形成收縮的空間張力,形成了“鼓不離人”的視覺感受。輻射和聚集的能量程度依據表演者的身體結構和肌肉力量呈現出差異化。女性和兒童的太平鼓表演兩者均衡,而男性表演者則較多的呈現向外輻射。第三,“鼓纏人”還表現在一般空間中表演者的交錯互動中。京西太平鼓表演人數限定為雙數,主要目的是為了完成“對舞”的形式。兩人或者四人對舞的形式需要的是表演者的互動,決定了一般空間中矢狀維度上的向前、向后的空間張力特征,太平鼓這種舞蹈形式與強調在村落文化中承擔著人際關系互動的民俗意義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
同身體表現層面的限制與釋放相對應,京西太平鼓動作形態在空間及空間張力的作用下,體現著“守護與讓渡“的另一個二元性:表演者以道具鼓恪守自己邊界,同時試探對方的邊界,彼此的個人空間不共享、不交疊,但卻在一般空間中一來一往交錯進退。拉班—芭特妮芙動作分析體系認為身體表達、空間配置這些外在可見的表現,都源自動作發生的內在動機,從而為繼續深入考察京西太平鼓身體表達的內在意圖提供了力效層面的理論支撐。
三、 個性與共性交織的力效
動作最初發生的內在沖動被拉班稱為“力效”。②Laban identified space,weight,time and flow as motion factors toward which performers of movement can have different attitudes depending on temperament,situation,environment and many other variables. The attitudes toward the motion factors he called in German antrieb,a combination of an (on) and trieb (drive),representing the organism’s urge to make itself known. In English translation,antrieb has become Effort. 力效代表個體想要“讓別人知道自己的沖動”。在德語中,動作發生的沖動被稱為antrieb,是an (on)和trieb (drive)的組合,英文譯為“Effort”,郭明達譯為“力效”。參見:BARTENIEFF I,LEWIS D. Body Movement[M/OL].Routledge,2013:51[2022—12—29].https://www.taylorfrancis.com/books/9781136758379.每個人的動作都和力效緊密相關,力效是動作的起源和內在方面。拉班對力效給予極高的評價:人類的力效可能性豐富多變,這種變化正是人類戲劇性行為的主要來源。③LABAN R von,ULLMANN L. The Mastery of Movement[M].Alton:Dance Books,2011:9—12.拉班—芭特妮芙動作分析體系將力效劃分為四個可以被觀察的要素,分別是時間(Time)、空間(Space)、重量(Weight)和流暢度(Flow)①因為動作與心理活動的緊密聯系,拉班認為力效四要素與榮格(Carl Gustav Jung)的意識四功能有關。時間要素與人的決策力相關聯,反映著讓事物以非預期的、快速的(Sudden)方式發生,還是以逐步的、持續的(Sustained)方式發生。空間要素與人的注意力相關聯,反映著人對事物的反映方式是直接的(Direct)還是間接的(Indirect)。重力要素與人的意圖相關聯,決定去做某件事是持有堅定有力的(Strong)態度還是怠慢無力的(Lignt)態度。流暢度要素與人的表現力相關聯,反映著人適應事物發展的過程,它可以控制(Control)這個過程,或者可以放任自流(Free)。由于流暢度要素貫穿于其他三要素之中承載能量的流動和分配,在開展動作分析時往往強調前三個要素的主體地位。參見:BARTENIEFF I,LEWIS D. Body Movement[M/OL].Routledge,2013:51—53[2022—03—29].https://www.taylorfrancis.com/books/9781136758379.。力效是人類神經能量的釋放,它無法脫離內心活動的參與,是人的智力、情感和精神狀態的可見表現,是追求被認為有價值目標或精神狀態的結果,這種追求過程的意向和通過行動實現意向之間的連接,存在于外在的身體表現、空間配置和內在的隱蔽沖動矛盾中。聚焦于京西太平鼓的力效考察,就是希望能夠厘清這種連接內心的沖動與外在動作展現的關系。
拉班對于力效秉持著群體力效的共性和個體力效的差異并存的觀點。一方面,認為力效比思想更容易傳播,并且一群人的力效,在集體的場域創造了氣氛。②參見:THORNTON S. A Movement Perspective of Rudolf Laban[M].London:Macdonald and Evnas,1971:47.力效是反映尋求內在情感態度的外在表現,是可以觀察到的最重要的動作發展模式,直接反映著人的心理態度、性格以及他所追求的價值觀。上述力效要素根據舞蹈目的和價值指引的需要,在表演者的記憶和動作習慣中被有意的挑選加工、分離或整合形成固定的力效組合,進而配合有規律的重復動作序列形成特定的舞蹈種類。當舞蹈動作力效在族群心理特質和動作模式的長期積淀中完成固化,群體的動覺共情就隨之產生,在群體儀式表演及其代際傳承中加強族群的團結。根據身體和空間的使用方式考察,京西太平鼓表演者群體的力效呈現出有規律的重復序列:每一個套路的開始以擊鼓作為標志,需要軀干和四肢在瞬間完成快速定向聚合,呈現為“快速/重/直接”的力效。擊鼓動作完成后能量向外擴散,表演者抖動鼓柄上的金屬環使之相互碰撞發聲并根據不同的套路完成四肢軀干的動作,呈現“持續/輕/間接”的力效。套路動作結束時身體再一次回到聚合狀態,擊鼓重復。表演者使用擊鼓聲、抖環聲強化了力效的效果,表演通過鼓點的間隔調整動作進程。由此,可以分析出京西太平鼓表演在套路動作力效表達方面,呈現出“快速/重/直接—持續/輕/間接—快速/重/直接”的重復序列特征(見圖1),配合不同套路的身體參與部位等形成不同的套路動作風格。

圖1 京西太平鼓套路動作力效重復序列③ 圖片來源:莎日娜繪制。
另一方面,拉班承認每個個體都有擴大個人力效能力發展范圍的傾向的個性化特征,鼓勵個人可以發展他的自然能力,并且通過力效的實踐經驗實現。拉班一直在尋找被認為是“典型風格”(Typical Style)之外的東西。他對動作的偏差和變化很感興趣,他關注一個社區、一個社會階層或一個歷史時代的典型舞蹈特征進行區分,以便最準確地感知風格和個人自發的特征。④LABAN R,ULLMANN L. The Mastery of Movement[M].Alton:Dance Books,2011:106.非遺舞蹈不同于劇場表演,表演者極富個性化,這也決定著非遺舞蹈力效的豐富多樣。錄制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京西太平鼓視頻資料⑤巫允明.中國原生態舞蹈文化(視頻集錦)[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10.顯示:裹腳老年女性的“大小搧鼓”“斗公雞”套路動作范圍基本上局限于近身距離、身體擰轉傾斜幅度不明顯、步伐距離較近等形態,呈現出“持續/輕/間接”的力效組合(見圖2)。而當代京西太平鼓的傳承人高洪偉(男)的舞蹈動作騰踏跳躍、干脆利落、張力十足,呈現出“快速/輕/直接”的力效特征(見圖3)。對比舊時裹腳女性和今時傳承人的太平鼓表演,可以發現明顯的變化—空間和時間兩個力效要素走向兩極的對立分化。究其原因,表演者性別發生變化,使得太平鼓力效呈現出不同的狀態。據高洪偉介紹,其父親高啟殿是三家店地區有記載以來表演太平鼓的第一位男性,也是從他開始,賦予了太平鼓不同于舊時女性打鼓的力效特征。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即表演者性別的差異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非遺舞蹈的形態變化。然而即便是同性別表演者,因為自身身體構造和生活經驗的不同,也會造就不同的力效模式—京西太平鼓的另一位男性表演者李根國的表演則呈現出“快速/直接/重”的力效特點(見圖4),與高洪偉在力效的重量要素中出現對立。據了解李根國常年練習武術,中國傳統武術低重心的動作模式對他的影響也表現在太平鼓表演中。

圖2 女性表演者動作力效① 圖片來源:莎日娜繪制。

圖3 高洪偉動作力效② 圖片來源:莎日娜繪制。

圖4 李根國動作力效③ 圖片來源:莎日娜繪制。
拉班—芭特妮芙動作分析理論通過“身體、力效、空間和形體形式”四個具有相對獨立卻又不可分割的視角,以主題二元性的整體動作觀念,對特定的舞蹈形態開展全面觀察,為探究中國非遺舞蹈的動作形態研究提供了一種從舞蹈本體出發的視角和方法。舞蹈形態如何被文化賦予意義、被環境塑造、被傳承變異等問題或許可以通過理性邏輯指導下的分析方法描述、觀察和辨識,從而對舞蹈的結構、風格及其隱含的深層文化主題進行更深層面的闡釋。以京西太平鼓為代表的中國非遺舞蹈,是蘊含深刻文化意味的集體生活模式在群體中的傳承。從動作本體出發研究其塑形原因,總結中國非遺舞蹈的研究經驗,建立在西方哲學邏輯基礎上的拉班—芭特妮芙動作分析理論體系,不失為一種研究視角的補充和完善,對于該理論的實踐和發展也具有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