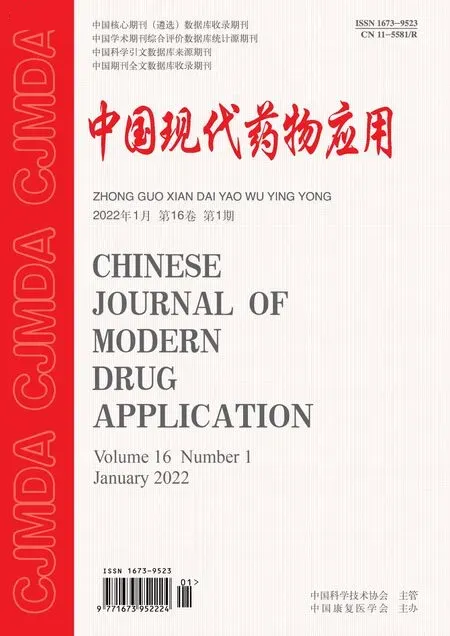內鏡下黏膜切除術治療胃腸道息肉的效果及安全性分析
張彬
胃腸道息肉屬消化內科常見病癥的一種,是因胃腸道局部黏膜有增生發生,乳頭狀樣的病變組織形成,患病初期癥狀表現并不明顯,伴隨著病情的逐步發展,消化道極易有腹痛、出血等表現,影響患者機體健康、生活質量,又因該癥存在癌變風險,需及時進行手術治療[1]。既往臨床常以內鏡下電切術對該癥實施治療,其治療隆起型、帶蒂型息肉效果較為顯著,但其難以控制切除扁平型的深度,容易導致切除不徹底,同時也容易引發各類并發癥,療效理想度較低。近幾年,EMR在胃腸道息肉治療中的應用逐步廣泛,該術式集中了黏膜下注射、電凝切除,療效顯著。為明確EMR 治療的實際價值,本文選取本院134 例胃腸道息肉患者展開對比研究,分析EMR 的治療效果,具體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9 年4 月~2020 年4 月在本院急診的胃腸道息肉患者134 例,隨機分為對照組和觀察組,每組67 例。對照組男35 例,女32 例;年齡23~64 歲,平均年齡(46.30±7.77)歲;類型:24 例帶蒂型,26 例隆起型,17 例扁平型;是否多發:35 例單發,32 例多發;息肉位置:37 例結腸,30 例胃部。觀察組男36 例,女31 例;年齡24~65 歲,平均年齡(46.34±7.45)歲;類型:26 例帶蒂型,27 例隆起型,14 例扁平型;是否多發:38 例單發,29 例多發;息肉位置:40 例結腸,27 例胃部。兩組患者的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納入標準 患者均符合胃腸道息肉相關診斷標準并經檢查后確診;對本次治療手段可耐受;無精神疾病;患者均認真閱讀了本次研究相關資料,同意加入。
1.3 排除標準 心、肝、腎功能存在嚴重損傷者;存在既往治療史者;存在凝血功能異常或有出血傾向者;難以遵醫囑積極治療者。
1.4 方法 對照組給予內鏡下電刀切除術治療,借助內鏡探查息肉具體位置,在與息肉相距2 mm 處以電刀直接將息肉切除,最大程度向黏膜下層切,盡量對肌層結構實施保護,完成切除后,開始常規止血。
觀察組給予EMR 治療,借助內鏡查看息肉具體位置,混合靛胭脂、腎上腺素、生理鹽水后,在息肉基底部注射,后深入套圈器,套住病灶,切除范圍為黏膜、下方組織,達固有肌層后止,需對固有肌層實施保護,將套圈器收緊,開始切除,息肉若直徑>2 cm 或為扁平型,可借助套圈器分開多次切除,完成切除后,借助內鏡觀察創面,確定全部切除,創面良好后,以凝血酶對創面實施沖洗,將切除組織送檢。術后2 d 需臥床,食物選擇半流質,同時給予奧美拉唑。
1.5 觀察指標及判定標準 ①對比兩組成功切除率、復發率。術后隨訪1 年,記錄兩組復發情況。以內鏡檢查術后3 個月時病灶位置覆蓋新生肉芽組織、黏膜上皮或形成瘢痕,即為切除成功[2]。②對比兩組炎癥因子水平,包括IL-1β、IL-8、IL-6,取手術前后患者空腹3 ml 靜脈血,以酶聯免疫吸附法對上述指標實施測定。③記錄并對比兩組并發癥發生情況,包括腹痛、腹脹、便血等。
1.6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23.0統計學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檢驗。P<0.05表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成功切除率、復發率 觀察組患者的成功切除率100.0%高于對照組的85.1%,復發率4.5%低于對照組的19.4%,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兩組患者成功切除率及復發率比較 [n(%)]
2.2 炎癥因子水平 觀察組患者的IL-1β、IL-8、IL-6 水平均低于對照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患者炎癥因子水平比較()

表2 兩組患者炎癥因子水平比較()
2.3 并發癥發生情況 觀察組患者的并發癥發生率低于對照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兩組患者并發癥發生情況比較 [n(%)]
3 討論
胃腸道息肉早期癥狀較為隱匿,伴隨著病情的逐步進展,患者會出現腹痛、腹瀉、便血、便秘等癥狀,此時病癥多為中晚期,給后續臨床治療增加了不確定性和難度,對患者預后十分不利。胃腸道息肉常用內鏡常規檢查檢出,近幾年伴隨著內鏡技術的持續發展,顯著提升了內鏡利用率,大幅提升了胃腸道息肉的檢出幾率。可見,內鏡技術的積極探索對臨床疾病的前瞻性檢查意義十分重大。
胃腸道息肉患者可發生糜爛癥、繼發出血,部分甚至有惡變風險,特別是廣基息肉、扁平息肉,惡變的風險尤其高,所以,臨床建議盡早將病變組織切除,提升治療效果,改善預后結局,對患者轉歸十分有利。既往臨床常以內鏡微創手術對該癥實施治療,其優勢在于學習曲線較短、簡便易行。但臨床實踐顯示,該術式缺少觸覺輔助,因而難以精準掌握切除病灶的深度,將其用于治療隆起型、帶蒂型息肉時,在深度上,病灶組織界限較為明顯,因而,相對容易掌握切除的深度;而將其用于扁平型息肉的治療時,因內鏡下難以區分組織深度的界限,切除深度掌握上較難,切除若過淺,可能難以將病灶組織徹底切除,遠期復發的風險增加,而若切除過深,則會引發消化道穿孔,限制了其臨床應用[3]。
所以,探尋對癥治療新型手段,對上述缺陷加以彌補,可使消化道息肉治愈幾率顯著提升,手術療效得以改善,患者生活質量可提升,其現實意義十分關鍵。近幾年,臨床研究者持續優化治療消化道息肉的機制,諸多治療新式方法獲臨床驗證,其中EMR 在該癥治療上效果較為突出。
EMR 屬內鏡下治療的一種新型手段,其經在息肉基底部注射靛胭脂、靛胭脂混合液,促使息肉隆起,有利于分離息肉組織對應的消化道黏膜層、肌層,術中借助套取器,可徹底切除病灶組織,其優勢在于效果確切、易操作、安全性較高等。相較于電刀傳統的切除術,EMR 可清晰觀察胃腸道息肉病灶的界限,特別是扁平型息肉,切除病變的效果得到保障,對病變黏膜組織徹底清除十分有利,同時不會對黏膜肌層造成損傷,術后患者恢復加快。在內鏡下完成手術會損傷消化道的黏膜,黏膜組織內部的炎癥反應激活,炎性因子得到表達、分泌,并入至血液循環,因此,經對術后IL-1β、IL-8、IL-6 水平實施測定,可反映炎癥反應實際程度。
本研究結果顯示,觀察組患者的成功切除率高于對照組,復發率低于對照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觀察組患者的IL-1β、IL-8、IL-6 均低于對照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提示了與電刀切除術相比,EMR 治療取得了更為顯著的療效,可使炎癥反應減輕。根據王紅霞[4]研究結果顯示,其文中選取胃腸道息肉患者84 例展開對比研究,對照組、觀察組分別采用電刀切除術、EMR 治療,結果顯示,觀察組成功切除率(100.0%)高于對照組(85.71%),復發率(4.76%)低于對照組(19.05%),與本文數據基本一致,證實了本文的可靠性。
本文結果還顯示,觀察組患者的并發癥發生率為7.5%,低于對照組的23.9%,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提示與電刀切除術相比,EMR 的安全性較高。根據袁琰[5]研究中選取1 年間胃腸道息肉患者76 例展開對比研究,以雙模擬為依據分為常規組和研究組,每組38 例,常規組、研究組分別給予電切除術、EMR治療,結果顯示:研究組并發癥發生率(5.26%)低于對照組(23.68%)(P<0.05),與本文研究數據基本一致。而在王紅霞[4]研究中也曾指出,觀察組并發癥發生率7.14%低于對照組的23.81%(P<0.05),與本文數據基本相符,再次證實了本文的真實性,也驗證了本次研究的主題,證實了胃腸道息肉治療時選擇EMR 的療效確切,且存在較高的安全性。
綜上所述,以EMR 對胃腸道息肉展開治療,獲得了顯著的療效,不僅創傷小,且存在較高的安全性,能夠有效提升成功切除率,降低復發風險,減輕炎癥反應,應用價值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