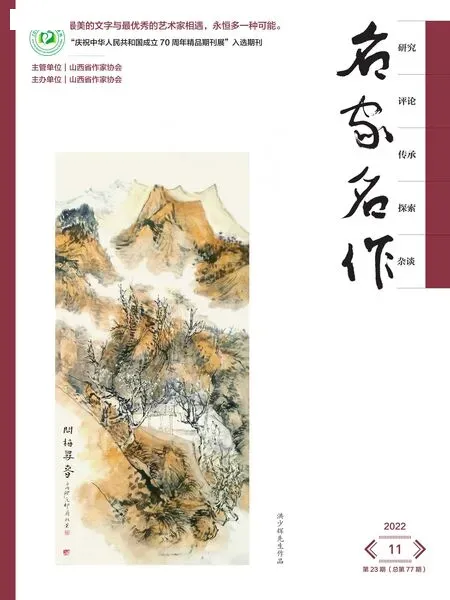巴赫賦格曲中的巴洛克美學
徐浩亮
一、巴洛克音樂風格的起源
巴洛克一詞起源于葡萄牙語(Barroco),意思是奇形怪狀或者說不規則的珍珠,現在指歐洲17世紀和18世紀初的豪華建筑風格,音樂家們也借此來概括表示同一時期的音樂作品風格。巴洛克風格最初是由天主教會在反宗教改革期間頒布的,作為恢復天主教重要性的一種方式,它的形成也和宗教有著密切的聯系。在這期間藝術成為宗教有力的宣傳工具,可以用它來表達教會的自信。
二、巴洛克音樂與美學
巴洛克時期的音樂作品在風格上是非常復雜的,比較常見的特點是在氣勢上非常雄弘有力量,但又時而氣氛緊張時而生機勃勃,這種莊嚴高貴的特點,也是來自之前文藝復興時期非常標志的古典藝術精華同禮教觀念約束的結合。我們也會在其中看到巴洛克風格的美學作品的影子。
首先我們來討論巴洛克美學的活力,這種活力體現在視覺藝術中,然后探索如何將這種類似的原則應用在音樂中。例如,圖1所示的意大利藝術家濟安·貝爾尼尼(Gian Lorenzo Bernini)的大衛雕像是以對角線為基礎的,大衛彎下腰,抿住嘴唇,準備戰斗,頭部、腳和手臂形成的連線,正好構成了一個斜著的十字形,這種非常不穩定的角構圖,充滿了動感和戲劇沖突,十分具有張力,正如哈里斯( Harris )和祖克爾(Zucker)的貼切描述,“貝爾尼尼向我們展示了一個不那么理想、更真實的大衛(相比米開朗基羅)——一個正在積極對抗哥利亞(Goliath)的人”。在巴洛克時期,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對角線形狀的藝術作品,讓人對雕塑的定向運動和能量產生錯覺,感覺這個雕塑永遠在運動一樣。又比如在創作《劫奪珀耳塞福涅》這個作品時,貝爾尼尼剛剛22歲,作品中已經采用了典型的對角線構圖,表現了暴力與柔弱的對比。通過局部細節甚至可以看到冥王的手指幾乎要掐入少女柔弱的大腿肌膚,讓人甚至能感覺到她的體溫。巴洛克式建筑也在貝爾尼尼和博羅米尼(Francesco Borromini)等藝術家的推動下達到了頂峰。帕諾夫斯基(Panofsky)說道:“巴洛克建筑將墻體分解甚至彎曲,以此來表達質量和構件能量之間自由的動態相互作用,并且呈現一種類似戲劇的場景,將相互沖突的元素融入一個空間整體中,通過明暗對比的值,甚至表明外部和內部空間之間的一種滲透式的相互關系來使之變得生動。”他所描述的就是博羅米尼的圣依華堂(如圖2)。博羅米尼的圣依華堂的每個方位都融合成了一個不斷增長的實體。他將教堂的立面與宮殿的庭院相連,進一步融入立面。這座矗立的建筑的頂部是一座輝煌、扭曲的尖塔;塔尖不是簡單地直升到一個頂點,而是逐漸上升和旋轉,直到頂部一個華麗的十字架并指向天空。整個建筑的凹凸結構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種動態效果。教堂內部也使用了相同的整合和動態技術,令人眼花繚亂的幾何體構成復雜的韻律,看起來很紛亂,但是其平面疊著一圈圈兩兩疊加的等邊三角形,呈現出了一種高度的智慧。雖然它的內部平面圖只包含在一個簡單的幾何圓圈中,但在這個圓圈中,三角形和圓形邊緣的組合能把人們的目光引向更高的地方,一直朝向穹頂的頂部(如圖3)。

圖1 大衛雕像

圖2 圣依華堂

圖3 圣依華堂局部
從藝術史的角度來看,巴洛克風格源于矯飾主義,這種風格夸大了比例和特征,直到看起來是一種不自然的理想狀態。帕諾夫斯基說:“在意大利早期階段,巴洛克是對矯飾主義的反抗,而不是對‘經典’文藝復興的反抗。它意味著刻意恢復經典原則,同時,在風格和情感上都是對自然的逆轉。”帕諾夫斯基補充道:“巴洛克藝術放棄了矯飾主義雕塑的原則,即通過旋轉的構圖讓觀眾圍繞著群體和人物旋轉……巴洛克式的雕塑和群體既不否認二維的‘視圖’和三維的身體之間的沖突,也不利用這種沖突讓觀看者感到不安和不滿:他們恢復了一種視圖原則,但這一視圖不再通過將構圖訓練成一種凸現安排來實現,而是包含了許多的扭曲、透視縮短和空間價值……‘一維’假定了一個虛擬投影面的特征,在這個平面上投射了塑性和空間元素。”帕諾夫斯基進一步闡釋了巴洛克風格:“巴洛克帶來了完全意義上的現代風景,意味著無限空間的可視化捕捉,并由它的一部分來表示。”巴洛克藝術美學旨在創造一個完整、不斷移動、空間無限、可被視為一個單一部分的現實概念。從這個意義上說,巴赫的多重主題賦格曲在其潛在的巨大方向性上可以與他所處時代的藝術和雕塑相媲美;如果覺察到任何分割的節奏或過早地回到主音都將會與這些理念相對抗。
三、巴赫的賦格曲與巴洛克美學
巴赫的音樂作品屬于典型的巴洛克風格,他被譽為“西方近代音樂之父”,他的音樂創作也體現了這個時期的音樂高峰。尤其是他的賦格曲,是他作品的核心,一定要理解了賦格曲才能真正理解巴赫。他一生創作了非常多的賦格曲,比如《哥德堡變奏曲》《無伴奏大提琴組曲》等,都有賦格的段落。而在他的賦格作品中,最標志的特征就是結束的主音處經常會遇到大規模的有明確目標導向和聲運動;這種連續和聲運動都是朝著最終主音的目標積極前進的。這與巴洛克風格的美學是一致的,它穩定了恒定的運動和活力,同時這也符合視覺藝術中動態和定向運動的審美。由于基本結構有著高度復雜的裝飾,人們經常發現和聲會不斷重復,相似的音色和音量也總是處于不斷變化中。
賦格曲本身也是一種復調音樂,但形式更為復雜一些,往往開始時,一個聲部先單獨演奏出一個主題片段或是簡短的旋律,接著出現另一個聲部又把這個主題翻高五度或者四度來模仿,使其相互對比、結合,也叫作答題。
在整個結構上一般有呈示部、發展部和再現部。賦格曲中的呈示部可能有多種形式,也有可能是標準的開場陳述,然后以交替的主題和答題來呈現主題。副呈示部用同樣進入聲音的順序呈現了同樣的主題。副呈示部是建立在一個已經存在的主題之上的。然而,在副呈示部中,主體不是采用直述形式;相反,它可以是倒影或擴大等。我通常將“不完整”的呈示部(即沒有讓每個聲音進入主題)簡稱為“呈示部”,或者更少見的是“偽呈示部”,這取決于呈示部在多大程度上遵循開場的標準。雙重或三重呈示部則分別由兩個或三個主題同時構成。需要明確的是,第二個主題本身的呈示部與同時包含第一和第二個主題的呈示部是有區別的。前者是簡單的呈示部,后者是雙重的。
在呈示部中,把主題旋律用所有的聲部展現一遍,然后進入以主題和答題個別音調發展而成的插部。然后主題和插部又在不同的新調上一再出現,形成發展部。賦格曲發展部是一個廣泛的術語,包括插曲和“迷失”的中間部分。發展部的中間入口通常與周圍素材沒有標準的呈示關系。也就是說,沒有主題部分能作為迷失入口的答案。一般來說,發展部由一個或多個具體的有動機的圖形組成,然后過渡到一種呈示類型。不太常見的是,連續的多個發展部可以描述為弱韻律。
接著主題再次回到最開始的原調,為再現部。這就是賦格曲的整個框架結構。在賦格曲中太早回到最開始的主題可能會導致過早停滯,這是不可接受的。因此,當和聲在賦格曲開始時離開最初的主題后,如果“主題”的響度在結尾靜止前很長一段時間內反復出現,通常要用非主題和聲的更深層次的延長來重新詮釋。在巴赫的單主題賦格曲中,由于原調中很少使用韻律,不可分割結構的原則是顯而易見的。換句話說,主音上的韻律通常只最后出現。然而,這種想法需要對二、三賦格進行更多的闡釋,在進入新的主題之前,公認的主音通常只有一個韻律。
考慮到巴赫是一個虔誠的路德宗信徒,人們自然會有個疑問,巴赫是如何以及為什么會受到“天主教”巴洛克美學的影響? 但在實踐中,巴洛克風格的美學理念超越了純宗教理念,使許多新教建筑也采用了新穎的巴洛克動態美學。例如,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巴赫于1747年拜訪過他),盡管他喜歡新教,但在他的無憂宮畫廊中擁有大量巴洛克風格的畫作。雖然日耳曼遠離巴洛克的起源地意大利,但日耳曼國家的藝術深受巴洛克美學的影響。米奈在他的《巴洛克與洛可可》一書中稱:“是威尼斯人和倫巴第人提出了賦予天花板空間靈活性的想法,他們拒絕了畫家們從舞臺設計師那里借鑒的建筑元素,敢于讓人從萬有引力定律束縛中釋放出來,在天空中自由旋轉。日耳曼的藝術家們進行了研究,并把巴洛克推向了更高的層次;他們通過增加消失點的數量,扭曲了空間,并賦予旋轉的運動,使位于教堂不同區域的觀眾看到的畫面都變得栩栩如生。事實上,正是在教堂里,這種藝術找到了表現的領域,因為在宮殿里——除了宏偉的樓梯之外——建筑規模太小,無法充分發揮這些對空間可能性的推測。”
事實上,人們可以看到意大利巴洛克風格的影響遠至北方的哥本哈根的救世主教堂(如圖4)。它的塔尖建于巴赫去世前后,直接受到博羅米尼的《圣伊沃·德拉·薩皮恩扎》的影響,展現出一種輝煌的動態向上推力。的確,巴洛克美學在德累斯頓的傳播十分有意義,因為巴赫從1717年到1741年在那里進行了商業演出。德累斯頓的選帝侯奧古斯都一世和奧古斯都二世,在17世紀末和18世紀用巴洛克和洛可可風格對這座城市進行了現代化改造。他們重建了1685年(巴赫出生的那一年)燒毀的新城,并在老城西北部建立了腓特烈施塔特。德累斯頓成為新教薩克森州的天主教中心,因為薩克森州選帝侯,波蘭國王奧古斯都為了登上王位而改信天主教。國王去世后,為了獲得“選舉撒克遜宮廷作曲家”的稱號,巴赫創作了一首天主教的彌撒曲(并不是康塔塔,在奧古斯都國王的官方哀悼期間是不允許創作的)。此外,在德累斯頓期間,巴赫很可能結識了天主教會的狂熱作曲家揚·迪斯馬斯·澤倫卡。巴赫并不是簡單地停留在新教徒里,他非常熟悉天主教的藝術美學。

圖4 救世主教堂
四、結語
在西方音樂史中,巴洛克時期是一個宗教發揮很大作用的時期,所以這個時期的音樂創作與宗教之間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性和統一性。而作為這個時期的代表人物,巴赫的音樂深刻地表達了那個時代人世間的喜怒哀樂。他的作品充斥著理性的秩序,具有很高的美學價值。通過對巴赫音樂創作中美學價值的探討,可以為現代音樂創作者們提供重要的參考價值,推動現代音樂藝術的健康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