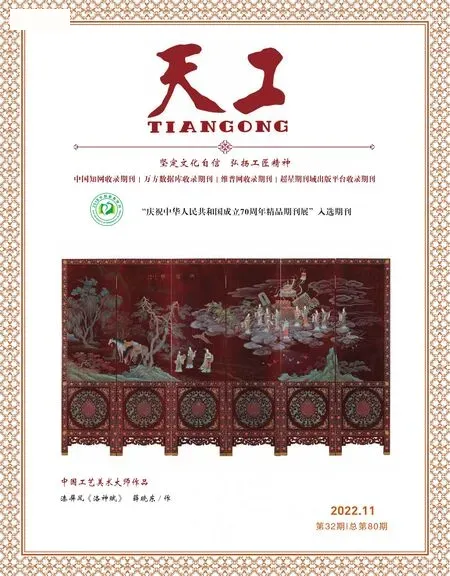戍邊的騰沖農民畫家余水迎作品藝術特色研究
楊紅紅 云南師范大學美術學院
一、傈僳族農民畫家余水迎簡介
傈僳族農民畫家余水迎,1999年10月生,是云南省保山市騰沖市滇灘鎮聯族村委會棋盤石人。余水迎于2020年開始進行農民畫創作,經筆者對余水迎的訪談了解,他最初是受到家鄉老一輩農民畫家余海青老師等的影響,才開始進行農民畫學習的。“余海青老師他們畫農民畫好看,我就喜歡了,所以我就跟著他們學農民畫。”余水迎真誠地說道。在2020年6月16日至6月22日,共計7 天的時間里,余水迎參加了騰沖市2020年農民畫創作培訓班(滇灘抵邊傈僳族村寨棋盤石舉辦)。這次培訓對余水迎的影響很大,也是他正式進入農民畫創作的起點。
二、余水迎農民畫作品賞析
(一)《砍春頭》作品臨摹中的學習和敬意
余水迎的作品《砍春頭》是一件臨摹習作,準確地說是余水迎對傈僳族農民畫家余全發同名作品的學習和臨摹。這是余水迎在剛剛進入農民畫學習階段的一件習作。在《砍春頭》(如圖1)中,余水迎描繪了傈僳族男子服飾早期的“喜鵲衣”樣式,這類衣服、包頭和褲子為黑色,長衫和吊筒為白色,由黑色與白色兩種顏色搭配起來的外褂,有一種黑白相間的趣味性。傳統的傈僳“喜鵲衣”分為獵裝、便裝和盛裝三種,三種著裝均由包頭、長衫、大襟褂、短褲、吊筒、草鞋組成。畫面中男子腰間佩帶長刀,據了解這是傈僳族男子的生活習俗,只要出門都帶著,半插式的木質刀鞘上也有著精美的裝飾。旁邊女子的服飾以靛藍布為基調,身上服飾是小小的方塊和長條形的五色拼花布做成的拼貼,有前襟和后披褂之分,其中前襟及膝,外罩五色拼花布和條紋布,兜縫于前襟;后襟及膝彎,邊腳豎鑲一塊小長方形五色拼花布,女性服裝上有些小裝飾品,這樣衣服可以更加垂墜,勻稱合身。服裝褂背及腰,襟邊鑲以彩色條布。女性頭上用藍黑布作為包頭,現實生活中傈僳族人在舉行儀式時包頭更為復雜精致,在畫面里畫家做了精簡的處理。在這個臨摹的作品中能夠看出余水迎對前輩畫家的敬意,也是對傈僳族傳統的展現與延續。

圖1 臨摹作品《砍春頭》余水迎/作
(二)情感寄托的顯現
余水迎從2020年開始進行傈僳族農民畫創作,他創作的素材多為自身的生活經歷以及身邊的生活場景及人物。其中創作最多的是他與新婚妻子的人物肖像畫。現實生活中,余水迎的婚戀屬于自由戀愛,這樣的情感也反映在其農民畫《互贈》(如圖2)的創作中,畫中身著傈僳民族服飾的兩人情投意合,互換禮物,將甜蜜的愛戀置身在綠地高山的自然環境之中,能夠看出創作者對大自然的依戀。由于歷史上封閉的環境因素和特殊的生產方式,傈僳族對自然的依賴比較大,從而養成了他們熱愛自然和親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在傈僳族的“集體無意識”觀念中,人與自然是共生一體的。在傈僳族古老的神話傳說中,山水有神。關于人類如何與自然共生、愜意生活的問題,傈僳族文化中蘊含著生態智慧和啟示。因此,在余水迎的農民畫創作中,對親人傳達情感的情景都創設于大自然的山水中。

圖2 《互贈》 余水迎/作
(三)現代生活方式的多樣性反映
在余水迎的農民畫創作中還有傈僳族勞作的場景,《舂糍粑》(如圖3)就展現了傈僳族舂糍粑的場景。畫面中青年男女穿著民族服飾,在傈僳族特色農家房屋中制作糍粑。畫面中服飾的色彩呈現更為豐富,對人物的刻畫畫家采用了將棕色塊面與線條結合的方式,還描繪出傈僳族特色農家房屋,大塊面平鋪的色彩與極富當地民族圖案特色的點線面相結合,碰撞出當地人們親近自然、辛勤勞作的生動場景。應注意的是,相比前幾幅作品,這幅作品的人物處在動態中,人物動作更為復雜,畫面也更加豐富。同時對女性五官的刻畫也更生動自然,這與近年來余水迎不斷的創作練習與在人物畫技巧上的鉆研是分不開的。

圖3 《舂糍粑》余水迎/作
(四)對極邊家鄉的熱愛
騰沖位于云南省西南地區,處于中緬邊境,歷史上屬于古代西南絲綢之路的要沖,也是著名的僑鄉、文化之邦和翡翠集散地。由于地理位置重要,中國歷代都派重兵駐守,明代時還建造了石頭城,被稱為“極邊第一城”。云南騰沖滇灘鎮位于姊妹山以南,云峰山以北,大西橫斷山脈三縱谷盆地中,分站駐地海拔1 500 米,執勤通道海拔2 000 米,地理環境錯綜復雜。為守護好國門安全,滇灘分站全體民輔警駐扎在邊境線上,枕戈待旦,鎮守邊關,用實際行動鑄牢防控屏障。傈僳族青年畫家余水迎作為極邊之城的一員也加入了這個集體。這也使余水迎有機會從生活里跳脫出來,開始從另外一種角度對自己的家鄉進行整體的審視與描繪。
余水迎的農民畫創作較多的是關于日常生活的主題,然而他的創作內容和眼界并沒有限于對生活和情感的刻畫,還有《傈僳山寨》等作品的創作。《傈僳山寨》(如圖4)是余水迎對自己的家鄉云南省保山市騰沖市滇灘鎮聯族村委會棋盤石風景的描繪。在畫面中,這里青山環繞,一座座傈僳族民居散落在山腰,雞犬相聞,恍如人間桃源,一片悠然自樂的景象。整個作品疏密相間、自然閑適,展現了當代傈僳族青年眼中極邊第一城的自然環境和生活氛圍,向世人展示了當代傈僳族人的田園生活,給人無限遐想,體現了當代社會人們對田園生活的眷戀與鄉愁。

圖4 《傈僳山寨》 余水迎/作
(五)滇邊年輕人的團結
在騰沖生活著很多少數民族,多民族之間的商貿、聯姻、生活使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構建出多元的文化空間,并且在繼承與變革中不斷向前發展。在《民族團結》(如圖5)這一作品中,余水迎描繪了在傈僳族的民居前,各民族兄弟相互暢飲、和平切磋的友好場景,也是民族團結、和諧共處的美好畫面的記錄。這幅作品也體現了余水迎作為青年傈僳族農民畫家對生活中多民族同胞的兄弟情誼的深刻表達。

圖5 《民族團結》 余水迎/作
三、余水迎農民畫的藝術特色
(一)創作主題的生活化
余水迎美術創作的主題具有生活化的表征,相對余海青等老一輩的傈僳族農民畫家對傈僳族傳統節日上刀山、下火海題材的描繪,他的作品更聚焦平時生活狀態的表現,愛情、勞作、友情、團結,都是這位年輕的傈僳族農民畫家豐富的創作題材。
(二)造型方式的傳統表達
余水迎的美術作品大多數是人物畫,畫中人物形象是以線造型,純色平涂,這也是中國畫中人物畫創作的傳統方式。可見雖然余水迎是遠在西南邊境極地的傈僳族,但是他的人物畫造型方式仍然受到中國傳統人物畫創作方式的影響,從這一方面可以看出在藝術文化中中華文化認同的統一性。
(三)作品材料的不斷探索
余水迎的創作開始是采用水粉和水粉紙進行繪畫,因為水粉顏料和紙張比較普遍,但是也有材料性狀不夠穩定、容易被損壞的問題,后來改用丙烯和素描紙,丙烯顏料的性狀較為穩定,不容易被涂抹掉,顏色保持更為持久。在用丙烯進行農民畫創作的同時,余水迎也積極地進行素描的練習。雖然在素描的明暗處理上有待進步,但是對人物素描的比例把握能力已有明顯提高,這在他近期的農民畫創作中已經體現出來。
四、戍邊農民畫不斷探索的精神追求
(一)戍邊文化與視角
騰沖傈僳族所在的極邊之城的地理位置和歷史上騰沖傈僳族的生活境況造成了騰沖傈僳族戍邊的特點。通過對傈僳族口傳文學木刮《打豬調》《豐收調》等十二調及傈僳族習俗等的多方考證,確認騰沖傈僳族蔡氏等姓氏明宣德年間就在今膽扎、猴橋、聯族等地開荒種地,后參加“王驥三征麓川”,與王驥部隊并肩作戰。“三征麓川”結束后,傈僳族為了防御外敵入侵,駐守邊關要隘,并世代在邊關繁衍生息至今。至此,“關卡”“保衛”等概念滲透到了民族文化中,呈現出了顯性的文化事象和觀念意識。然而,作為當代社會戍邊成員的一員,余水迎在其作品中呈現出的更多主題是對家鄉傈僳山寨詩一樣美的表達和對家人飽含情感的描繪。似乎戍邊的事與景就是他的生活,他駐守著邊境,也就駐守著他的家鄉、他的生活。
(二)民族文化多樣性的表達
余水迎農民畫作品展現出了文化多樣性。近年來,學術研究中強調文化的多樣性,然而文化多樣性的前提是文化獨立性,在傈僳族農民畫中展示了騰沖傈僳族獨有的文化特征和民族內涵,這是騰沖傈僳族文化多樣性展現的前提。作為一名二十歲出頭的小伙子,在農民畫創作中體現的各種傈僳族服飾文化和生活狀態,正是傈僳族年輕人在這個信息更迭的時代對本土傈僳族文化的認同,以及在多元民族社會中對民族意識的肯定與自信。
(三)年輕傈僳族人的自我闡釋與交流寄予
近年來,余水迎積極地參加騰沖市文化館舉辦的美術培訓班,同時努力練習素描,以提高繪畫中物象表達的準確性。隨著對農民畫創作經驗的積累,他發現在繪畫創作過程中技能的突破是必經之路,尤其是對人物形象的造型和表達方面,因此他下定決心,進行素描人物的學習。沒有素描基礎的他,一邊在感嘆素描難畫,一邊迎難而上,這種對繪畫技能學習的內驅力就在云南騰沖邊疆傈僳族小伙子的內心中不斷生發,認真練習,越畫越好。對繪畫的鉆研與渴望,促使余水迎以及其他傈僳族農民畫家自發、自覺地鉆研與學習。
五、結語
余水迎作為一名騰沖的傈僳族同胞,他響應政府的號召,加入民兵的戍邊工作,在戍邊工作之余進行農民畫創作。作為一名戍邊的傈僳族農民畫家,他堅守著對祖國、民族、家鄉的熱愛,一幅又一幅農民畫創作,畫出了他對伴侶的思念、對家鄉的守望與對生活的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