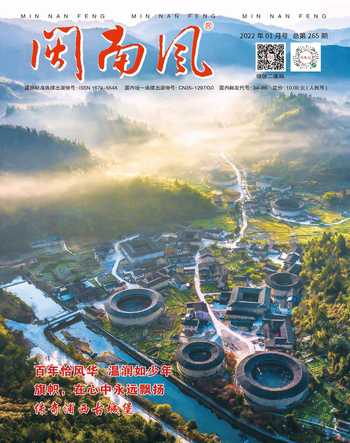心安處
石映芳
想起來挺好笑的,上初三的那年因為看到了一篇關于湘西趕尸的文章,就死活不肯一個人去晚自習了。那篇文章把趕尸的細節刻畫得淋漓盡致,仿佛那一排排面目猙獰的尸體就在眼前直挺挺地向你走來,令人毛骨悚然,我的膽子其實還算挺大的,晚自習回家與同伴一起走一段路后,還要獨自拐進一條小路才能到達村口,而那條小路邊就有幾座墳墓,我都能泰然自若地走過去,可自從讀了那篇文章后,每次路過那些墳堆時,都戰戰兢兢,總覺得墳頭隨時都會出現詐尸。
多年后,去湖南張家界旅游,看了一場魅力湘西的演出,其中有一幕關于趕尸的情景,卻給了我不一樣的感受:出征的號角聲響起,“兒啊,早去早回!”在慈母依依惜別的目光中,戰士們奔赴遠方的沙場。光影明滅中,狼煙四起,炮聲隆隆,這群勇士戰死他鄉,血流成河,尸體堆積如山。趕尸人口中念著咒語,使勁搖著招魂鈴,一具具尸體從地上直挺挺立起,臉色煞白,動作僵硬,昏暗的燈光加上不時響起的囂叫,整個畫面十分神秘詭異。一具具尸體在趕尸人法力的驅使下費力地站起又倒下,倒下再站起,如此往復,竭盡全力,所有人都為他們的執著所感動。“兄弟們,我們回家去了!”隨著趕尸人一聲悲愴的吶喊,所有的尸體仿佛被注入了一股神奇的力量,他們竟齊刷刷地排成了幾條長隊,動作堅定有力,步伐整齊劃一,在招魂鈴的引領下向家鄉的方向走去。回家!回家!母親在家苦苦等待,故鄉的一草一木在聲聲呼喚。肉身雖死,信念永不滅,不管有多遠,不管有多難,魂兒定要回歸故土,回到親人身邊,那是他們的根,他們的心安處!所有的恐怖感在頃刻之間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蕩氣回腸的感動之情。等戲演到親人認領趕回來的尸體那一幕,臺上臺下已是一片淚雨紛飛。
祖父是個唯物主義者,從不信鬼神,他向來反感繁瑣的封建迷信儀式,主張一切從簡。那年祖母去世,我們當地殯葬風俗有一道“請水”的儀式,就是要孝男孝女早早起床,讓長子拿著個盛水的缽盆,由哀樂隊吹吹打打,領著到約定的溪邊取一缽清水回來給死者擦身,祖父覺得這既傷財又折騰人,就把這道儀式給省略了,直接讓人從自家屋里的水龍頭接了盆水,給祖母擦身,而且還交代父親說以后他去世也要這樣做。
祖父雖對這些繁瑣的儀式嗤之以鼻,卻十分在意他死后的落葬之地,他是個悶葫蘆,不善言談,卻常常念叨著:“我死后一定要回高南。”他早早就交代叔公以后要在高南給他找墳地。祖父出生于縣城高南村,十多歲時被崎嶺鄉的遠房親戚領養,后來那家親戚又搬回小溪縣城的黑市街,黑市街雖然離高南村不遠,但終是回不了原生地,祖父把回故鄉的愿望寄托在了百年之后。
祖父不茍言笑,很少跟兒孫們談心聊天。但他卻經常對我提起童年在高南生活的一些情景:一望無垠的稻田,金燦燦的稻子在風里翻涌,鳥雀成群地飛來飛去,漂亮的錦雞時常在稻田里出沒,碗口大的河蚌和肥碩的螃蟹隨處可見;花山溪在南山橋下潺潺地流淌,男孩子喜歡站在橋的欄板上,接二連三往溪里跳,在花山溪的懷抱里暢游,快樂得像小魚兒;祖父常跟著家里的漁船去捕魚,他小小年紀就是捕魚能手,總能滿載而歸,換回不少買柴米油鹽的錢……那時的日子雖苦,但自由和快樂卻無處不在。那片土地珍藏了祖父多少美好的回憶!
小溪的中山公園是老人們休閑娛樂聚集之處,喜歡打橋牌的祖父天天都要去那里報到,回家后不時就會聽他提起誰又去世了,誰死后回老家,了卻了一樁心愿。言語中雖有悲傷,但更多是替他們感到欣慰。年老的人開始正面死亡,很多人也都能“視死如歸”,塵歸塵,土歸土,落葉終將歸根,回到剪不斷臍帶的血地——故鄉,成了多少人的臨終愿望。
祖父最終因突發腦溢血,住進了縣醫院。他失去了言語功能,再也說不出一句話來。叔公到醫院探望。祖父用那只還能動彈的手緊緊抓住叔公,眼睛直勾勾地看著他,嘴唇費力地抖動著,卻怎么也發不出聲音。叔公摸了摸他的頭,老淚縱橫:“老哥啊,我知道你要說什么,你就放心吧,我一定會帶你回家的!”十幾天后,祖父就被安葬在高南村銅鼓巖對面的青山上,他終于回到了記憶里那片散發著芬芳和歡笑的熱土,回到了魂牽夢縈的故鄉。
蘇軾曾經寫下“吾心安處是故鄉。”我想,對于多數人的來講,更應是“故鄉是吾心安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