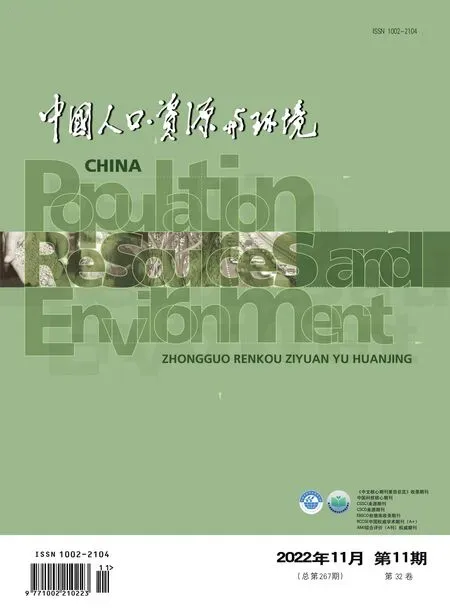環境與經濟目標設置何以影響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
李紅霞,鄭石明,要蓉蓉
(1.華南理工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廣東 廣州 510641; 2.暨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公共政策研究院,廣東 廣州 510632)
空氣污染和氣候變化是當今人類面臨的兩大挑戰。2022年《全球風險報告》指出全球進入氣候緊急狀態,氣候行動失敗和極端天氣事件成為全球最緊要的十大風險之首,人為環境破壞被列為全球第七大風險。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2015年,全球196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巴黎協定》,旨在將全球變暖氣溫升幅控制在工業化前水平2 °C以下。2020年9月,習近平在聯合國大會上,正式宣布中國“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雙碳”)的目標。由于碳排放與污染排放復雜關聯,具有同根、同源和同過程的特點,近年來中國開始致力于同時控制二氧化碳和空氣污染物的排放。戰略規劃層面,“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提出“協同推進減污降碳”。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意見》,強調要以實現減污降碳協同增效為總抓手實施環境保護與氣候治理。減污降碳協同治理已經上升為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策略,減污降碳協同增效對“雙碳”目標的實現至關重要。
《中國城市二氧化碳和大氣污染協同管理評估報告(2020)》指出:“2015年到2019年期間,中國約有1/3的城市實現了二氧化碳與主要大氣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顆粒物)的協同減排。中部地區城市相比東部和西部地區城市,CO2和大氣污染物排放協同管理績效相對較好”。大氣污染治理與應對氣候變化的協同效應已成為環境與氣候領域的研究熱點。已有大量研究圍繞交通、能源、工業等重點行業,采用“明確減排對象(政策、技術、標準、措施、行動等)-確定污染物和溫室氣體核算方法-相應減排量計算”的思路,開展區域或城市大氣污染物和溫室氣體協同減排效應評估。然而,現有研究仍未明確二氧化碳和大氣污染物協同管理績效的差異成因,即哪些因素會影響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為回答這一問題,以下從目標設置視角,對中國城市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的影響機制開展實證研究。
該研究主要貢獻包括如下三個方面:第一,針對現有研究單純從減排技術、政策或措施層面無法解釋城市協同管理績效差異的問題,從更高層面的目標設置視角出發,檢驗PM2.5/PM10濃度目標、經濟增長目標對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的影響作用,為協同管理績效影響機制分析提供新視角、新思路。第二,檢驗了目標設置與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間的中介效應,發現環境目標可通過能源結構調整、產業結構升級提升協同管理績效,但交通運輸結構的中介效應不顯著,這一發現深化擴展了結構減排對中國減污降碳影響的實證研究。第三,采用不同污染物測算協同管理績效,對回歸結果進行敏感性檢驗,發現環境與經濟目標對不同污染物與CO2協同管理績效的影響存在差異。該結果表明減污降碳協同增效應明確協同控制的污染物對象及其改善目標,并根據當地實際,精準識別實現城市高協同減排水平的治理措施,采取差異化協同治理策略,這對減污降碳實踐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1 文獻綜述
大氣污染與溫室氣體的協同治理是目前氣候變化領域的熱點問題,許多國家和國際組織都在對其進行系統研究[1-4]。國際上對該問題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20世紀90年代, Ayres等[5]指出溫室氣體減排的間接效應包括大氣污染物減排及其相應產生的健康效應。之后到21世紀初,眾多研究以發達國家為研究對象,探析大氣污染物與溫室氣體之間的協同效應、協同方法學以及協同治理路徑規劃等[6]。21世紀之后,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相關研究逐漸增多[7-8]。以下,圍繞前述研究問題,重點從大氣治污與碳減排協同效應、經濟增長與減污降碳兩方面進行梳理闡述。
首先,大氣治污與碳減排協同效應方面,現有研究的關注點主要包括“由碳及污”或“由污及碳”的單向協同效益[9-10]、綜合減排措施的雙向協同效益[11-12]、健康與成本協同效應評估[13]等。其中,“由污及碳”研究中,學者們指出以大氣污染物為目標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對CO2減排產生了積極協同效果[14-17]。目標設置作為公共政策和治理戰略的核心維度[18],在減污降碳領域中并未得到充分研究。以目標為研究視角,僅少數學者實證了目標責任制、環境目標設置在空氣質量改善中的積極作用[19-21]。例如,Zhang等[22]基于中國267個地級市的截面數據,發現PM2.5濃度削減目標每增加1%,城市PM2.5年均濃度下降0.528 3 μg/m3。然而,環境政策的協同減排效應也受到部分學者質疑,Sinn[23]于2008年首次提出“綠色悖論”這一相反觀點,認為有時政府雄心勃勃的環境減排政策,反而可能因為生產者前瞻性的動態供給側反應,通過加速化石能源開采及消耗,對溫室氣體排放造成適得其反的效果[24],并在一些研究中得到證實[25-27]。盡管如此,大氣污染物與溫室氣體的同根同源性已基本達成學術共識,這為減污降碳協同管理提供了理論基礎。以協同成效模擬評估結果為科學依據,美國、歐盟、英國等不同國家或地區已經不同程度地開展了空氣污染與溫室氣體的協同控制實踐[28],中國學者也開始探索并規劃“雙碳”背景下減污降碳的協同治理路徑[29-32]。
其次,經濟增長與減污降碳研究方面,已有大量學者分析了經濟增長帶來的大氣污染排放或碳排放效應[33]。根據環境庫茲涅茨理論(EKC),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程度之間呈現倒“U”型曲線關系。通過采用實證方法,眾多研究檢驗了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排放之間的線性或非線性特征(如“U”型、倒“U”型、“N”型、倒“N”型等)[34-36]。CO2作為一種特殊的環境污染物,該理論亦被用于解釋經濟增長與碳排放之間的關系[37]。但由于各個研究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環境污染指標選取、樣本數據特征等存在差異,學界對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排放之間的關系并未達成共識[38]。總體而言,探討經濟增長對大氣污染或碳排放影響效應的研究成果頗豐,但從經濟目標設置維度分析減污降碳協同效應的研究卻十分少見,僅有少數學者探討了經濟增長目標對減污或降碳效應的影響。例如,Chai等[39]以2006—2017年中國30個省份為研究對象,發現經濟增長目標與PM2.5濃度呈倒“U”型關系。Du等[40]以2000—2010年中國230個地級市為研究對象,發現經濟增長目標負向影響PM2.5濃度,當環境目標被納入考核體系后,該種負向影響會有所減弱。宋晨晨[41]基于2004—2014年230個地級市面板數據,發現經濟增長目標“層層加碼”及“硬約束”顯著加劇環境污染,地方存在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目標超額完成的情況。
綜上,現有研究存在如下不足:①研究視角上,現有文獻大多僅關注環境政策或經濟增長對減污或降碳效應的單一影響機制,系統探析環境與經濟目標對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影響的研究較為少見,有學者指出未來仍需進一步探索目標、政策、措施、技術和政治維度的協同效應[1]。②方法學上,與經濟或社會科學方法相比,目前科學與工程計算方法仍是減污降碳協同管理效果評估最常見的方法[4],但由于假設太多,這些定量結果只能作為預測或理論值,目前仍十分缺乏基于經驗數據的回顧性實證檢驗研究。③眾多學者強調協同效應在政策制定和綜合決策中的作用,然而現有文獻多為純科學研究,可用于政策參考或決策的研究較少。④全球、國家層面的大氣污染物與溫室氣體減排協同效應研究較多,而在城市層面分析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的研究較少。總體而言,目前針對城市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差異的量化實證研究仍不多見。因此,以下從目標設置視角出發,通過實證分析環境與經濟目標對城市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的影響機制,為中國減污降碳協同增效以及實現“雙碳”目標政策制定提供科學依據。
2 理論基礎與機理分析
參考自然科學視角的協同效應理論及管理科學視角的目標設置、EKC等理論,構建“目標設置-結構效應(能源、產業、交通)→協同管理績效”分析框架,論證環境與經濟目標設置對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的影響機制,如圖1所示。考慮到不同環境污染物來源、物理化學生成機理差異較大,此處選取PM2.5和CO2作為減污和降碳的代表性指標。

圖1 環境與經濟目標設置對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的影響機制
首先,環境目標對減污降碳的影響機制方面,其作用路徑可描述為“環境目標設置-環境規制政策/措施-結構減排效應-減污降碳-提升協同管理績效”。根據目標設置理論,設定明確的、具有挑戰性的具體目標能有力地推動執行力的提升并提高績效[42]。目標設置一直是中國政府績效評估和管理的核心。以空氣質量改善為目標,近年來中國政府出臺了《大氣污染行動計劃》(“大氣十條”)、“打贏藍天保衛戰”等一系列環境政策,涉及能源、產業、交通等多個領域。公開的環境目標約束有助于強化政府的環境規制行為,目前已有一些證據支持環境目標設置與空氣質量改善存在正相關關系[22]。以下重點從結構減排角度,圍繞能源、產業、交通運輸三方面,闡述環境目標對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的潛在作用路徑:①能源結構方面,環境目標約束下,為加速能源結構調整,地方政府配套實施了燃煤電廠改造、燃煤鍋爐淘汰/整治、“煤改氣”“煤改電”工程建設等控制煤炭能源使用的一系列措施。由于PM2.5和CO2的同根同源性,即二者很大程度均來自化石燃料燃燒,減少煤炭等化石能源的消耗顯然可同時減少二者排放。②產業結構方面,環境目標約束下,地方政府實施的嚴控“兩高”(高污染、高能耗)行業、淘汰落后產能、壓縮過剩產能等一系列措施,可通過產業調整政策的直接效應、倒逼企業技術創新的間接效應(即“波特假說”)兩種路徑推動產業結構升級[43]。隨著“高污染、高能耗”的第二產業占比下降,第三產業占比增加,可促進PM2.5與CO2排放協同下降。③交通運輸結構方面,環境目標導向下地方政府大力推動“公轉鐵”“公轉水”等運輸結構調整措施,通過降低單位貨物周轉量能耗并減少道路擁堵,可協同減少PM2.5與CO2排放。綜上所述,環境目標趨向于提升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
其次,經濟目標對減污降碳的影響機制方面,其作用路徑可描述為“經濟目標設置-經濟增長政策/措施-結構效應-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政治錦標賽理論[44]認為,在中國的集權型政治體制下,上級官員主要根據經濟增長來評估和提拔下級官員。因此,下級官員有強烈的動機發展經濟以獲得晉升。為了在激烈的經濟增長競爭中獲得優勢,地方政府往往設定高于上級政府目標基準的經濟增長目標(即“層層加碼”現象)[43],以向上級釋放“能力信號”[44]。目前已有研究證實經濟目標與地方實際經濟增速具有顯著正相關關系[45]。對于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的關系,EKC理論[46]指出,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存在倒U型曲線關系,環境污染首先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增加而持續惡化,但當經濟發展水平達到某個臨界點后環境污染由高趨低,環境質量逐漸得到改善。基于此,從結構效應維度,經濟目標對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的作用路徑可能如下:①能源結構方面,為實現更高的經濟增長目標,地方政府傾向于擴大經濟活動。但由于中國整體還處于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期,眾多城市仍處于EKC曲線“拐點”左側,加之可再生能源的不穩定性,這使得經濟增長勢必會增加以化石燃料為主的高能源消費,從而導致PM2.5與CO2排放增加。②產業結構方面,在經濟增長目標占主導地位的情形下,地方政府通過扭曲地方要素資源配置、“逐底競爭”(降低本地環境規制水平)[40,47]等方式,引入短期內可快速實現經濟增長的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工業企業,可抑制產業結構升級[48-51],進而導致更多PM2.5與CO2排放。③交通運輸結構方面,經濟目標約束驅動下,社會經濟活動的擴大必然會產生更多的交通運輸需求,這對公路、鐵路、航空運輸等會造成不同程度的壓力,導致PM2.5與CO2排放增加。因此,總體認為經濟目標設置趨向于降低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
然而,需注意到,與PM2.5排放量不同,PM2.5濃度還受氣象條件影響,這意味著盡管環境或經濟目標減少或增加了PM2.5排放量,但進一步轉化為PM2.5濃度時其變化趨勢可能部分甚至完全取決于有利或不利氣象條件。因此,此處不提出環境與經濟目標如何影響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的研究假設,僅作為一項探索性研究,通過后續的實證分析得出相關結論。
3 模型構建與變量說明
3.1 模型構建
為分析環境與經濟目標設置對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的影響,構建如下基本計量模型:

其中:rankit為被解釋變量,表示第t個城市第i年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envgoal1it、envgoal2it和gdpgapit為解釋變量,分別表示第t個城市第i年PM2.5濃度目標、PM10濃度目標和經濟增長目標(城市與所在省份經濟增長目標的差值衡量);coalit、instruit、roadit為中介變量,分別為第t個城市第i年的煤炭消費下降幅度、產業結構升級指數、公路客運量下降幅度;Xit為控制變量,ui為城市效應,λi為年份效應,εit為擾動項。
同時,擬利用中介效應模型,檢驗結構減排層面,環境與經濟目標設置對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的影響機制效應,包括:能源結構協同減排效應、產業結構協同減排效應、交通運輸結構協同減排效應。中介效應模型設定如下:

其中:Medvarit為中介被解釋變量,包括coalit、instruit和roadit三個中介變量。若式(1)中的coalit、instruit和roadit系數符號符合預期且統計顯著,同時,式(2)中的β符號顯著,則表明環境與經濟目標通過能源結構、產業結構、交通運輸結構調整影響了協同管理績效。
3.2 變量說明
(1)被解釋變量: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參照《中國城市二氧化碳和大氣污染物協同管理評估報告(2020)》中的計算方法,通過二氧化碳減排率和大氣污染物(以PM2.5為代表)下降率綜合排名計算衡量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計算公式如下:

Ⅰ、Ⅱ、Ⅲ內部按照(CO2減排率+PM2.5濃度下降率)數值從大到小排名。綜合排名越靠前(如排名第一),表示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rank)相對越高。
(2)解釋變量:包括環境與經濟目標兩類。①環境目標。借鑒相關研究[22],選取城市級PM2.5和PM10濃度下降目標(envgoal1和envgoal2)衡量,2013—2017年期間環境目標數據來自2014年31個省級政府與原環境保護部(現為生態環境部)簽訂的《目標責任書》以及2013年國務院發布的《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2018—2020年期間環境目標數據來自各省份/城市出臺的藍天保衛戰實施方案。②經濟目標。借鑒相關研究[40],選取城市經濟增長目標(gdpgoal_city)與所在省份經濟增長目標(gdpgoal_pro)之間的差值(gdpgap)衡量。根據城市或省份每年政府工作報告,當城市或省份當年有明確的地區生產總值預期增長目標(即GDP增長目標)時直接提取其值,當年GDP增長目標為區間目標時取均值處理。
(3)控制變量。從以下三個角度對相關影響因素進行控制:一是根據IPAT模型[52],考慮加入人口規模、富裕程度、科學技術三方面社會經濟因素,即選取城市總人口數lnpopu、人均國內生產總值lngdppc、科學技術支出lntech三項指標作為控制變量(取自然對數);二是考慮到氣象要素與大氣污染密切相關,故在控制變量中引入大氣壓力airpress、平均相對濕度humi、日照時數sunlight、降雨量rain、平均氣溫temp、平均風速windspeed六項氣象指標;三是考慮到低碳試點政策對減污降碳的潛在影響,增加“是否為低碳試點城市”carbon作為控制變量,carbon為虛擬變量,即當年該城市是低碳試點城市時賦值為1,否則為0。
(4)中介變量。結構減排是中國減污降碳協同增效的重要手段,因此本研究重點考慮并檢驗能源結構、產業結構、交通運輸結構三方面所產生的協同減排中介效應。能源結構調整體現為清潔能源替代傳統能源以減少對化石能源的使用,故采用煤炭消費下降幅度coal作為中介變量檢驗能源結構協同減排效應;產業結構升級體現在積極發展第三產業,以提高第三產業占比減少對環境的破壞,借鑒相關研究[53],采用產業結構升級指數instru作為中介變量檢驗產業結構協同減排效應;交通運輸結構調整體現在發展鐵路、水路、航空、管道等多式聯運,降低公路運輸占比以減少CO2和顆粒物排放,故采用公路客運量下降幅度road作為中介變量檢驗交通運輸結構協同減排效應。
3.3 數據來源與描述性統計
選取中國278個地市(包括4個直轄市;未包括遵義市、畢節市、銅仁市、三沙市、儋州市、綏化市、襄陽市、呼倫貝爾市、海東市、廣安市、吐魯番市、哈密市和普洱市;未涉及西藏和港澳臺地區)為研究對象,考慮到2004年之前城市經濟目標數據缺失較多,故研究區間為2004—2020年。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的原始數據來源說明如下:①CO2排放量數據根據中國碳排放數據庫1997—2019年31個省份逐年碳排放數據(CEADs,https://www.ceads.net.cn/data/province/)、1997—2017年中國縣(市、區)級逐年碳排放數據(https://www.ceads.net.cn/data/county/)、2019—2020年31省份逐日碳排放數據(https://essd.copernicus.org/preprints/essd-2021-153/)綜 合測 算獲得。基于上述數據集,該研究2004—2020年城市CO2排放量數據集計算處理步驟如下:首先,根據中國碳排放數據庫的中國縣(市、區)級碳排放清單面板數據,該數據通過DMSP/OLS和NPP/VIIRS衛星反演獲得[54],覆蓋全國2 735個區縣,計算城市所轄范圍內區縣碳排放加和獲得城市級CO2排放量年均值,并進一步逐年計算2004—2017年各城市在所屬省份中的CO2排放占比;其次,基于中國碳排放數據庫2004—2019年31省份逐年碳排放數據、2019—2020年31省份逐日碳排放數據,以2019年各個省份CO2年均值為校準年值,形成2004—2020年省級逐年CO2排放清單;最后,基于2004—2017年城市逐年CO2排放占比,與2004—2020年對應省份CO2排放量相乘,計算獲得2004—2020年城市CO2排放清單,其中2018—2020年城市逐年CO2排放占比采用2010—2017年CO2排放占比均值代替。經分析檢驗,步驟二中各城市逐年CO2排放占比在2010年后相對較為穩定,因此步驟三處理過程相對合理。②大氣污染物PM2.5濃度數據根據清華大學PHD數據庫2000—2016年PM2.5濃度數據、全國城市空氣質量實時發布平臺(簡稱“平臺”)2013—2020年城市PM2.5濃度年均值綜合獲得。前者為MODIS衛星氣溶膠觀測與空氣質量模式模擬等多源數據利用機器學習算法追算獲得,后者為空氣質量自動監測站點觀測值。基于平臺PM2.5年均濃度數據,以2013—2016年為校準年,通過融合清華大學PM2.5濃度數據(圖2),最終形成2004—2020年城市PM2.5年均面板數據。

圖2 2004—2020年城市PM2.5數據集處理過程
解釋變量環境與經濟目標數據來源說明如下:①環境目標數據。2013年之前各城市未設置PM2.5與PM10濃度下降目標,2013—2017年環境目標數據來自《目標責任書》與《大氣污染行動計劃》,主要根據網站信息與文獻資料綜合整理獲得,2018—2020年環境目標數據來源于各省份或城市出臺的藍天保衛戰實施方案,主要根據各地生態環境局網站收集整理獲得,此處均統一為污染物年均濃度下降百分比。②經濟增長目標數據。來自歷年政府工作報告,通過地方政府網站、統計年鑒特載、北大法寶及相關新聞報道收集整理獲得。控制變量包括社會經濟數據與氣象數據兩大類,社會經濟數據指標來自《中國城市統計年鑒》,由于年鑒數據發布存在時滯性,2020年社會經濟數據采用2019年年均值代替;氣象數據指標來自中國氣象數據共享網(http://www.nmic.cn/),通過自行處理城市日均原始數據計算年均值獲得。中介變量包括煤炭消費下降幅度、產業結構升級指數、公路客運量下降幅度三項指標,2020年數據均采用2019年年均值代替,其中煤炭消費量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中國能源統計年鑒》,由于城市級煤炭消費量數據缺失問題,此處采用省級煤炭消費量代替城市煤炭消費量面板數據納入模型;產業結構升級指數、公路客運量原始數據均來自《中國城市統計年鑒》。變量描述性統計見表1。其中,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rank為被解釋變量,觀測值樣本為4 667個。gdpgap、envgoal1、envgoal2為解釋變量,經統計,gdpgoal_city、gdpgoal_pro和gdpgap的平均值±標準差為10.75±3.33%、9.17±1.85%和1.62±2.13%,envgoal1、envgoal2的平均值±標準差為0.90±1.81%、0.50±1.00%。

表1 變量描述性統計
各城市與所在省份經濟增長目標對比情況如圖3(a)所示,為確保所收集數據的準確性,將其與Du等[40]研究中的經濟增長目標特征對比,發現該研究與其獲取的經濟目標數據較為一致。根據城市經濟增長目標時間趨勢,城市經濟增長目標在2000—2010年、2011—2020年、2021—2022年三個階段分別呈現出“先增加、再下降、再回升”的變化特征。各城市與所在省份經濟增長目標之差與減污降碳百分比(即CO2減排率和PM2.5下降率之和)的關系如圖3(b)所示。各城市與所在省份經濟增長目標之差與CO2減排率和PM2.5下降率之和呈現負相關關系。以下,將進一步利用計量回歸模型進行實證研究。

圖3 經濟增長目標與減污降碳協同減排水平
4 實證結果與分析
4.1 基本回歸結果
環境與經濟目標設置對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的基本回歸結果見表2。根據Hausman檢驗與LR聯合顯著性檢驗結果,此處采用雙固定效應模型,即控制城市和年份效應進行回歸,并進行穩健標準誤控制。模型1中未考慮控制變量,模型2為加入控制變量的基本回歸結果,模型3和4分別在基本回歸模型上增加了carbon與envgoal1、gdpgap與envgoal1的交互項,以分析環境與經濟目標的交互作用是否對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產生影響。
模型1—模型3均顯示,gdpgap的系數顯著為正(P<0.10),表示城市與所在省份經濟增長目標之差每增加1%,其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降低1.452~1.929個單位。envgoal1的系數為負(P<0.05),表示城市PM2.5濃度目標每增加1%,其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升高2.826~3.659個單位。envgoal2的系數為負(P<0.01),表示城市PM10濃度目標每增加1%,其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升高6.407~8.951個單位,該值略高于envgoal1系數可能與設置PM10濃度目標的城市大多亦設置了PM2.5濃度目標,該類城市對環境質量改善重視程度較高有關。carbon與envgoal1交互項的系數不顯著,gdpgap與envgoal1交互項的系數顯著為正,表明城市經濟目標越高,環境目標對城市減污降碳的正向影響越小。結合前述影響機理,此處解釋環境與經濟目標設置影響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的可能原因如下:①大氣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具有同根同源性,因此大氣污染物濃度削減目標下的環境治理行動亦有利于二氧化碳減排,從而提升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這與眾多學者證實大氣污染防控措施對二氧化碳減排有積極作用的發現較為一致[14-15],否定了環境目標對減污降碳的“綠色悖論”效應。②城市經濟增長目標越高,經濟增長目標中的城市間競爭通過規模效應(即擴大經濟活動)和“逐底競爭”效應等增加二氧化碳和大氣污染物的排放[40],降低了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
從其他變量看,煤炭消費下降幅度coal的系數顯著為負(P<0.01),即煤炭消費量的下降可顯著提升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這與減少煤炭燃燒可同時削減大氣污染物與CO2有關;產業結構升級指數instru的系數顯著為負,表明增加第三產業占比可提升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這與第三產業比第二產業污染排放相對更少有關;公路客運量下降幅度road的系數為負但不顯著(P>0.10),即交通運輸結構調整并非必然提升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氣象要素方面,rain、temp、windspeed的系數顯著為負(P<0.10),即更大降雨量、更高氣溫及風速可提升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這可能與其促進了大氣污染沉降與擴散從而改善空氣質量有關。lnpopu、lngdppc、lntech、airpress、humi的系數不顯著。
與此同時,參照余泳澤等[43]研究,采用系統GMM法、解釋變量替換、工具變量法、被解釋變量替換四種方式對基本回歸結果進行了穩健性檢驗。其中,解釋變量替換方式為將gdpgap替換為城市經濟增長目標、城市與國家經濟增長目標之差;工具變量法參照Nunn等[55]研究,采用所在省份城市數量與未來一期國家經濟增長目標、未來一期省份經濟增長目標的交互項,作為gdpgap的工具變量;被解釋變量替換方式為將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替換為CO2減排率與PM2.5下降率的二者加和。結果發現,上述四種處理方式下的實證結果與表2中基本回歸結果基本一致。為節省篇幅,此處未將檢驗結果一一羅列。
4.2 區域異質性分析
考慮到中國東、中、西部經濟發展差異較大,將樣本劃分為中部、東部和西部地區三類,采用雙固定效應模型檢驗區域異質性,回歸結果見表3。結果顯示:①經濟目標方面,東部、西部子樣本gdpgap系數顯著為正(p<0.10),中部子樣本gdpgap系數為正但不顯著,即中國仍總體處于經濟增長加劇PM2.5污染與碳排放的階段。②環境目標方面,中部子樣本envgoal1、envgoal2系數均顯著為負(p<0.01),東部、西部子樣本envgoal1、envgoal2系數均不顯著,這與李巍等[56]研究發現類似,即環境規制對環境的提升作用在創新技術最先進和最落后地區失效,這可能與西部地區環境規制水平整體更低[57]、東部地區減污降碳協同治理的邊際效應遞減[15]或相對更強的地方政府競爭引致環境目標效力降低[58]有關。以上發現部分解釋了相比東、西部地區,中國中部地區城市CO2和大氣污染物排放協同管理績效相對較好這一現象,未來仍需開展進一步實證研究,對其內在機制進行量化檢驗。

表3 區域異質性回歸結果
4.3 中介機制檢驗
以下對能源結構、產業結構、交通運輸結構的協同減排機制進行中介效應檢驗。以coal、instru、road為被解釋變量,環境與經濟目標為解釋變量,利用雙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回歸,結果見表4。可以看出:①PM2.5濃度目標均可在1%水平下顯著提升煤炭消費下降幅度及產業結構升級指數,這表明存在能源結構和產業結構協同減排效應;同時,PM2.5和PM10濃度目標在1%水平下顯著促進交通運輸結構調整,但由于表2基本回歸結果中road的系數不顯著,即未檢驗出存在交通運輸結構協同減排中介效應。②模型8中,gdpgap在1%水平下顯著降低煤炭消費下降幅度,結合表2基本回歸結果中coal的系數顯著為負,表明更高的經濟目標亦可通過能源結構這一中介路徑阻礙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提升。

表2 基本回歸結果

表4 中介效應回歸結果
4.4 多污染物與CO2協同減排檢驗
考慮到不同污染物的排放源差異,為檢驗環境與經濟目標設置對不同大氣污染物及二氧化碳協同減排的敏感性,將大氣污染物PM2.5替換為AQI指數、臭氧O3、PM2.5+O3三類,以及將CO2排放量替換為CO2濃度,采用公式(3)重新計算多污染物與CO2協同管理績效的排名,獲得rank_AQI+CO2、rank_O3+CO2、rank_PM2.5+O3+CO2與rank_PM2.5+CO2′,并替代基本回歸模型中的被解釋變量rank得到回歸結果見表5。結果顯示:模型12、14中envgoal1、envgoal2系數為負但均不顯著。這表明由于不同污染物排放源存在差異,采用不同污染物測算協同管理績效時,前述回歸結果對不同污染物是敏感的。

表5 環境與經濟目標對多污染物與CO2協同減排的影響
5 結論與政策啟示
以2004年至2020年環境與經濟目標數據為樣本,基于PM2.5下降率與CO2減排率測算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實證分析環境與經濟目標設置對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的影響效應及其區域異質性,并進一步檢驗能源結構、產業結構、交通運輸結構調整產生的中介效應,以及不同污染物種類對回歸結果的敏感性,主要結論如下。
(1)PM2.5/PM10濃度目標、經濟增長目標均與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顯著相關。城市與所在省份經濟增長目標之差每增加1%,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降低1.452~1.929個單位;城市PM2.5、PM10濃度目標每增加1%,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分別提升2.826~3.659、6.407~8.951個單位;同時,城市經濟目標越高,環境目標對城市減污降碳的正向影響越小。
(2)環境與經濟目標對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存在明顯區域差異。東、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目標對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的負向影響顯著、而中部不顯著;中部地區PM2.5、PM10濃度目標對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的正向影響顯著,而東、西部不顯著。
(3)環境PM2.5/PM10目標可通過能源結構調整、產業結構升級提升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但交通運輸結構的中介效應不顯著。同時,更高的經濟目標亦可通過能源結構這一中介路徑阻礙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提升。
(4)由于不同污染物排放源存在差異,采用不同污染物測算協同管理績效,發現PM2.5濃度目標對PM2.5與CO2濃度、O3與CO2協同管理績效的影響均不顯著。
上述結論蘊含的政策啟示包括:①應著重從目標協同角度考慮減污降碳協同增效。以往大氣污染物與溫室氣體的協同治理研究尤為關注技術、政策或某一具體措施層面的協同效應,而忽略了目標維度的減污降碳協同效應,未來各地政府在設置多重目標(能源、環境、經濟等)時,應通過科學合理的方式強化目標協同、減少目標沖突,實現多污染物與CO2協同管理績效的最大化。②應根據各地區對環境與經濟目標的異質性反應,制定差異化引導和激勵機制。可加大對西部地區環境治理設施投資及環保技術升級的支持力度,完善東部地區排污權交易等市場激勵型環境政策,充分發揮出東、西部地區環境目標對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的積極作用。同時需盡快調整政府績效評價體系,建立GDP增速與GDP質量雙考核的經濟發展評價制度,引導地方政府經濟增長競爭由傳統的速度競爭向質量競爭轉變。③考慮到能源結構調整與產業結構升級對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具有積極作用,未來應從能源供給側和需求側共同發力,助推經濟發展與能源消耗、環境污染“雙脫鉤”,同時應將碳排放量大的高耗能行業作為結構調整重點,鼓勵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加速產業結構升級優化。但交通運輸結構調整并不必然提升減污降碳協同減排水平,因此各地應區分不同環境指標,對交通有關措施(如客貨運輸結構優化、運輸裝備“油改電”/“油改氣”、新能源車船推廣應用、柴油貨車限行、老舊機動車淘汰等)開展系統的多污染物與CO2協同效益評估,并開展實證檢驗,識別并選取高協同減排水平的治理措施最優組合,以提升城市減污降碳協同管理績效,防止政策“千篇一律”。④現有減污降碳協同管理實踐往往忽略針對不同環境指標,分地區、分時段設計精細化的減污降碳最優協同控制方案,未來應加強國家頂層設計,明確協同控制的溫室氣體(CO2、CH4等)及大氣污染物(PM2.5、O3、PM10、NO2等)指標,設置重點區域/省份短中長期協同改善目標(如排放量/濃度目標值、濃度下降百分比、碳達峰年限、碳排放量下降百分比、單位GDP碳排放強度、人均碳排放量等),結合目標考核協同強化各城市/省份和國家目標的一致性,促使地方政府選擇并實施可實現減污降碳目標的最優協同控制路徑,從而賦能中國“雙碳”目標的科學化、精確化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