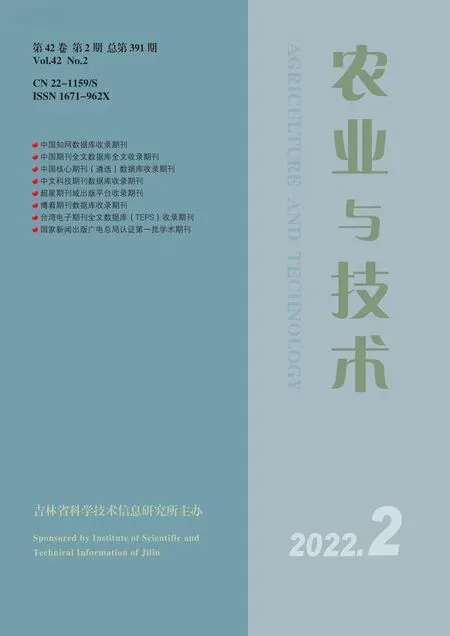水分梯度對川西北高原設施栽培巨菌草莖生長的影響
周揚 宋思夢 周旭 陳梁婧 張茂娟 梁蔡佳 王欣然
(四川民族學院橫斷山區生態修復與特色產業培育研究中心,四川 康定 626001)
菌草(JUNCAO)是指可作為食、藥用菌培養基并具有綜合開發利用價值的草本植物[1]。菌草技術是由福建農林大學國家菌草研究中心林占熺團隊歷經20a余研發而成的集農業、生物、工程于一體的新興多學科交叉技術。從最初的栽培食藥用菌,拓展到菌草飼料、菌草菌物飼料、菌草菌物肥料和生物質能源與材料開發等領域,圍繞“植物—菌物—動物”三物循環生產,我國開展了系列的研究與推廣應用,建立起菌草綜合利用技術與產業發展體系,實現一草多用、綜合利用、循環利用[2]。其中,巨菌草(Pennisetum giganteum z.x.lin)是推廣應用最廣泛的菌草種類之一。巨菌草別稱王草、皇竹草、巨象草、甘蔗草,隸屬于被子植物門單子葉植物綱禾本科狼尾草屬,是一種多年生禾本科直立叢生型植物,具有較強的分蘗能力,適宜在熱帶、亞熱帶、溫帶生長和人工栽培。其生物轉化率高,蛋白含量高(種植4周粗蛋白在10.80%以上),年鮮草產量可達200~400t·hm-2,地上部分器官中莖的生物量最大,脆嫩多汁,味甜,適口性好,可用作家畜鮮食飼料或加工成青貯及顆粒飼料,同時莖稈可榨汁制作飲料、提取纖維或精油用于輕工業等[3,4],此外,巨菌草多采用截斷“莖稈”來進行大批量無性繁殖[5]。因此,研究巨菌草,尤其是其莖器官的生長發育,對區域生態保護及特色產業培育方面有一定實踐價值。
川西北高原地處青藏高原東南緣,是四川省乃至整個長江、黃河流域重要的生態功能區和水源涵養區,且動植物資源(菌類、牦牛、藏系綿羊、藏香豬、藏雞等)十分豐富[6,7]。但因海拔過高、地勢陡峭、高寒干冷,加之道路、水電站、旅游景點開發等人為干擾嚴重,使得該地區生態環境問題突出,植被退化明顯,畜牧業因冬季草地枯萎而發展滯后[8]。引種巨菌草并開發相關生態衍生產業,發揮巨菌草在水土保持、重金屬土壤修復、畜牧業飼料、特色藥食用菌栽培等方面的生態與經濟功能,對川西北高原地區生態保護與重建、區域經濟健康發展十分重要。然而,川西北高原的氣候較為寒冷,降水稀少,干濕季分明,年蒸發量是年降雨量的2~7倍,干旱程度極高[9],這對巨菌草的健康生長發育與莖稈無性繁殖活力有一定考驗。因此,本研究在川西北高原地區,采用設施栽培增溫增濕控水的情況下,通過盆栽控制變量實驗探討水分梯度對巨菌草莖器官生長性狀的影響,擬為川西北高原巨菌草引種與水分科學管理提供理論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地概況
研究地(E102°17′,N30°12′,海拔1400m)地處中國最高一級階梯向第二級階梯云貴高原和四川盆地過渡地帶,屬橫斷山系北段川西高山高原區,境內地理環境復雜,植被退化明顯。境內土壤類型有山地燥褐土、山地燥紅土、山地褐土、山地黃棕壤、山地暗棕壤、山地棕壤、山地棕色針葉林土、山地灰化土、山地草甸森林土、高山草甸土、高山寒漠土等。氣候屬高原型季風氣候,平均日照時數1324~2079h·a-1,氣溫7.0~15.5℃·a-1,年輻射總量超過6000MJ·m-2,無絕對無霜期,大雪、干旱、冰雹、大風等惡劣天氣及災害性天氣頻繁。降水極少,干濕季分明,降水量69.35~664.4mm·a-1,蒸發量1500~2200mm·a-1,相對濕度50%~70%·a-1。在康定市姑咱鎮四川民族學院B校區農學實驗樓3樓玻璃溫室中進行巨菌草盆栽實驗,采用設施栽培的形式控制處理組的溫濕度一致,且無降水干擾。
1.2 實驗材料
盆栽實驗的土壤取自瀘定縣德威鎮德威鄉,其土壤質量含水量為83.85g·kg-1,容重為1.43g·cm-3,田間持水量為25.60%,總空隙度、毛管孔隙度、非毛管孔隙度分別為43.71%、28.42%及15.29%,排水能力為17.36mm,見表1。該土壤透氣透水能力適中,肥力質量中等,經太陽暴曬消毒后過篩,均勻裝入口徑40cm、深25cm的聚乙烯圓臺形花盆中。盆栽實驗的巨菌草種節自福建農林大學國家菌草工程技術研究中心、菌草綜合開發利用技術國家地方聯合工程研究中心及菌草科學與技術研究院引進,種源純正,種節為4月齡,莖稈綠化,木質化程度>85%,腋芽飽滿,完整健康,無霉爛與病蟲害。

表1 所選土壤物理性質背景值
1.3 研究方法
將巨菌草種節留葉鞘,去除葉片和頂端嫩芽,按照15~25cm長度進行砍切(每節保留2~3個芽);將砍好的種節浸泡在3‰尿素溶液中12~24h,清水沖洗后在高溫(不超過30℃)高濕(100%)環境中催芽3~5d;選取90根單稈雙芽種節及時扦插于90個花盆中(裝有16kg德威鄉土壤),澆透定根水。按照等距離擺放好花盆,育苗1個月,補充水分,及時清除雜草。
2021年6月16日,巨菌草成苗后,按照控制變量法,選擇60盆長勢相似的巨菌草幼苗進行水分梯度實驗。以每日稱重補水法與土壤水分儀相結合的方式,控制保持盆中土壤水分在25%田間持水量為重度干旱脅迫處理組(WHC25),50%田間持水量為輕度干旱脅迫處理組(WHC50),75%田間持水量為正常水分處理組(WHC75),100%田間持水量為水淹脅迫處理組(WHC100)。
1.4 室內實驗與監測
花盆中土壤物理性質等背景值采用環刀法測量。室外自然環境因子數據源自當地氣象監測站,玻璃溫室內環境因子數據源自干濕球溫度計每日早、中、晚3次監測均值。6月16日—7月14日實驗期內,分別每隔7d對各水分梯度組內4株代表性植株進行連續測量莖器官生長指標(莖粗、節數、節間長、莖稈總長)。其中,莖粗為巨菌草植株第5節處的莖圍長,節間長為莖桿總長除以節數。
1.5 數據處理與分析
分別用Excel 2007、SPSS 24.0、Origin 9.0進行數據整理、統計分析、圖形制作。運用單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測算不同次測量日前后莖器官形態差值變化及不同水分梯度對莖器官形態特征的影響,Levene's test檢驗方差齊性時差異程度用Duncan多重比較,Levene's test檢驗方差不齊時差異程度用T2 Tamhane's test多重比較,顯著性水平P=0.05。文中圖表數據均為平均值±標準誤,WHC25、WHC50、WHC75、WHC100分別代表25%、50%、75%及100%田間持水量處理組。
2 結果與分析
2.1 設施栽培與室外自然環境因子比較
6月16日—7月17日實驗監測期內環境因子變化情況見圖1,室外自然環境下降雨天數16d,累積降雨量70.30mm,平均日照時間14.00h,平均最高氣溫24.41℃,平均最低氣溫15.97℃,平均溫度18.83℃,平均相對濕度74.17%。玻璃溫室內平均氣溫29.11℃,比室外高出10.28℃,平均相對濕度71.94%,比室外低2.23%。設施栽培的溫濕度更適宜耐高溫、耐干旱的巨菌草生長。
2.2 水分梯度對巨菌草莖生長的總體影響
水分梯度顯著影響了巨菌草莖生長指標(莖粗、節數、節間長、莖稈總長)(P<0.05)。由表2可知,WHC75組中巨菌草累計節間長增量最大(1.75±1.03cm),WHC100組巨菌草的累計莖粗(0.95±0.22cm)、累計節數(6節)、累計莖稈總長(52.59±3.52cm)增量均最大,而在WHC25中植株死亡。表明隨干旱脅迫加劇,巨菌草莖粗、節數、節間長、莖稈總長銳減,各水分梯度中,100%田間持水量(輕度水淹脅迫)巨菌草莖器官生長最好,其次是75%田間持水量組(正常水分梯度),50%田間持水量組(輕度干旱脅迫)巨菌草莖器官長勢較弱,25%田間持水量組(重度干旱脅迫)巨菌草無法生產存活。

圖1 室內外環境因子變化圖

表2 不同水分梯度對川西北高原設施栽培巨菌草莖生長指標的總體影響
2.3 水分梯度對巨菌草莖粗的影響
從各水分梯度下巨菌草莖粗增額來看,WHC100組>WHC75組>WHC50組>WHC25組,均有顯著性特征。即水淹脅迫狀態下巨菌草莖粗增幅最大,其次為正常水分梯度,再者為輕度水分脅迫狀態,重度水分脅迫下巨菌草死亡,隨盆中土壤水分減少,植株莖粗增幅越小。連續監測不同水分梯度下巨菌草莖粗增幅變化如圖2所示,WHC75組巨菌草莖粗增幅隨控制實驗時長增加不斷提升;WHC100組巨菌草莖粗增幅隨控制實驗時長增加先升高后降低,在6月30日—7月7日有最高值;WHC50組巨菌草莖粗增幅隨控制實驗時長增加而緩慢降低;WHC25組巨菌草莖粗增幅僅在6月16—23日有變化,6月30日監測時植株已凋萎死亡。
2.4 水分梯度對巨菌草節數的影響
從各水分梯度下巨菌草節數增額來看,WHC100組>WHC75組>WHC50組>WHC25組,均有顯著性特征。即水淹脅迫狀態下巨菌草節數增幅最大,其次為正常水分梯度,再者為輕度水分脅迫狀態,重度水分脅迫下巨菌草死亡,隨盆中土壤水分減少,植株節數增幅越小。連續監測不同水分梯度下巨菌草節數增幅變化如圖3所示,WHC75組和WHC100組巨菌草節數增幅隨控制實驗時長增加先升高后降低,在6月30日—7月7日有最高值;WHC50組巨菌草節數增幅隨控制實驗時長增加而緩慢升高,在6月23—30日間節數無變化(增幅為0),在6月30日—7月7日及7月7—14日間增幅變大但差異不顯著;WHC25組巨菌草節數增幅在6月16—23日無變化(增幅為0),6月30日監測時植株已凋萎死亡。

圖2 不同水分梯度對川西北高原設施栽培巨菌草莖粗差的影響

圖3 不同水分梯度對川西北高原設施栽培巨菌草節數差的影響
2.5 水分梯度對巨菌草節間長的影響
從各水分梯度下巨菌草節間長增額來看,WHC75組>WHC100組>WHC50組>WHC25組,均有顯著性特征。即正常水分狀態下巨菌草節間長增幅最大,其次為水淹脅迫狀態,再者為輕度水分脅迫狀態,重度水分脅迫下巨菌草死亡,隨盆中土壤水分減少,植株節間長增幅越小。連續監測不同水分梯度下巨菌草節間長增幅變化如圖4所示,WHC75組巨菌草節間長增幅隨控制實驗時長增加先降低后升高,在6月23—30日間增幅最小,在7月7—14日間增幅最大;WHC100組巨菌草節間長增幅隨控制實驗時長增加先升高后降低,在6月30日—7月7日有最高值;WHC50組巨菌草節間長增幅隨控制實驗時長增加先升后降再升再降,無明顯規律;WHC25組巨菌草節間長增幅在6月16—23日較大,6月30日監測時植株已凋萎死亡。
2.6 水分梯度對巨菌草莖稈總長的影響
從各水分梯度下巨菌草節間長增額來看,WHC100組>WHC75組>WHC50組>WHC25組,均有顯著性特征。即水淹脅迫狀態下巨菌草節間長增幅最大,其次為正常水分狀態,再者為輕度水分脅迫狀態,重度水分脅迫下巨菌草死亡,隨盆中土壤水分減少,植株莖稈總長增幅越小。連續監測不同水分梯度下巨菌草莖稈總長增幅變化如圖5所示,WHC75組和WHC100組巨菌草莖稈總長增幅隨控制實驗時長先升后降,WHC75組在6月23—30日間增幅最大,WHC100組在6月30日—7月7日間增幅最大;WHC50組巨菌草莖稈總長增幅隨控制實驗時長增加先降后升,在6月30日—7月7日間增幅最小;WHC25組巨菌草莖稈總長在6月16—23日間有一定增幅,6月30日監測時植株已凋萎死亡。

圖4 不同水分梯度對川西北高原設施栽培巨菌草節間長差的影響

圖5 不同水分梯度對川西北高原設施栽培巨菌草莖稈總長差的影響
3 結論與討論
水分梯度顯著影響了川西北高原設施栽培巨菌草莖器官的生長指標(莖粗、節數、節間長、莖稈總長)。輕度水淹脅迫狀態下巨菌草累計莖粗、節數、莖稈總長增量最大,其次為正常水分梯度;正常水分狀態下巨菌草累計節間長增量最大,其次為輕度水淹梯度;而隨干旱脅迫加劇,巨菌草莖粗、節數、節間長、莖稈總長均不斷銳減,在輕度干旱脅迫中尚能繼續生長,重度干旱脅迫中巨菌草凋萎死亡。因此,川西北高原設施栽培巨菌草在正常水分(75%田間持水量)或輕度水淹(100%田間持水量)狀態下莖器官生長旺盛,且在3周后漲幅達到最大值,低于50%田間持水量后長勢逐漸變差,達到25%田間持水量后巨菌草無法正常生長。
干旱或水淹帶來的水分脅迫作用是限制植物生長發育與形態指標的重要因子,尤其是干旱條件可能會引起膜傷害和膜透性增加及生物自由基積累,而自由基累積會危害植物正常生長,其影響嚴重性僅次于病蟲害等生物脅迫[10]。膨壓與光合作用是植物抵抗水分脅迫的首要生理反應[11],本研究表明,巨菌草細胞具有較強的維持膨壓能力以幫助其在適度干旱脅迫下維持正常生長。當外界供水減少出現輕度干旱脅迫(50%田間持水量),巨菌草在低滲透壓狀態下較強的膨壓維持能力促使其繼續保持氣孔開放進行光合作用,保護葉綠素,降低質壁分離,積累有機物,促進莖粗、莖長、節間長、節數等增加;且體內抗氧化物類和小分子物質可以清除部分活性氧自由基抵御不良環境[12]。而當水分下降至25%田間持水量時,膨壓維持能力逐漸降低,影響葉片生長,降低光合速率,抑制光反應中的原始光能轉換、光合磷酸化、電子傳遞及暗反應等,葉表面氣孔開度減小,CO2吸收量減少,光合作用進一步下降,化學能無法被足夠量的CO2進行碳同化,出現光抑制現象,進一步不可逆地破壞了葉綠體超微結構,巨菌草整體出現凋萎死亡。而在正常水分(75%田間持水量)及輕度水淹(100%田間持水量)狀態下,巨菌草較強的滲透調節機制持續穩定體內滲壓平衡與蛋白質結構穩定性[10,12]。此外,隨外界水分條件變化,巨菌草莖生長指標的增幅均在中后期變化更大,這說明巨菌草形態適應對短期內突然的環境變化具有一定緩沖時期。在本研究基礎上,后期可進一步增加水分梯度對川西北高原設施栽培巨菌草莖內生理生化指標的影響,進一步加深其對水分脅迫響應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