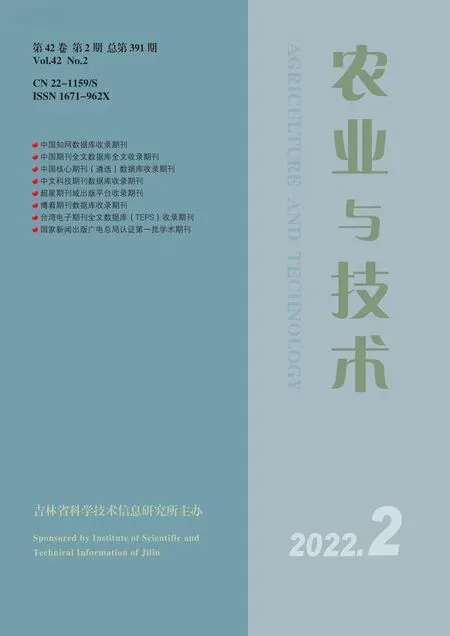農地利用碳效應及時空演變特征研究
——以新疆為例
劉 芳
(安徽工程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安徽 蕪湖 241000)
CO2、CH4等溫室氣體的大量排放引起氣候變暖,氣候變化背景下農業生產活動和糧食安全問題成為全球共同關注的問題。農地利用方式失宜、農地利用結構變化是碳排放產生的重要來源。學者們有關農地利用碳效應的研究主要從碳排放的變動趨勢、驅動因素與經濟增長的脫鉤關系、碳排放效率以及農地低碳利用影響因素等幾個維度展開,如文高輝等[1]、景勇等[2]、康韻婕等[3]分別運用LMDI或STIRPA模型對洞庭湖地區耕地、四川盆地土地和山西省農地碳排放影響因素或低碳效率進行分解、測度;鄧楚雄[4]基于GM(1,1)法分別對長沙市的農地凈碳排量變化趨勢進行預測;陳欽坪等[5]基于對福建農戶的調查,分析了兼業活動如何影響農戶農地低碳利用程度;朱靈偉等[6]運用STIRPAT和GWR模型對農地利用碳排放的空間因素進行判別;劉瓊和肖海峰(2020)[7]論證了農地經營規模如何通過財政支農這一中介變量影響農戶的農地低碳利用行為。已有研究對深入認識農地利用碳效應提供了不同的視角和科學參考。研究范式表現為以固有的因素分解法或預測方法對不同地域的農地碳排放作相關測算,基本上忽略農地利用的碳匯功能。事實上,不同種類的農業植被、林地、草地碳匯功能差異顯著,改進農地利用方式,優化農地資源配置,可以充分發揮農地碳減排功能,使其產生正外部效應,成為溫室效應緩解的“助手”。研究農地利用碳效應需要結合利用方式和結構變化考察其碳排量和碳匯量,精準識別其排碳和固碳能力。
農地利用方式變化和農地結構的變遷對碳效應變化重大影響,進而影響著局部氣候和當地的生產活動。分析新疆農地利用碳效應有助于從碳減排的角度優化配置農地資源,以實現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的雙贏。本文結合新疆14個地州的面板數據,著力刻畫農地在不同利用方式和結構變化下的碳效應,運用Kernel密度函數估計法探究碳效應的地區差異和動態演進趨勢,并基于優化農地結構視角,提出相關建議。
1 研究方法
農地利用碳效應等于農地利用碳排量減去碳匯量,計算公式:
NC=∑CPi-∑CHi=∑Pi×θi-∑Hi×λi
(1)
式中,NC為碳效應,即差額為正,表示凈碳排;差額為負,表示凈碳匯;CPi為各類碳源的碳排量;CHi為各類農地碳匯量;Pi為各類碳源的數量;θi為各類碳源的碳排系數;Hi為各類農地的面積;λi為單位農地的碳匯系數,各類碳源、碳匯的系數參見已有[8,9]研究。
Kernel密度函數估計法是利用連續的密度曲線來描述隨機變量的分布形態,對其概率密度做出有效估計的一種分析方法,也是用于探究非均衡分布的非參數方法。假設f(x)是隨機變量X的密度函數,在點x的概率密度估算公式:
(2)


(3)
Kernel密度函數因表達式差異有多種形式,借鑒相關研究[10,11],本文選擇高斯核函數表達式,具體形式:
(4)
2 新疆農地利用碳效應分析
2.1 不同農地利用方式下的碳排量時空差異分析
通過搜集年鑒源數據,運用上述公式計算出新疆農地利用的碳排量,如表1所示,顯然實施不同的農地管理方式,碳排量差異顯著。研究期間,新疆農地碳排總量持續增長,碳排強度則呈現明顯的N型波動趨勢。碳排總量變動趨勢可以分為3階段:第1階段為2001—2007年,碳排量一直持續不斷地增長;第2階段為2008—2012年,碳排量較前幾年有所下降,并在800萬t范圍內小幅度波動;第3階段為2013—2019年,碳排量再次較快速地增加,直至達到1040.20萬t。從農地利用方式看,生產設施用地承載的畜禽養殖活動碳排量居首位,其次是化肥、農膜和農用柴油3類化學性要素投入產生的碳排放。畜禽養殖碳排放增多與養殖規模擴大息息相關。牧民安居工程的實施使廣大牧民改變原有的游牧生活,畜禽飼養方式也由草地散養改為養殖小區集中圈養;而由于資金和技術有限,畜禽糞便無害化處理不到位,導致糞尿廢水污染和氨氣、二氧化硫等溫室氣體的大量集聚排放。在西部大開發戰略指導下,新疆糧食作物、經濟作物以及林果種植面積不斷增長,各種農作物,特別是棉花對化肥和農膜的依賴度不斷增加;規模化種植和生產作業大大促進農業機械的推廣應用,柴油投入量也隨之增長。盡管新疆很多地州也在推廣測土配方施肥,力求精準施肥,而由于“農技推廣一公里”難題和農戶對配方肥的弱信任度問題,減肥效果并不顯著,使得農田氨類溫室氣體不斷累積。各地州對比結果如圖1所示,2019年農地碳排總量位居前3位的是喀什地區、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簡稱伊犁州)和阿克蘇地區,分別占全疆農地碳排量的16.06%、13.98%和9.61%;喀什地區的碳排量居首位主要因為其耕地和園地面積都比較大,紅棗、核桃和棉花等經濟作物對化肥需求量大,同時該地區也是重要的畜牧養殖區;碳排量較少的是吐魯番地區和克拉瑪依市。
2.2 新疆農地碳匯量時空差異分析
新疆2001—2019年林地、園地和草地碳匯量如表2所示,各地州農地碳匯量見圖1。

圖1 2019年新疆各地州農地碳排量、碳匯量和凈碳排對比
研究期間,新疆農地碳匯總量和碳匯強度均呈穩步增長趨勢。從農地利用結構看,林地碳匯占比較大,基本維持在74%~84%,表明近十幾年,新疆天然林、人工林等10大防護林生態保護工程取得一定成效,退耕還林工作有序推進,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土壤植被,林地碳匯功能得以維護。園地碳匯量占比最小,但增長速度最快,年均增長率達到7.72%。主要原因是多年來,新疆自治區黨委、人民政府大力發展林果業。新疆的紅棗、核桃、香梨、蘋果等特色林果主產區分布于環塔里木盆地,葡萄、枸杞等主要分布于吐哈盆地、伊犁河谷和天山北坡經濟帶。林果業的蓬勃發展不僅使新疆果農實現增收,也綠化了自然環境、凈化了空氣,生態效益顯著。草地碳匯量占比由24.89%下降到14.00%,碳匯量年均遞減率為2.17%。草地碳匯量的減少反映了新疆草地逐年退化的嚴酷現實;盡管實施了退牧還草、退耕還草、草畜平衡等工程措施,但由于水資源匱乏,生態用水得不到有效保障,草原治理速度趕不上沙化、退化和損失速度。

表1 新疆農地不同利用方式下的碳排量及碳排強度

表2 2000—2018年新疆農地碳匯量
各地州因自然資源稟賦差異、生產要素投入、經濟發展水平以及農業產業內部結構調整差異,林地、園地和草地碳匯量空間差異較為顯著。林地碳匯量較高的區域是阿勒泰地區、伊犁州及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簡稱巴州),且阿勒泰地區的林地碳匯量是林匯最少的克拉瑪依市的101倍;園地碳匯量較多的是喀什地區、阿克蘇地區、巴州,而草地碳匯量較多的是伊犁州,其次是阿勒泰地區和塔城地區,而克拉瑪依的園地和草地碳匯量均是最少的。從區域分布看,北疆林地和草地的碳匯量要高于南疆和東疆;而園地碳匯量的大小排序是南疆>北疆>東疆,這充分證實了自治區政府在南疆大力發展特色林果業產生顯著的生態績效。
2.3 新疆農地利用碳效應動態演進趨勢分析
為清楚觀察不同區域年際間農地碳效應的動態演進趨勢,對新疆14個地州的農地碳效應進行Kernel密度估計,核密度分布圖如圖2所示。研究期間,新疆14個地州農地碳效應密度函數曲線中心向右小幅移動,波峰由陡峭變得稍微平緩,變化區間有所變寬,這表明新疆農地利用碳效應的地區差距逐年擴大,且變化態勢較為明顯。波峰特征表現為由“一主兩小”格局逐漸演變為“一主一小”,右側小峰二合為一、變得平坦且不斷向右外延伸,峰值經歷了先下降后上升再次下降的波動,這意味著新疆農地利用碳效應由三級分化演變為兩級分化,農地利用結果為凈碳匯的地州的差距呈現微弱的聚集趨勢,而結果是凈碳排的地州差距呈現擴散趨勢,由于凈碳排地州的數量遠多于凈碳匯的地州,綜合效果是區域集聚特征有所弱化。

圖2 新疆各地州農地碳效應動態演進
2.4 新疆農地利用結構變化對單位面積碳效應的影響
農地結構變化是影響碳排、碳匯增減變化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耕地、建設用地會貢獻碳排量,林地、草地則貢獻碳匯量。因此,退耕還林還草以及建設用地還耕等措施可以增加碳匯。反之,毀林毀草開荒、建設用地擠占農地則會導致碳排放增加。本文采用“差值法”確定農地類型轉變所引起的碳效應[12]。新疆農地結構變更引發的碳效應,如表3所示。17a間,建設用地轉為耕地的碳匯量基本維持在53000~55000kg·hm-2,退耕還草碳匯量在1400~2200kg·hm-2波動,退耕還林的碳匯量在900~1700kg·hm-2波動。顯然,建設用地轉為耕地的碳匯效果要大大高于退耕還草和退耕還林。相反,如果耕地轉為建設用地,毀草開荒、毀林開荒則產生相應數量的碳排放。農地利用類型轉化和結構的變更導致的碳效應不容忽視,通過加強土地用途管理,嚴格建設用地抑制溫室氣體排放,充分發揮農地的碳匯功能。

表3 農地結構變化對農地利用碳效應影響
3 政策建議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議。改進農地利用方式,增加環境無害化要素的投入。為農資生產企業提供優惠的財稅支持政策,促進生物菌肥、生物農藥以及殘膜回收機的研發與推廣,為農戶減少化學性肥藥投入和農膜污染提供替代品和技術支撐。探索多元化畜禽糞便資源化利用途徑和技術。加強土地流轉,實現規模集中養殖,提升畜禽糞便無害化處理水平,提高有機肥還田率,從而增加土壤有機質并減少畜禽養殖碳排放,打造循環低碳種養模式。規范國土資源開發與利用。合理安排城鎮建設用地,提高土地集約利用水平,避免非法建設用地擠占耕地,滿足生態建設和環保用地需求,避免建設用地速增導致碳排放聚集。加強天然林保護和人工林建設,繼續實施新一輪退耕還林還草工程。將退耕還林還草工程與精準扶貧、鄉村生態建設協同推進,制定合理的補貼政策,提升農戶和牧民營林營草的積極性和穩定性,加快林草生物蓄積量增長,充分發揮林草固碳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