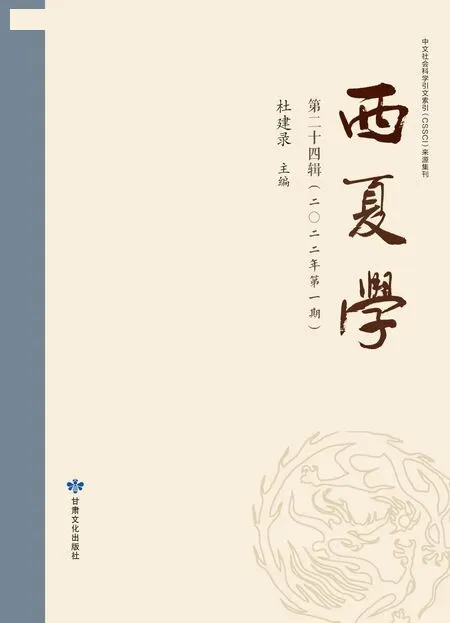北宋武臣趙武墓志銘考釋
薛 鈺
一、墓志簡介及錄文
山西晉中左權(quán)縣文物局收藏一方《宋趙公墓志銘》,墓主人的身份是宋故供備庫副使趙武,蓋呈正方形,邊長73厘米、厚19厘米,志蓋豎書三行篆書“宋故供備趙公墓志銘”。志呈正方形,志文楷書,37行,滿行37字,共1252字。墓志銘青石石質(zhì),品相完整,字跡清晰。志文記載了北宋下層武官趙武的家族世系、仕宦經(jīng)歷、北宋恩蔭制度以及當時駐宋夏邊界堡寨禁軍等情況。學界目前尚未對該墓志做考釋,筆者不揣淺陋,對墓志及相關(guān)問題做簡單的分析,不當之處,祈望專家指正。墓志錄文收于《三晉石刻大全·晉中市左權(quán)縣卷》①劉澤民總主編,李玉明執(zhí)行總主編,王兵主編:《三晉石刻大全·晉中市左權(quán)縣卷》,三晉出版社,2010年。中,但為對比研究方便,將該方墓志錄文移錄如下:
宋故供備庫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上騎都尉天水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趙公墓志銘并序
新授唐州司戶參軍王臨撰
新授嵐州司理參軍張希杰書
新授石州定胡縣尉兼主簿武經(jīng)篆蓋
公諱武,字德臣,姓趙氏。其先本晉卿宣孟之裔,子孫散居河汾間。由高祖而上,世為太原陽曲人,晦跡不仕。宋受天命,太宗皇帝收復河東,括三晉之民,北伐燕薊,而曾祖隸名籍中,駕還,從至京師,因以家焉。自曾祖已下,三世皆葬開封府祥符縣戴婁鄉(xiāng)之原,故今為開封祥符人。公少自挺立,風力疆毅,喜諭兵、騎、射、擊、刺之事。年十三,以祖蔭補茶酒班殿侍。寶元、康定間,夏賊警邊,朝廷召募智勇翹捷之士,捍御疆埸①《三晉石刻大全·晉中市左權(quán)縣卷》中錄文為“場”,原拓片為“塲”,經(jīng)查閱古籍資料,“疆場”為“疆埸”的誤寫,因此此處應為“疆埸”。。公以才藝應選,廷試授三班借職,秦鳳路準備差使②《三晉石刻大全·晉中市左權(quán)縣卷》中標點為“廷試授三班,借職秦鳳路準備差使”,筆者根據(jù)查找相關(guān)官職,“三班借職”為一官名,“秦鳳路準備差使”為一官名,因此將其重新標點為“廷試授三班借職,秦鳳路準備差使”。,累遷至供備庫副使,歷任丹坊州高陽關(guān)教押軍隊,麟府并代沿邊城寨主③《三晉石刻大全·晉中市左權(quán)縣卷》中標點為“歷任丹坊州高陽關(guān)教押軍隊麟府,并代沿邊城寨主”,根據(jù)下文知墓志趙武擔任過橫陽寨主,橫陽寨為麟州境內(nèi)堡寨,因此將其重新標點為“歷任丹坊州高陽關(guān)教押軍隊,麟府并代沿邊城寨主”。、遼州監(jiān)押、監(jiān)華州荊姚鎮(zhèn)酒稅。以元祐三年七月八日致仕,是月十有六日,以疾卒于荊姚之官舍,享年六十有八。公生平為人不峙崖岸,與朋僚交際以至對仆御廝養(yǎng)輩,劇談款語,披胸懷,瀝肺腹,雖家私縷細之事,一無隱避。人有過失,亦面斥言之。不知者或以公為激訐;其知者以為中心夷坦,不疑于物也。在高陽關(guān)日,督修教場、射棚,河北兵素號驕悍,以放役稍晚,總管至視功,遂傲然不肯致敬。公召諸校撫而戒之,立命各領(lǐng)所部歸營,迄且無事。時客省張公亢為帥,聞之大喜,以公為可任,以幹繁劇,待之猶弟侄也。后為麟州橫陽寨主,有都巡檢者暴而虐,用其眾士卒多怨憤。既而私役禁旅,伐木燒炭,一卒躓于冰而斃,群卒遂喧噪,相與訟于官。時郡倅與都巡檢交密,欲誣訟者對本官無禮度、犯階級,將以軍令盡斬之。移文取證于公,公曰:“彼但以政苛役苦,怨憤所致,故訟于官,奈何欲誣以死也?”力為辯之,訟者三十余人因得不死,人人感激公之恩焉。公素家貧,歷官又以廉約自任,而俸入薄,食口眾,然門下常延儒生,教其諸子。人或趙公徒竊好事之名,畢竟何益耳。公不屑也,愈督勵其諸子為學。及后二子相繼以進士登科,習其素業(yè)者,又皆以藝能邊功,食祿于朝,然后鄉(xiāng)間親友莫不服公遠識,知公積慶之有基也。公善草、隸書,其于射馭技能、音律之事,靡所不精,而尤長于擊釰④《三晉石刻大全·晉中市左權(quán)縣卷》錄為“劍”,原拓片作“釰”,同“劍”(《集韻?驗韻》)。。故朝請郎王公嘉材,與公交游最厚且久,常謂人曰:“公之擊釰,方其少時,天下殆無敵手。”自十八登仕路洎終凡五十年,効官多在邊鄙,備嘗出入戰(zhàn)陣間。一時同輩出公下者,往往建節(jié)旌、取侯封,公獨連蹇敷奇,職卑位下,不得施其所能。親舊見者,為之驚嗟嘆息,公處之每自恬然。但曰:“爵位高下,豈不有定分?國家祿廩不患不厚,但患無以補報,取尸素之讖耳。”故其涖官臨政,始終本末,未嘗有少懈怠,為茍且偷安之計。嗚呼!以公之志節(jié)器局,使得時而駕,盡其材識,見于行事,則古之名將良吏,庶幾有可比蹤者矣。然而不克焉,蓋命也夫!夫曾祖仲超,贈左千牛衛(wèi)大將軍;妣張氏,南陽縣太君。祖握,捧日都指揮使,殿前馬步軍都軍頭,賀州刺史;妣齊氏,中山縣君。父景,東頭供奉官,贈太子左衛(wèi)率府率,妣魯氏,長安縣太君。公凡三合姓:董氏,崇德縣君;蘇氏,旌德縣君;李氏,永安縣君。子男六人,畏孝先,未仕;次僧,僧早亡;次孝杰,承議郎;次孝孫,右侍禁;次孝立,前延州司法參軍;次孝周,三班借職。孫男十三人,起三班借職,光弼、光朝、光佐、光庭,并舉進士;光業(yè)、光道、光羲、光遠、光凝,皆幼,余三人早亡。孫女八人。公向任遼州日,愛其風俗淳古、土物豐阜,遂居于遼。故公之卒也,諸孤奉公之柩,歸葬于遼州遼山之北原,以夫人董氏、蘇氏祔,時四年八月十有七日也。臨素辱①《三晉石刻大全·晉中市左權(quán)縣卷》中錄為“辱”,但原拓片“辱”字無法辨認。公相善,諸孤以襄事有日,來求銘于臨,辭不獲已,乃銘之曰:
稟其粹,德既臧,命也窒,晦厥光。
積之厚,流之長,宜子孫,熾而昌。
清河張恩刊

二、志主世系生平及仕宦經(jīng)歷
志主趙武,字德臣,由墓志知趙武于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卒于荊姚之官舍,得壽六十八,可推斷他生于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志文提到“其先本晉卿宣孟之裔,子孫散居河汾間”,即他的祖先是晉卿趙盾的后裔,子孫世代居住在山西西南部的黃河和汾河之間。據(jù)記載,“衰、盾之后,分晉,為諸侯,都邯鄲。王遷,為秦所滅,子代王嘉。嘉子公輔,主西戎,居隴西郡”①[唐]林寶:《元和姓纂》卷七《三十小·趙》,中華書局,1994年,第996頁。。鄭樵《通志·氏族略》曰:“秦并代,使嘉子公輔主西戎,世居天水。其趙宗室散出者,皆以國為氏。居涿郡者后有天下。”②[宋]鄭樵:《通志》,中華書局,1995年,第56頁。即宋國主涿郡趙姓也源于天水,且趙宋經(jīng)常被稱為“天水一朝”“天水一代”。因此墓主開頭提到其祖先有可能是攀附宋國主,也有可能是替趙武身為河南開封人葬在山西遼州找一個合理的理由。
趙武一家“由高祖而上,世為太原陽曲人”。這里的高祖應為唐高祖李淵,即趙武家族自唐朝起就在太原陽曲定居。唐末五代十國時期,北漢割據(jù)政權(quán)以此為國都。因此趙武家族所在地在宋太宗滅北漢之前屬北漢統(tǒng)治。志文提到“宋受天命,太宗皇帝收復河東,括三晉之民,北伐燕薊”,“收復河東”指的是宋太宗即位之后,于太平興國四年(979)滅北漢,取得了“并州、汾州、憲州、嵐州、忻州、代州、遼州、沁州、石州、隆州、寶興軍、固軍、岢嵐軍共十州三軍四十四縣”③李昌憲:《中國行政區(qū)劃通史·宋西夏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33頁。。
宋太宗平定北漢之后,“凡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戶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兵三萬”④[宋]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二〇《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中華書局,2004年,第447頁。,宋朝收編了這些降兵降民,也就是說墓志中提到的“括三晉之民”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括民活動,而是收編了降民降兵。接著,宋太宗一鼓作氣繼續(xù)發(fā)動對遼戰(zhàn)爭,于太平興國四年(979)六月“北伐燕薊”,趙武曾祖趙仲超“隸名籍中”,參加了北伐戰(zhàn)爭,戰(zhàn)爭結(jié)束后,趙仲超作為降兵須依宋廷規(guī)定至京畿,即“駕還,從至京師,因以家焉”。宋朝規(guī)定:“自國初以行舉,誘致偏方之士,而聚之中都,向之為閩、蜀、唐、漢偽官者,往往慕化從順,愿仕于本朝,由是家不尚譜牒,身不重鄉(xiāng)貫。”⑤曾棗莊、劉琳:《全宋文》第二百六十七冊卷六○三四《陳傅良一八·答林宗簡書》,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43頁。如杜昌業(yè)“仕江南李氏,為江州節(jié)度使。江南國滅,杜氏北遷,今為開封府開封人也”⑥[宋]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卷三〇《居士集卷三十》,中華書局,2001年,第450頁。;曾文照在南楚滅亡后“舉國入朝,授亳州永城令”⑦[宋]徐鉉:《徐騎省集》卷三〇《大宋故亳州蒙城縣令賜緋魚袋曾君墓志銘》,中華書局,1971年,第148頁。;偽唐監(jiān)察御史李逖在偽唐滅亡后“以族北遷……為汲縣尉冠氏主簿”①[宋]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卷三八《司封員外郎許公行狀》,中華書局,2001年,第558頁。。宋朝為瓦解五代十國時期割據(jù)政權(quán),規(guī)定降國臣子必須遷到京畿,因此趙仲超舉家遷到北宋京師所在地——河南開封。
據(jù)志文知,墓主曾祖父名趙仲超,贈左千牛衛(wèi)大將軍,元豐改制前為三品,后為從三品,多為宗室命之,也用作武臣贈典。宋朝為因死節(jié)或特殊功績者贈官,用來勉勵為國效忠的臣僚②陳文龍:《北宋前期贈官制度考論》,《史學月刊》2019年第9期。。根據(jù)志文推斷,趙武曾祖在參加北伐戰(zhàn)爭時功績突出,再加上他與趙宋王朝同出一族,特贈其“左千牛衛(wèi)將軍”。祖父名趙握,曾任捧日都指揮使、殿前馬步軍都軍頭、賀州刺史,其中“捧日都指揮使”“殿前馬步軍都軍頭”是長期駐扎在開封、受三衙直接統(tǒng)率的中央禁軍。《宋史》中有這樣一條記載:“會將北伐,召歸。授馬步軍都軍頭、領(lǐng)薊州刺史、樓船戰(zhàn)棹都指揮使。”③[元]脫脫等:《宋史》卷二八九《高瓊》,中華書局,1985年,第9692頁因此猜測趙武祖父趙握應該是參加北伐戰(zhàn)爭而被提拔。他的父親趙景,曾任東頭供奉官,為從八品武臣官階。
趙武是通過祖先蔭庇進入官場的,“年十三,以祖蔭補茶酒班殿侍”。康定、寶元年間,宋夏戰(zhàn)事頻繁,朝廷招募大量善武之才,趙武作為蔭補官員必須經(jīng)過呈試才能得實際官職,趙武經(jīng)廷試得“三班借職”,又任秦鳳路準備差使,累遷至供借庫副使,歷任丹坊州、高陽關(guān)教押軍隊,麟府并代沿邊城寨主、遼州監(jiān)押、華州荊姚鎮(zhèn)酒稅。趙武于“元祐三年七月八日致仕,是月十有六日,以疾卒于荊姚之官舍”,其有子名“孝先”“僧”“孝杰”“孝孫”“孝立”“孝周”。
三、墓志所見之宋代恩蔭制度及遷轉(zhuǎn)之制
(一)墓志所見恩蔭制度
志文提到墓主趙武“年十三,以祖蔭補茶酒班殿侍”,恩蔭制度是北宋職官選任的一種重要制度,宋立國之初,宋太祖就恢復了唐朝的恩蔭制度,規(guī)定“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嘗歷兩任”④[元]脫脫等:《宋史》卷一五九《蔭補》,中華書局,1985年,第3727頁。官員的子弟可以奏補為“千牛”或“齋郎”,宋太祖時恩蔭制度比較嚴格,蔭補人數(shù)也比較少。太宗時期,蔭補范圍開始擴大,宋代的各種恩蔭制度在這個時期也基本確定下來。真宗時期,恩蔭制度基本形成比較完整的體系。在慶歷三年(1043)頒布《任子詔》之前,宋仁宗基本上采用了真宗時期的恩蔭制度,但也做了一些調(diào)整,如天圣元年(1023)規(guī)定從此文官子弟蔭補為文官官職,武官子弟蔭補為武官官職。宋真宗時期確立了較詳細的蔭補法,仁宗統(tǒng)治初期沿用此法,其中規(guī)定:“大卿、監(jiān),帶職少卿,監(jiān),諸州刺史,子授三班奉職,弟、侄、孫借職。”⑤[宋]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八四,真宗大中祥符八年,中華書局,2004年,第1912頁。從墓主趙武家族的官職來看,其父親為東頭供奉官,從八品的品級顯然不夠蔭補級別。其祖父曾任捧日都指揮使、殿前馬步軍都軍頭、賀州刺史,由上史料可知,趙武可憑其祖父官職蔭補為三班借職,但墓志記載蔭職為茶酒班殿侍。
趙武是在“年十三”恩蔭入仕的,根據(jù)墓志推算出此時為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雖仁宗時期的蔭補制度大抵沿用舊制,但隨著此時的恩蔭范圍不斷擴大,朝廷出現(xiàn)大量冗官,所以宋仁宗時期對蔭補制度開始嚴格起來,逐漸在舊制的基礎(chǔ)上進行一些改變,以減少冗官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如天圣四年(1026)“詔臣僚奏房從子弟恩澤,降舊例一等”①[宋]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一〇四,仁宗天圣四年,中華書局,2004年,第2426頁。,明道二年(1033)“詔三丞以上致仕無子者,聽官其嫡孫若弟、侄一人,仍降子一等”。從這些詔令來看,雖然仁宗將官員蔭補的范圍擴大到從七品以上,但是蔭補的官職品級比宋真宗時期降低,即在原來的基礎(chǔ)上降一等授官,如原來授三班奉職,此后便只能授三班借職。三班借職,屬三班小使臣階列,為宋前期入品武階最低的一階。茶酒班殿侍位在三班借職之下。趙武受蔭時間在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因此,趙武有可能是因為宋仁宗時期對蔭補之法的嚴格限制而被降級授官為茶酒班殿侍。
趙武受蔭得官茶酒班殿侍,此職多為虛職,不擔任實際差使。墓志記載:“公以才藝應選,廷試授三班借職。”這里指的應該是趙武通過呈試出官的情況。宋朝規(guī)定文臣出官要經(jīng)銓試,武臣出官要經(jīng)呈試。宋仁宗時期小使臣出官按能力分為中格、優(yōu)等,其中“小使臣中武藝超群,策論詳細而道理明暢者為異等,由皇帝親自引見聽旨”②張雅萍:《北宋小使臣選任研究》,河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墓志記載趙武“于射馭技能、音律之事,靡所不精,而尤長于擊劍”,他武藝超群,再加上他善謀略,因此得皇帝親自引見“廷試”,從而得以出官。又墓志記載“自十八登仕路洎終凡五十年”,即可推算出趙武出官是在寶元元年(1038)。
(二)墓志所見遷轉(zhuǎn)之制
趙武出官得官三班借職,后又擔任秦鳳路準備差使,累遷至供備庫副使,歷任丹坊州、高陽關(guān)教押軍隊,麟府并代沿邊城寨主、遼州監(jiān)押、華州荊姚鎮(zhèn)酒稅。《宋史·職官志》九中記載:“武臣三班借職至節(jié)度使敘遷之制:三班借職,三班奉職,右班殿直,左班殿直,右侍禁,左侍禁,西頭供奉官,東頭供奉官,內(nèi)殿崇班,內(nèi)殿承制,內(nèi)殿承制,供備庫使……”趙武經(jīng)過呈試得三班借職,其升遷理應按照敘遷之制來進行,但他的墓志內(nèi)容中并未出現(xiàn)除三班借職和供備庫副使以外武臣敘遷的任何一個遷轉(zhuǎn)官階,只提到他擔任的具體職事。
從三班借職到供備庫副使,宋代武官需要經(jīng)過磨勘升遷。據(jù)上文,趙武于寶元元年(1038)經(jīng)呈試出官,官階為三班借職,于元祐三年(1088)致仕,官階為供備庫副使,從三班借職經(jīng)五十年升十一階至供備庫副使,由此可以推知趙武大約四五年即磨勘升遷一個官階。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規(guī)定使臣的磨勘年限為七年,到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規(guī)定“減武臣三年遂定為五年磨勘之制”①[宋]章如愚:《群書考索》,臺灣商務(wù)印書館,1986年,第205頁。“今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勘”②[宋]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四三,仁宗慶歷三年,中華書局,2004年,第3431頁。。由此可見,趙武磨勘年限與歷史記載相符。
四、墓志所涉橫陽寨禁軍之事
墓主趙武曾在橫陽寨擔任寨主,志文提到“既而私役禁旅,伐木燒炭”,這說明當時橫陽寨有禁軍駐扎。“橫陽寨西至故俄枝寨四十里,州城西至大橫水六十里,西南至浪爽平五十里。”③[清]周春著,胡玉冰校補:《西夏書校補》卷之六,中華書局,2014年,第603頁。“大中祥符二年(1009),始置橫陽、神堂、銀城三寨,皆在屈野河東,以衙前為寨將,使蕃漢義軍分番守之。又使寨將與緣邊酋長分定疆境。”④[宋]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八五,仁宗嘉祐二年,中華書局,2004年,第4469頁。天禧四年(1020)又置橫陽堡,“北控橫陽河一帶賊路,東至府州靖化堡八十五里,西至西界下和市俄枝谷,南至故連谷縣,北至橫陽河”⑤[宋]曾公亮等撰,鄭誠整理:《武經(jīng)總要前集》卷一七《寨堡十二》,湖南科學技術(shù)出版社,2017年,第1051—1052頁。。慶歷五年(1045),又設(shè)銀城寨、神堂寨、橫陽堡、神木堡、惠寧堡、肅定堡⑥[元]脫脫等:《宋史》卷八六《地理志·河東路》,中華書局,1985年,第2136頁。。一般來說,堡的規(guī)模比寨大,且大多設(shè)在交通要道,寨多設(shè)在山地的險要之處。堡寨的設(shè)置與當時的邊境軍事情況密切相關(guān),戰(zhàn)事平息,堡寨被廢棄,外敵入侵,則再設(shè)堡寨。
橫陽寨位于屈野河東,屈野河西土地肥沃,適合耕種,西夏人常來此地侵擾,天圣初政府將河西職田列為禁地,官私不得耕種。嘉祐二年(1057),為防止西夏人在此地耕墾畜牧,麟州武戡、通判夏倚新筑二堡,派駐禁兵三千、役兵五百,“從衙城紅樓之上,俯瞰其地,猶指掌也”⑦[元]脫脫等:《宋史》卷三二六《郭恩》,中華書局,1985年,第10522頁。,若有緊急情況,則麟州和橫陽堡派兵救援,驅(qū)趕來耕種的西夏人,若夏人兵多,則可在堡內(nèi)躲避。元祐六年(1091),孫貴為河東第一路副將,駐橫陽堡,梁乙埋率十五萬人來犯麟府,孫貴率兵出戰(zhàn)擊之⑧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一百四十四冊卷三一○四《蘇過五·孫團練墓志銘》,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96頁。,在這之前他擔任過橫陽堡兵馬監(jiān)押。由此可以看出,橫陽寨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位于屈野河東,而屈野河西是宋與西夏經(jīng)常爭奪之地,若西夏進犯河西之地,橫陽寨則首當其沖。因此宋廷在橫陽寨常置禁軍也證明了此地所處的重要戰(zhàn)略位置。
志文提到“有都巡檢者暴而虐”“私役禁旅”,都巡檢為中級統(tǒng)兵官,掌土軍、禁軍招填、教習之政令,巡防捍御盜賊。統(tǒng)兵官苛待、私役軍士在軍中是常事,“緣邊主兵官多役軍士斬薪燒炭,往往逃避山谷,或聚而為盜”①[宋]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一一,仁宗明道元年,中華書局,2004年,第2578頁。,又有“弓箭手自西事后來闕數(shù),不曾招填,多為堡寨官員私役,百種侵漁,人甚苦之,以致教閱惰廢”②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四十八冊卷一○三四《呂誨一·論邊備弛廢奏》,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81—82頁。,而宋廷對在戰(zhàn)斗之余的個人行為,如私役禁軍,沒有設(shè)立統(tǒng)一的法規(guī),僅以各種監(jiān)察機構(gòu)糾正不法行為,懲罰措施僅限于削降官爵、停職、罰金等③上官紅偉:《北宋中下級統(tǒng)兵官研究》,西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這就不難理解志文中提到的都巡檢私役軍士,反而還誣告眾士卒的事了。墓志反映出當時北宋禁令法規(guī)對中下級統(tǒng)兵官缺乏約束力,也反映出北宋將兵法的弊端。
五、結(jié)語
趙武墓志的出土為我們了解趙武的生平事跡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資料。趙武世代為山西人,他的曾祖父曾是北漢軍士,后因宋太宗收復河東,其曾祖父又跟隨太宗攻遼,之后便舉家遷到河南開封,其祖父是禁軍將領(lǐng),趙武憑祖父恩蔭入仕,后一直在宋夏邊界任職,最后葬于山西左權(quán)縣。筆者通過對墓志的解讀,了解到趙武曾歷任秦鳳路準備差使、供備庫副使、丹坊州、高陽關(guān)教押軍隊、麟府并代沿邊城寨主、遼州監(jiān)押、華州荊姚鎮(zhèn)酒稅等官職,墓主一生都在邊界任職,為邊界軍政事務(wù)做出了貢獻。
趙武因祖蔭入仕,但是他的蔭補官職卻比真宗時等級低,這反映出仁宗親政后對官員蔭補有所限制,恩蔭制度逐漸嚴格完備。趙武的官階升遷以及差遣經(jīng)歷,體現(xiàn)了北宋下級武臣的主要任用方式和差遣官職。橫陽寨中下級統(tǒng)兵官都巡檢私役禁旅,反映出北宋禁令法規(guī)對中下級統(tǒng)兵官缺乏約束力,也反映了將兵法的弊端。趙武墓志的出土恰能補正史書記載的一些缺漏,對厘清趙武家族世系、仕宦經(jīng)歷以及宋代官制、恩蔭制度具有很大的幫助。此外,墓志也透露出“重文輕武”的社會風氣對西北邊塞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