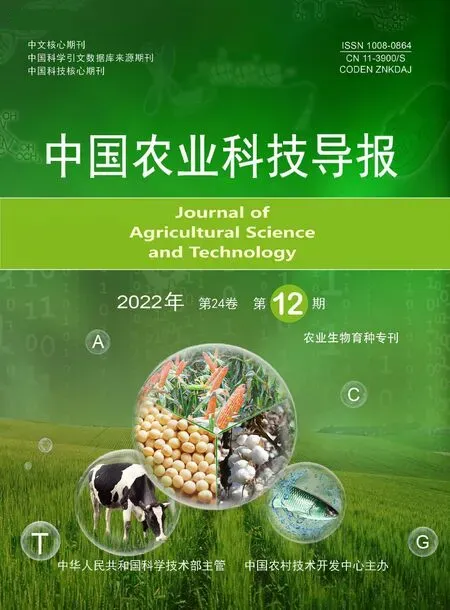農業基因回路設計合成技術發展動態與策略
林敏, 王磊, 谷曉峰, 燕永亮, 劉柱, 涂濤, 姚斌*
(1.河南大學農學院,中原食品實驗室,河南 開封 475004; 2.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北京 100081;3.海南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海口 570100; 4.中國農業科學院北京畜牧獸醫研究所,北京 100091)
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蓬勃興起,生命科學與生物技術呈現出新的發展態勢。隨著生物組學、系統生物學和合成生物學等前沿生命學科與材料、計算和工程學科等高度交叉融合,新一代基因工程技術不斷取得新突破,進入一個智能、精確、定向和定量的新階段[1-4]。基因回路設計與合成是新一代基因工程興起的技術核心,其標志性技術特征包括:①顛覆性,即采用工程學的模塊化概念和系統設計理論,顛覆自然法則與傳統生產模式;②智能性,即智能響應環境和內源信號,大幅度增強農業生物的生產性能與抗性;③精準性,即實現基因精準整合、特異性表達以及高效生物合成[5-9]。
近年來,歐、美、澳等國家和地區紛紛出臺國家或區域級研究計劃,在農業基因工程領域展開競爭。如美國2018年出臺《美國創新戰略》并發布“2030年農業研究科學突破預測”,2020年通過《無盡的前沿法案》,擬在未來5年內向包括基因工程和合成生物技術在內的十大關鍵技術領域及農業、醫藥、食品和環境等產業投入1 000億美元。歐盟委員會2018年頒布最新版本的生物經濟戰略《歐洲可持續生物經濟:加強生物與經濟、社會和環境之間的聯系》,2021年啟動“地平線歐洲”第九個研究框架計劃。世界新興國家如印度和巴西等,紛紛把基因工程、人工智能和云計算等列入國家科技優先發展戰略。大型跨國公司,如孟山都和先鋒等,為保持其技術優勢和市場壟斷地位,投巨資開展農業生物的基因智能改造與定向表達研究,搶占基因定向表達、作物表觀遺傳調控、農業微生物組合合成與高效轉化等前沿領域的技術制高點[10-12]。目前,我國基因智能改造和定向表達技術在農業、資源、環境等領域還處于起步的階段,亟需加快創新基因回路設計與合成技術,精準調控農業動植物生產性狀,培育優質、高產、抗逆的動植物新品種,創制高附加值農產品或農用品,推動我國農業從單功能、低效益、高污染、高資源依存型的傳統農業向多功能、高效益、綠色低碳、高科技支撐型的現代農業轉變。本文簡要總結了農業生物基因回路設計與合成技術的發展動態,深入探討了我國農業生物基因智能設計與精準表達技術的發展策略與優先領域,旨在為創制新一代農業生物新品種或新產品提供技術支撐。
1 加強基因回路設計與合成技術創新,促進我國農業高質量綠色發展
1.1 培育新一代高產作物新品種,保障我國糧食安全
據《國家人口發展規劃(2016—2030年)》預測,到2030年我國人口數量將達到14.5億,糧食總需求量增至7.2億t。因此,糧食產量需要在現有基礎上提高15%。與此同時,隨著現代化和城鎮化推進,我國耕地面積年減少500萬畝(33.33萬hm2)并呈剛性趨勢。近年來,我國糧食進口量持續增加,單純依靠常規技術難以確保糧食基本自給和穩定供應,需要科技創新為農業發展注入新動力。株型性狀直接影響作物的光合作用效率,進而決定作物產量,培育具有“理想株型”的作物新品種是大幅度提高作物產量的重要途徑[13-16]。目前我國在水稻、玉米等作物株型基因挖掘與功能解析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并選育了一批高產作物新品種,為突破作物產量瓶頸提供了有效解決方案[17-20]。解析作物株型性狀(分蘗、株高、穗型、器官大小等)形成的遺傳調控回路并闡明其互作調控規律,挖掘具有重要育種價值的株型性狀關鍵調控元器件,開展模塊化、智能化元件改造,構建和優化株型性狀模塊和調控回路,對促進我國主要作物產量增長和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1.2 創制新一代抗病蟲農作物重大新品種,推動我國綠色農業革命
全球農作物每年因為病蟲害導致的產量損失在11%~30%,全球氣候變暖以及農業種植結構調整等原因導致病蟲害爆發和流行更加頻繁[21]。我國農業生態系統比較脆弱、耕作模式單一,近幾年新發生的病蟲害逐漸增多,特別是外來入侵物種很容易打破生態系統的平衡, 導致病蟲害的爆發流行,如原產于美洲熱帶和亞熱帶地區的雜食性害蟲草地貪夜蛾危害尤為嚴重[22-26]。2019年,在我國云南監測到國內入侵的草地貪夜蛾為玉米型草地貪夜蛾入侵,由于其較強的遷飛能力和繁殖能力,將對玉米生產和我國糧食安全產生極大威脅。黃萎病是棉花生產上的主要病害之一,每年造成的皮棉產量損失約占全世界的皮棉產量的10%~20%,嚴重發病的年份可以達到25%~30%。我國每年由此造成的皮棉產量損失高達7.5萬~10萬t[27-30]。蘇云金芽胞桿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 Bt) 殺蟲蛋白如 Cry1Ab、Vip3 等對不同昆蟲(如鱗翅目、鞘翅目、雙翅目等)有特異毒殺作用[31]。利用高效表達Bt殺蟲基因的玉米是防治草地貪夜蛾等害蟲的理想手段。隨著功能基因組學研究的快速發展,調控主要農作物的重要農藝性狀如抗病、抗蟲、抗逆、高產、優質和養分高效利用等關鍵功能基因群、調控網絡、代謝路徑和蛋白機器已經得到解析。對這些基因群及調控元件進行人工設計與智能改造、發展基因群高效組裝技術、基因群定向協調表達技術,培育新一代抗病、抗蟲等農作物新品種[21,32-33]。
1.3 發展微生物組設計育種策略,確保農業生產的可持續性
當前,我國農業發展已進入新的歷史發展階段,正在由過度依賴資源消耗、增加投入品而滿足量的需求,向綠色生態、高效、可持續發展轉變。但我國農業發展面臨資源條件和生態環境兩個“緊箍咒”,資源與生態環境承載能力已到極限,生態安全面臨嚴重威脅。我國耕地僅20億畝(1.33億hm2),土壤普遍瘠薄,其中中低產田占70%,尚有7億畝(0.47億hm2)鹽堿地未能開發利用,同時在糧食生產、食品安全、化肥、農藥和抗生素用量過度、農業廢棄物污染、連年耕作土傳病害嚴重等方面承壓較重,亟需重大農業生物技術的突破和替代應用,農作物微生物組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全新的角度和思路[34-35]。自然界中正常生長的農作物或養殖動物表面及體內富集了數量龐大且種類繁多的微生物,其集合被稱為農業微生物組[36-38]。動物腸道和植物根際是營養最為豐富的地方,也是共生微生物最主要的定植場所,該類相對集中的微生物群落被看作是宿主的一個“器官”,與其他器官一樣,相對獨立并發揮多種功能,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特征[39]。根際微生物是一類保持土壤肥力、促進作物生長、抑制土傳病害的重要農業微生物,在保持包括水稻、玉米等在內的非豆科作物節肥增產和提高品質等方面具有巨大的應用潛力[40-42]。開發新的微生物組調控策略改善畜禽腸道健康將為解決畜禽產業中面臨的替抗問題、飼料轉化效率問題、疾病問題、新飼料原料利用問題等提供新的思路和手段[43-44]。
1.4 創建飼料高效轉化基因回路,促進農業資源循環利用
我國蛋白源飼料嚴重缺乏,導致飼料行業過度依賴大豆進口,加上中美貿易摩擦的不斷升級以及疫情防控導致的大豆貿易運輸受阻,嚴重阻礙了我國畜牧行業持續健康的發展。低蛋白日糧策略可以有效降低飼料生產成本,提高蛋白質轉化和利用率,最大程度緩解未消化蛋白進入后腸引發動物腸道微生物紊亂并誘發腸炎和腹瀉的問題,并降低不能被動物消化和吸收而排出體外還造成極大的蛋白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我國非糧飼料資源豐富,但長期以來無法得到有效利用,9億t秸稈的利用率不足25%,其不但成為潛在的環境污染源,更造成了極大的資源浪費。因此,迫切需要深化飼料行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力發展非常規蛋白資源在飼料行業的高效高質化應用,實現產業轉型升級發展。通過優化及重構微生物中心代謝途徑,精準調控及組裝廢棄物分解及功能轉化的合成模塊,利用輔因子供應及底盤生物循環系統改造等手段開發非糧飼料資源高效轉化合成的生物反應器系統,如將秸稈木質纖維素類淀粉化,實現秸稈能量飼料化利用,或將棉籽粕、動物羽毛等廢棄物資源蛋白化,實現農業廢棄物資源化利用。
1.5 開發益生元件生物合成與調控技術,支撐我國養殖產業健康發展
我國正從小康全面邁入富裕階段,對動物食品尤其代表高品質蛋白的養殖類畜禽和水產品的消費需求猛增,驅動我國養殖業迅猛發展與結構優化。然而,隨著抗生素“濫用”引起的藥物殘留、細菌耐藥性等負面問題不斷突顯,“綠色加無抗”成為了畜牧養殖業發展的必然趨勢。據報道,歐盟等國禁用飼用抗生素后,飼用藥物使用量大增,使每頭豬的飼養成本增加6美元以上[45]。根據農業農村部發布的第194號公告,我國已于2020年正式實施飼料禁抗,抗生素的全面禁用對我國畜牧養殖業產生了巨大影響。腸道微生物分為有益或有害兩類菌群,與宿主健康、免疫、發育、神經傳導、疾病控制等關系密切。益生元不被宿主動物消化吸收卻能夠選擇性地促進體內有益菌的代謝和增殖,從而改善宿主健康[46-47]。因此,通過對益生元件的收集與鑒定,構建可用于大規模創制的益生元件或模塊庫,并針對底盤生物人工智能設計益生元件生物合成的調控回路,建立高效合成多種益生元件的人工智能微生物體系,對于創建支撐我國健康養殖及動物產品安全的技術產品具有重要的意義。
2 國內外發展動態
2.1 作物株型回路設計技術可實現農藝性狀的精準調控,是針對不同種植環境下提高作物產量的核心技術
第一次綠色革命成功的關鍵是對作物株型進行了優化改良,解決了多個發展中國家糧食的自給問題[48-49]。圍繞全球氣候變化的影響,針對作物株型的遺傳改良一直備受關注,并占據著作物遺傳改良的關鍵位置[15-16,50-52]。作物植株形態的優化包括多方面,例如株高、分蘗數、葉片夾角以及生殖器官形態等[53-54]。株型優化不但可以提高作物的單產和群體產量,還可使其適于機械收割,降低生產成本。株型優化依賴于發掘發育相關的元器件和解析調控回路,并在此基礎上有針對性地對回路進行精準優化改良,從而達到提高產量的目標。
鑒于株型優化對產量提高的重要性,針對株型調控的元件挖掘及調控回路構建成為農業合成生物學領域的研究熱點之一。早期的株型研究主要集中在模式植物擬南芥,研究人員解析了植物器官決定和細胞分化的調控回路,為作物株型改良打下了深厚的理論基礎[52]。隨著合成生物學和表觀遺傳學等前沿理論與技術發展,為揭示不同作物的株型性狀調控差異以及各個性狀之間的相互關聯,解析作物株型發育的關鍵元件和信號模塊,智能優化株型調控回路,從而實現作物株型動態精準調控,提供了顛覆性的新策略[55-56]。目前,我國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株型調控元器件及回路有限,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相比,在對作物株型發育的元器件功能解析及回路構建上仍有一定的差距,阻礙了作物株型優化進程。因此,亟需在該領域加大研發力度,發掘株型發育與優化的元器件、建立調控回路,并在此基礎上結合轉基因及基因編輯技術對調控回路進行精準設計,從而快速、準確地對作物株型進行優化。
2.2 綜合利用資源高效挖掘、基因編輯和合成生物等技術,快速創制抗病蟲目標性狀突出的農作物新品種
隨著生物技術的發展,尤其是宏基因組和單細胞測序技術的發展,從微生物基因組中高通量挖掘抗病蟲、耐除草劑以及次生代謝產物合成基因受到廣泛關注,已為現代基因工程育種提供了有重要應用潛力的候選元器件和靶標回路[57-59]。近年來,作為顛覆性技術的合成生物學興起,為培育抗病蟲害農作物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其通常采用的策略是在植物中引入抗病蟲活性物質的生物合成基因,重建抗病蟲活性物質的生物合成途徑,從而達到抗病蟲的目的[60]。德國BASF公司和瑞士Evolva公司已經形成聯盟,共同研發基于合成生物學的作物抗病蟲害新技術[61]。國際上報道對草地貪夜蛾有防治效果的是來源于蘇云金芽胞 桿 菌 的cry1Ab、cry1F、cry1A、105+cry2Ab2、vip3Aa20基因等;MIR162(Vip3A)對草地貪夜蛾具有很好的防控效果。據統計,1996—2016年基因工程作物的應用使產量增加了6.58億t,帶來1 861億美元的收益;全球累計減少農藥使用量6.71億kg[62]。
我國已建成了涵蓋基因克隆、遺傳轉化、品種培育、安全評價等全鏈條的研發與產業化設施平臺,克隆了具有重大育種價值的抗病蟲、耐除草劑基因,創制出一批具有重要應用前景的抗蟲作物新品系。近年來,我國在作物抗刺吸式害蟲基因發掘與抗性機制解析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進展,特別是在水稻抗稻飛虱研究方面已處于國際領先地位,從作物種質資源中克隆一系列抗褐飛虱和抗蚜蟲基因[21]。此外,采用基因編輯技術加快野生種質資源的人工馴化,加快抗病基因的原位編輯與聚合,實現精準設計抗病蟲育種,為未來的農作物抗病蟲改良提供新的思路[63-64]。
2.3 農業微生物組與宿主互作機制研究不斷深入,為新一代微生物制劑研發奠定了重要基礎
農業微生物組被認為是作物或養殖動物的第二基因組。根際微生物組對植物健康生長和土壤活力質量具有重要作用[65],而腸道微生物不僅參與營養物質的消化吸收,還在宿主代謝和健康中具有重要調節功能。微生物組研究的高速發展得益于高通量非培養測序手段,能短時間內獲得生態系統全部微生物的組成和結構,其中包括自然界不能培養的85%以上的暗物質[66-68]。但是植物體系因細胞器DNA污染,使得內生微生物組測序平臺欠缺,導致多方面研究落后于動物和環境體系[69-70]。在認識根際有益微生物基礎上,深刻了解底盤物代謝網絡、功能模塊作用機制和調控元件,設計并合成具有預期功能的生物元件和器件,將其組建為微生物促生模塊,并在適當的“底盤”微生物中組裝、測試、優化,以產生新型結構化合物,從而實現針對地上農作物的特異、高效、安全、環保的促生功效[71-72]。
豆科植物與根瘤菌的共生結瘤作用對于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與維持生態系統氮循環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40-41]。環境中的氮素精確調控豆科植物與根瘤菌間的共生結瘤。在氮貧瘠土壤中,根瘤菌誘導植物根系發育形成根瘤器官,并將空氣中的氮氣轉化為可供植物直接利用的形式[73]。研究氮素營養吸收、運輸、存儲和代謝相關基因在共生關系建立中的細胞信號調控網絡,鑒定可控氮素營養代謝結構元件,對于促進豆科植物高效結瘤、提高農業生產、減少化肥施用、保護生態環境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義[74-76]。我國科學家解析了目前為止國際上規模最為宏大的豬腸道微生物基因集和基于宏基因組組裝的基因組,探索了宿主基因型對豬腸道微生物群組成的影響,證明在遺傳多樣性和環境均勻性加劇的條件下,微生物群組成和特定類群的豐度是可遺傳的[77-78]。2019年,美國國家科學院、工程院和醫學院聯合發布題為“Science Breakthroughs to Advance Food and Agricultural Research by 2030” 的研究報告,將農業微生物組列入未來10年農業領域亟待突破的五大研究方向之一。
2.4 農業廢棄物資源高效轉化與合成技術應用前景廣闊,是解決農業資源短缺和利用率低下等問題的有效途徑
農業廢棄物資源高效生物轉化技術作為一種具有顛覆性意義的新興技術,可以通過優化及重構微生物中心代謝途徑,精準調控及組裝廢棄物分解及轉化酶功能模塊,實現體內或體外的高效合成與轉化[79]。截止到2021年,全球高效生物轉化與合成相關行業整體爆發式增長,市場規模達到736.93億美元,較2020年增長767.5%,其中農業和食品領域被預測是未來市場需求最大和應用前景最廣的領域[80]。目前,主要的瓶頸在于預處理技術不夠成熟和轉化效率不高兩方面[81]。我國農業廢棄物資源利用受制于以效應微生物及酶蛋白為代表的核心技術不成熟,整體利用效率低,轉化技術穩定性差。
我國是畜禽養殖和飼料生產大國,近幾年飼料行業發展迅速,飼料總產量和生產總值均以兩位數增長,2021年全國工業飼料總產量達到2.9億t,連續10年位居世界第一,約占全球總產量的1/4,全國飼料工業總產值已經接近萬億元[82]。我國生物飼料的發展已取得長足的進步,目前在飼料酶、飼用微生物、發酵飼料等領域的技術創新和產品研發上取得很好的成績,品種不斷增多,功能逐漸拓展,在國際市場也占據了一席之地,大大推動了我國飼料產業的技術升級和發展。農業廢棄物資源高效生物轉化與利用目前已成為畜牧業發展的新增長點,也是國際競爭的主戰場之一,其應用能從源頭上有效緩解動物產品安全與公眾健康、減少養殖環境污染,也是進一步解決飼料資源短缺的現實需要。目前已有較好的研發和產業基礎,要進一步整合成生物學、基因編輯技術、納米技術、人工智能等高新技術,開展農業廢棄物資源高效生物轉化與合成生物學的基礎研究、應用技術研究,建立系統的分子智能設計與綠色智造平臺,推進農業廢棄物資源高效生物轉化與合成技術的研發和應用。
2.5 在飼料全面禁抗的背景下,益生元件生物合成與調控技術為創制綠色健康養殖產品提供重要支撐
養殖動物的共生微生物,尤其是消化道共生微生物,在參與養殖動物免疫與病害防治、營養代謝與品質調控、繁殖與發育維護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由腸道微生物產生的益生元件則是目前最具潛力的抗生素替代品之一,對于解決目前飼料行業中抗生素濫用等問題具有重要的作用[83]。益生元作為直接參與飼料代謝和分解的元件,成為人們開發新一代飼料添加劑和飼料益生元件的重點關注對象[84-85]。如活菌代謝活動分泌(代謝產物)或細菌死亡溶解后釋放的短鏈脂肪酸(SCFA)、酶類、多肽類、磷壁酸等可溶性因子,能夠對宿主產生有益影響;其抗菌活性成分如細菌素、酶類、小分子物質和有機酸等,對革蘭陽性和革蘭氏陰性菌具有抑制或殺滅作用[46]。尤其是許多益生菌所產生的低聚糖、多酚和高分子聚合物(如聚谷氨酸)等益生元對調控畜禽動物免疫力、生長性能和提高肉蛋品質等方面具有很好的效果[86-87]。
隨著分子生物學的飛速發展以及二代、三代全基因組測序技術和轉錄組分析技術的出現,從基因水平上研究益生元件的生物合成機制,并發掘新型益生元件生物合成模塊已成為可能。與其他促生長物質(抗生素、益生素等)相比,其除具有安全、無毒、無殘留、耐氧、耐酸、不易失活的優點外,還具有腸道定植能力強、耐熱穩定性好、能耐受各種不良飼料加工條件和貯藏條件,在飼料中使用沒有配伍禁忌等優點,可長期作為預防性使用[88]。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日本就有在飼料中添加益生元件的研究。據報道,日本的仔豬飼料中約有40%都添加了益生元件[89]。與此同時,美國、歐盟等也對飼用益生元件進行了大量研究,特別是歐盟在2006年實施禁用飼用抗生素以來,益生元件作為替代品在動物疾病預防上成為主流。我國對飼用益生元件的研究起步較晚,并且主要集中于寡聚糖類益生元的抗病和促生長機制等方面的理論研究。今后應針對養殖動物的腸道微生物宏基因組與養殖動物健康之間的關系,高通量篩選新型飼料益生元件,集成與整合益生元件庫,高效合成并創制具有更強抑菌活性和生長調控功能的新型益生元件產品,推動我國由傳統養殖大國轉變為健康養殖強國。
3 發展策略
3.1 總體目標
設計和創建主要作物重要性狀調控、重大農業病蟲害防治、根際微生物與轉基因作物互作、飼料高效轉化和抗生素替代等相關元器件和基因線路,實現基因智能改造和定向表達,為培育新一代轉基因作物新品種提供技術支撐。
3.2 發展策略
針對影響作物產量、抗病蟲、根際微生物、農業廢棄物資源利用以及抗生素應用泛濫等各種農業問題,綜合利用合成生物學、表觀遺傳學、基因組學、代謝組學等理論和技術,對關鍵基因群及調控元器件進行人工設計與智能改造,重點解決精準化與智能響應、適配性與系統優化的關鍵瓶頸問題,創造綜合性狀優良的作物新材料、發展共生基因組育種、促進農業資源循環利用的人工智能微生物和植物體系,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實現我國農業綠色發展(圖1)。

圖1 農業生物基因農業生物基因回路設計與合成技術發展策略Fig.1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gene circuit design and synthesis technologies for agricultural organisms
3.3 優先領域
3.3.1 作物農藝性狀調控回路設計技術 要針對我國糧食安全和高產優質作物品種精準設計的重大需求:①解析水稻、玉米、大豆、苜蓿等主要農作物株型性狀(分蘗、株高、穗型等)形成的遺傳調控回路并闡明其作用機理,挖掘具有重要育種價值的株型性狀關鍵調控元器件及模塊;②以水稻、玉米、大豆、苜蓿等作物為底盤,開展模塊化基因智能改造,構建和優化株型性狀模塊和調控回路,創制株型改良、產量增加的水稻、玉米、大豆、苜蓿等優異育種新材料。通過挖掘和解析水稻、玉米、大豆、苜蓿等作物株型發育關鍵調控元器件和回路,設計和優化株型性狀調控元件和模塊,創制水稻、玉米、大豆等主要農作物新材。
3.3.2 作物抗病蟲調控回路設計技術 針對當前農業生產中重大抗病蟲作物新品種和國家糧食安全的迫切需求,重點開展以下研究。①通過對草地貪夜蛾有效的目標基因遺傳轉化,篩選優良的抗蟲轉基因玉米新材料;建立草地貪夜蛾的篩選和鑒定體系,獲得遺傳穩定的轉基因抗性品系,開展分子特征、目標性狀有效性和穩定性等研究,篩選出優良的抗蟲轉化體,并開展生物安全評價。②系統研究真菌聚酮等具有高抗病蟲功能的微生物次生代謝產物相關合成途徑和調控機制,在酵母菌等底盤生物中人工設計并構建組合合成模塊,通過合成生物學、RNA干擾、基因組組裝等技術創造具有抗黃萎病、枯萎病等多種病害的陸地棉新材料,并開展中間試驗。③以底物通道理論設計相關抗病蟲害物質的生物合成路線,形成可在植物亞細胞結構區域或細胞器定向表達的生物合成模塊,在優選方案基礎上獲得生物合成途徑穩定重建的轉基因植物,測定相關抗病蟲害活性物質的含量,評估轉基因作物的抗病蟲害能力。
3.3.3 作物根際互作促生模塊設計技術 針對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大需求,發展共生基因組育種策略。①系統定義作物的種傳及逐代獲得的內生菌、根表及根際微生物,以穩定定植的共生菌為供體向水稻傳遞生物學性狀。②構建與作物根系適配、高效利用氮的土壤微生物共出現網絡,挖掘促生微生物功能系統;建立根系微生物底盤代謝網絡,鑒定參與促生的反應途徑及相關酶系,開發設計有利于根際互作的合成起始單元及后修飾的功能元件。③構建豆科植物高效結瘤的遺傳調控網絡,鑒定強環境耐受性、高效結瘤結構元件,并通過高效轉化上述重要元件及基因線路,實現結瘤的智能改造與定向表達。
3.3.4 多酶系功能模塊的組裝與調試技術 針對我國飼料糧嚴重短缺,種、養殖業有機廢棄物綜合利用效率低、飼料轉化技術不成熟、穩定性差等問題,進行多酶系功能模塊組織和調試:①通過秸稈、棉籽粕的資源營養分析,確定降解轉化的反應途徑、代謝流分布及相關酶系,開發設計秸稈、棉籽粕轉化相關酶系的合成生物元件、合成線路和生物功能系統,組裝和調試生物轉化的完整線路,并分別對底盤生物與轉化酶系的調控回路進行多層次的重新設計,解決底盤細胞的合理優化問題,最終獲得具有應用潛力的高效轉化酶系或菌株;②建立完善羽毛降解元器件的克隆技術,開展具有重要應用價值的羽毛降解相關新元器件的篩選與鑒定工作,創建羽毛廢棄物高效生物轉化系統。通過分解轉化系統模塊的功能化組裝和調試,基于底盤生物細胞轉化驗證其應用價值,實現農業有機廢棄物的高效飼料化。
3.3.5 益生元件生物合成與調控技術 針對畜禽養殖業抗生素應用泛濫的問題,突破益生元件生物合成與調控技術。①在對重要養殖動物與其腸道微生物互作研究的基礎上,重點突破益生元件生物合成的理論和技術難題。通過已構建的養殖動物腸道微生物純培養物資源庫和宏基因組文庫,挖掘可調控畜禽動物免疫力、生長性能和肉(蛋)品質的益生元件,并進行功能模塊的優化和改良。②利用基因工程技術及合成基因組學等方法,從轉錄、翻譯、信號通路和翻譯后修飾等不同層次智能設計益生元件生物合成的調控回路,優化合成線路中系統模塊的功能化組裝,建立高效合成多種益生元件的人工智能微生物體系。
4 結語
21世紀初,生命科學與生物技術的飛速發展推動農業育種由“耗時低效的傳統育種”向“高效精準的分子育種”的革命性轉變,可望突破傳統農業瓶頸和資源剛性約束,培育細胞農業、低碳農業和智能農業等未來農業新業態和新動能[90-94],促進以二氧化碳為基礎原料,生產碳水食物的碳循環經濟和以氮氣為原料合成蛋白質的氮循環經濟發展[95-97]。未來10年,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人口增長、環境污染和資源匱乏等問題以及確保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實現,基因回路設計和合成技術為代表的新一代基因工程將廣泛應用于農業生產[4],為光合作用、生物固氮、生物抗逆、生物轉化和未來食品等世界性農業科技難題提供顛覆性的技術路線和革命性解決方案(表1)。

表1 基因回路設計和合成技術在農業和環境領域的應用前景Table 1 Application prospects of gene circuit design and synthesis technologies in agriculture and environment fields
2022年美國施密特未來智庫發布《美國生物經濟:為靈活和競爭性的未來規劃路線》,把中國列為未來爭奪全球主導地位的主要競爭對手,建議從政策體系、技術創新、成果轉化、基礎設施、人才培養等方面推進生物經濟戰略,以保持美國全球科技和經濟的霸主地位,引領規模超過4萬億美元的全球生物經濟發展。中國作為發展中的世界農業大國,面臨國際貿易競爭日趨白熱化,農業資源和生態環境的剛性制約日益突出,食物消費結構亟待加快轉型升級,農業生產結構需要不斷優化等重大挑戰,迫切需要加快基因智能設計與定向表達技術等新一代基因工程創新,創制新一代農業生物新品種,突破性地提高對光、肥、水和土地等資源的利用率,促進我國農業高質量綠色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