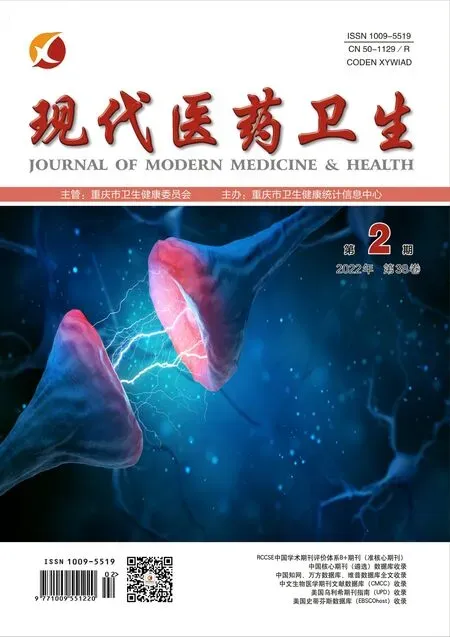泄濁祛瘀方聯合非布司他治療濕濁瘀阻型痛風性腎病的臨床研究*
吳紫紅,殷 貝,宋恩峰
(1.重慶北部寬仁醫院腫瘤科,重慶 401120;2.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二臨床醫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0;3.武漢大學人民醫院中醫科,湖北 武漢 430060)
痛風性腎病又叫“痛風腎”,是痛風常見并發癥,相關研究中通常認為其誘因為體內嘌呤代謝系統失衡,引發尿酸在血液中堆積,導致血尿酸水平升高,尿酸鹽沉積在腎臟組織,最終引起腎臟損害。痛風性腎病患者早期可能出現腰痛、血尿、蛋白尿等,若治療不及時,病情控制不佳,可持續進展至晚期表現為腎衰竭[1]。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迅速,人們對海鮮、動物內臟等富含嘌呤的高蛋白營養食物的攝入量顯著增加,導致痛風性腎病的發生率逐年上升[2]。有研究發現,血尿酸水平輕度升高即可誘導正常大鼠出現內皮功能障礙,引起腎血管阻力升高,從而導致腎臟實質損害[3]。該病治療關鍵在于早期發現,及時治療,積極改善腎功能,延緩腎衰竭進展。西醫的治療原則主要是控制血尿酸水平,但在降低血尿酸水平的同時,常存在一定的不良反應,如別嘌呤醇常誘發過敏性皮疹,甚至會引起致命性過敏反應等[4]。中醫藥作為治療痛風性腎病的一種傳統治療手段,具有癥狀改善明顯、復發率低、不良反應較少、可提高患者生活質量等優勢。本研究采用泄濁祛瘀方聯合非布司他治療濕濁瘀阻型痛風性腎病,并取得了顯著的臨床療效。
1 資料與方法
1.1資料
1.1.1一般資料 選取2020年4月至2021年4月武漢大學人民醫院80例痛風性腎病患者,采用隨機均分原則分為治療組和對照組,各40例。治療組中,男28例,女12例;年齡27~75歲,平均(47.58±12.06)歲;病程3個月至8年,平均(3.46±0.67)年。對照組中,男27例,女13例;年齡30~73歲,平均(47.48±11.66)歲;病程2個月至10年,平均(3.44±0.83)年。本研究經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患者知情并簽署知情同意書。2組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1.2診斷標準 西醫診斷標準參照由美國風濕病協會于1997年制定的痛風性腎病的診斷標準[5]:(1)有原發性高尿酸血癥病史:其中男性尿酸水平大于417 μmol/L,女性尿酸水平大于357 μmol/L,同時排除其他原因所致的繼發性高尿酸血癥;(2)至少具有下列腎臟損害之一:①尿檢異常,出現蛋白尿、血尿等;②腎功能受損,血清肌酐、尿素氮及腎小球濾過率(eGFR)等指標異常;③部分患者以泌尿系結石為腎臟受損的主要癥狀。中醫診斷標準參照中華中醫藥學會腎病分會《尿酸性腎病的診斷、辯證分型及療效評定(試行方案)》[6]制定的濕濁瘀阻型痛風性腎病的診斷標準,主癥:腰脊酸痛隱隱,關節紅腫灼痛,拒按,肢體困重,屈伸不利,顏面或下肢水腫。次癥:關節痛風石形成或關節變形,面色晦暗,頭重昏蒙,口中黏膩或口苦,厭食,小便黃赤,大便黏滯或秘結。
1.1.3納入與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1)符合上述濕濁瘀阻型痛風性腎病中、西醫診斷標準;(2)年齡18~75歲,性別不限。排除標準:(1)年齡小于18歲或大于75歲;(2)由其他病因誘導的繼發性痛風性腎病,如其他類型腎臟病、血液病、腫瘤放化療或利尿劑(噻嗪類)等所致;(3)合并有心腦血管等其他重大內科疾病;(4)對本研究所用藥物過敏;(5)妊娠或哺乳期婦女;(6)有精神障礙或依從性差。
1.2方法
1.2.1治療方法 所有患者進食清淡飲食,禁高嘌呤類食物,適當多飲水等,必要時給予碳酸氫鈉口服堿化尿液。對照組予以非布司他口服(江蘇省萬邦生化制藥有限公司,國藥準字號:H20130058),每次40 mg,每天1次。治療組在對照組基礎上加用泄濁祛瘀方治療,泄濁祛瘀方組成:土茯苓30 g,川芎30 g,萆薢15 g,當歸15 g,川牛膝30 g。用法用量:水煎煮,大火煎開,文火再煎30 min,取汁450 mL,每天1付,分2次服用。2組治療4周為1個療程,連續治療2個療程。以上中藥均由武漢大學人民醫院中藥房提供。
1.2.2療效判定標準[6](1)臨床控制:臨床癥狀、體征消失;尿酸降至正常水平,肌酐、尿素氮恢復或處于正常水平;24 h蛋白尿定量(24hUTP)為正常或蛋白尿(-)。(2)顯效:臨床癥狀、體征明顯改善;尿酸水平下降明顯,較治療前下降大于20%,肌酐、尿素氮水平下降大于50%或恢復至正常水平;24hUTP水平下降大于40%或蛋白尿減少2個(+)。(3)有效:臨床癥狀、體征均有好轉;尿酸水平較治療前下降10%~20%,肌酐、尿素氮水平較治療前下降20%~50%;24hUTP水平下降小于40%或蛋白尿減少1個(+)。(4)無效:臨床癥狀、體征改善不明顯或無改善;尿酸水平變化不明顯,肌酐、尿素氮水平下降小于20%,而嚴重者會升高,出現病情惡化傾向;尿檢蛋白尿略有緩解,甚至可見蛋白尿水平不降反升,提示疾病加重。
1.2.3觀察指標 (1)臨床療效:觀察患者治療后主要及次要癥狀、體征變化情況,計算治療后總有效率,總有效率=(臨床控制例數+顯效例數+有效例數)/總例數×100%。(2)腎臟相關指標:于治療前后監測血清尿酸、肌酐、尿素氮、β2微球蛋白(β2-MG)、α1微球蛋白(α1-MG)及eGFR、24hUTP等指標變化情況,同時監測尿N-乙酰-β-D-氨基葡萄糖苷酶(NAG)、視黃醇結合蛋白(RBP)及中性粒細胞明膠酶相關脂質運載蛋白(NGAL)等指標,觀察早期腎損傷情況。(3)不良反應:觀察治療過程中有無消化道癥狀、肝功能損害、過敏等。

2 結 果
2.12組臨床療效比較 治療組總有效率明顯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2組臨床療效比較
2.22組血清尿酸、肌酐、尿素氮及eGFR水平比較 治療后,2組血清尿酸、肌酐、尿素氮及eGFR水平優于治療前比較,且治療組優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2組血清尿酸、肌酐、尿素氮及eGFR水平比較
2.32組血清β2-MG、α1-MG及24hUTP水平比較 治療后,2組血清β2-MG、α1-MG及24hUTP水平優于治療前,且治療組優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2組血清β2-MG、α1-MG及24hUTP水平比較
2.42組尿NAG、RBP、NGAL水平比較 治療后,2組尿NAG、RBP、NGAL水平優于治療前,且治療組優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表4 2組尿NAG、RBP、NGAL水平比較
2.52組不良反應發生情況比較 治療組中,腹瀉1例,惡心嘔吐2例,經護胃、止嘔等對癥處理后癥狀消失;對照組中,惡心1例,便秘1例,谷丙轉氨酶水平輕度升高2例,予以護胃、通便、護肝等對癥處理后恢復至正常。2組在治療期間均未出現藥物過敏現象,無藥疹出現。2組不良反應發生情況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3 討 論
隨著人們生活及飲食習慣的改變,高蛋白及嘌呤類食物攝入明顯增多,導致高尿酸血癥發生率日益上升,成為我國第二大代謝性疾病,其主要特征是尿酸生成過度或排泄減少導致血尿酸水平增高,進一步發展引起腎臟損害,并發痛風性腎病[7]。一項動物實驗研究顯示,給痛風性腎病模型小鼠胃注腺嘌呤和OXO混合物可抑制尿酸酶活性,導致血尿酸水平升高,誘發痛風性腎病[8]。ZHANG等[9]研究發現,尿酸單鈉的結晶沉積物激活nod樣受體蛋白3炎癥小體信號通路可啟動炎性反應,引起腎臟損傷。目前,痛風性腎病的西醫治療手段主要是降低血尿酸水平,減輕腎臟損傷。但近年來研究發現,使用降尿酸藥物存在較多不良反應,如別嘌醇可能導致嚴重過敏反應[4]。
血清尿素氮來源于人體蛋白質分解代謝,通過腎臟排泄,可反應腎臟功能情況;血清肌酐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應腎實質損傷情況;eGFR常作為評估腎功能分期的重要指標。痛風性疾病患者出現早期腎損傷時,血清尿酸、肌酐、尿素氮水平變化不明顯,可通過檢測血清β2-MG、α1-MG及24hUTP水平進行預估[10]。其中,24hUTP有助于診斷及預估腎臟病變,具有重要意義;β2-MG水平主要反應腎小球濾過功能受損;α1-MG水平可較早反映腎小管損傷狀況。尿NAG、NGAL、RBP在早期腎小管損傷后比較敏感,其水平在血肌酐水平升高之前的12~72 h內即可顯著升高,因此檢測尿NAG、NGAL、RBP水平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早期腎小管的損傷程度[11]。
痛風性腎病歸屬于中醫學“痹證”“歷節風”等范疇。朱丹溪《格致余論》提出“瘀濁凝澀”是該病的基本病機。近年來中醫藥在治療痛風性腎病方面有了新進展,臨床收效良好。如非布司他聯合七葉皂苷治療可明顯緩解痛風患者疼痛,降低血清尿酸水平,減輕水腫,提高臨床療效[12]。符靜泉等[13]研究發現,貓須草水提物對尿酸代謝可能具有雙重調節作用,即上調OAT1蛋白表達促進尿酸排泄、下調URAT1蛋白表達抑制尿酸重吸收,從而減輕尿酸對腎臟的損傷。本研究中,泄濁祛瘀方由土茯苓、川芎、萆薢、當歸、川牛膝5味藥組成。土茯苓利濕泄濁、通利關節,川芎活血化瘀、行氣止痛,二者共為君藥,為全方主攻的方向,使濕濁去、瘀血除。萆薢為臣,增強土茯苓祛濕利關節之功。當歸為佐,既佐助川芎活血止痛,又佐制其化瘀太過耗傷血液。川牛膝為使,引火下行,使濕濁從小便去,其還能補肝腎強骨骼,緩解腰膝疼痛癥狀。全方以攻邪為主、兼顧扶正,驅邪不傷正、扶正不戀邪,共奏泄濕濁祛瘀血之功。研究表明,土茯苓中落新婦苷成分發揮抗炎鎮痛、降尿酸、利尿等多種藥理作用,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腎臟前負荷,保護腎功能[14]。LI等[15]研究發現,川芎嗪具有廣泛的抗血小板活性、增加腎臟灌注量的作用,其可能與抑制蛋白激酶B信號通路有一定的關系。萆薢及川牛膝主要化學成分為皂苷類,具有抗炎、護腎、調脂、抑制脂質過氧化、抗凝等多種作用[16-17]。當歸具有抗炎、調節血液黏稠度、抗血栓形成等作用,能降低炎癥細胞中組織胺、5-羥色胺、前列腺素E2等水平,從而減輕腎臟血管炎性反應,保護腎小管[18]。
綜上所述,泄濁祛瘀方聯合非布司他治療濕濁瘀阻型痛風性腎病療效顯著,能明顯改善患者血肌酐、尿素氮等腎臟相關指標,且不良反應發生率較低,用藥安全性較好。本研究存在樣本量小、隨訪時間短、用藥單一等問題,尚需進一步擴大研究,以探討中西醫結合治療痛風性腎病的臨床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