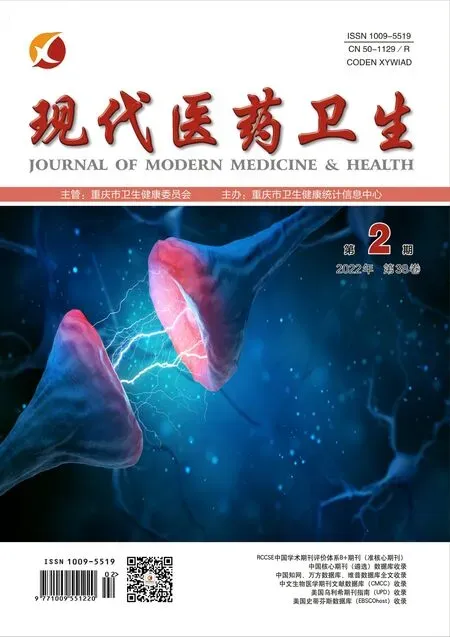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相關肝損傷研究進展
胡亞秋 綜述,蔡大川 審校
(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感染病科,重慶 401336)
腫瘤免疫治療是指通過重新啟動并維持腫瘤-免疫循環,恢復機體正常的抗腫瘤免疫反應。腫瘤免疫治療并不直接作用于腫瘤細胞或組織本身,而是通過調解機體免疫系統來達到抗腫瘤目的,包括單克隆抗體類免疫檢查點抑制劑(ICIs)、治療性抗體、癌癥疫苗、細胞治療和小分子抑制劑等。
免疫檢查點存在于T細胞表面,起著分子開關的作用,共刺激信號和共抑制信號之間的平衡決定了細胞毒性T細胞的激活和免疫應答的強度,可促進或抑制免疫系統對腫瘤細胞等威脅的反應。近年來,備受關注的ICIs主要有細胞毒性T淋巴細胞相關抗原4(CTLA-4)抑制劑和程序性細胞死亡蛋白1(PD-1)及其配體1(PD-L1)抑制劑。這些抗體已證實對黑色素瘤、腎細胞癌、非小細胞肺癌、頭頸部腫瘤、霍奇金淋巴瘤和肝細胞肝癌等多種類型腫瘤有效。然而,諸多臨床試驗報道了運用ICIs治療的腫瘤患者發生了免疫相關不良事件(irAEs)[1]。irAEs可發生在全身各個組織系統中,其中ICIs相關肝損傷引起了世界范圍內肝病專家的重視,但是ICIs引起的免疫介導型肝炎(IMH)的定義在臨床試驗和產品標簽上并未統一。本文就ICIs相關肝損傷在臨床表現、發病機制、病理組織學特點和管理策略等方面的研究進展進行綜述。
1 ICIs相關肝損傷流行病學特點及發生機制
IMH較為常見,發生率為2%~30%,但嚴重的肝臟毒性在臨床上較罕見,致死性的肝臟毒性發生率小于1%。目前,IMH發生機制仍處于探索階段。研究者普遍認為,ICIs所致不良事件的發生與其作用機制密切相關。免疫檢查點作為免疫應答中的“分子剎車”,維持著免疫系統穩態,使用ICIs后的免疫系統被非特異性激活,通過T細胞、抗原、細胞因子這三要素介導對正常組織的損傷。ICIs可誘導T細胞高度活化,不僅產生了針對腫瘤抗原的特異性應答,而且造成了正常組織的損傷。此外,CD8+陽性T細胞介導細胞裂解,新抗原、腫瘤抗原和正常組織中的自身抗原釋放(抗原表位播散)可引起T細胞分化、自身免疫耐受降低,活化的CD4+T細胞最終可分化為Th1和Th17淋巴細胞,刺激前炎癥細胞因子如干擾素和白細胞介素-17的產生,導致自身組織損傷。
ICIs相關肝損傷的發生還可能與肝臟組織中PD-L1的表達有關。腫瘤細胞表達的PD-L1與T細胞表面的PD-1結合后可抑制T細胞功能。當腫瘤患者使用ICIs后,腫瘤細胞和肝臟枯否細胞及肝竇內皮細胞表面表達的PD-L1被拮抗,T細胞被非特異性激活,同時對腫瘤及肝臟組織產生破壞。從代謝途徑上看,ICIs系完全人源性單克隆抗體,屬于大分子物質,不能經腎臟過濾,也不經過細胞色素P450或其他藥物代謝途徑[2]。目前尚無研究總結包括納武單抗在內的ICIs的代謝特點,推測其與內源性免疫球蛋白G相似,在細胞內由溶酶體酶水解,最終代謝為小分子肽和氨基酸,因此其代謝途徑及終產物與ICIs所致肝損傷的發生無明確關系。
2 ICIs相關肝損傷的臨床特點
2.1臨床表現 IMH大多表現為無癥狀的谷丙轉氨酶(ALT)和谷草轉氨酶(AST)水平升高,單獨的血清總膽紅素水平升高十分少見,但也可發生在ALT或AST水平持續升高之后。根據患者血清AST/ALT水平可將肝損傷分為5個等級:(1)1級肝損傷:AST/ALT升高,小于正常值上限3倍;血清總膽紅素水平升高,小于正常值上限1.5倍。(2)2級肝損傷:AST/ALT升高,為正常值上限的3~5倍;血清總膽紅素水平升高,為正常值上限1.5~3倍。(3)3級肝損傷:AST/ALT升高,為正常值上限的5~20倍;血清總膽紅素升高,為正常值上限3~10倍。(4)4級肝損傷:AST/ALT升高,超過正常值上限20倍;血清總膽紅素升高,為正常值上限10倍。(5)5級肝損傷:致死性肝損傷[3]。
GUO等[4]的一項囊括17項臨床試驗的薈萃分析結果顯示,使用CTLA-4抑制劑引起的所有級別的肝臟毒性的OR值為1.24(95%CI:0.75~0.25,P=0.39),引起的高級別肝臟毒性的OR值為1.93(95%CI:0.84~4.44,P=0.12);而PD-1抑制劑引起的所有級別的肝臟毒性的OR值為1.52(95%CI:1.24~1.86,P<0.01),高級別肝臟毒性相應的OR值為0.48(95%CI:0.29~0.80,P=0.05)。提示CTLA-4抑制劑所引起的所有級別和高級別的肝損傷發生率比PD-1抑制劑高,其可能與兩種信號分子在免疫應答中發揮作用的階段不同有關。T細胞表面的CTLA-4分子與抗原遞呈細胞表面的B7結合,削弱免疫應答起始階段T細胞的活化;相反,PD-1分子是在免疫應答后續階段與周圍組織細胞表面的PD-L1分子結合從而抑制T細胞功能[5]。二者在免疫應答的“總路”和“支路”發揮作用,因此相應抑制劑所引起的肝損傷發生率有所不同。
2.2發生時間 ICIs相關肝損傷可發生在接受治療后的任意時間點,絕大部分發生在開始用藥后的6~12周[6]。CTLA-4抑制劑相關肝損傷發生的中位時間為9.9周,PD-1抑制劑相關肝損傷則為14.1周,聯合用藥時肝損傷明顯提前2.9周[7]。
2.3損傷類型 在臨床試驗中,絕大多數肝損傷患者表現為肝細胞損傷型。梅奧診所的一系列報告描述了17例運用ICIs治療黑色素瘤后出現急性肝臟毒性的患者,其中76%的患者表現為肝細胞損傷型,24%表現為膽汁淤積型[8]。值得注意的是,法國大型腫瘤中心開展的一項回顧性觀察性研究發現,在303例接受ICIs治療的患者中,60%的肝損傷患者表現為膽汁淤積型肝損傷,其余30%表現為肝細胞型肝損傷,10%表現為混合型肝損傷[9]。這一結果與其他研究結果相去甚遠,其可能原因為該研究中心納入的患者均為3~4級肝損傷,其肝損傷嚴重,肝細胞攝取、處理和排泄膽紅素的能力嚴重下降,因此出現膽汁淤積的風險增加。除此之外,英國劍橋大學的DOHERTY等[10]報道了罕見的嚴重類固醇抵抗、PD-1誘導的膽管損傷所致的肝臟毒性事件,3例癌癥患者在使用帕博利珠單抗或納武單抗后出現了黃疸、肝功能紊亂甚至急性肝衰竭,其中1例患者因急性肝衰竭而死亡,3例患者肝臟病理活檢示損傷主要發生于膽管,包括不同程度的膽管損傷、膽管減少,甚至膽管缺失綜合征。
另外,JACLYN等[11]報道了1例罕見的肝結節再生性增生(NRH)病例,該男性患者(35歲)患有黑色素瘤,既往無自身免疫性疾病和肝臟相關病史,在接受帕博利珠單抗治療3周后出現全身水腫和腹腔積液。NRH是一種罕見的肝臟良性病變,肝實質出現彌漫性再生結節,造成門脈高壓(16 mm Hg),肝臟穿刺病理活檢僅顯示肝竇輕微擴張充血,并未提示顯著的小葉型或門脈炎癥及纖維化。
2.4影響因素 患者的基礎肝病是否影響IMH的發生值得探究。日本的一項薈萃分析顯示,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病(NAFLD)的腫瘤患者發生PD-1抑制劑相關肝損傷的概率遠高于未合并NAFLD的腫瘤患者,而合并其他慢性肝病的患者發生PD-1抑制劑相關肝損傷的概率與未合并其他慢性肝病的患者無明顯差異,因此認為NAFLD是PD-1抑制劑相關肝損傷的潛在危險因素[12]。有研究在原發性肝細胞肝癌患者中評估納武單抗的安全性和療效,結果顯示,在劑量-爬坡階段分別有10例(21%)和7例(15%)患者出現血清AST/ALT升高(所有級別的轉氨酶水平升高),與文獻普遍報道的所有級別肝損傷發生率無明顯差異,并且在合并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合并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無嗜肝病毒感染的隊列間評估病毒因素對肝損傷的影響時無陽性結果[13]。
ICIs的類型也影響肝損傷的發生。CTLA-4抑制劑所引起的所有級別肝損傷發生率為3%~9%[14],而PD-1抑制劑所引起的所有級別肝損傷率為1%~3%,3~4級肝損傷更罕見[15-16]。當兩種類型的ICIs聯合應用時,ALT水平升高的發生率接近11%~20%,3~4級肝損傷發生率升高到了11%[17]。MILLER等[18]回顧性分析了自2010年到2018年的5 762例接受ICIs治療患者,其中100例患者發生了肝臟毒性,CTLA-4抑制劑與PD-1/PD-L1抑制劑聯合治療患者肝臟毒性發生率高達9.2%,而采用CTLA-4抑制劑、PD-1/PD-L1抑制劑單藥治療時的發生率僅為1.7%、1.1%(P<0.001)。
當有一個或多個非肝臟的免疫相關損傷發生時,肝損傷的風險隨之升高,最常見的組合為皮膚損傷合并肝損傷(18.3%)[19]。另外,當惡性腫瘤出現肝臟轉移時,浸潤的腫瘤細胞促進肝臟自身抗原、壞死前細胞因子的表達,或激活炎癥途徑,從而導致嚴重的肝細胞損傷[20]。
3 ICIs相關肝損傷的病理組織學特點
腫瘤免疫治療介導的肝炎在組織學表現上與自身免疫性肝炎(AIH)具有一定的共性,但與AIH的差異更為明顯[21],且不同類型的ICIs引起的肝臟毒性在病理組織學表現上也不盡相同。
AIH除了在血清學上有特征性的標志物,如抗核抗體、平滑肌抗體、γ-球蛋白,其組織病理學以界板性肝炎為主[22],有時可見炎細胞和塌陷網狀支架包繞肝細胞形成“玫瑰花結”。病情嚴重者可出現肝臟的纖維化甚至肝硬化,浸潤細胞主要是漿細胞,伴有CD8+和CD4+淋巴細胞浸潤。除輕型炎癥外,幾乎所有AIH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纖維化,若疾病未得到控制,還可發展為肝硬化。PD-1抑制劑所引起的肝實質損傷主要表現為小葉型肝炎伴輕度門脈區浸潤[23],44%的患者可出現門脈區纖維化,同時伴有組織細胞、CD8+和CD4+淋巴細胞浸潤。此外,50%以上的患者會出現肝細胞片狀壞死、嗜酸性小體(不含纖維蛋白的微小肉芽腫)及膽管損傷,個別患者會出現肝外膽管擴張[24],部分患者伴有脂肪變性或脂肪性肝炎。
CTLA-4抑制劑相關肝損傷比PD-1抑制劑更為嚴重[22],出現的時間也較早[25],患者病理結果表現為全小葉肝炎、肉芽腫性肝炎。浸潤的組織細胞主要分布在肝竇中,淋巴細胞浸潤以CD8+淋巴細胞為主伴散在分布的中性粒細胞。巨噬細胞與纖維蛋白沉積所構成的微小肉芽腫是其特征性表現,部分患者伴有中央靜脈和門靜脈的內皮炎癥。CTLA-4抗體與PD-1抗體聯用時,其病理學結果更為典型,表現為伴有嚴重中央小葉壞死的肉芽腫性肝炎,在臨床上應引起高度重視。
4 ICIs相關肝損傷的管理
4.1診斷與監測 由于大多數患者在臨床上表現為無癥狀的轉氨酶水平升高,在初次給藥后的8~12周內應每4周監測肝生化學指標,若出現了轉氨酶或膽紅素水平的改變,臨床工作者應警惕ICIs相關肝損傷的發生,并根據通用不良事件術語標準(CTCAE)對肝損傷進行分級。
免疫介導型肝炎的診斷具有挑戰性,尤其對同時接受其他藥物治療、合并其他慢性肝病、原發性肝癌或肝臟轉移性腫瘤的患者,應排除其他可能引起肝功能異常的因素。當患者合并慢性病毒性肝炎等基礎疾病且基線肝功能異常時,通常難以辨別是否有免疫相關的肝損傷,因此,作為“金標準”的肝臟穿刺活檢可進一步明確肝損傷的原因及損傷程度,有助于指導治療。
4.2治療與難點 免疫相關不良反應的管理都應該建立在CTCAE分級上,其核心就是停用ICIs[26]和免疫抑制治療。美國胃腸學會最近更新的相關專家意見表示:1級肝損傷是最常見的,應該每1~2周監測患者肝功能,一旦出現肝臟情況惡化,需要重新評估肝損傷等級,重新制訂診療方案[27]。針對2級肝損傷,應暫停使用ICIs直到肝酶水平降低到1級以下;而針對有癥狀的2級肝損傷,可予以口服0.5~1.0 mg/(kg·d)的潑尼松。3級肝損傷患者應立即停藥,并口服或通過其他途徑接受劑量為1~2 mg/(kg·d)的甲潑尼龍治療。若使用類固醇激素3~5 d,患者肝功能未得到改善,可考慮使用二線的免疫調節藥物,如硫唑嘌呤、嗎替麥考酚酯。有研究指出,在暫時或永久停用ICIs后,3級肝損傷患者在不使用皮質類固醇的情況下,肝功能可自動恢復到正常水平。4級肝損傷患者應立即永久停用ICIs且住院治療,靜脈注射劑量為2 mg/(kg·d)的甲潑尼龍,并根據最初的反應進一步增加劑量。
針對類固醇激素和麥考酚酯難治性的患者,有學者建議將新型免疫抑制劑他克莫司或抗胸腺細胞球蛋白[28]作為三線治療方案。但是,長期使用皮質類固醇或免疫抑制劑會降低機體免疫功能,削弱免疫治療的療效,增加機會性感染的風險。部分合并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的患者甚至出現乙型肝炎病毒再激活。因此,免疫相關肝炎的管理,尤其是皮質類固醇和免疫抑制劑治療的適應證,需要進一步的對照研究。盡管及時停藥及使用皮質類固醇激素能有效治療ICIs引起的肝損傷,但使用皮質類固醇激素后再次行肝臟穿刺活檢時可發現,與初發病時比較,門脈區炎癥由1級進展到3級。另外,針對上文提及的膽汁淤積型肝損傷患者,類固醇和其他免疫抑制劑效果甚微。當出現影像學或病理組織學證實的膽管炎時,應立即使用熊去氧膽酸、消膽胺或脂溶性維生素。對于罕見的NRH患者,因為其肝臟結構發生了改變,因此只能通過經頸靜脈肝內門腔靜脈分流術來緩解門脈高壓。有研究者利用腫瘤移植的小鼠作模型開展研究時發現,在CTLA-4抑制劑和PD-1抑制劑聯合治療前,預防性使用腫瘤壞死因子(TNF)阻斷劑可以預防irAEs的發生[29]。目前驗證其安全性的一期臨床試驗(NCT03293784)也在進行中,但是TNF阻斷劑能否預防免疫相關肝損傷有待進一步探索。ICIs相關肝損傷患者在肝功能恢復后,是否可以繼續接受免疫治療也引起了關注。有文獻報道,重新接受相同的ICIs治療后,相同的irAEs復發率高達28.8%[30]。
5 小結與展望
隨著人類在抗腫瘤藥物上的不斷探索,以ICIs為基礎的抗腫瘤免疫治療方興未艾,其介導的irAEs特別是肝損傷值得關注。但是,目前仍有較多問題未得到解決:(1)ICIs治療所引起的肝損傷發病機制尚不完全清楚,其與除肝臟外其他組織器官發生的irAEs、AIH、藥物性肝損傷的發生機制有何異同?(2)國外許多臨床試驗排除了潛在慢性肝病患者,例如病毒性肝炎、酒精性肝病、NAFLD等,該類人群是否更易發生IMH,各個級別肝損傷發生率有無差別?(3)尤其是在亞洲地區,原發性肝癌往往有慢性乙型肝炎和肝硬化基礎,這類患者與其他腫瘤患者相比,IMH的發生率是否更高?IMH的治療是否更困難?(4)合并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患者發生IMH的風險是否更高?(5)類固醇激素治療3~4級肝損傷的同時是否影響腫瘤免疫應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