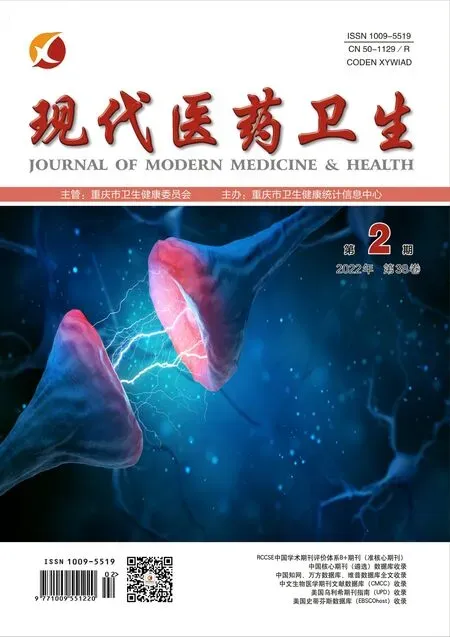經驗治療和診斷驅動治療在兒童ALL化療期IFD中的應用研究*
張亞停,方建培,王 健,李 楊,張莉紅,周敦華
(1.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兒科血液專科,廣東 廣州 510120;2.林芝市人民醫院兒科,西藏 林芝 860000)
兒童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ALL)化療過程中容易出現中性粒細胞缺乏伴發熱[1-2],也容易出現侵襲性真菌感染(IFD)。IFD是引起兒童ALL治療相關死亡的一個重要原因[3-6],因此控制IFD是白血病治療過程中最重要的目標之一。目前,已開展的IFD治療方法包括預防治療、經驗治療、診斷驅動治療和目標治療。由于IFD確診困難、病死率高,除在患兒出現中性粒細胞缺乏伴發熱時應用氟康唑預防IFD外,多采用經驗治療或診斷驅動治療。目前,國內有關經驗治療和診斷驅動治療在兒童ALL中性粒細胞缺乏伴發熱中的相關應用研究較少見。本研究分析了經驗治療或診斷驅動治療的臨床應用價值,旨在為兒童ALL化療期IFD的治療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回顧性分析2018年2月至2020年12月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兒科血液專科106例接受抗真菌治療的ALL患兒資料。所有患兒根據形態學、免疫學、細胞遺傳學和分子生物學分型確診,均有中性粒細胞缺乏伴發熱。根據治療方法分為經驗組(45例)和診斷組(61例)。本研究獲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
1.2方法
1.2.1治療方法 據患兒臨床特征、細胞免疫學與生物學特性對治療反應進行臨床危險度分型,并按華南地區兒童ALL治療協作組2016方案化療。該治療方案包括誘導緩解、鞏固、再誘導和維持治療,總療程2.0~2.5年。在患兒出現中性粒細胞缺乏伴發熱時進行血培養、血常規、C反應蛋白(CRP)、降鈣素原(PCT)檢測,以及血清1,3-β-D-葡聚糖抗原檢測(G試驗)和(或)血清半乳甘露聚糖檢測(GM試驗),并根據臨床表現和體征做鼻竇或胸部CT、腹部B超或CT等檢查。依據《中國中性粒細胞缺乏伴發熱患者抗菌藥物臨床應用指南(2016年版)》[1]、《中國血液病/惡性腫瘤患者侵襲性真菌病的診斷標準與治療原則(第六次修訂版)》[7],并結合本科室抗菌藥物應用經驗,應用亞胺培南或美羅培南進行抗感染治療。若2 d后仍發熱,且CRP及PCT水平明顯升高、臨床癥狀加重時加用替考拉寧;若無效或特別感染時,聯合或更換左氧氟沙星、替加環素、利奈唑胺等藥物。若應用這些藥物抗感染治療4 d仍發熱,或本來治療有效但3 d后再次出現發熱時,開始采用經驗治療。當患兒出現以下指征之一時采用診斷驅動治療:出現真菌感染臨床表現,鼻竇或肺部CT有真菌感染征象,皮膚黏膜有真菌感染證據,B超或腹部CT示肝脾膿腫等;G試驗和(或)GM試驗陽性。經驗治療和診斷驅動治療首選藥物為伏立康唑。伏立康唑具體用法為每次6 mg/kg,每12小時1次。抗真菌治療持續至臨床狀況穩定。伏立康唑無效時聯合或更換其他抗真菌藥物(兩性霉素B或卡泊芬凈)。治療過程中觀察患兒發熱情況、生命體征,并復查血常規、CRP、PCT等,跟蹤至治療后4周。
1.2.2觀察指標 觀察2組IFD發生率、病死率及發熱時間、用藥時間、不良反應、轉入小兒重癥監護室(PICU)情況,以及是否更換抗真菌藥物等。

2 結 果
2.12組一般情況比較 經驗組中,男28例,女17例;年齡1~14歲,平均(8.3±5.1)歲;誘導治療階段22例,鞏固治療階段5例,再誘導治療階段18例。診斷組中,男31例,女30例;年齡1~14歲,平均(8.5±4.9)歲;誘導治療階段33例,鞏固治療階段10例,再誘導治階段18例;開始治療時有臨床及影像學表現48例,G試驗和(或)GM試驗陽性13例。2組一般情況比較,差別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2組一般情況比較
2.22組IFD發生情況及轉入PICU情況 經驗組中,1例確診為IFD,血培養標本檢出念珠菌;診斷組中,9例確診為IFD,其中5例血培養標本檢出念珠菌,2例肺部病灶活檢檢出曲霉菌,1例肝臟組織活檢檢出曲霉菌,2例肺泡灌洗檢出肺孢子菌。診斷組IFD發生率大于經驗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經驗組中,IFD相關死亡1例(死于感染性休克);診斷組中,IFD相關死亡2例(1例死于感染性休克,1例死于肺出血)。2組IFD相關病死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經驗組中,轉入PICU 2例(均因重癥肺炎);診斷組中,轉入PICU 3例(2例因重癥肺炎,1例因感染性休克)。2組轉入PICU情況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2.32組抗真菌藥物應用情況比較 2組應用藥物之前發熱時間、藥物應用時間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2組更換藥物及不良反應發生情況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2組抗真菌藥物應用情況比較
3 討 論
隨著兒童ALL化療強度的增大,以及靶向藥物[8-9]及造血干細胞移植的應用[10],IFD發生率呈上升趨勢[11]。關于兒童ALL中性粒細胞缺乏伴發熱,IFD是其中最關鍵的因素之一[12],但IFD確診困難、病死率高[13],因此早期診斷IFD對兒童ALL的轉歸和預后比較重要。盡管G試驗、GM試驗、影像學檢查、聚合酶鏈式反應方法在IFD的診斷方面已經取得了很大進步[14-15],但仍存在很多挑戰。
目前,IFD有4種治療手段,分別是預防治療、經驗治療、診斷驅動治療和目標治療,臨床多采用前兩種治療手段[7,16-17]。(1)經驗治療:具有IFD危險因素患者在應用廣譜抗生素治療4~7 d后無效且持續出現不明原因的中性粒細胞缺乏發熱,或起初抗細菌有效但3~7 d后再次出現發熱時,給予抗真菌治療。經驗治療是以發熱為起點,不具備任何微生物學或影像學證據,目的是早期應用抗真菌藥物以降低IFD的病死率。一些有關兒童抗真菌的指南建議,若廣譜抗生素應用96 h后仍發熱,則應開始經驗治療[18]。由于經驗治療只是以發熱作為治療依據,特異度較低,有可能造成過度應用抗真菌藥物,并且一些抗真菌藥物和化療藥物一起使用時會增加化療藥物的不良反應,如三唑類會增加長春新堿的毒性。(2)診斷驅動治療:應用廣譜抗生素治療仍發熱,且具有IFD微生物學(如肺部CT出現曲霉菌感染相關影像學改變)或影像學(如GM試驗/G試驗陽性,非無菌部位或非無菌操作所獲得的標本真菌培養或鏡檢陽性)特征,但又不能達到確診或臨床診斷時給予抗真菌治療[7]。診斷驅動治療既能使患兒盡早應用抗真菌藥物以保證療效,又減少了抗真菌藥物的過度應用,但可能會存在啟動抗真菌藥物晚而影響抗真菌的效果[7]。經驗治療和診斷驅動治療各有優缺點,具體選擇依賴于患兒的危險因素及醫生的綜合判斷,但應用抗真菌藥物會增加治療費用和不良反應。YUAN等[19]研究發現,采用診斷驅動治療和經驗治療時,患者生存率類似,但前者持續時間比后者短,且費用比后者低。關于血液腫瘤患者經驗治療和診斷驅動治療費用對比的meta分析指出,診斷驅動治療比經驗治療的費用低,且不會增加患者病死率[20]。但以上多為成人血液病方面的研究。SANTOLAYA等[21]研究發現,診斷驅動治療和經驗治療同樣有效,其中診斷驅動治療可減少抗真菌治療費用。該研究是為數不多的有關兒童血液腫瘤經驗和診斷驅動治療的對比研究,盡管該研究認為,診斷驅動治療相對于經驗治療有一定優勢,但診斷驅動治療需要更多的診斷手段去支持。鄭珊珊等[22]研究發現,診斷組IFD發生率為27.5%(11/40)高于經驗組的7.1%(2/28),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2組IFD相關病死率分別為7.5%(3/40)和3.6(1/28),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提示診斷驅動治療和經驗治療均有助于早期抗真菌治療,應根據實際情況作恰當選擇。
本研究結果顯示,經驗組應用抗真菌藥物之前發熱時間短于診斷組,其原因是經驗組以單一發熱為治療依據,而診斷組要等待影像學表現及微生物學檢查結果。診斷組IFD發生率大于經驗組,其原因是診斷組要參考臨床及影像學表現、微生物學檢查結果等,開始抗真菌治療時間要晚于相對經驗組。診斷治療組應用抗真菌藥物時間短于經驗治療組,其原因是診斷驅動治療相對于經驗治療更有針對性,而且治療時間短相應的治療費用也會降低,這對降低兒童ALL治療總體費用有積極意義。
綜上所述。經驗治療和診斷驅動治療是治療兒童ALL化療期IFD的有效手段,在臨床中要根據患兒具體情況進行選擇。若患兒屬于低危IFD患兒,則可以采用診斷驅動治療以增加針對性,減少患兒總體治療費用。兩種治療方案的選擇還需要更多前瞻性研究來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