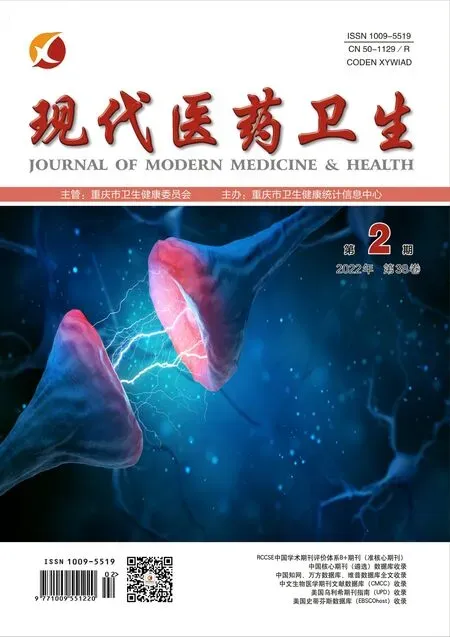穴位注射鼠神經生長因子聯合遠近配穴針刺法對GDD患兒的影響
孫 瑞
(周口市中心醫院兒童康復醫學科,河南 周口 466000)
全面性發育遲緩(GDD)是指5歲以下兒童在粗大運動、精細運動、語言、認知、日常活動能力等發育能區中,存在2個或2個以上的發育能區顯著落后于同齡兒童的神經發育障礙性疾病[1-2]。引起兒童GDD的因素有很多,常見的有遺傳因素(如甲狀腺功能低下、苯丙酮尿癥、遺傳代謝性腦病等)、產前因素(包括胚胎期藥物致畸、宮內營養不良、宮內感染等)、環境因素(如營養不良、食物中毒、環境污染等)[3-4]。GDD主要臨床表現為神經能力衰弱,運動和語言功能差,嚴重影響兒童正常成長和生活,會給家庭帶來巨大壓力。因此,尋求有效的治療方法來修復患兒神經功能,進一步提高其運動和語言功能是臨床醫學的重點和難點。相關研究表明,鼠神經生長因子具有保護和修復神經元的多重功能,通過穴位注射能夠補充GDD患兒的神經生長因子[5-6]。但由于腦部神經是所有組織器官中最難修復的,且修復周期較長,往往需要采用綜合措施進行修復。隨著中醫療法的逐步發展,遠近配穴針刺法等傳統中醫治療手段越來越受關注,該措施能夠通過刺激相應穴位及經絡,降低神經應激情況,改善神經功能[7]。本研究探討了穴位注射鼠神經生長因子聯合遠近配穴針刺法對GDD患兒的臨床療效。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取2017年1月至2019年1月本院接受治療的150例GDD患兒,隨機分為對照組和觀察組,各75例。納入標準:(1)臨床表現符合面性發育遲緩診斷標準[8];(2)腎臟、肝臟功能正常;(3)無重大腫瘤疾病;(4)患兒家屬自愿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1)腦腫瘤;(2)其他神經發育障礙性疾病,如腦性癱瘓、發育協調障礙等;(3)遺傳性代謝性疾病及染色體疾病;(4)難以配合治療。對照組中,男35例,女40例;平均年齡(2.91±1.32)歲;平均病程(16.58±5.01)個月。觀察組中,男38例,女37例;平均年齡(2.74±1.21)歲;平均病程(14.38±4.98)個月。2組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1.2.1治療方法 對照組注射鼠神經生長因子:取18 μg鼠神經生長因子(廈門北大之路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國藥準字:S20060052),加入2 mL生理鹽水混勻。選取患兒腎俞、頸夾脊及足三里3個穴位,充分消毒后緩慢注射藥物,每個穴位注射0.3~0.5 mL,注射后輕輕按壓針眼處,以防藥物外漏。觀察組在對照組基礎上聯合遠近配穴針刺法:局部選穴為太陽穴透率谷穴、頭臨泣穴透目窗穴,遠部選穴取雙側外關穴和中渚穴。患兒取臥位,以70%乙醇消毒穴位部與周邊及醫生手部,以1.5寸毫針斜刺太陽穴,快速進針至帽狀腱膜下,將針身傾斜與頭皮呈15°平刺至率谷穴,得氣后小幅度捻轉針身,頻率200 r/min,行針1 min后留針30 min,每10 min行捻轉手法1次,捻轉1 min。由頭臨泣穴透目窗穴采用直刺的手法將1.5寸毫針入外關穴、中渚穴,得氣后改為平補平瀉手法,頻率與捻轉次數同上。每天針刺1次,2周為1個療程,共治療3個療程。
1.2.2觀察指標 (1)神經功能:治療前后取患兒清晨靜脈血3~5 mL,采用雙抗夾心型酶聯免疫吸附法測定神經元特異性烯醇化酶(NSE)、髓磷脂堿性蛋白(MBP)水平。(2)運動功能:應用粗大運動功能評定量表(GMFM88)[9]和AIberta嬰兒運動量表(AIMS)[10]評估患兒運動功能,分數越高表示運動功能越強。(3)語言功能:應用S-S語言發育遲緩檢查法[11]評定患兒語言功能情況,患兒語言功能與S-S評分成正比。(4)睡眠質量和日常生活能力:采用匹茨堡睡眠質量指數量表(PSQI)[12]評估患兒睡眠質量,最低分為0分,最高分為21分,分數越低表示患者睡眠質量越好;采用Barthel指數(BI)評估患兒日常生活能力,分數越高表明患兒日常生活能力越強。
療效評價標準[10]:患兒能完成俯臥位重心轉移、前臂支撐、仰臥位手觸膝、上肢支撐坐、扶持坐、拉坐起及扶持站等動作則為顯效;患兒能基本完成俯臥位重心轉移、前臂支撐、仰臥位手觸膝、上肢支撐坐、扶持坐、拉坐起及扶持站等動作則為有效;患兒無法完成以上動作則為無效。總有效率=(有效例數+顯效例數)/總例數×100%。

2 結 果
2.12組NSE、MBP水平比較 2組治療前NSE、MBP水平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2組NSE、MBP水平低于治療前,且觀察組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2組NSE、MBP水平比較
2.22組GMFM88、AIMS評分比較 2組治療前GMFM88、AIMS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2組GMFM88、AIMS評分高于治療前,且觀察組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2組GMFM88、AIMS評分比較分)
2.32組S-S評分比較 2組治療前S-S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2組S-S評分高于治療前,且觀察組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2組S-S評分比較分)
2.42組PSQI、BI評分比較 2組治療前PSQI、BI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2組PSQI、BI評分高于治療前,且觀察組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表4 2組PSQI、BI評分比較分)
2.52組臨床療效比較 觀察組總有效率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5。

表5 2組臨床療效比較
3 討 論
兒童是家庭的希望和祖國的未來,其健康成長一直備受關注。近年來,隨著醫學水平的不斷提高,諸多醫療技術和藥物在治療某些疾病的同時,也會對嬰幼兒產生危害,引發一系列神經系統疾病[13-14]。GDD是一種臨床常見的兒童慢性神經系統疾病[15],主要表現為神經、語言和運動功能受損,以及學習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低下,會影響患兒的生活質量,嚴重時可導致患兒死亡[16-17]。因此,恢復GDD患兒神經功能,進一步改善其語言功能和運動功能是臨床治療的重要目標。
目前,康復訓練是調節神經系統和運動系統的主要手段,但其訓練周期較長、難度較大、訓練內容較復雜,再加上患兒行為認知能力和身體素質較差,大多數患兒無法完成該訓練,因此治療效果不是很理想[18]。鼠神經生長因子是從小鼠頜下腺中提取的一種生物活性蛋白,醫學研究表明其可以作為神經系統的保護劑和營養劑,在臨床上主要用于神經細胞的修復,改善神經疾病所引起的運動障礙[19-20]。但神經系統修復難度大、周期長,單一的治療手段很難達到較好的修復效果,臨床需要采用綜合措施以達到最佳治療效果。遠近配穴針刺法作為一種傳統的中醫療法,將近部穴位與遠部穴位配合使用,既體現了針灸取穴原則中“腧穴所在,主治所在”的局部取穴原理,也體現了“經脈所通,主治所及”的遠道取穴原理[21-22]。遠近配穴針刺法將遠近取穴與針刺法相結合,近處取穴以太陽穴為主,太陽穴屬腧穴之一,具有醒腦開竅、疏風解熱的功效;遠處取穴以外關穴為主,外關為少陽焦經絡穴,屬八脈交會穴之一,具有舒筋通脈的功效。而針刺法可通過對遠近穴位的物理刺激起到扶正祛邪、調和陰陽的作用,從而改善大腦皮層腦神經血液循環,刺激語言中樞神經細胞。因此,遠近配穴針刺法可促進神經系統的修復,進而對語言、肢體功能起到調節作用。
本研究結果顯示,觀察組臨床療效明顯高于對照組,2組治療后NSE和MBP水平均升高,且觀察組升高幅度更大。NSE主要存在于神經元和神經內分泌細胞之中,在顱腦受到損傷時會釋放[23]。MBP是一種含有多種氨基酸的強堿性膜蛋白,位于致密的髓鞘與髓核中,主要維持髓鞘結構和功能的穩定[24],當神經系統受損時,其分泌會增加。因此,NSE和MBP水平可反映神經系統損傷程度。本研究結果顯示,2組治療后GMFM88、AIMS、S-S、PSQI、BI評分均有所改善,且觀察組明顯優于對照組。提示穴位注射鼠神經生長因子聯合遠近配穴針刺法對患兒語言、運動功能具有一定調節作用,可顯著改善患兒睡眠質量,提高患兒日常生活能力。究其原因可能是鼠神經生長因子對神經系統具有一定修復作用,且加用遠近配穴針刺法可舒筋通脈,提高神經反射通路中各個運動神經元的興奮性,改善肌張力,進而促進患兒神經功能、語言功能和相關肢體功能的恢復。
綜上所述,穴位注射鼠神經生長因子聯合遠近配穴針刺法療效顯著,能明顯改善GDD患兒神經功能、運動功能、語言功能和睡眠質量,提高其日常生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