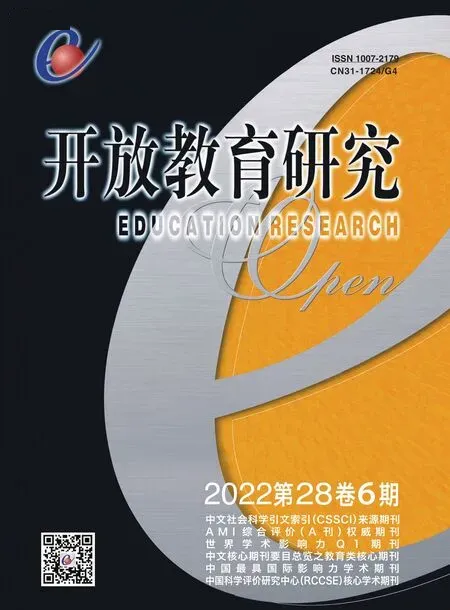質量與量化
眾告
開放大學的前身——廣播電視大學何時開始全面講求質量的,已經記不太清楚了。只曉得創辦初期,授課請名校師資,教材由強校編寫,教學媒體為衛星傳輸+廣播電視,正如當時教育部長所說“統一教材,統一播課,統一新生錄取標準,還有統一考試,從而保證了教學質量,效果很好”(蔣南翔,1980)。其中,“新生錄取”與“統一考試”涉及“入口”與“出口”,質量的把控的確不容小覷。再后來,隨著教育開放力度的加大,“寬進嚴出”逐漸成為我們辦學質量對外昭示的代名詞了。
記得曾任英國開放大學校長、時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助理總干事20年前在上海舉行的“世界開放大學校長會議”期間說過這么一些話,“一些大型遠程教育大學在建立之初,政府并沒有將其定位高質量的大學”。并舉例道,印度尼西亞特布卡開放大學的“建立是為了避免政治問題的發生。”韓國開放大學的建立是為了將其“作為國家面對信息技術革命的一項政策工具”(約翰·丹尼爾,2003)。可見支持并滿足國計民生也是高質量所在。
而英國開放大學自身卻有點不一樣,正如其創始人之一珍妮·李所說,“在這所大學開辦的第一刻起,就不應該在質量標準上有半點放松。”于是,它比拼牛津,追趕劍橋,雖然難以入流,但卻始終參加英國高等教育質量保證署(QAA)的系列評估與評審,盡管常顯疲態與失望。英國開放大學Sun教授曾經這樣表示,“有人說英國開放大學就像一個旋轉門,表面上每個人都可以進來,但是大多數人轉了一圈又出去了”(白濱,2012)。于是,“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就是英國開放大學最主要的產出就是無法完成學業的學生,有約65%的學生由于各種原因可能無法畢業”(奧蒙德·辛普森,2006)。可見,英國開放大學正是以這種英國式的“寬進嚴出”保證了其固有的質量。因此,我國開放大學如何確保應有的教育教學質量,實現中國式的“寬進嚴出”,從而成為“擦亮牌子”與“受人尊重”的大學(荊德剛,2021),此乃真正的當務之急!
說起質量,盡管其原本之意只是“有無”和“符合”,但實際上我們習慣于將其認知為“好壞”與“高低”。盡管其通常只是“積淀”與“建設”出來的,我們卻習慣于依靠“監測”與“保障”。如今,我們終于從遠程教育轉軌到開放教育,但“從社會大眾和政府部門到國外同行,都十分關注質量問題,都有期待,又有眾多不解和疑慮”(王一兵,2012)。因此,我們有責任也有義務,首先確立并宣示我們的“高等教育大眾化的質量觀”(潘懋元,2000)。這就需要我們正面回答開放大學的質量到底是什么?它與傳統大學質量的異同究竟在哪里?
其次,質量通常不是“擺設”和“修飾”,它實際上是一種文化,所以有“質量文化”一說(菲利浦·B·克勞士比,1979)。既然是文化,它就是一種現象,需要歷史的積淀和時代的滋潤。在開放大學,它作為各相關利益者的價值理念和行為方式所構成的集體人格,就是一種內心的涵養、狀態的反映、無需提醒的自覺和舉手投足的自信。倘若沒有健康的質量文化,那么我們平時所講的質量意識、質量標準、質量管理、質量保障乃至質量評估等等,都將是一句空話。
同時質量本身僅僅體現了“質性”或“質素”,因而難以直接度量,因此需要“量化”。當然,這個量化后的數量恐怕不只是我們常說的“大小”和“多少”,它作為與質量對應的固有屬性,真實反映了教育目標的實現、教育活動的狀態以及教育效益的增值等。比如,規模形態、條件結構、資源分布、利用效果、活動空間、呈現方式、交流互動、發展趨勢以及幸福感、滿意度等我們常常念叨的那些個大數據(劉振天,2022)。只不過以往我們相比較于“質”,對“量”的認識過于簡單和片面了,因而對質量與數量這對既矛盾又統一,既對立又轉化的雙重規定性認識不足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