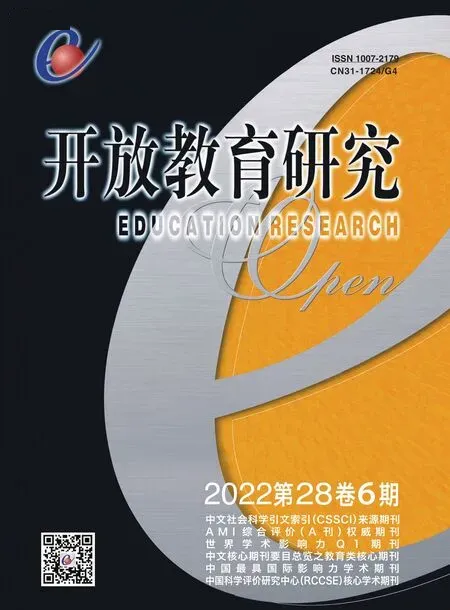在線協(xié)作知識建構的知識進化:內涵、本質與模型
蔣紀平 滿其峰 胡金艷 張義兵
(1. 南京師范大學 教育科學學院, 江蘇南京 210097;2. 河南科技學院 信息工程學院, 河南新鄉(xiāng)453003;3. 河南師范大學 教育學部, 河南新鄉(xiāng) 453007)
一、問題提出
知識經濟時代創(chuàng)新越來越受到關注,它已不是時代精英的特權,而成為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Drucker,1985)。在線協(xié)作知識建構是學習者在學習社區(qū)與其他學習者分享、共建與共創(chuàng)的社會性學習活動(Aalst,2009),學習者通過觀點的持續(xù)改進,不斷創(chuàng)造知識,形成社區(qū)公共知識(Scardamalia & Bereiter,1994),是一個動態(tài)發(fā)展的過程。但在線協(xié)作學習的知識進化在實踐中還存在一些問題:首先,它仍以個體為單元分析思維或知識的獲得。近年來,少數(shù)研究者開始從群體感知(李艷燕等,2021)、學習者的集體認知責任(殷常鴻,2021)、團隊創(chuàng)造力(Sawyer,2014)和小組內部成員的相互影響(馬志強等,2022)等方面開展研究,注重以集體為單位開展分析;其次,知識觀、進化論、生態(tài)學、自組織理論等難以直接應用于知識進化,使得在線協(xié)作知識建構的知識進化研究缺少相應的框架和理論指導,研究較零碎,知識進化的內涵、機制等不夠清晰,未形成體系;再次,知識進化過程分析僅采用測試、量表等進行結果性評價,且采用網(wǎng)絡分析方法構建的網(wǎng)絡結構是靜態(tài)的,需要更加關注學習者協(xié)作的動態(tài)演化過程和時間序列分析。
知識建構理論不同于容器隱喻下的獲得性學習,它強調成員間的對話和社區(qū)知識的創(chuàng)造,反對任務式的流程教學,提倡基于原則的靈活教學(Scardamalia & Bereiter,2002)。本研究從進化認識論的視角,剖析在線協(xié)作知識建構的知識進化內涵,以認識論、本體論和自組織方法論透視其進化過程和各要素的相互作用,并在此基礎上構建在線協(xié)作知識建構的知識進化理論模型,為學習過程中數(shù)據(jù)的獲取與分析提供理論指導,深入揭示知識種群的進化機理,推動在線協(xié)作學習理論與實踐的發(fā)展。
二、知識進化內涵
進化認識論最早由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唐納德·坎貝爾(Campbell,1960)提出,是由生物進化引發(fā)的一種哲學認識論,是進化論與認識論的結合。英國哲學家卡爾·波普爾(1972)首次將其應用于知識進化。
(一)進化單位
新達爾文主義和現(xiàn)代綜合進化論將種群看作選擇的單位(Gontier,2006)。奧卡薩(Okasha,2001)主張群體選擇,認為群體是選擇的單位,而不是個體。坎貝爾等(Campbell et al.,1989)從兩個層次解釋選擇機制,第一個層次是系統(tǒng)發(fā)育,即發(fā)生在祖先身上的自然選擇為現(xiàn)在的生物提供了一般智慧,使物種跨代適應;第二個層次是個體發(fā)育,如感知、試錯學習和科學探究等選擇機制縮短了個體的選擇時間,使一些適應在短時間內成為可能。
在線協(xié)作知識建構的知識進化不僅是個人學習的結果,更是社區(qū)成員之間相互激發(fā)、討論、主動尋求創(chuàng)新的結果,問題求解的過程也是新知識產生的過程。知識種群的進化建立在個體知識進化的基礎上,個體知識與種群知識的協(xié)同進化,團隊協(xié)作對知識進化起著重要作用。本研究在借鑒進化認識論的單位-種群的基礎上,結合社會心理學和社會建構主義等理論,將在線協(xié)作知識建構的知識進化基本單位確立為知識種群。
(二)進化機制
遺傳、變異和自然選擇構成了達爾文學說的主要思想。坎貝爾(Campbell,1960)試圖解釋知識增長的問題,提出了盲目變異和選擇性保留機制,將有機體適應外部環(huán)境提供存儲程序的任何過程都視為“知識”。西蒙頓(Simonton,1999)在坎貝爾的基礎上,提出了隨機變異與選擇性保留機制,認為知識創(chuàng)造還受到認知、人格特點和環(huán)境等因素的影響。波普爾(1972:121)認為問題解決是試錯的過程,他采用猜想和反駁的邏輯解釋知識和科學發(fā)現(xiàn),認為科學進步、人類和動物的試驗及學習都遵循自然選擇的進化過程,逐步消除那些被證偽的理論。科學知識進化的證偽主義簡化模式為P1→TT→EE→P2①,即它有多種試探性解決辦法——變種或突變,但只有一種排除錯誤方法。其他研究者關于認識的進化模型一般都有三個組成部分,遵循遺傳、變異和選擇的基本原理,具有譜系學的特征(Bradie,1986)。這三條原理組合起來,構成了進化的積累性選擇機制。在線協(xié)作知識建構的知識進化遵循上述三條基本原理,但又具有復雜的特性,呈現(xiàn)分裂、融合、突變、自我生長、死亡、復活等進化軌跡(蔣紀平等,2019)。
(三)進化特性
知識進化不是達爾文主義的遺傳變異,也不是拉馬克主義的獲得性遺傳,而是由生物進化引發(fā)的人的認識進化,更加重視人的主體性和創(chuàng)造性。知識進化中,知識主體帶有明確的方向性和目的性而主動適應環(huán)境,通過遺傳和變異等進化路徑,實現(xiàn)知識的創(chuàng)造。生物進化與知識進化的異同見表一。

表一 生物進化與知識進化的異同
進化認識論從人的實踐尤其是社會性理解認識結構和能力的發(fā)生發(fā)展,除了關注個體認識能力,還注重研究認識種系進化。理查德·道金斯(2018)認為,文化傳播的單位覓母(meme)②得到了復制,基因比環(huán)境更具有決定作用,這與生物進化有相同的譜系學原理,但知識變異與生物學變異相反,生物變異是隨意的,不能預見某個種群處于主導地位的選擇,種群只能等待,而知識變異的設計具有明確的方向和目的,科學家提出假說是為了解決問題。兩者最大的不同在于生物進化是由復制因子控制的,而人類是能夠自由選擇的,生物和大腦不只是運輸工具,還是互動的主體。福爾邁(1994)發(fā)現(xiàn),認識能力的個體發(fā)育、種系史的進化和科學認識史之間的聯(lián)系很少得到研究。知識的發(fā)展往往以意圖明確又合乎理性的要素為基礎,人的自由意志和理性都是生物進化和知識進化的結果,是基因與模因的復雜互動的累積結果(尤里斯·布斯克斯,2018)。
人類學習包含三種隱喻:獲得、參與(Sfard,1998)和知識創(chuàng)造(Paavola & Hakkarainen,2005)。知識創(chuàng)造隱喻認為人們不僅是知識的消費者,也是知識的創(chuàng)造者和建設者,強調社區(qū)成員通過對話生成概念制品(conceptual artifacts)的重要性,學習者要超越個體知識從而對集體知識的增長作出貢獻。進化認識論認為知識進化是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過程,尋找把小創(chuàng)造積累成大創(chuàng)造的機制,注重知識動態(tài)的發(fā)展與演化、變異與選擇的相互作用以及問題的生成過程(趙南元,1994)。在線協(xié)作知識建構不僅是多人通過小組進行學習,更是嵌入社區(qū)內成員相互作用、主動進行的知識創(chuàng)新,故在線協(xié)作知識建構的知識進化應是創(chuàng)造隱喻下的知識創(chuàng)造過程。
三、知識進化的本質
在線協(xié)作知識建構的知識進化反映了知識經濟時代知識觀的變革,本研究以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為透鏡,透視知識進化的本質。
(一)認識論視角:客觀知識的創(chuàng)造
波普爾(1972:109-114)提出了三個世界理論,分別是物理世界(世界1)、個人頭腦中的精神世界(世界2)和思想客體的世界(世界3)。世界3是人類智力活動的產物,是可以改進的,科學知識屬于第三世界。與承認世界1和世界2的笛卡爾二元論不同,波普爾特別強調世界3對人類文明的重要貢獻,因為它使人類具有非凡的想象能力,能夠與現(xiàn)成的或涌現(xiàn)的思想進行合作并采取行動,將其轉化為可行的解決方案和公認的解決問題的知識(Hong et al.,2016)。
工業(yè)時代重視個人天才的培養(yǎng),注重個體頭腦中的知識,即世界2知識。在此觀念指導下的在線學習主要集中探索認知信念與個體學習之間的關系(Ding et al.,2015),認為學習是從現(xiàn)有權威源獲取和積累知識,強調個人頭腦中世界2知識的變化,如在線平臺發(fā)帖中的“我在想”或“我知道”屬于“第二世界”。知識經濟時代則重視團隊協(xié)作,重視認知觀點與知識創(chuàng)造之間的關系。在此觀念指導下的在線協(xié)作知識建構注重將個體頭腦中的知識經過概念制品和團隊成員交互生成的社區(qū)公共知識,注重知識從世界2向世界3轉變,即世界3知識的增長(Bereiter,2002)。社會文化理論認為知識不是獲得的,而是在實踐中產生的,并體現(xiàn)在實踐工具中(Vygotsky,1981)。知識建構理論打破了個人頭腦中容器隱喻的心智模式,提出了以概念制品為中介的成員協(xié)作的設計模式,不斷抽象出理論并改進知識的狀態(tài),世界3的知識成為復制與重建的對象,成員一直在從事生產性工作,最終目的不是為了提升個人的心智,而是提升集體創(chuàng)造知識的能力(Bereiter,1994)。在線協(xié)作知識建構使知識創(chuàng)造從一種隱喻落地為一種實踐,知識進化也體現(xiàn)為世界3客觀知識的創(chuàng)造。
(二)本體論視角:集體知識的形成
根據(jù)知識的本體不同,知識創(chuàng)造可以分為不同的層面,如個體、團隊、組織和組織間(Agazarian,1992)。團隊雖然由個體組成,卻以整體的形式存在,學習的主體不再是個體而是團隊(桑新民,2004)。隨著社會心理學和社會建構主義等理論的傳播和信息技術的推進,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團隊協(xié)作對知識進化的作用。勒溫(Lewin,1951)的群體動力學理論和彼得·圣吉(1998)的團隊學習中系統(tǒng)思考都是以群體作為分析單元,認為團體是可以思考的,可以克服個人思想的局限,且個體貢獻與團體認知交織在一起(Stahl,2010)。集體知識的進化是知識創(chuàng)造功能和知識應用功能的協(xié)同增長的過程(Bell et al.,1996),認知共同體的形成為集體知識發(fā)展提供了動力基礎(Hakanson,2005),其成員不僅共享知識和技能,而且互動(Hendrik,2002)、協(xié)調和協(xié)同促進集體知識的進化(Bandura,2000),群體認知至關重要。另外,個人知識、小組知識和組織知識三個層面之間相互轉化,個人知識向組織知識轉變,組織知識反過來促進個人知識發(fā)展(West,2014),且集體知識的形成是主要目的,個人知識增長是副產品(張義兵,2018)。
基于此,在線協(xié)作學習文化中,成員不是被分配任務,也不是聚焦于完成項目或活動,而是共同承擔集體認知責任,自己制定目標和計劃,在公共社區(qū)貢獻自己的觀點,每個成員都平等地對話并持續(xù)改進觀點,在民主的文化中協(xié)同增長知識,形成集體知識(Scardamalia,2002)。故在線協(xié)作知識建構聚焦于集體知識的形成,知識進化體現(xiàn)為由傳統(tǒng)的個體知識掌握為主轉向以集體知識形成為主。
(三)方法論視角:自組織進化
在線協(xié)作知識建構是學習者相互協(xié)同工作,自主產生、自主演化,實現(xiàn)知識從簡單到復雜、從無序到有序、從低級到高級的演化過程(吳彤,2001),屬于自組織系統(tǒng)。協(xié)同學創(chuàng)始人哈肯(Haken,1976)認為競爭與協(xié)同是系統(tǒng)演化的動力,系統(tǒng)中諸子系統(tǒng)相互協(xié)調合作,集體行為協(xié)同是系統(tǒng)整體相關性的內在表現(xiàn)。在線協(xié)作知識建構的知識進化可以采用自組織理論進行分析。已有研究基于生態(tài)觀建構理論體系(Hutchins,1995),從組織生態(tài)學的角度關注組織種群演化的動態(tài)性(Hannan,1977),研究其結構變化、生態(tài)位爭奪與組織設立、死亡、合并的生命周期(Tuckman,1965)及自組織促使系統(tǒng)自我進化的協(xié)同增效等。
基于自組織理論的方法論,在線協(xié)作知識建構的知識進化包含三個過程:一是知識由混亂無序到有序狀態(tài)的演化,涉及組織起點和臨界;二是知識水平由低到高的過程演化,體現(xiàn)了知識的層級躍遷;三是在相同層級上由簡單到復雜,是知識復雜性增加的演化。自組織理論為在線協(xié)作知識建構提供了非線性、合作與競爭、協(xié)作行為漲落等有力支持(李海峰等,2019),為知識進化分析提供了理論支持。
四、知識進化模型
本研究在認識論、本體論和方法論的基礎上,構建在線協(xié)作知識建構知識種群進化的理論模型,深入揭示知識進化機制。
(一)本體論-認識論的知識進化模型
元利興等(2002)認為僅考慮認識論和本體論兩個維度是不完善的,知識創(chuàng)造的過程還發(fā)生在這兩個維度的交叉層面。個人的主觀知識經發(fā)表轉化為他人有可能接受的客觀知識,學習是在社會文化環(huán)境中個體性與社會性的統(tǒng)一(Vygotsky,1981)。貝萊特(Bereiter,2002)提出基于概念制品發(fā)展抽象知識,把它們當作研究和討論的對象進行批判和改進,最終形成社區(qū)知識。本研究根據(jù)知識轉化的方向,構建了從低層面知識轉化為高層面知識的前饋知識創(chuàng)造過程和從高層面知識轉化為低層面知識的反饋知識創(chuàng)造過程(見圖1、圖2)。在不同的學習過程中會呈現(xiàn)不同的路徑,知識生成和進化呈現(xiàn)群智協(xié)同、過程非線性等新特征(陳麗等,2019),且知識流動的廣度和強度與交互水平呈現(xiàn)一定的相關性(田浩等,2020)。

圖1 前饋知識創(chuàng)造過程

圖2 反饋知識創(chuàng)造過程
(二)基于自組織理論的知識種群進化模型
在本體論-認識論的知識進化基礎上,本研究采用自組織理論方法論分析知識進化過程,以知識種群為單位,建立其形成與發(fā)展、競爭與協(xié)同、自組織生態(tài)化模型,為后續(xù)相關研究提供理論依據(jù)。
1. 知識種群的形成
學生在學習平臺上發(fā)表的零散觀點通過對話(蔣紀平等,2021)和概念制品的生成(Bereiter,2002),經過分裂、融合、自我生長、消亡等進化路徑,發(fā)展成具有一定規(guī)模和穩(wěn)定結構的知識種群。知識種群不是知識個體的簡單加總,而是個體間相互作用的集合體。知識種群的形成具有一定的社會性,生態(tài)位重疊會使知識種群在生存所需的小生境中競爭,還會受到種群內觀點的數(shù)量、廣度與深度(Hong et al.,2015)、密度、死亡率、多樣性等的影響,呈現(xiàn)動態(tài)發(fā)展的特點(見圖3)。但競爭可以促進種群在現(xiàn)有生態(tài)空間中的生態(tài)位選擇和生態(tài)空間創(chuàng)新,促進知識的演化和創(chuàng)新。

圖3 知識種群的形成
2. 知識種群之間的競爭與協(xié)同
知識種群在不斷地動態(tài)發(fā)展,研究者需要分析相鄰知識種群之間的微觀變化,揭示網(wǎng)絡結構的動態(tài)演化規(guī)律;追蹤多個知識種群在時間序列上的變化,分析種群間的競爭方式(見圖4)。與生物學中的生態(tài)位爭奪相比,知識空間的協(xié)同作用更加明顯,異質觀點的相互啟發(fā)和知識點交叉帶來了知識種群的協(xié)同共生。因此,本研究在辨識觀點差異、分析知識種群在多個時間片上連續(xù)變化的基礎上,探究知識種群競爭與協(xié)同的演化事件,歸納得到吞并、共存、互利等進化機制。

圖4 知識種群之間的競爭與協(xié)同
3. 知識生態(tài)系統(tǒng)層面的自組織進化
知識進化是復雜網(wǎng)絡中知識的動態(tài)轉化過程,具有自組織特征。系統(tǒng)通過非平衡的結構實現(xiàn)知識種群之間的交互,各個要素相互作用、不斷轉換,個人經驗跨越了無數(shù)制度化境脈和社會小生境,知識結構發(fā)生改變,并導致整個知識種群產生一系列演變。與生物進化不同的是,在線協(xié)作知識建構的知識進化呈現(xiàn)更復雜的特點(見圖5)。例如,不同領域的知識可以打破生物學的生殖隔離進行融合,體現(xiàn)學科交叉性,觀點可能經歷萌芽、分裂、融合、變異、自我生長、消失、死亡等(蔣紀平等,2019)進化路徑;暫時死亡的觀點可以復活,產生新的活力等。因此,知識進化不是終結性的,而是進化到一定程度時,有前景的觀點可能會突現(xiàn)或涌現(xiàn)到更高層級,呈現(xiàn)知識的層級躍遷,不斷創(chuàng)造新知識。在時間序列上,知識進化出現(xiàn)從孕育萌芽到成長、成熟再到躍遷的生命周期,呈現(xiàn)一定的生成性和下一階段新的生長點(胡金艷等,2021)。在線協(xié)作知識建構的知識進化體現(xiàn)出一定的目的性與調節(jié)性,通過系統(tǒng)內各要素之間的制約與協(xié)調,從混亂狀態(tài)自發(fā)地進化成為有序的結構,由簡單的有序結構演化為復雜的有序結構,帶來系統(tǒng)的自我進化增效(孫志海,2004),反映了知識進化的自組織過程。

圖5 知識生態(tài)系統(tǒng)層面的自組織進化
五、展望與總結
在線協(xié)作知識建構的知識進化分析與模型構建為揭示知識進化的機制奠定了基礎。隨著第四研究范式的興起,教育數(shù)據(jù)挖掘和學習分析技術為學習數(shù)據(jù)的分析提供了技術與方法,為數(shù)據(jù)賦能、技術賦能知識進化指明方向。
首先,分析單元從個體轉向群體。知識結構更加注重通過一定的社會關系結合起來的共同活動的集體,研究者可應用社會網(wǎng)絡分析、社區(qū)發(fā)現(xiàn)、聚類等方法分析復雜網(wǎng)絡中的群體結構和內部動力學機制,挖掘個人、小組、社區(qū)等不同層面知識的形成與相互轉化機制。
其次,分析方法采用針對過程的時序分析。結果性數(shù)據(jù)分析(如前后測分析)已不能全面剖析知識的進化過程,要細致闡明學習發(fā)生的過程,需要應用微觀發(fā)生法,采集動態(tài)的過程性數(shù)據(jù),應用時序分析、滯后序列分析和動態(tài)社區(qū)演化等方法分析知識種群從形成到成熟再到躍遷的生命周期、進化軌跡、進化速率和發(fā)展趨勢,揭示知識進化的動態(tài)機制。
再次,分析內容注重知識的語義分析。在線協(xié)作平臺上的觀點一般體現(xiàn)在非結構化的文本和各種概念制品中,需要側重于反映內隱知識的語義分析。比如,知識建構對話分析器(knowledge building discourse explorer)和認知網(wǎng)絡分析(epistemic network analysis)打破了傳統(tǒng)社會網(wǎng)絡分析側重對群體交互的外顯行為分析,轉向利用關鍵詞和認知結構來構建網(wǎng)絡。另外,結合自然語言處理、機器學習、深度學習等技術,大規(guī)模自動化處理非結構化數(shù)據(jù)、挖掘知識創(chuàng)新性和集體知識的形成等,利用計算機自動識別和及時診斷學生的知識狀態(tài),為學生提供個性化報告,在知識進化的不同階段給學生推送適合的學習資源與學習伙伴,提升知識進化的效率和效果,推動知識經濟時代團隊協(xié)同創(chuàng)新的理論與實踐的深入發(fā)展。
綜上,本研究基于進化認識論,分析了在線協(xié)作知識建構的知識進化以種群為單位的知識創(chuàng)造內涵;從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視角透視在線協(xié)作知識建構的知識進化,揭示其客觀知識創(chuàng)造、集體知識形成的自組織進化本質;基于自組織方法論構建了在線協(xié)作知識建構的知識進化理論模型,搭建了知識種群形成與發(fā)展、競爭與協(xié)同、自組織生態(tài)化的分析框架。后續(xù)研究可以結合教育數(shù)據(jù)挖掘和學習分析,深入挖掘知識進化的群體協(xié)作、動態(tài)進化機制,提供知識進化的個性化報告。
[注釋]
① “P”表示問題,“TT”表示試探性解決方法,“EE”表示消除錯誤。
② 道金斯將人類文化的復制因子稱之為meme(覓母),也譯作模因,即作為一種文化傳播單位,類似于生物學的遺傳因子gene(基因)。參見[英]理查德·道金斯(2018). 自私的基因(40周年增訂版)[M]. 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