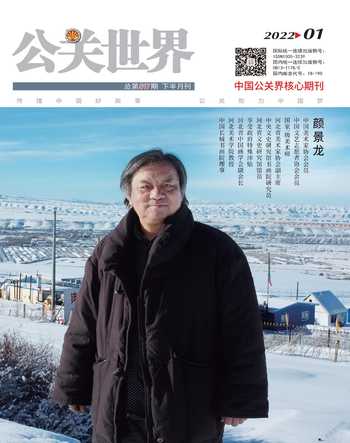鄉村治理體系:時代內涵、發展困境、推進路徑
李博士
摘要:為了全面落實、推進我國鄉村治理現代化建設再上新臺階,進一步夯實鄉村振興的基層基礎,必須堅持政治引領開創鄉村治理體系現代化新格局,必須堅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社會治理體系建設。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鄉村治理內生動力進一步增強,鄉村治理資源不斷下沉,鄉村社會持久、長期、全面穩定的制度基礎已經基本形成。盡管如此,通過對X縣調研走訪發現,我國農村鄉村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還處于一個“萌芽期”向“發展期”的轉化階段,鄉村治理方式整合程度依然亟需強化,構建三治合一的鄉村治理體系,成為實現鄉村善治的基本方法遵循。
關鍵詞:鄉村治理體系 自治 法治 德治 鄉村善治
一、引言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各級黨委政府帶領廣大人民群眾不斷探索和發展著具有中國特色的鄉村社會治理模式。尤其是黨的十九大以來,我國鄉村治理內生動力進一步增強,鄉村治理資源不斷下沉,鄉村社會持久、長期、全面穩定的制度基礎已經基本形成。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圍繞著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堅持基層探索和頂層設計良性互動,更加注重鄉村治理現代化建設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在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現代鄉村社會治理體制和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社會治理體系,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實現鄉村善治和鄉村社會持久、長期、全面穩定。為了進一步推進我國西北農村鄉村治理現代化建設,全面了解和研究其在鄉村治理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的階段性問題,本文以X縣為觀察視角,通過對X縣19個行政村調研走訪,形成160份有效調查問卷。嘗試以調查問卷和訪談記錄為基礎,對X縣鄉村治理現代化面臨的階段性問題進行初步探討。其中,男女比例方面,男性76人,占比47.5%,女性84人,占比52.5%;年齡比例方面,18-30歲,占比36.25%,30-60歲,占比59.38%,60歲以上,占比4.38%。問卷通過隨機抽樣的方式展開,共發放調查問卷180份,回收有效問卷160份,有效問卷比例為88.89%。
二、鄉村治理方式的整合程度亟需強化
在我國農村鄉村治理體系建設過程中,需要特別注意鄉村自治、法治、德治的相互作用。經過長期實踐探索,我國農村鄉村治理取得了顯著成效,但也存在法治建設不完善,德治功能不健全等狀況。目前,X縣鄉村治理正處于一個從“穩定”到“高質量”發展的歷史機遇期。無論是鄉村法治對自治的保障,還是鄉村德治對自治的引導,都是依托鄉村本土性生長力量來實現。實踐證明,鄉村治理方式整合程度越高,鄉村自治的基礎就越鞏固。
1.法治對鄉村自治保障的缺失
“法者,治之端也”。全面推進法治鄉村建設,是落實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促進全面深化農業現代化改革的重要保障,是維護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迫切需要。[ 1 ]目前X縣農村法治建設已經取得了初步成效,村民法治意識得到不斷增強,同時,鄉村法治建設對村民自治保障缺失依然存在,主要表現在:
第一,法治宣傳內容分散,法治文化本土性生長不足。黨的十八大以來,X縣法治宣傳路徑、載體不斷擴大,法治宣傳向基層下沉,群眾法治意識得到不斷提高。盡管如此,X縣法治宣傳依然存在宣傳內容分散,法治文化本土性生長不足的問題。問卷設置“您所在鄉村法治宣傳活動有哪些”,其中,87.5%的調查對象認為開展法治思想宣傳活動,83.13%的調查對象認為開展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宣傳,認為開展過憲法普法、民法典普法、網絡詐騙普法宣傳的占到60%左右,認為開展過盜竊、故意傷害等主題法治宣傳活動的只有57.5%。這意味著,X縣不同鄉村法治宣傳的重點不同,對于群眾法治需求重點把握不到位,宣傳內容相對分散。
第二,鄉村司法體系建設不完善,基層矛盾糾紛化解機制運行乏力。在以鄉鎮為中心的鄉村司法體系建設中,必須有效依靠村民自治,發揮村規民約、村民協商等傳統治理因素的積極調解作用,創新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不斷完善鄉村矛盾糾紛化解機制;必須暢通法治保障程序,實現基層矛盾糾紛調解與司法保障的有效銜接。問卷設置“您所在鄉村矛盾糾紛處理途徑有哪些”,基層群眾選擇村委會調解的最高,達到79.38%;其次是村民自我協商處理,達到70%,依靠村規民約處理的達到61.25%,而選擇專門矛盾糾紛組織調解的僅僅占到40%。這意味著,一方面,X縣基層群眾對傳統鄉村治理路徑依賴依然強烈,村民委員會作為鄉村治理主體的價值功能并未削弱;另一方面,X縣基層矛盾糾紛調解機制運行乏力,無論是自身組織建設,還是群眾信任支持,都略顯不足。此外,32.5%的人,選擇在調解失效時直接放棄,41.88%的人,選擇在調解失效時走法律程序。結合調研走訪發現,目前X縣基層矛盾糾紛調解機制體系建設不健全,部分鄉村尚未建立統一的糾紛調解組織,已經建立的調解組織結構功能單一,缺乏多層次調解程序以及與司法保障的銜接程序。具體來說,部分鄉村矛盾糾紛調解組織沒有將司法分流程序有效納入調解受理中,即按照村小組調解—村委會調解—村黨支部調解—專門矛盾糾紛調解組織調解—司法部門調解處理的程序實現矛盾糾紛案件的有效分流和司法銜接。
2.德治對鄉村自治引導的乏力
以德治村,具有潤物細無聲的強大感知力、影響力、凝聚力。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說:“鄉土社會秩序的維持,有很多方面和現代社會秩序的維持是不相同的。”[ 2 ]X縣鄉村治理很大程度上需要以德治教育引導村民重塑精神內核,不斷強化村民參與鄉村治理的認同感、責任感、歸屬感。
當前,我國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生產生活關系日益復雜化。在一個變遷很快的社會,傳統的效力是無法保證的。[ 3 ]首先,從德治教育主要內容和普及率來看,79.38%的人認為本村開展過愛國主義教育活動,71.88%的人認為本村開展過“三老”人員(老黨員、老干部、老勞模)模范教育活動,60%-70%的人認為開展過致富帶頭人講座、家庭美德教育主題活動、鄉村文明衛生主題教育活動等。可以看出,X縣鄉村德治教育活動開展相對集中,展現了德治教育的時代特征。同時,從德治教育的普及率來看,還有30%-40%人對德治教育活動開展情況較為陌生。這就意味著,X縣德治教育活動在宣傳、落實方面還有待進一步完善,德治教育普及率不足是導致其引導鄉村自治乏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其次,從德治教育的引導效果來看,關鍵在于能否有效防范、化解村級群眾矛盾糾紛。傳統村規民約作為鄉村德治資源的重要承載載體,本身就是鄉村傳統經驗、習慣的累積,在鄉村德治教育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通過調研走訪發現,X縣各村村規民約已經制定并積極實行,但部分村規民約的規定過于概括,同時缺乏對本村傳統文化的考察和挖掘,缺乏本土性,難以有效發揮傳統村規民約在鄉村德治教育中的積極作用。
三、著力構建政治引領的現代鄉村治理體系
黨的十九大提出:“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這為我國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提出:“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深刻闡述了全面堅持黨的領導開展鄉村治理的政治路線。至202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鄉村振興促進法》頒布,黨在鄉村治理體系方面的政策主張上升為法律規范,更加彰顯了“三治”合一的鄉村治理體系的重要價值和實踐意義。
1.堅持黨的政治引領力建設是根本保證
毫不動搖的堅持黨的政治引領力建設是建強農村基層黨組織的根本保證。“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旗幟鮮明講政治,是我們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根本要求。[ 4 ]只有不斷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對各類組織的政治引領力建設,才能發揮黨建引領鄉村治理的領導核心作用。《中國共產黨農村工作條例》第十九條指出:“加強農村黨的建設,以提升組織力為重點,突出政治功能”。政治屬性是政黨的第一屬性,政治領導力是政黨第一位的能力,[ 5 ]圍繞著新時代黨的建設的主線開展工作,必須把提高政治站位,把握政治方向,保持政治定力,樹立政治意識作為基層黨建的中心工作。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
2.構建三治合一的鄉村治理體系
隨著中國鄉村治理實踐的發展,“三治”合一的鄉村治理體系內涵進一步豐富,健全村黨組織領導的鄉村治理的有效實現形式,切實加強黨的政治引領功能建設是鄉村治理體系建設的題中之義。政治引領在國家治理中具有先導性、決定性、根本性作用。[ 6 ]要全面加強黨對農村工作的全面領導,實現鄉村治理現代化,要把政治引領落實到鄉村治理建設全過程,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治理制度機制優勢充分展現。同時,互聯網時代,科技創新性發展和應用前景進一步拓展,依靠科技支撐的鄉村治理效率顯著提升,“互聯網+”模式在鄉村治理現代化建設中的作用進一步凸顯。“智治”作為鄉村治理的實踐產物,其重要性不斷增強。作為考察鄉村治理體系的基本維度,政治引領、自治強基、德治教化、法治保障、智治支撐分別對應鄉村治理規范化、民主化、德教化、法治化、精細化,最終達到實現鄉村善治的目標。
【參 考 文 獻】
[1]劉儒.《鄉村善治之路:創新鄉村治理體系》.鄭州:中原出版社;北京:紅旗出版社,2019年11月,第137-142頁.
[2]費孝通.《鄉土中國》.成都:天地出版社,2020年,第80頁.
[3]費孝通.《鄉土中國》.成都:天地出版社,2020年,第84頁.
[4]趙樂際.《全面理解和準確把握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人民日報,2017 年,第004版,第3頁.
[5]趙樂際.《全面理解和準確把握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人民日報,2017 年,第004版,第2頁.
[6]求是.《“五治”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本方式》.求是網站:http://www.qstheory.cn/dukan/ qs/2020-02/01/c_1125497441.htm,2020-02-01.
(責任編輯:劉占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