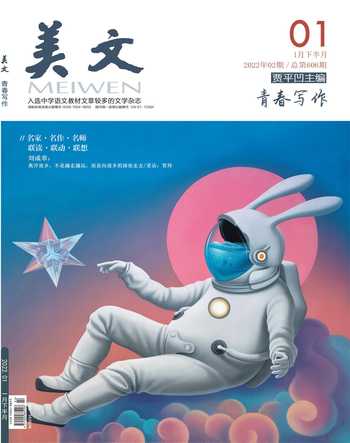鼓聲隆隆 心聲雄雄
孫曉娟
作為古老的一種民間鼓舞形式,安塞腰鼓是具備群體性、廣場性的一種藝術形式。20世紀80年代,導演陳凱歌、攝影張藝謀將它拍攝進了電影《黃土地》,臺灣電影人凌峰將它收進了紀錄片《八千里路云和月》。安塞腰鼓,不止是當地人歡愉的一種方式,還在第十一屆亞運會、香港回歸、國慶50和60周年慶典等大型活動、慶典上大放異彩,大受歡迎。
同樣受到極高贊譽的,是作家劉成章的同名散文《安塞腰鼓》。該文1986年10月3日發表于《人民日報》,隨后,入選《中國當代散文精華》和當代初中語文教材。
只有1000多字的文章,竟得到如此殊榮,實在是因為文本自身藝術成就甚高。
一、故土情深,地域感強
文章是從安塞腰鼓的表演者開始寫起的。“茂騰騰的后生”,作者用了典型的方言詞匯,來代表了他對表演者的最初定位。“后生”是陜北人對青年男子的稱呼,此詞一出,則鄉土感、親昵感頓出,拉近了作者與表演者、與讀者的距離。“茂騰騰”這個詞,給人一種蓬勃、向上、虎氣感的精神風貌,體現了劉成章作為延安人對青年們不經意間流露出的欣賞。“他們的身后”是高粱地。高粱地是典型的陜北風景,給了表演者極大的表演空間。要言之,安塞腰鼓的舞臺不是局促的斗室之內,而是古老厚重的黃土高原、無邊無垠的大天大地!這個舞臺,何其寬廣,何其豪邁!
作者用了一個來自《詩經》、來自民歌的典型手法“比興”,寫這群表演者,“樸實”地像“高粱”。這個樸實,一是來自表演者本身的血緣感,他們都是本地土生土長的陜北漢子,身材如高粱一般高挑,臉色如高粱一般康健;一是來自于他們的裝束。雖然原文中并未描寫他們的衣著,但有著陜北血統的人和觀看經驗的人知道,后生們必定是上衫下裳,頭裹羊肚子手巾,腳穿手工布鞋。唯有這種地域的樸實,才匹配得上,發自鼓槌、發自靈魂的吶喊。
打動我的還有這一句話,“它使你驚異于那農民衣著包裹著的軀體,那消化著紅豆角角老南瓜的軀體,居然可以釋放出那么奇偉磅礴的能量!”在我看來,這一句話,只有作為陜北人,才可以寫出來。一是陜北生活和詞匯,“紅豆角角”“老南瓜”,這是陜北人日常生活中最為熟悉的食物。二是鄉情視角,作者對于陜北鄉親的高度贊美,在他看來,平凡的農民身體之中或者說精神之中,本來就具有“奇偉磅礴的能量”。
“四野長著酸棗樹的山崖”,也是富有陜北特色的意象,很接地氣。
二、描述精彩,現場感強
欲揚先抑,這群后生,“神情沉穩而安靜”“腰鼓,呆呆地”,顯然是為了表演前的蓄勢。“但是:看!”作者用了一字一句,將表演的瞬間凝聚起來,將觀看者的視野限制起來,為腰鼓表演的鋪敘描寫,敲響了駭人視聽的第一槌!
“發狠了,忘情了,沒命了”,三個口語化的、排比的短句,概括了表演者投入、忘我、動情的表演姿勢與神態。“后生,如百十塊被強震不斷擊起的石頭,”這一個比喻句,寫出了表演者瞬間之內的上騰、跳躍、勁舞給人帶來的強烈震撼:陽剛、強健、粗獷、豪放!
隨后是五個比喻句組成的排比句:鼓點急促如驟雨,流蘇飛揚如旋風,腳步蹦跳如亂蛙,瞳仁閃射如火花,風姿強健如斗虎。這五個句子,是兩個層次,五個角度。前一個層次,一寫聽覺,鼓聲密集激烈;一寫視覺,流蘇飄逸飛舞。后一個層次,關注表演者三個細節,腳步靈活,眸光閃亮,身形矯健。這幾個點,抓得極為精準,工筆特寫,讓人如身臨其境、有參與觀賞之既視感。
三、聯想豐富、哲思感強
正當讀者讀到,空氣燥熱、陽光飛濺、世界亢奮之時,覺得表演即將達到高潮之際,作者卻宕開一筆,寫起了自己獨特的感受。
“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這既是寫表演現場,又是寫歷史幽思。安塞腰鼓如同其他軍鼓形式一樣,也來自于古代軍事活動,用以增強軍中士氣與傳遞軍事情報。殘陽戰旗,風嘶馬鳴,讓眼下的歡愉,多了幾分深沉與凝重。雷聲轟鳴、閃電千里,自是寫鼓聲之震耳欲聾震天動地,鼓聲之窈窕綿延威震四方。
“晦暗”與“明晰”是指鼓聲高亢與低沉不斷往復循環,既有樂理上的回環復沓,又有事理上的糾纏掙扎,最終突破重重束縛、羈絆、閉塞,整齊劃一、轟轟烈烈地怒吼、奔放與歡騰!
“掙脫了、沖破了、撞開了的那么一股勁!”這是說,安塞腰鼓帶給人的一種啟迪,一種精神!轟隆,轟隆,鼓聲陣陣;轟隆,轟隆,心聲隆隆。讀者會感覺到自己心底的什么力量油然而生,應和著這鼓聲,去突破、去探索、去開創!再關注表演者,后生們有力搏擊,生命力旺盛,使人熱血沸騰、激情澎湃。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作者由此深思和謳歌:“黃土高原啊,你生養了這些元氣淋漓的后生;也只有你,才能承受如此驚心動魄的搏擊!”“元氣淋漓”,這是一個多么美好而生動的表述!特別是當下,奶油膩歪、流量橫行,我們又是多么期待“元氣淋漓”的青年能夠熱情、蓬勃和昂揚!至此,作者也把個人與故土的關系厘清了,給本文增添了辯證思考的深度。
四、語言唯美,詩意感強
本文雖為散文,但意象之蘊藉、思維之凝練、語言之唯美,實在具備詩歌的特點。
一是修辭繁復、句式多變。文中多用比喻、排比、反復,形容準確、氣勢充沛。比如:“隆隆隆隆的豪壯的抒情,隆隆隆隆的嚴峻的思索,隆隆隆隆的犁尖翻起的雜著草根的土浪,隆隆隆隆的陣痛的發生和排解……”20個“隆”,一字兒地重復過來,真是在讀者的耳邊直接敲擊著牛皮鼓面,直擊心扉。短句居多,乃至一字一詞為一句,節奏緊湊鮮明,又間雜以長句,靈活多變。比如結尾部分:“交織!旋轉!凝聚!奔突!輻射!翻飛!升華!”一個詞就是一個句子,一個句子就是對鼓聲境界的高度評價,讓人有酣暢淋漓的痛快之感!
二是反復詠嘆、精心布局。劉成章早年寫詩,有深厚的語言功力,而內心深處和本文中始終有一股詩歌的內在旋律,這便是對故土的深情。比如:“好一個安塞腰鼓!”用直抒胸臆的方式,反復贊美和謳歌,線索一般,加深了對腰鼓發自內心的歡喜,也使文章結構有序、層次清楚。比如結尾部分,把大氣磅礴的腰鼓表演收束時,只以景作結,輕描淡寫,給人恍若隔世,大夢悠遠、余音裊裊之感。
整體上看,本文從立意、到抒情、到語言的淬煉,實在是值得反復欣賞和咀嚼,頓覺口齒生香、渾身得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