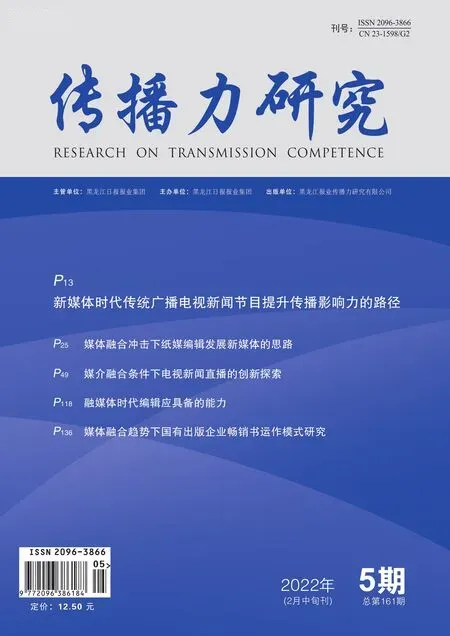試析故事元素在紀錄片中的應用策略
◎張 冰
(山東廣播電視臺,山東 濟南 250000)
一、前言
近年來,影視傳媒日益發展,其中發展態勢最為迅猛的是以網絡視頻為典型代表的新媒體正在一步步地走向成熟。影像傳播中最能以客觀事實為基準、真實記錄并且展示本質的方式當屬紀錄片。紀錄片的素材來源于生活,展示的都是客觀存在的人和事物,真實性是其基本特征;其無法替代的另一關鍵特征是故事元素。由約瑟夫·坎貝爾在他的著作《千面英雄》(1949)一書中提出的“英雄之旅”,確定了神話作品的一般敘事模式,好菜塢導演克里斯托弗·沃格勒將“英雄之旅”改為12個階段,“英雄之旅”已經被很多編劇采用,因為它能最有效地講述一個故事。它如同一個萬能公式,奠定了講故事的基本模型。比如,《北方的納努克》為什么可以流傳于世并持續播出讓觀眾至今懷念并且經久不衰,在當時的技術及一切設備都還不成熟的時候,它憑借其本身的最質樸、最真實的紀錄手法,為人們展示影片中以納努克為首的愛斯基摩人制造冰屋、捕獵、捉魚的場景。所以將故事元素有層次地加入到紀錄片中,無疑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故事元素與紀錄片的相輔相成,才得以將紀錄片創作的意義發揮到極致。
紀錄片《匠心晉韻》當中就著重加強了故事元素,由表及里,娓娓道來。從傳統非物質文化遺產山西磚雕出發,很容易讓人把注意力放在磚雕身上,在強調磚雕的同時也將手藝傳承人的故事線加入其中,強調人在影片當中的作用,喻人于物再喻物于人,有層次、有重點、有細節地將整個故事闡述出來。交代背景,介紹主人公,記錄真實生活,展現生活矛盾,揭露事物本質,這些都需要前期做大量的調研工作,要小組成員之間保持一致的思想進項策劃并分工,架構故事線,鏡頭有主有次,采訪過程中旁推側引,后期明確影片節奏點,在視頻剪接明確層次,將整個故事更好地展現出來也是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繼承和保護。通過紀錄片的表達反映文化的變遷和文明的精髓所在,讓這些優秀的文明借紀錄片之口,表達對世界的愛意和真誠,進而通過紀錄片這個媒介,使得更多人關注這些經久不衰的傳統文化。
在新媒體網絡充分發展的今天,研究這個課題有著深刻廣泛的現實意義。
二、紀錄片與故事元素的關系
(一)紀錄片中故事元素的由來與發展
一部優秀紀錄片的創作過程是繁雜而漫長的。在紀錄片發展的不成熟階段,學術界一直存在著兩種關于紀錄片的爭議:第一是紀錄片是客觀事實的展現,真實才是其根基與基礎。另一個聲音則是,紀錄片應該迎合大眾喜好,適應市場的需要,增加大量故事元素來保證它的觀賞性。關于兩者的比重問題,到目前為止,雖然沒有一個明確的定論,但不難發現,故事元素在紀錄片中的占比在逐步增加,紀錄片不再是單一的敘事,而是越來越故事化,這與大眾的審美取向密切相關。有人就有事件,一個完整的事件表達的就是一個故事。隨著紀錄片的發展與可看性的增強,紀錄片越來越強調人的作用,因為在紀錄片中,只有人才是所有故事產生的來源,是紀錄片中故事元素產生的地方,有了人這一元素的加入,風景紀實類紀錄片、動物紀實類紀錄片等多種類紀錄片,才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情味”和看點,這也在極大程度上增加和提高了整部影片的觀賞性與傳播價值。
(二)什么是紀錄片中的故事元素
首先,故事是對事物發展狀態和情況的一個描述,具有活躍性和銜接性的特點。我們說,由故事元素的貫穿組成了一個完整的故事,由點到面、由表到里組成。故事元素的產生有很多種方式,有的就地取材,有的參考歷史,也有的是由創作者主觀創造,等等。而紀錄片中的故事元素,是在真實的故事結構的基礎上,進行藝術加工的。在此,同樣可以引用“英雄之旅”的模式。正如許多故事,都有一個類似的模式。例如:有一個主人公去冒險,結交新朋友,遇到障礙,與壞人戰斗,回家后成為了一個改變的人。事實上,不論你是不是意識到,這樣的故事都有一個共同的敘事結構。以下是學者約瑟夫·坎貝爾在1949年提出的英雄之旅的三個階段:英雄離開普通世界;英雄冒險進入未知領域,并通過各種考驗和挑戰成為一個真正的勝利者;英雄凱旋。這每一個階段遇到的人或事件,都構成了我們故事的元素。
生活本身就是由矛和盾組成,有對抗、有沖突、有和解,但生活同樣是瑣碎的,所以紀錄片中的故事表達,只需要將這些矛盾點經過高度提煉和濃縮,重新排列和組合整理,最終呈現出來。
三、紀錄片中的故事化表達方式
紀錄片在制作的過程中,真實記錄的比例一定要大過情節的編排,這樣才能稱之為記錄,否則,過度的故事講述會扭曲紀錄片,使其成為一部故事片。必須在創作過程中恰當地表現故事,避免紀錄片因過度故事化而失去生活的真實感。
(一)基于真實的創作
在創作過程當中,把握事件的尺度、真實記錄才是紀錄片應遵循的原則。如果盲目地追求所謂的藝術效果和情感共鳴,加入大量故事元素用來提升氛圍,就會失去紀錄片本應具有的真實性。
所謂真實,每位受眾心中都有自己的定義,受眾有不同的審美觀,每個人的定義都是模糊的,如果創作者想一味地通過技術思維加上自己的審美來創造一種所謂的真實感是不現實的。真實感一直都是創作者用真實的方式展現出來的,需由觀眾自己判斷其真實性。
紀錄片《雨林深處的青春》展示了來自全國各地的三十多名大學生扎根海南鸚哥嶺熱帶雨林,為了科考以及環境保護,在惡劣環境中不斷與困難作戰的奮斗故事。在拍攝過程中,筆者尋找到了站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物,與他們近距離生活,時刻觀察他們的工作與生活習慣,并恰時地與他們交談。36歲的王偉峰,堅守深山12年,在雨林科考中被螞蝗咬、毒蛇襲擊、土蜂追剿,一次次“出生入死”,他始終保持那一顆不變的初心,當問起是否后悔時,他真誠地說“這已經是我的家了”;一位追隨男友而來的東北姑娘,從起初的不適應,到現在的習慣,再到發現新物種,她用堅守給自己交上了一份合格的青春答卷;從事檢測專業的劉季,在熱帶雨林找到了自己事業的同時,也收獲了自己的愛情。而對于初到大山的龍章巍,第一天進山就經歷了“山中高速”——一條僅容一輛摩托車經過的險崖峭壁,他感受到了命懸一線,也由一名“新兵”深刻地理解了科研的意義。黎族護林員符惠全說,“難的不是這里的路,而是在這里腳踏實地的研究。希望不久的將來自己可以成為鸚哥嶺的土行家。”附近的村民們說,這群大學生是雨林的保護神,而他們卻說,雨林才是他們的保護神。在艱苦環境中堅守的每一位年輕人,都經歷著各自的不易,但都因為熱愛迎難而上。在這檔紀錄片中,呈現的是一次四天三夜的科研考察為主線,在行走中記錄、在流動中拍攝,所呈現的效果細致、動人,充分展現了12年來這群年輕人的付出與努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長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擔當,節目以“青春是一場冒險”開篇,以“勇敢一次,不負青春”收尾,充滿了催人奮進的正能量,給人綿長的溫暖和深深的感動。
《匠心晉韻》創作過程中,并沒有對以韓永勝等老一輩磚雕師傅過多地夸張,過分地強調他們在整個行業的特殊性能及不可替代性,過分地強調和夸張會使觀眾失去判斷,把觀眾代入到你主觀想要特別展示給他們的東西,會讓影片顯得格外刻意。相反,應該記錄下他們的周圍環境,通過他們日常的生活習慣,讓觀眾從點滴中去了解。現在還有很多這樣別具匠心的手藝人,他們所做的事情,不僅僅是一生做好一件事,更是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和保護。通過紀錄片來反映文化的變遷和文明的精髓所在。讓這些優秀的文明通過紀錄片向世界表達它們的愛意和真誠,進而通過紀錄片這個媒介,使得更多人關注這些優秀的傳統文化。
(二)紀錄片中故事敘述的技巧
當確定要將故事元素集成到一部紀錄片后,就要確定怎樣去應用這些故事元素,如何讓作品達到可視化,如何完美地呈現故事中的矛盾元素,如何去構建角色以及如何將主人公日常生活中的瑣事簡化和凝練。
一是建構可塑性故事。紀錄片的籌備過程是一個非常漫長且枯燥的過程,彭輝執導的紀錄片《平衡》從1998年到2001年歷時三年時間才最終面世。由此可見,紀錄片的前期籌備過程是多么重要,特別是還要加入可塑的故事元素。紀錄片和故事片一樣,紀錄片也要有一條主線去拓展,但相比較故事片而言,紀錄片的故事線更加分散,所呈現出來的故事張力也沒有故事片那樣強烈。所以明確影片的主旨,明確要傳達的內容,以及如何利用現有的故事情節,在有限的空間內充分展現出脈絡尤為重要。這就需要在前期與主人公有大量的接觸,并對他有非常透徹的了解,而不是簡單地依靠口述,要在生活中真實地展現出來。
在籌備《匠心晉韻》過程中,確定選材與拍攝對象后,拍攝者用了大量的時間與被拍攝對象接觸,對磚雕及其博物館文化展開調查和學習,通過他們以及周圍人提供的故事素材,甄別和甄選出認為適合主題的、可塑性強的素材。片中所展出的磚雕,每一塊的背后都有不同的寓意和故事,且都具有極高的價值和繁雜的制作工藝,選擇幾個有代表性且操作性強的著重刻畫,目的是為了最終呈現出韓永勝與磚雕二者彼此成全的過程。
《匠心晉韻》中韓永勝一生以磚雕為生,秉承著“以搶救保護磚雕藝術品為己任,以弘揚傳承磚雕藝術品為使命”的宗旨,持之以恒地堅持做手工磚雕,并立志要將它傳承下去,創建博物館、義務傳承磚雕文化。眼看著磚雕由從前晉家大院必備到如今繁華快節奏的城市生活中因高樓拔地而起漸漸變成凋敝的狀態,似乎已經沒有了青磚紅瓦的一席之地的情況下,韓永勝是如何在這個過程中一直謀求創新的,其創新道路上的千難險阻就是重點刻畫和表現的。
二是強化細節。如何講好一個故事,如何走進故事本身,這需要加強表達手法,注重刻畫故事的細節,用細節去表現,用細節去鋪墊,用細節去過度,用細節去設置伏筆。當一個故事圍繞著主人公的變化而展開時,它就會形成一個堅實的基礎情節,但是只有這些還不夠,故事、人物和背景還需要有變化與細節的展示,這才能讓故事變得真實、深入人心。否則,影片只會以空洞的陳詞濫調或容易被遺忘的結局而告終。這樣有主有次的去表達,才能一改紀錄片本身帶給人的枯燥無聊的形象。
《匠心晉韻》中主人公韓永勝有一把學徒時用的刻刀,韓永勝在這漫長的歲月中如何堅守初心,從他手上的老繭也能看出一二。所以在多個片段中都有這個元素的出現。而不同磚雕的出現,也表示了每個時期的創作和想法的不同,從較為古老的板式到加入一些現代元素,在磚雕的故事線索中,強調最多的是傳承,這樣有新有舊的對比,傳承意味不言而喻。
(三)故事敘述要避免過于主觀
紀錄片在中國興蓬勃發展的過程中,一批文藝工作者就究竟紀錄片“是創造多一些還是創作多一些”展開過很激烈的討論,這也導致了當時中國市場上的紀錄片創作分為了兩個流派。筆者認為,過于極端地把紀錄片硬歸于哪一個流派,會阻礙紀錄片的發展。創作者不必為想要觀眾渲染出一個美麗景象而將自己的主觀色彩強加其中,從而忽略了其真實的元素。目前,我國紀錄片的發展道路任重道遠,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社會需求,紀錄片這些文化產品也是一樣的,自由但不野蠻地生長,才是目前紀錄片發展的正確方向。
人物紀錄片,自由就體現在人上。紀錄片的拍攝過程應該是在創作者對于主人公有充分的了解,并在前期做了大量調研后才逐步展開的。可以做適當的發散擴展,但如果盲目地要達到自己理想的效果而局限主人公太多,就會有大量刻意的痕跡,那最后呈現的作品就不是真正由主人公身上真實傳達出來的。
《匠心晉韻》在紀錄過程中,著重和主人公強調要忽略鏡頭存在,用自己最真實日常生活狀態去雕刻,去介紹。大量的素材累積后結合故事本身自然會有創作者想要的狀態呈現出來。在前期過分地編排和完成進度,反而會事倍功半,讓整部作品的節奏和線條模糊不清。
四、結語
綜上所述,本文重點闡述了故事元素在紀錄片中的應用策略。我們認為,在影片創作完成之后,對紀錄片中的故事線索會有新的認識,在紀錄片的故事創作中,創作者需要有一個信念,這個信念就是“真實”,真實性包括真人、真事以及真情實感,只有有了真實的底線,才能有真情實感的作品呈現出來,才能得到社會好的反饋與時間的考驗。匠人精神永不過時,這也是我們希望的愿景。為未來留下探尋來時路的鑰匙,是傳媒人的責任和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