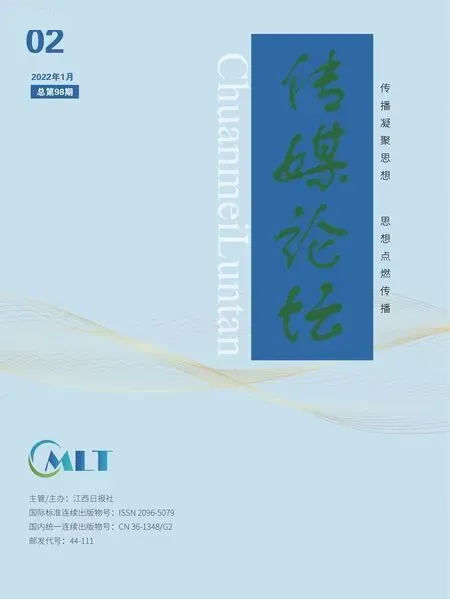互動儀式鏈視域下主流媒體融媒創新
——以《鄉村振興大擂臺》為例
吳樹娜
全面實施鄉村振興, 是黨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重大歷史任務。廣電媒體作為主流輿論陣地,承擔著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的使命,應不斷尋求創新突破,走進村居,為鄉村振興發出“強音”。單一的傳統功能電視已步入沒落,取而代之的是互聯網智能多屏時代。 新媒體的誕生打破時空限制,帶來多個場景的并存和融合,這種轉換完全顛覆了公眾話語的建構及其內容意義。在瞬息萬變的媒體環境下,廣電媒體要把鄉村振興故事講得更好,傳得更遠,勢必借助融媒渠道,通過互聯網思維驅動策劃創意,將宏大敘事轉化為通俗化、大眾化、青春話的語態,實現傳播力、引導力達到最大化。 本文借助美國社會學家柯林斯的互動儀式鏈理論,對主題綜藝直播互動展開研究,以期提高廣電媒體在融合轉型中的傳播效能。
一、互動儀式鏈下的主題綜藝直播融入
美國社會學家蘭德爾·柯林斯的互動儀式鏈理論是整合微觀和宏觀社會理論在當代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從愛彌兒·涂爾干的宗教儀式研究和以歐文·戈夫曼為代表的符號互動論中吸取靈感,柯林斯關注微觀場合中的人際互動,并把宏觀社會類型視為微觀互動的后果。[1]
在互聯網浪潮之下,電視節目愈發跳出傳統的大屏平臺,與小屏聯動創新,謀求更大范圍的傳播效力和破圈。移動端網絡直播形式的興起,為廣電節目創作提供了新角度。 據傳媒內參統計,2020年直播用戶從2016年的3.1億人增至5.26億。各大網絡平臺借勢推動“直播+”發展,其中涵蓋了影視、綜藝、興趣、競技類等內容,甚至瑣碎的生活場景也成為直播的內容之一。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詢)2021年4月調查數據顯示,在眾直播形態當中,受訪用戶對公益類“直播+”內容的滿意度最高。觀看文化科普、公益類內容的用戶占比接近四成。[2]可見,正能量精神更能獲得觀眾的青睞, 積極向上的價值觀呈現更能收到社會各界各領域的支持。一向對用戶流量有著敏銳觸角的綜藝市場也紛紛涉獵直播元素,使得觀眾獲得更好的體驗感和參與感。
從互動儀式鏈觀點看,直播形式與節目的嫁接會讓觀眾產生更多行為,構成多樣化的信息生產與傳播體系形成跨越時空邊界的互動儀式鏈。《鄉村振興大擂臺》為全國首檔鄉村振興主題綜藝節目, 通過打擂臺的方式,掀起廣東鄉村振興比拼熱浪,奏響南粵鄉村的田園牧歌。節目中的融媒生產與跨屏互動不斷豐富鄉村全媒體傳播體系,以全景式和沉浸感的直播植入滿足觀眾深度的感情體驗,提升鄉村振興宣傳與服務能力。第一屆節目中采取“直播助農”的方式打破傳統鄉村產業的柵欄和藩籬,整合資源渠道,為農村數字經濟發展提供動力。第二屆節目將融媒思維貫穿到底, 大膽創新 “探村直播”環節,深入到全省21個參賽鄉鎮,走訪了151個村莊,行駛了7.5萬多公里路程,拍攝素材達2200多小時,以網絡直播間作為媒介呈現田間美景, 進行即時動態的雙向互動。以下將聚焦《鄉村振興大擂臺》“探村直播”環節,剖析互動儀式鏈中“探村直播”的要素與結果。
二、“探村直播”的互動儀式鏈要素與結果
(一)“探村直播”互動儀式的構成要素
柯林斯引入情感社會學的概念, 拓展完善了戈夫曼互動儀式理論的框架,將情感能量看作儀式的核心機制,認為其流動和理性選擇催生了互動儀式鏈條的形成,并據此提出互動儀式的四個條件: 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聚集在同一場所;對局外人設定了界限;關注焦點是同一活動或對象;分享共同的情緒或情感體驗。[3]網絡直播平臺互動儀式的形成要素為:
1.虛擬空間的身體共在。
隨著網信事業的發展, 用戶社交的交互性得到了增強,柯林斯互動儀式理論所提到的“身體”在場已超越,新媒介讓觀眾從本土中解放出來,由“身體在場”轉換為“虛擬在場”。 實現了直播參與者在虛擬空間的共同在場。在《鄉村振興大擂臺》的“探村直播”中,身在異鄉的不同觀眾通過直播端口聚集在直播間這一虛擬空間, 廣東鄉村美景真實展現在觀眾面前。觀眾與主播一同“探村”,共享相同的時間,聯結起情感樞紐,形成虛擬共同在場際遇。
2.相互的關注焦點是互動儀式的重要構成要素。
人們對于共同關注的焦點事件會進行交流和互動,在這一過程中, 一旦產生情感共鳴便會催生更強烈的表達欲望,希望與同一群體中的成員共享情緒,在互動儀式中獲得情感體驗。[4]基于對主播和直播平臺的關注,聚合在“直播間”中隨著直播內容不斷轉變共同關注焦點。從評論區中觀眾發表的“好久沒回老家啦!想看看現在怎么樣了!!”“進來瞧瞧廣東周邊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到底什么村能代表江門參賽~好期待”等評論,可以看出直播間的觀眾都有著“鄉村發展”這一共同關注焦點。且廣東鄉村的全景式呈現使畫面中的村民、居住環境、農特產品等都成為受眾的“互動焦點”,觀眾通過文字、表情包等方式表達看法、抒發感情,推動互動儀式鏈的順利進行。而直播房間中的右上角的“關注”按鈕選項,則可以讓用戶對直播間產生持續關注,延長互動儀式,形成長期共同關注焦點。
3.對局外人的限制是柯林斯互動儀式鏈存在和形成的重要部分之一。
直播間是天然的界限,參與節目“探村直播”抽獎、評論、點贊等儀式互動都是需要用戶注冊賬號,完成身份認定,沒有注冊的人群則無法進入共同的情境,難以實現互動儀式。“房間” 內的用戶獲得了穩定的成員身份感。“房間”外的人自然被阻隔在外。
4.直播間中的共同情感。
情感凝結則是通過完成“聚合”共同在場的用戶,在直播房間評論、點贊等交互方式來形成。“探村主播”的角色不僅嵌入了自己對于廣東新農村的期待, 更融入了自己鄉土情結。而觀眾也實時進行自我呈現,回應主播流露出的情感,實現了感官上的在場確認與體驗。以第一期為例,肇慶探村主播走進“兩廣源流博物館”時,直播間的用戶評論“我去的時候,博物館還在建,沒想到建成了這么好看!”“我也想去逛逛”“居然還有一個這樣的博物館?!”等,主播在逛博物館的過程帶著自己的期許,同時也帶著觀眾的訴求。可見,“探村直播”的互動行為充分滿足了柯林斯互動儀式鏈情緒共享的構建基礎。
(二)“探村直播”互動儀式的結果
當互動儀式鏈的組成要素得到有效綜合,并積累到高程度的相互關注與情感共享時,會達到“個體的情感能量、代表群體的符號認可、群體的團結、道德感”結果體驗。[5]
1.直播中的情感能量產出。
虛擬空間的界限使得觀眾之間、觀眾與主播之間產生共振的磁場。 觀眾隨著主播的話語喚起對家鄉的集體回憶,包括居住環境、家鄉美食、童年趣事等。當“探村主播”聊起小時候最喜歡到田里抓螞蚱時,會引起直播間的評論:“美好的回憶啊!”“我也是”“想起家鄉的那片田好美”。 現場主播對于鄉村美好生活表達出來的情緒與語態、虛擬空間視聽呈現、觀眾用戶點評三者重構了回憶場鏡像,在兩個空間的銜接中喚醒集體記憶與情緒共振。
當被問及評論、點贊之后會有什么感覺的時候,許多用戶表示:“挺開心,主播回復了我的問題”“為自己的家鄉點贊,很自豪”。這說明用戶在互動過程中會產出能量,形成自我滿足式的感情。
2.直播中形成的群體符號。
以柯林斯“感情的俘虜”視角來看,在互動儀式中,參與者累積的情感能量在群體壓力下不斷重復, 在變成被動性和消沉性之前一直持續。[6]在雙方的互動中,信息內容被重新賦義,“一來一回”的互動大大提高了“主播”與“觀眾用戶”雙方的黏合度,且雙方的互動將演化為共享符號, 并形成情感能量和符號認可。《鄉村振興大擂臺》“探村直播”中,觀眾透過主播的視角,對廣東鄉村發展進行共同見證,并在見證過程體驗到欣喜與振奮之后,忍不住向其他用戶傾訴情感“鄉村變化太大了!”“現在的鄉村跟以前完全不同!”“這環境,比城市還宜居”。觀眾重復的聲音轉換為共同興奮,積累高度的情感能量,形成群體的情感共鳴并將之符號化。從而引發觀眾對鄉村發展變化的共鳴。觀眾更加切實地感受到鄉村振興帶來的新面貌,使公眾成為宏觀議題的參與者和見證者,在共享情感中,鄉村振興參與者的自我身份認同得以構建。
3.直播中群體團結的養成與歸屬感的獲得。
在節目剛啟動“探村直播”時,直播間都是新用戶,互動較少,彼此陌生。隨著“探村”系列的不斷更新,部分用戶成為忠實粉絲, 主播與用戶、及用戶之間關系逐漸拉近,彼此的互動次數增多。關注點即由分散到集中,群體成員的注意力會迅速集中到某一共同事件中。比如在陽江閘坡鎮的直播中,“探村主播”李靜雯帶著觀眾品嘗海鮮大餐,云游海邊,還當場教授觀眾們如何在拍出最靚的打卡照,讓觀眾仿佛身臨其境。
主播和直播房間在整個互動儀式中屬于群體團結的符號,成為用戶間的聯系紐帶,起到凝聚機制的作用。直播技術的使用不僅是喚醒了共同的記憶,而且也喚醒了“相遇的體驗及團結之情”。 以新媒介跨越其傳輸空間,使許多處于異地的個體聚集于直播間而獲得了“共同的體驗”,凝聚群體成員,讓成員獲得歸屬感,形成群體團結。
4.直播中道德感的建立。
在直播間中用戶個體對于維護群體團結有著清晰并且明確的態度。每當“探村”直播間中出現個別有針對性的惡評,或刷屏與直播內容無關的廣告,則會受到其他用戶的集體抨擊。 對于違反直播禮儀的用戶, 主播也擁有“禁言”和“踢出直播間”功能權利。所以在直播間中,無論是用戶、還是平臺和主播都會在互動中維護群體的團結,建立道德感。
三、主題綜藝融媒創新的啟示意義
新興媒介生態表明“邊走邊看邊播”和具有“臨場感”的移動視頻直播時代已經到來。對于移動視頻直播平臺這一新媒體應用而言,用戶黏性是其價值實現的重要要素之一。主題綜藝如何探索融媒路徑,以放大節目效果,關鍵同樣在于維持住現有的龐大用戶群、在吸引新用戶的同時留住老客戶。
(一)以小見大,“原生態”產生“零距離”
社交媒體時代新聞生產作為“傳者中心”的價值已被消解,我們必須回歸到“用戶中心”的實踐中去重新探索內容生產的規律和制約因素。[7]用戶參與網絡直播互動的情感需求較為復雜多元,不同的互動行為基于不用的情感動因。“網絡直播+綜藝”節目的突破口,是將網絡直播作為一種生產要素納入節目制作環節,對互動式傳播與單向式傳播、實時傳播與先錄后播加以區分,切實將網絡直播融入節目敘事結構之中, 從而保證節目創設的有效展開。[8]
直播拍攝實時性與“一鏡到底”的特點使得節目內容難以進行二度創作,無剪輯的內容呈現原生態和未知性,更能滿足“越來越求真”的觀眾胃口,吸引觀眾眼球。“探村直播”中出現的“懸念”真實自然的,帶給了觀眾很強的參與感,實現了節目與在線觀眾的“零距離”。此外,由于“探村直播”選題以小見大,內容精準直接,聚焦廣東美麗鄉村,以受眾需求為導向,提升受眾參與度,增強用戶持續關注意愿。
(二)直播會話交替充當有節奏的連帶
柯林斯指出, 有節奏合作與情感連帶是互動儀式的必備構成要素。[9]在主流媒體不斷提升傳播力和引導力的過程中,直播媒介敘事是其連接到人民群眾,并在人民群眾中傳播主流價值觀的有效路徑。[10]情感是人類社會的剛需和社交的根因,有溫度、陪伴式的內容因普適性等特征更易引發用戶關注和熱議,這一現象在自帶社交基因的直播間中更為明顯。直播間的信息交互相較于其他媒介平臺更具有實時性、互動性的本質,直播等互動模式的植入勢必使得電視節目中的的雙向即時互動增強,提高其傳播力,以擴充節目效果。
然而,為了讓傳播效果最大化,將觀眾用戶共通的情感推向高潮,主播在與觀眾用戶互動時需保持交談的話語交替,保證傳播者與接受者都處于共同節奏中。“探村直播”互動儀式鏈的成功構建,是因為主播在探村過程中站在群眾的角度去了解鄉村發展情況,且在與觀眾用戶交流中有意識地將某些話題拋給觀眾用戶發表評論,強化觀眾對于鄉村振興的情感表達,吸引觀眾聚精會神地參與其中。因此,通過直播互動過程中進行宏大敘事必須最大程度喚起情感和社會集群的團結性,并反饋到他們共同行動與相互的關注焦點之中。
(三)跨平臺聯動集聚情感能量
互動儀式中成功建立起情感協調的結果就是產生了團結感。[11]然而,觀眾對于節目情感狀態的延續則是需要保證傳播效果具有規模性和連續性。《鄉村振興大擂臺》除了讓直播陣地發揮社會價值之外,還通過融媒方式空間進行擴充,以實現可持續發揮。主播們用自己的社交帳號分享探村趣事,節目組將探村視頻通過碎片化的方式在各類媒體平臺發布,傳遞關鍵信息點,以親民的語態捕獲年輕群體,引導年輕人對鄉村振興議題的關注與了解。而播出時嵌入視頻相關信息二維碼,讓大屏觀眾有一個全新的觀看形式。 如此打開二次內容傳播渠道,持續為系列直播引流,與節目相關的議題通過多樣的新媒體互動形式被裂變式地放大,形成長尾效應,使得“探村直播”互動儀式中積聚的情感能量更為充沛持久。
四、結語
互聯網消解著電視媒體早些年來打造的傳播權威,將自媒體與權威媒體放在同一流量池中競爭,但在沖擊著廣電媒體生存空間的同時,也給了這些傳統媒體更廣闊的傳播空間。 一檔節目的傳播能否真正實現媒體融合,在制作前期就需結合融媒思維進行策劃,讓內容帶有跨屏屬性,捕捉年輕用戶的“痛點”與“趣點”,并從需求側出發進行形態突圍與內容創新。
《鄉村振興大擂臺》“探村直播”搭建大小屏全媒體矩陣,提供了一個構建互動儀式的良好平臺,把單項輸出與接受變為真雙向交互, 再放大到年輕人直播社交的節目模式,激發了主題綜藝更大的潛在能量和價值。同時,《鄉村振興大擂臺》形成了全民參與鄉村振興的精神共振,為廣電媒體節目打造全媒體傳播體系補充了有益的發展方向,為講好鄉村振興故事提供了新型傳播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