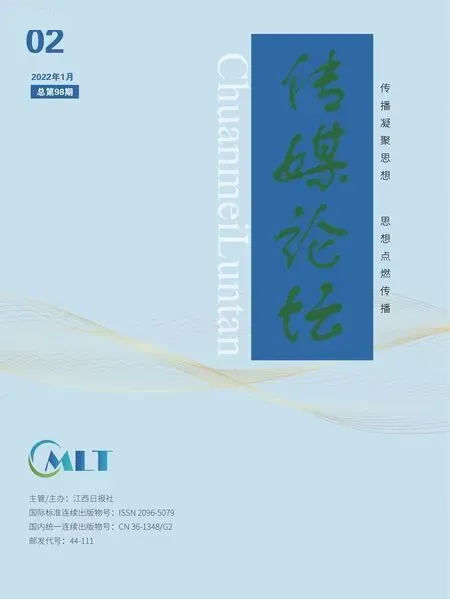編輯視角下書稿隱性差錯典型例析
李 晨
質量是出版的生命。作為書稿質量的第一責任人,責任編輯負責從選題策劃到出版成書的全部環節, 要從政治導向、學術價值、編排設計等方面嚴格把關,發現問題并通過查證妥善處理,確保書稿質量。[1]
所謂顯性差錯易察,隱性差錯難辨。本文列舉了編校稿件的過程中可能遇到的隱性差錯, 探索總結了避免隱性差錯的質疑核查路徑, 以期在今后的工作中有側重地做好甄別核改工作。
一、科學性和常識性差錯
書稿內容必須符合客觀事實和生活實際, 但有些作者為貼合主題虛構文章,東拼西湊,生搬硬造,內容毫無邏輯。如閱讀理解《一棵樹上的兩種果實》中寫著“到果實成熟的季節了,東家孩子吃了自己的石榴后,看上了蔓延過來的櫻桃,他哭著要吃……”讀過去覺得沒什么問題,可筆者抱著質疑一切的態度審視書稿, 發現櫻桃應該在春末夏初成熟,石榴應該在夏末秋初成熟,不應是“一棵樹上的兩種果實”。再如稿件中提到卡牌類游戲是“從唐代的游戲‘葉子戲’演變過來的”,接著又說“據說是韓信為了讓思鄉之情甚切的將士們……”韓信是秦末漢初人,與唐代游戲有何關聯?
有些是由于作者缺乏常識致誤。在一本科普讀本中,作者將諺語“今冬麥蓋三層被,來年枕著饅頭睡”解釋為“此時給麥蓋好被子,使它免遭嚴寒凍傷”。而在這句諺語中,“被”意指“雪”,其本意是“到了冬天,小麥經歷多次大雪,第二年就會有好的收成”。再如,稿件中提到90后胳膊上的疫苗疤痕為預防天花接種的牛痘。查證后發現,我國已于1981年取消在全國范圍內接種牛痘疫苗, 該疤痕應是接種卡介苗留下的。
這類差錯覆蓋面極廣,涉及的知識點較為瑣碎,如身份證的正面應為國徽面,企業法人不是自然人等,難以歸類統計。編輯應具有高度的敏感性,“習焉”不可“不察”,不要被習慣性認知蒙蔽雙眼,讓錯誤從眼皮下溜走。[2]
二、時效性差錯
編輯在處理稿件時,要注意內容選材的時效性,如非必要,盡量不選用滯后于現實狀況的陳舊資料[3],如三孩政策已放開,案例還是二孩時代;某數學教輔中提到個人收入超過3500元的部分將征收3%的稅,而2018年通過的新個稅法已將起征點改為5000元;2019年交付的稿件中稱濟南市槐蔭區二環西路的拖機路(張莊路)到目前為止仍然是濟南市唯一一條沒有下水道的公路,經查證,拖機路于2017年5月半封閉施工,鋪雨水管緩解汛期積水。
還要注意稿件中內容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發展和演變,如稿件中俄國、蘇聯與俄羅斯的說法,北京與北平的說法等。某書稿中提到“俄國作家”肖洛霍夫,但其生活經歷和文學創作主要集中于蘇聯時期,應稱其為蘇聯作家。
在稿件中,地名、單位名、學科名等要用新的,這需要編輯把握好具體的時間節點。在地名方面,2019年某年鑒提到濟陽縣、章丘市、長清區萬德鎮、歷城區彩石鎮等。但在此之前,濟陽縣與章丘市已區劃調整為區,萬德鎮、彩石鎮已成為街道辦事處。在單位名方面,稿件中提到監察部、環保部,要注意其撤銷的時間;提及濟南鐵路一中、濟南植物園、青島海洋大學等說法, 要注意其更名濟南中學、泉城公園、中國海洋大學的時間。在學科名方面,2019年某年鑒提到“思想品德”一科,而在2019年,初中階段“思想品德”教材名稱已全部改為“道德與法治”。
三、專業類差錯
在遇到超越自己專業領域的材料時, 編輯要謹慎對待, 通過查找專業資料來核實專業術語及知識點的正誤。如作者在介紹南京時提及詩句“南京犀浦道, 四月熟黃梅”,經查實,此處的“南京”指成都。某書稿在講漢語語法與修辭知識時提到“和離”意指“和平離婚”,是“生造詞,不能用”,經查實,“和離”始見于唐代《唐律·戶婚》,是古代離婚制度中的一種,并為近代法律沿用,不是生造詞。稿件中提到“爭取科舉致仕”的說法,“致仕”舊時指辭官,而不是進入仕途當官。再如書稿中提到“將專諸、魚腸等寶劍埋于墓穴中”,經查證,“專諸”指的是人。某稿件中提及作者被全國排舞廣場推廣中心評為先進個人,查證后,應為全國排舞廣場舞推廣中心。某校代表隊榮獲全國旅游院校服務技能(酒店服務)大賽一等獎”,查證后,應為飯店服務。
在教育類圖書中,這類差錯就更加繁雜了。如兒童繪本中常見的“味覺地圖”的描述有誤,研究證明舌頭分區與味覺感知無明顯關聯;某版本生物教材中,內環境一圖中淋巴的箭頭指向了組織液;某物理教輔中提及氨的物理性質是“密度比空氣大”,實則小于空氣;某化學教輔中的化學方程式“2H++OH-=H2O”,應為“H++OH-=H2O”,配平錯誤;某數學教輔中提及“設被3除余1的正整數為x,則x=3n+1,n∈Z”,Z應是N+。凡此種種,需要編輯謹慎對待,認真核查。
四、引文類差錯
稿件中引用領導人講話、格言短句或其他出版物中的段落時,編輯一定要注意核對原文,不可疏忽大意。核查原文可有效排除字形、句讀、語句脫漏等錯誤,如:
孔明曰:“曹操收袁紹蟻聚之窮于夏口, 區區求教于人,而猶言‘不懼’,此真大言欺人也!”孔明曰……虞翻不能對。
這里連續兩次出現了“孔明曰”,且后面莫名其妙地出現了“虞翻不能對”,核查后應為:
孔明曰:“曹操收袁紹蟻聚之兵,劫劉表烏合之眾,雖數百萬不足懼也。”虞翻冷笑曰:“軍敗于當陽,計窮于夏口,區區求救于人,而猶言‘不懼’,此真大言欺人也!”孔明曰……虞翻不能對。
還要注意引文出處的核查,如孟子的“食色,性也”,常被認為出自孔子;《左傳》中的“肉食者鄙”,常被認為出自孟子。
此外,要處理好引文的真實性和科學性問題。如書中引用“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減五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100到50到25到12.5,單純減少一半無法減少到1匹。
引文的其他成分如標題等也常有錯誤, 如書稿中提及教師[2015]5號文件為《教育部〈嚴禁中小學校和在職中小學教師有償補課的規定〉》,查證后應為《教育部關于印發〈嚴禁中小學校和在職中小學教師有償補課的規定〉的通知》。值得注意的是,引文參考文獻的各類信息都不能有錯,如姓名、朝代、國別、書名、出版地、出版社、年、卷、期、頁碼等。
遇有可疑之處, 編輯可視情況選擇權威工具書或知網、維普等數據庫資源來查證。編輯還可以通過搜索引擎查詢引文在權威工具書中的具體篇章、頁碼,再按圖索驥進行查證。[4]
五、資料類差錯
在編校過程中,要注意史實、人物、時間、地點、職務等資料的準確性。遇到此類資料,編輯要多疑防范,避免差錯。 如書稿中提及“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 圓明園是在1860年被英法聯軍燒毀的,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發生于1900年;某作者寫道“文天祥作為一介貧賤書生”,《宋史》中交代文天祥家世說“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與史實不符;書稿中提及“岳飛一筆揮就‘還我河山’四字”,并配有杭州岳王廟“還我河山”牌匾圖,經考證,這是岳飛書法集字而成,“一筆揮就”之說純屬臆想;某稿件提到“教師報的記者胡玉敏采訪陳校長”,查閱資料發現,相關文章為刊載于《中國教師》雜志的《做適應學生天性的教育——一所薄弱學校的蛻變與重生》一文,胡玉敏為責任編輯,范姜頤為記者;某教材給出蘇軾的生卒年月為1307—1101,實際應為1037—1101;某稿件提及“中國貴州澧縣石家河文化遺址”,澧縣位于湖南省常德市,而石家河文化遺址位于湖北省天門市;一本黨史讀本在介紹濟南首個縣級黨支部誕生地時,交替出現閻樓村、閆樓村的說法,查證后發現,百度百科中為閆樓村,山東衛視、舜網等媒體通稿中為閻樓村,地圖中也為閻樓村,故全書查替。
在書稿中, 作者經常不加分辨地采用互聯網上的資料,編輯要注意核實其真實性;即便是已發表的內容,編輯仍需留意形勢及政策變化, 看其中的觀點及提法是否適應現今形勢。
六、圖片照片類差錯
1.張冠李戴。由于書稿配圖與其他圖片相似,圖片選用存在差錯。如書稿中濟南戰役與遼沈戰役的圖片混淆,三黃雞與杏花雞的配圖錯放,耳機“qdc雙子座”與“拜亞動力榭蘭圖”的圖片放反等。在一本黨史讀物中有五三慘案紀念碑的圖片,而實際上五三慘案紀念碑有多處,介紹時圖文非同一地址。
2.圖文不符。例如文字中為雨天,圖片中為雪天標識;文字中為上午,圖片中鐘表顯示下午四點;文字中介紹垃圾分類,配圖中“垃圾”完好無損;文中印章的長為5.5厘米,寬為3.7厘米,圖片中印章的長近乎等于寬。
3.知識性差錯。此類錯誤考驗編輯的知識儲備,如歷史教科書在介紹北魏孝文帝時期的銅錢時,選用了太和五銖和宣和通寶的配圖, 而宣和通寶為宋徽宗時期所造。再如屈原、祖沖之所穿衣服出現“左衽”失誤,正常漢服是前襟向右。[5]
4.繪制差錯。此類問題多出現于傳統文化圖書中,由于美編對各歷史時期的服飾、建筑、車馬、餐飲、家具、兵器等了解不夠深入,繪圖時存在“穿越”現象。如圖片中秦始皇穿黃色龍袍,歷史上秦始皇酷愛黑色,隋唐才開始穿黃袍;如圖中所畫古書的訂在左,書名在右,實際恰恰相反。另一種情況是美編對歷史典故“想當然”而出現差錯。如岳母刺字,岳飛背上的“精忠報國”應為“盡忠報國”;再如程門立雪,配圖中兩名學生站在門外的雪地里,實際上兩人侍立的地方為屋內。
5.引導性差錯。在兒童讀物、教輔圖書中,編輯要注意插圖中的師生形象不能對使用者造成不良引導。 如小孩的頭發染為紅色、小孩喝酒、小孩趴著寫字等,都不適宜出現。
6.排版差錯。在一個決策樹分析示例圖中,兩分支的文字均為“建設新廠(投資1.2億美元)”,此處差錯是排版人員重新作圖時復制粘貼一個分支后忘記改字,編輯疏于核對所致。此處,第二個分支應為“擴建舊廠(投資5000萬美元)”。
七、數據類差錯
1.具體數據差錯。如某考試教材中介紹應急照明燈具照度時,提到“疏散走道、人員密集場所內、樓梯間內的地面最低水平照度不應低于0.501x,11x,51x”, 經查實,應為“0.51,1.01,5.01”。
2.數據計算差錯。對書稿中的數字、公式,編輯應實際計算加以復核。如某校共招生1231人(高中570人,職專561人),計算后發現應為1131人。某配額表中,配額100人,但所有區縣的名額加起來不足100。
3.年齡差錯。在一本2018年交稿的校長自傳中,稿件前面稱自己今年49歲,后面寫自己1968年出生,實為50歲,時間上有矛盾。
4.史實差錯。如一本黨史稿件講解四五烈士時提到“鄧恩銘和他的21位戰友被一起押往濟南緯八路刑場”,查證后發現,雖然四五烈士確有22人,但有1人死在獄中,此處應為20位戰友。
4.統計數據差錯。書稿中出現統計數據時,編輯應查閱統計年鑒或官方網站, 以權威機構發布的數據為準。如某稿件中關于新冠肺炎的國內新增數據與境外輸入數據與實際情況不符,奧運會獎牌榜采用的數據與實際數據不符等。
八、公式排版錯誤
此類差錯多是手工錄入過程中排版人員疏忽所致,也有部分是作者原稿錯誤所致,需要編輯仔細查對。

編輯不是數理化文史哲門門皆通的全才,面對書稿,編輯要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感,應具備質疑一切的態度和根據質疑探索求證的能力。 面對書稿中的所有圖文符號,編輯應逐處推敲加以核查,做到“逢引必核,逢疑必問,逢典必查,逢錯必糾”,嚴把圖書質量關,決不能走進“文責自負”的誤區放之信之。[6]同時,編輯應樹立終身學習的觀念,不斷充實與完善知識儲備,與時俱進地掌握最新政策法規及行業標準,做一個“編風”優良的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