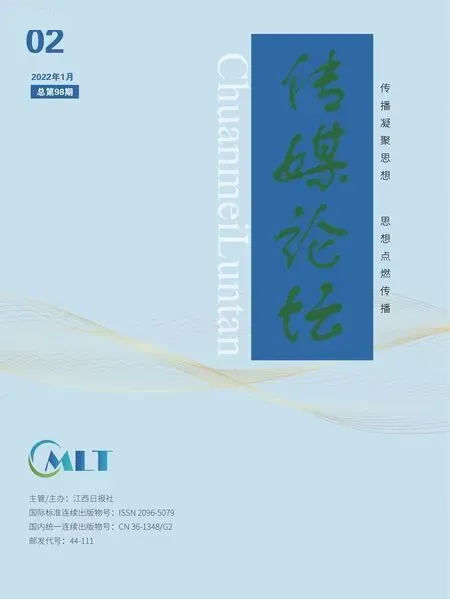框架理論視域下新聞報道對公眾情緒的影響研究
——以社會倫理報道為例
張 悅 魏曉紅 吳 輝
一、引言
目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社會結構失衡、道德文化失范等帶來的社會心理問題越來越多。 不信任感、偏見、易怒等社會心理問題逐漸增多,公眾情緒不穩定成為影響我國社會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 每一起熱點事件的爆發,與公眾情緒的長期積累緊密相關,同時,媒體報道的失焦和偏向也會影響該類案件的輿論走向, 極易引發公眾的關注和討論。 而且媒體具有為公眾進行“情緒設置”的作用,媒體報道中潛在或顯在的態度、情感傾向會為事件奠定情感基調, 極大影響公眾對事件的認知。因此,研究媒體的情緒傳播機制,分析媒體報道和公眾情緒呈現的關聯性,對媒體正面引導公眾情緒,避免新聞“后真相”,有積極意義。
框架研究是社會科學研究中的一個熱點研究領域,它為新聞媒體如何呈現社會生活、影響人們的認知與情感提供了理論解釋。 媒體通過新聞框架進行公共認知的生產和塑造,形成框架效應,而情緒反應可以介導框架效應,影響個人觀點和態度的改變。
國內學者的框架理論研究主要聚焦于“傳播中的框架”,即新聞媒體如何呈現的框架,較少涉及“個體心中的框架”,即新聞對公眾情感的框架。本文探討不同框架下的新聞報道對公眾造成了怎樣的認知以及情感變化,研究新聞框架與受眾情緒之間的關系, 研究結果對拓展和深化框架理論有一定的學術價值。
二、理論梳理與文獻綜述
(一)框架研究
1.框架理論及新聞框架
框架理論緣起于兩條線索, 其一是源于社會學理論。戈夫曼(Goffman,1974)首次將框架的概念應用于傳播情境中,框架理論即“個人組織事件的心理原則和主觀過程”;其二是源于心理學理論。在心理學界形成了關于個人認知過程的假設建構——基模[1]。
借鑒戈夫曼的理論, 學界逐漸將框架概念引入媒介研究。美國學者塔奇曼(Tuchman,2008)發現大眾媒體受制于“窗口”的視野來描述世界,框架成為新聞選擇和凸顯機制必不可少的內核[2]。吉特林(Gitlin,1980)首次提出“框架化”機制,即新聞生產者通過選擇、遺漏和凸顯三種機制處理信息[3]。恩特曼(Entman,1993)還總結了新聞文本的框架分析工具,框架分析不僅設置議程,而且影響讀者如何界定問題,尋求原因以及評估解決方案[4]。綜上,新聞框架是新聞工作者對信息進行快速識別和分類的工具,是媒介機構報道議題時使用一致的詮釋套路[5]。
框架視角下的社會倫理新聞報道研究多以內容分析法為主,部分學者對媒體報道的框架進行比較分析,或是以個案分析的方式探討社會倫理報道中框架構建體現的倫理失范現象。楊明明(2018)對三家具有代表性的媒體進行歷時性系統研究, 認為意識形態與媒體屬性對媒體報道中的框架構建起到了重要作用[6]。黃雅蘭(2020)認為歐美性暴力報道以渲染事件細節為主, 并提出應將此類“事件性框架”報道置于社會性別的時代背景下進行考察[7]。
(二)公共輿論的情緒
1.情緒化表達
公共輿論是理性的公眾在公共領域中對公共事務經過協商、公開討論后所表達出的觀點、價值判斷和意志傾向的集合[8]。知覺而又不易確切捕捉到的公眾情緒,是公共輿論的有機組成部分,是潛輿論的表現形式[9]。日益固化的社會圈層以及貧富懸殊、利益分化等因素,加深了公共輿論場的復雜性與多樣性,公眾的情緒表達欲望被撬動。
媒介機構作為傳播內容的“制造者”,能主動建構場景、形塑內容,深入影響公眾的情緒表達方式[10]。然而,以“弱信息、強情緒”為特征的網絡空間造成了信息傳播的窄化和公眾的認知偏差,公眾情緒呈現非理性的特征[11]。公共事件一旦發生,網絡空間的“病毒式傳播”方式和群體從眾心理會導致負面情緒的擴散[12]。
2.情緒分類
“情緒分類說”將情緒分為彼此獨立的基本情緒類別,美國心理學家Etman(1971)將情緒劃分為六種基本類型:快樂、悲傷、憤怒、恐懼、厭惡和驚奇[13]。“情緒維度說”認為無需把握具體情緒,而是對情緒進行傾向性分析。例如,Watson和Tellegen(1985)的“積極-消極情感模型”是二類情感傾向劃分策略的代表[14],也有學者通過微博語料中的表情符號、詞性等特征將情緒傾向劃分為積極、消極和中立(無明顯情緒)三類維度(Park Paroubek,2010)[15]。本研究通過查詢帶語義標注信息的情感詞典,整合“分類說”與“維度說”兩大劃分法則,將不同情緒類型分別歸類為積極情緒或消極情緒,對文本進行情感分類。
(三)新聞報道框架對情緒化表達的影響
框架效應是指對一個議題敘述的變化所帶來受眾意見的變化(劉雙慶,2020)[16]。在新聞傳播學研究中,框架效應關注新聞框架如何影響個體心中框架的過程(Shulman,2018)[17]。 而暴露在特定的新聞框架下會導致個體產生憤怒、恐懼、悲傷等情緒反應,并形塑個體對事件的解讀,即產生穩定的“情感-認知結構”模式(Nabi,2003)[18]。國外有學者對情緒在框架效應的中介作用進行了實證研究,主要聚焦不同傾向的新聞框架對不同情感的影響。Lecheler等(2015)以移民報道為研究對象,考察了正面框架新聞和負面框架新聞影響實驗對象產生的情緒反應差異,并驗證出憤怒和熱情這兩種情緒會顯著地調節框架效應[19]。
從目前梳理到的文獻來看, 國內外學者對新聞報道和公眾情緒的研究也主要聚焦于單一的新聞報道框架研究,從媒體視角出發考察新聞媒體對輿論本身的影響,進而提出輿論引導策略, 卻很少以公共情緒表達作為研究本體。 盡管有少量研究探討新聞報道與受眾情緒之間的變量關系,但在研究方法上多停留于經驗總結層面,較少使用嚴謹的實證分析。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與框架建構
本文選取鮑毓明事件作為典型案例進行研究。為了保證數據的完整性與科學性, 研究者首先采用Python網絡爬蟲工具,抓取“鮑毓明”事件發博量最多的9家媒體內容,共計229條,并將報道主題劃分為“案件細節”“調查進展”“處罰懲治”“問責監管”“社會協助”和“法律科普”6類,將報道傾向劃分為“正面報道”“中性報道”和“負面報道”3類。再次采用Python技術抓取以上新聞報道的微博評論,共計28688條。用SPSS軟件分析新聞報道類型與公眾情緒的相關性關系。
(二)公眾情緒識別
情緒識別旨在對包含情緒傾向的主觀性文本進行情感分類。 首先將微博評論樣本根據發布時間依次劃分至20個時間單位,其次根據“中文情感詞匯本體庫”,通過計算機編程為每一條評論標注情緒類型——“積極”“消極”或“中立”。“積極”包括期待正義、公道、大快人心等關鍵詞;“消極”包括憤怒、厭惡、恐懼等關鍵詞;“中立”包括依法辦案、實事求是等關鍵詞。
(三)研究假設
對報道主題進行初步分析后, 發現并提出以下研究假設:H1:報道主題框架為“案件細節”或“調查進展”的新聞對公眾“中立情緒”有正向影響;H2:報道主題框架為“處罰懲治”或“問責監管”的新聞對公眾“消極情緒”有正向影響;H3:報道主題框架為“社會協助”或“法律科普”的新聞對公眾“積極情緒”有正向影響;H4:“正面報道”對公眾“積極情緒”有正向影響;H5:“負面報道”對公眾“消極情緒”有正向影響;H6:“中性報道”對公眾“中立情緒”有正向影響。
四、實證分析
(一)框架呈現
1.報道主題
根據事發時間及輿情演變過程, 本研究將鮑毓明事件劃分為20個時間單位及兩個時間階段, 第一階段集中于鮑毓明案件的具體情況報道, 第二階段集中于對該案件當事人的最終司法調查結果。 不同階段的新聞報道框架情況如表1。
根據表1,新聞媒體對該事件的報道框架具有以下特征:

表1 媒體報道主題分時段統計表(單位:條)
第一,不同階段報道框架各有側重。在第一階段輿論形成期,媒體對該事件的報道側重于“案件細節”和“調查進展”,分別占比37.5%和33.3%,對案件的及時發布滿足了公眾對信息的需求。在輿論高潮期,社會各界集中于對當事人的譴責以及對司法辦案透明的關注,媒體利用“調查進展”和“問責監管”框架的報道數量增多,占比分別是32.9%和20%。第二,注重事實呈現,忽視人文關懷。“案件細節”始終是媒體報道的主要框架,但“社會協助”框架和“法律科普”框架始終占比很低,各為3.5%。媒體過分注重對事件過程的挖掘, 忽視對受害人的隱私保護和精神撫慰,同時也缺少對案件相關的法律科普,以防范社會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
2.報道傾向
從表2中可以看出,新聞媒體對鮑毓明事件的報道傾向主要以“中性報道”為主(126篇,占55.02%);“負面報道”次之(87篇,占37.99%);“正面報道”最少(16篇,占6.99%)。整體而言,新聞媒體對社會倫理類新聞事件進行報道主要以客觀中立的態度, 側重于對事件進行客觀描述。同時,對于案件丑聞和施暴者罪惡行為的報道主要采用批判的態度, 但在譴責的同時強調社會各界對被害者的協助與聲援及有效的法律政策。

表2 媒體報道傾向分階段統計表
(二)公眾情緒基本態勢
第一階段輿論形成期,頭條新聞發布鮑毓明事件后,由于公眾對“幼女”等弱勢群體先天的同情,該案件首次姚晨等明星發聲引起社會關愛幼女等弱勢群體的高潮,公眾“積極情緒”的占比上升至31.6%。第二階段輿論高潮期,9月17日媒體發布關于鮑毓明案件的司法調查結果:現有證據不能證實鮑毓明的行為構成性侵犯罪,李星星篡改年齡。案情披露后,輿情發生反轉,輿論再次出現引起社會的關注,公眾情緒逐漸聚合,評論數占總評論數的11%。第一階段輿論爆發期,南風窗發表一篇對鮑毓明事件細節披露的報道, 該事件迅速形成熱點效應,“消極情緒”占比最大,達49.1%。第一階段輿論高潮期,韓紅、高潮,公眾評論數量占第二階段總評論數的84.1%。

表3 公眾情緒的各階段分布統計表(單位:條)
(三)新聞報道框架與公眾情緒的回歸分析
1.報道主題與公眾情緒的回歸分析
由表4可知,報道主題為“案件細節”“調查進展”的新聞對公眾“中立情緒”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分別在0.001和0.05水平上顯著;報道主題為“處罰懲治”“問責監管”的新聞對公眾“消極情緒”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分別在0.001和0.05水平上顯著;報道主題為“社會協助”“法律科普”的新聞對公眾“積極情緒”沒有顯著影響,不支持研究假設。

表4 媒體報道主題與公眾情緒的回歸分析
2.報道傾向與公眾情緒的回歸分析
由表5可知,“正面報道”對公眾“積極情緒”沒有影響,不支持研究假設;“負面報道”對公眾“消極情緒”有正向影響,并在0.001的水平下顯著;“中性報道”對公眾“中立情緒”有正向影響,并在0.001的水平下顯著。

表5 媒體報道傾向與公眾情緒的回歸分析
五、結論
(一)媒體報道缺陷
1.極致煽情化取代人文關懷
根據實證分析結果,“負面報道”對公眾“消極情緒”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媒體報道中多處出現細節描寫,如“她出血,暈厥”“他先是掐我的脖子”等,通過對場景的再現和極致煽情來表達憤怒情緒,以博得社會的同情。這種寫法不僅容易激化公眾的負面情緒, 撕裂社會群體之間的信任, 而且細化施暴過程的種種細節會過度曝光受害者隱私,易對當事人造成二次傷害,缺失人文關懷。
2.報道傾向單一影響輿論引導
鮑毓明事件中負面報道多、正面報道少,如某媒體發布的《三問高管被指性侵養女案》一文說“‘禽獸不如’‘令人作嘔’‘難以置信’,是大多數人讀完報道的第一反應”,如此態度明確、立場鮮明的報道將媒體議題賦予了道德屬性,對鮑毓明的批判為公眾設立了一個道德標靶。公眾有了明確的批判對象,事件的關注點陡然攀升。但是媒體建構的“上層階級與普通百姓”“高管與幼女”二元對立的局面導致公眾情緒極化,報道沒有起到正面宣傳的作用。
3.追責缺失導致報道焦點偏移
鮑毓明事件真相揭露后, 由于當事人均已受到相關處罰,“處罰懲治”的議題占比較多,而“問責監管”“法律科普”的報道議題并未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該事件的聚集群體逐漸疏離,說明該事件中法律報道議題并未形成。但事實上, 對于這起復雜的案件, 不應僅為事件簡單定性,追究相關司法部門的責任缺失、科普相關法律知識,或許更為重要。諸如鮑毓明為何依然在國內正常執業、違規辦理韓某某戶籍年齡背后的隱因、“收養” 產業鏈為何屢禁不止等,應該成為媒體追蹤報道的核心。
(二)情緒疏導策略
1.堅持平衡報道原則
首先要平衡報道傾向。 新聞媒體應以解決問題為導向,加大正面報道的力度,而非刻意強調消極應對的錯誤走向,把握輿論監督與正面引導的協調統一。其次要平衡報道議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報道主題框架為“處罰懲治”“問責監管”的新聞對公眾“消極情緒”有正向影響。因此,媒體應通過輿情數據準確研判輿論走向,通過議題之間的轉換互動,平衡公眾的情緒。在報道涉嫌施害者的處罰措施后,公眾以消極情緒為主,可適當報道其他議題積極調節公眾情緒。
2.用理性報道進行善意傳播
實證分析結果表明,“中性報道”對公眾“中立情緒”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因此,媒體應尊重客觀事實,進行理性報道,向公眾客觀敘述事件的發生過程,而不應一味地進行情緒煽動,以保證報道的客觀性和真實性。媒體應堅持事實平衡、堅守新聞責任、永葆敬畏之心,須在善意的底線上引導輿論, 用理性報道彌合社會信任的裂痕。同時,妥善保護當事人的隱私,幫助受害者以正當途徑來實現訴求。
3.積極培養公眾法治觀念
媒體應調整固化的報道思維,從“高董與幼女”的矛盾沖突議題解脫出來,從法理的角度進行理性傳播。實證分析結果表明,主題框架為“法律科普”的報道較少,僅占3.5%,不易為公眾創造“學法、懂法、用法”的良好輿論環境。媒體不妨借此契機,邀請法律專家科普防性侵法治教育、梳理懲罰施害者的法律規制、講解收養法律常識,以提升公眾法律素養,培養公眾法治觀念,促進法治社會建設。
4.探索社會倫理報道的成熟模式
在“鮑毓明案”中,以“案件細節”“處罰懲治”為主題框架的報道數量最多,分別占35.8%和24.9%。媒體對社會倫理事件的報道不應停留于就事論事的層面, 而應努力擔負起環境監測、輿論監督的職能,圍繞“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思路進行精耕細作式的報道。我國目前對這類事件報道缺乏成熟的報道模式, 局限于刺激眼球的性侵過程報道, 對案件背后涉及的權利沖突和利益糾葛避而不談。以類似事件為契機,深入挖掘事件背后的“原因”,報道“新聞背后的新聞”,才是媒體做好此類報道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