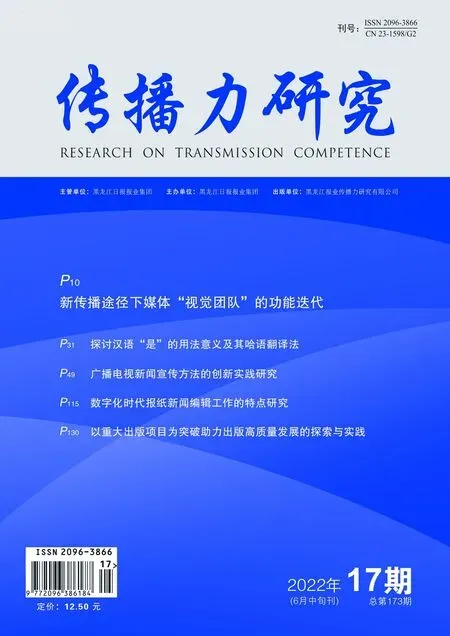身份認同的找尋與建構:從霍米·巴巴的文化位置觀看《綠皮書》
◎薛 柯
(蘇州大學傳媒學院,江蘇 蘇州 215127)
電影《綠皮書》根據真人真事改編。1962年,非裔鋼琴家唐·謝利博士準備從紐約出發,向南開展全國范圍的巡回音樂會。在種族隔離制度尚未終結的年代,唐·謝利雇了意裔托尼·維勒歐嘉作為司機兼私人助理在旅程中保護他的安全。一路上,兩人互相了解、扶持,共同度過了許多難關,建立了跨越種族和階級的友情,并完成了自我身份的認同與建構。20世紀,美國的殖民統治給非洲裔帶來了巨大的痛苦。到如今,橫亙在美國社會中的種族鴻溝依舊沒有彌合。白人至上的社會秩序下,黑人在信貸、教育、執法等眾多社會領域仍然遭受著歧視和暴力。電影《綠皮書》幫助人們了解20世紀30年代美國的社會風貌,思考被殖民主體和殖民主體的身份認同問題,也使人們重新反思當下的種族問題。
霍米·巴巴的文化位置觀是對其文化翻譯理論結果的進一步闡發。巴巴認為,模擬作為一種文化翻譯的手段,為殖民主體和被殖民主體的身份帶來混雜性,由此產生認同上的矛盾狀態。但同時,文化翻譯的過程中會打開一片“罅隙性空間”,通過占據這片混雜性的、居間的空間,可以實現文化意義的再現。
一、研究方法
(一)對象
本文將以電影《綠皮書》中兩位主人公唐·謝利博士和以托尼·維勒歐嘉的為代表的白人群體人物的身份認同意識和行為作為研究對象。
(二)方法
本文將采用文本分析法,觀察總結電影主人公作為被殖民主體和殖民主體的自我身份的找尋與認同行為,借助霍米·巴巴的文化位置觀理論分析其身份認同的轉變,探究他們對自我身份的建構。
二、研究結果
(一)被殖民主體的身份矛盾
1.主動的模擬
霍米·巴巴指出,有兩種文化翻譯。一種是指作為殖民者同化手段的文化翻譯,另一種是后殖民批評家所提倡的作為文化存活策略的文化翻譯。模擬時常被當作殖民主體進行強勢文化翻譯的手段,成為一種殖民控制形式。殖民主體要求被殖民主體采納霸權即殖民主體的文明,譬如,價值觀、宗教、風俗等,摒棄自己的文明與信仰。他們建立起壓制性行政管理及教育制度,通過讓被殖民文化拷貝或“重復”殖民者的文化來覆蓋殖民地的異域文化,實現思想、社會風俗上的高度統一,完成教化的使命,以便更好地征服新空間,鞏固統治。
電影《綠皮書》中的主人公之一,杰出的非裔黑人鋼琴演奏家唐·謝利可以被視作一個被殖民主體在殖民主體文明的教化下,認可殖民主體文化,并主動進行模擬的例子。他從小接受古典音樂教育,獲得了三個博士學位;藝術造詣深厚,多次受邀到美國白宮進行鋼琴演奏;生活優渥,生活起居一應有白人管家照料;談吐不凡,深諳上流社會的社交禮儀與文化……他對美國精英階層的文化始終呈現積極模擬的態度,在教育背景、經濟及社會地位上儼然躋身上層社會,在現實的物質生活中遠離了底層黑人社區,在精神生活上遠離了黑人族裔文化。不論是在心理上還是行為上,他都貫徹著白人的思考方式與行為準則,通過模擬塑造了自我的精英形象。
2.缺失的認同
雖然唐·謝利在藝術上有著極高的造詣,但他黑色的皮膚注定不會被白人群體完全接受,在現實生活中屢遭種族歧視。在羅利,他只被允許用樹林里的廁所;在路易維爾,他在酒吧喝酒時被三個白人男子挾持并羞辱;在日落鎮,他因日落后內不允許出現黑人而被針對;受邀在伯明翰演出,他不被允許坐進餐廳吃飯……白人群體對他的態度與他對殖民主體的文化模擬程度的高低并無關系,只因為他有著黑人的基因,生存空間與自由就不得不面對巨大的擠壓。
沒能在白人社區中立足,唐·謝利在黑人同胞中同樣面對著不被認可的境地。西裝革履、出行有白人管家跟隨左右的他與作為被雇傭者、地位低下廉價黑人勞動力之間有著巨大的身份割裂,當與他們無聲地對視時,貧苦的黑人們的目光復雜又不解。他時常因沒有人陪伴而感到孤獨,獨自一人在陽臺喝威士忌,看著樓下玩鬧的黑人同胞。但當其他黑人向他發出一起玩的邀請,他又無法說服自己降低身份加入他們的行列,故遭到了鄙夷和謾罵。他無法融入底層黑人的群體,不認可他們的生存方式與文明,黑人們亦沒有將他視為同胞。
由此可見,唐·謝利通過模擬習得的個人文化中帶有的明顯混雜性,讓他處于白人與黑人社區的中間地帶,不僅缺乏殖民主體文化的認同,也缺乏被殖民主體文化的認同。
被殖民主體對殖民主體的模仿不可能完全成功。被殖民主體的原始身份和文化殘留決定了模擬殖民主體文化的人塑造出的個人形象是介于與原體的相似和不似之間的“他體”,既帶有“被殖民”的痕跡,又與難以擺脫本土的特征,甚至出現從模擬走向“戲弄”的趨勢。這種文化的混雜性導致了唐·謝利面對身份問題時的巨大矛盾,他沒有收獲身份認同,難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在當唐·謝利與托尼爭執時,他絕望地大喊:“我獨自受苦,因為我不被同胞接受,因為我不像他們。如果我不夠黑,不夠白,不夠男人,那么告訴我,我到底是誰?”振聾發聵的吶喊讓他積累數十年的矛盾、屈辱、崩潰一瞬間爆發,充分表達出他無法活得自我認同和位置的痛苦與迷茫。
(二)殖民主體的身份混淆
1.糾結的模擬策略
霍米·巴巴在文化位置觀中將“殖民話語的矛盾性”表述為:“既然殖民者的模擬策略總是要求屬民與殖民者保持足夠的差異,以便繼續有臣民可以壓迫,那么它就永遠也不會完全成功。”殖民主體一方面打著文明教化的旗號,試圖用自己的文化規訓被殖民主體;另一方面又害怕他們被改造成和自己一模一樣的人,這就證明他們秉持的種族差異和劣等性概念是錯誤的,也證明他們的殖民話術是虛偽的。同時,又因為模擬的運作發生在情感和意識形態領域內,故而它與嚴苛暴政和赤裸裸的鎮壓殺戮有所不同,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被殖民地人民加以利用,害怕被殖民主體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此,巴巴指出“殖民權力和知識是最難以把握也是最有效的策略之一。”
有了上述考慮,殖民主體的模擬策略往往是糾結的。殖民話語一方面鼓勵并引導被殖民主體通過模擬殖民主體進行自我改進并逐漸接近他們的“優雅文明”,但另一方面殖民者則用種族差異和劣等性概念對這種改進與接近進行否定和抵制。如同電影中,雖然唐·謝利已經通過主動地完成了對殖民主體文化的高度模擬,但是白人群體仍然拒接給予他平等的地位和待遇。只因白人不愿意接受一個黑人接受了高等教育就與他們平起平坐,通過種族歧視的方式暗示唐·謝利:你依舊來自劣等的民族。
2.兩面增勢的矛盾狀態
然而,以唐·謝利為代表的精英黑人的出現還是給白人群體帶來了恐慌和驚異。盡管許多邀請唐·謝利進行演出的白人對他黑人的身份有所顧忌,但都不得不承認他的藝術造詣是普通人難以望其項背的。出身于市井、混跡在夜總會打工的托尼在為唐·謝利工作前十分排斥黑人,將來家中工作的黑人工人用過的水杯扔進了垃圾桶。但在接受唐·謝利的采訪時,他就對這位黑人擁有的資產與教養感到詫異。雖然拒絕了對方提出的雇傭要求,但與之交流的態度已經不同于對待普通黑人。在旅行中,唐·謝利數次糾正托尼的不文明行為,制止他偷竊的行徑,并指導他用優雅的詞句與妻子通信……經過長久的陪伴與扶持,托尼完全接納了唐·謝利,并多次出手援助、支持他。
這種轉變證實了巴巴的文化位置觀中極具創新性的一點:被殖民主體對殖民主體不一定總是減勢的,而是“兩面增勢的”,這種矛盾狀態的結果是被殖民主體對殖民主體同時具有吸引力和排拒力。由于殖民主體的文明并不是盡善盡美的,殖民者在生活實踐中也經常會產生誤差與偏失。如作為白人的托尼粗魯、自大、愛使用暴力。同時,被殖民主體在接受文化翻譯時展現出了強大的學習天賦和主動性,這使得他們的不完全處于劣勢地位,如德才兼備的唐·謝利。這種矛盾狀態打斷了殖民統治涇渭分明的權威,打亂了人們通常認為的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的簡單關系。于是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在優越與自卑、純正與摻雜、模仿與戲弄的矛盾狀態中,經常形成一種既排斥又吸引的依存關系。
巴巴的文化位置觀還指出,當部分殖民主體看到儼然成為自己影子般投射的被殖民主體之后,在道德的層面上會形成一種罪惡感與優越感交互混雜的模糊狀態,從而改變自己對他們的看法與態度。在看到老板被旅旁酒吧里的白人欺侮時,托尼感到不公和憤怒,立刻站出來用暴力制止了他們的行為,將唐·謝利解救出來,并叮囑他以后不論去哪里都要帶上自己。由此可見,面對具有進步性的、高度模擬的被殖民主體,殖民主體會對被殖民主體有了更為全面的認識,態度也會隨之發生轉變。
(三)雙重身份的建構
上文提到,殖民主體與被殖民主體都處于不同程度和形式的矛盾狀態中。因此,在強制性的文化翻譯過程中,殖民主體的權力并不是絕對的權威,被殖民主體也不是完全被動的受害者。通過雙方不斷的文化商討和交流,總會產生某種對抗和抵制的可能性。
因此,巴巴在文化位置觀中提出了“第三空間”的概念。巴巴認為,在文化翻譯的過程中會打開一片“罅隙性空間”,通過占據這片混雜性的、居間的空間,可以實現文化意義的再現。這里所說的罅隙的、混雜的和居間的空間其實就是“第三空間”。這是個人或群體的自我地位得以闡述的策略性跨文化空間,是在不同的狀態之間存在的一個持續不斷的運動過程和交流過程。這種認同絕不是簡單的從單一的某種認同到另一種認同的運動,而是不斷的接觸往來、爭斗和挪用的過程,也就是后殖民論者常說的文化商討過程。
面對二者的身份建構問題中,巴巴推崇一種“雙重身份”的策略。雙重身份并不是某人真的有著兩個不同的身份,而重在指出:身份的協商具有重復性,有時候需要連續地重復、不斷地修訂和重新定位。在影片的最后,唐·謝利就完成了自我的找尋和雙重身份的建構。通過一路南下巡演,他受到的種族歧視愈發嚴重。而伯明翰,作為演出嘉賓的他卻只能在雜物間休息,也不被允許進入餐廳用餐。從前面對此種境遇,他都選擇默默接受。但經過了雨夜與托尼關于身份認同的爭執與交流,這一次他選擇主動向餐廳經理表達自己需要進入餐廳用餐的合理需求,爭取自己應得的權利。在引發沖突并被不斷拒絕后,他果斷選擇不再為他們提供演出。這一晚,他第一次嘗試走進底層黑人的聚集地橘鳥酒吧。在這里,向來只演奏斯坦威鋼琴的他在酒吧老板和托尼的鼓勵下在酒吧的簡陋鋼琴上彈奏了古典音樂,而不是唱片公司要求的流行音樂。他高超的演奏技術立刻獲得了在場黑人的歡呼,許多黑人拿著樂器上臺與他一同合奏。值得一提的是,他們合奏的曲目正是唐·謝利和托尼出發伊始時托尼播放的黑人音樂,彼時唐·謝利還對它一無所知。影片的最后,他達成了與自己的和解,在保持原本的涵養、素質不變的前提下,逐漸接受黑人底層文明,主動融入到黑人社群文化中。通過與殖民主體的文化和被殖民主體文化的多次協商,唐·謝利在文化實踐中建構了自我的雙重身份。而一開始極度排斥黑人的托尼,也因唐·謝利的相處而不再對黑人種族懷有歧視與敵意,甚至多次主動維護唐·謝利,并歡迎他來自己的家中一起過圣誕節。作為殖民主體的一員,他也經歷了矛盾狀態,但卻在文化協商中轉變了偏見,對自我和唐·謝利的身份都有了全新的認知。
三、結語
不論是過去殖民地的受奴役者和被壓迫者,還是現在多元文化社會中的移民、難民、少數族,都面對著被擠壓的生活空間和缺失的身份認同問題。他們“既是此又是彼”,或者既非此又非彼,身陷于文化翻譯的動蕩過程之中。他們居住于一個“文化之間”的世界,于矛盾和沖突的傳統中嘗試建構自己的身份認同。正是這種生發性的文化轉換,為這些“移民”贏得了寶貴的后殖民視角,將他們置于一種“閾限性”空間,開辟出一片批判性思考的新天地。《綠皮書》帶來的,不僅是人民對被殖民主體的思考,更是對殖民主體文化翻譯過程與身份建構的反思。自我身份的找尋和建構在后殖民背景下固然困難,但后殖民文化認同的邊緣視角需要被看到,需要被闡發,這也許是這部電影帶給人們的重要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