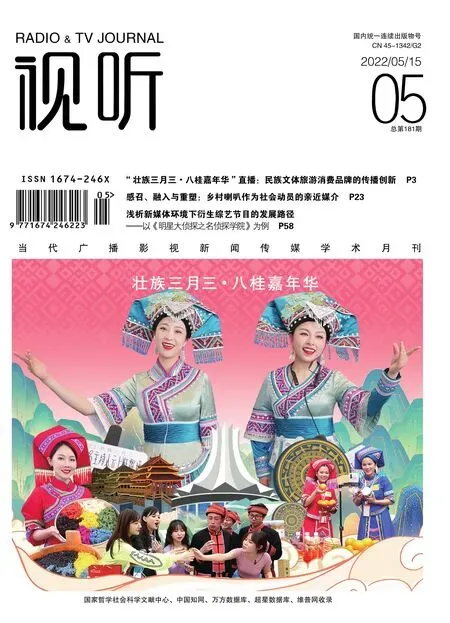中國文化對外傳播創新策略探析
——以科幻電影《流浪地球》為例
張 淦 李曉燕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對外開放格局的不斷擴大,文化領域的對外交流與合作越發頻繁。2019年,電影《流浪地球》在海內外上映,引發全球觀眾廣泛熱議和好評。早些年因為《三體》而知曉劉慈欣的海外媒體和讀者再一次把目光聚焦在這部由劉慈欣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上來,表現出了對中國科幻、中國電影和中國文化的濃厚興趣。《流浪地球》在海外的高關注度源于影片對中國文化、中國形象的全新演繹,為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提供了有益啟示。本文從跨文化傳播的視角,分析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現狀,解析電影《流浪地球》對外傳播的創新策略,進而為中國文化對外傳播提出建議。
一、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現狀
(一)中國文化“走出去”取得的成就
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進一步發展,中華文化對外傳播與交流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因為文化的傳播和交流關系到國家形象的構建,所以從官方到民間皆采取了多種方式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并取得了顯著成就。比如,孔子學院在全球162個國家(地區)建立550所孔子學院和1172個孔子課堂,成為海外大眾學習中文和中華文化的重要途徑;莫言、劉慈欣等中國作家的作品先后在海外獲獎并暢銷;李子柒在國外受到熱捧,以1410萬的YouTube訂閱量刷新了吉尼斯世界紀錄。這些中華文化“走出去”的成功案例,為傳播中華文化、塑造中國國家形象發揮了重要作用。經過官方和民間的共同努力,中華文化在海外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影響力,一些中華文化符號如功夫、中餐、熊貓等得到了各國人民的喜愛。
(二)面臨的問題
雖然近年來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取得了諸多成就,但也存在諸多不足。比如,傳統文化的傳播缺乏貼近大眾喜好和與時俱進的傳播形式;部分內容門檻較高導致受眾面較窄,如古詩詞、鄉土文學等;對流行文化缺乏重視,輸出的文化符號大多注重本土文化價值,但忽視受眾的精神需求和觀賞習慣;為了獲得海外評論界認可,部分影視創作者在對外傳播“自我東方化”時,將視角立足于現代西方的他者位置,按照西方的價值立場進行生產和創作①。這些問題制約了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難以促進海外受眾對中華文化的理解與喜愛,其中有些不足甚至進一步加深了舊有的刻板印象及誤解。
二、科幻電影《流浪地球》對外文化傳播的創新性策略
2019年,由劉慈欣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流浪地球》上映,票房口碑雙豐收,成為春節檔的最大黑馬,極大地提高了國內觀眾對國產科幻片和本土科幻文學的興趣和信心。同時,《流浪地球》在海外也引發了廣泛關注,因為《三體》而知曉劉慈欣的西方大眾和媒體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了中國科幻。英國《金融時報》認為“《流浪地球》是中國科幻電影的巨大飛躍”,美國《紐約時報》認為“隨著中國在太空達到一個里程碑——2019年1月探測器在月球背面著陸,中國科幻電影也迎來了發展”。在海外社交平臺Twitter、Facebook上,《流浪地球》引發了國外網民的討論。美國流媒體巨頭網飛則買下了該片在海外的播放權,將其翻譯成28種語言,面向190多個國家和地區播放。《流浪地球》能在海外引發話題性,進而擴大中國文化的吸引力和影響力的原因在于,該片作為一部科幻電影,可以在跨文化傳播的過程中,通過大眾喜聞樂見的傳播符號,講述關乎全人類共同命運的中國故事,從而最大限度地跨越文化、民族、國家的界限,獲得全球觀眾的喜愛。
(一)家國情懷與人類命運融為一體——“核心自我”定位的全球化
美國學者艾瑞克·克萊默認為,“自我”是跨文化傳播過程中的關鍵因素。明確自我的定位及自我和環境中不同因素所組成的關系以及如何看待它們,在跨文化交際中起著重要作用。“自我”作為一個文化概念存在于信仰、價值觀、態度、需求所盤踞的各個領域內②。在跨文化傳播過程中,“核心自我”的定位范圍將影響受眾對不同維度文化的接受程度。科幻這一文藝類型產生于工業革命以后,是唯一沒有任何歷史傳承的、全新的文藝類型,科幻文藝作品往往把視角定位于全人類的高度,更便于不同文化背景受眾的理解和接受。因此,在電影市場,科幻電影總是備受世界不同國家觀眾的喜愛。科幻電影在跨文化傳播的過程中,要將文化輸出給全球受眾,需要引發不同文化背景受眾的共鳴,所以科幻影視創作就必須關切文化認同③。
《流浪地球》延續了科幻電影創作的傳統,將主人公的核心自我定位于“地球人”。正是基于這種全球化的自我定位,影片把中國文化特有的家國情懷放大至全人類的格局和視野。雖然影片的主要角色均為中國人,但是在敘事中,該片并沒有刻意強調主人公的中國背景,也沒有把中國傳統文化符號和角色綁定,而是把一個個擁有中國背景的個體放到了全人類共同拯救地球的集體主義情景中。影片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地域、民族、國籍等差異,將所有角色的第一屬性首先定位為“地球人”,所有人關注的是地球和人類的命運,從而成功地構建起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話語體系。這種安排可以使不同地區的受眾產生“移情”效果,表現人類在天災面前的命運與共,但在電影中的解決方案又是基于中國主流意識形態中的集體主義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電影通過全球化的視野去傳遞中國式的價值觀,使得海外受眾更容易理解人物的思維和行為方式,從而在無形之中加深了對中國文化的理解與認同。
(二)超現實的視聽盛宴——貼近大眾喜好的傳播形式
根據美國著名傳播學者約書亞·梅羅維茨的“消失的地域”理論,人們每天所關注的,是媒介所傳達的內容,它的形態本身往往更加深刻地觸動和改變著我們的生活。比如,在報紙等非電子媒介主導的時代,政治人物的形象往往都是高大、神圣的,而在現在更加私人化、社交化的電子媒介時代,政治人物的形象則向親民的方向轉型,避免扮演“偉大的領導人”④。由此可見,當今的電子媒介時代可以說是一個視覺文化時代,所塑造的傳媒環境是親民、平等的。在這個背景下,跨文化傳播需要貼近大眾喜好的形式,灌輸式的文化傳播在今天很難再發揮作用。
科幻電影長期被市場青睞的重要原因在于其擁有受眾喜聞樂見的表現形式。因為科幻電影對視覺效果要求較高,投資較大,主要表現現實中不存在或尚不完善的事物,所以能打造出受廣大普通觀眾所喜愛的視聽奇觀,迎合了“讀圖時代”受眾偏愛圖像信息的觀賞習慣和審美需求。《流浪地球》的投資高達4億元人民幣。由于影片中的明星并不多,所以其中大部分資金都投入到了特效和服道化的制作中,向觀眾呈現了一場震撼的視聽盛宴。依托視覺奇觀,電影中塑造的末日世界從一開始就能吸引觀眾(包括擁有其他文化背景的海外受眾)的注意力。可見,優秀的視聽效果能跨越民族、國家、文化的差異,對廣大普通觀眾產生吸引力。《流浪地球》用高質量的特效,將原著小說中那些天馬行空的文字打造成為一場極具觀賞性的視聽盛宴。例如,小說原著中對流浪地球的描寫:“我們的星球也成了一個巨大的彗星,藍色的彗尾刺破了黑暗的太空”,這個標志性的場面在電影中被完美地還原出來,不僅照顧了原著粉絲,充分利用粉絲效應提高了影片熱度,也滿足了普通觀眾的審美需求。
布魯內爾大學設計學院的相關人士在對京劇視覺表達的相關分析中曾指出,雖然語言是用來表達想法的第一途徑,但也可以通過“想法—圖像—語言”的轉換程序,達到更好的交流目的,即構思良好的形象設計,是能夠輔助另一種語言的表達形式⑤。這一發現也適用于電影領域。通過視覺符號向海外受眾傳達中國主流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更有利于對方的理解。在《流浪地球》中,中國的鄉土情結、集體主義、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思想被轉化成為影片中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和細膩逼真的視覺特效。同時,影片中超現實的場景是基于中國人對于家園的熱愛所設計的。例如地下城,如同把現代的中國城市搬入了地下,人們的娛樂、學習同現實中別無二致。這些具有強烈中國特色的場景不僅能引發中國觀眾的共鳴,也會引發廣大海外觀眾的興趣。而且這些日常化的活動往往發生在非日常化的空間中(即地下),這種強烈的反差能給觀眾帶來一種新鮮感。這種日常與非日常、民族與跨民族元素的組合,是科幻電影中塑造超現實性場景的常見創作手法,不僅符合創作規律,也符合電子媒體時代信息傳播的規律。由此可見,在跨文化傳播中,擁有一個親民且適合的表現形式,可以增進不同文化背景觀眾的相互交流與理解,進而構建良好的國家形象。
(三)彰顯文化自信——創作者主體意識的提升
在對外文化傳播中,一些影視創作者把西方對東方的想象符號作為交換資本,呈現的是歐美所謂“東方主義”中古老、神秘、落后的東方,使得創作中的“自我東方化”“他者化”現象層出不窮。部分作品站在“他者”視角上去審視和塑造中國,既不符合新時代中國主流社會對于堅持文化自信的共識,也無法消除海外受眾對中國的刻板印象和誤解。例如,影片《滿城盡帶黃金甲》中充斥著西方人“熟知”的中國元素,如大面積的黃色和紅色、古裝、武俠等。類似這種“自我東方化”的策略能迎合海外受眾的刻板印象和偏見,但是無法代表一個全面、真實、客觀的中國形象,帶著明顯的局限性和片面性⑥。
美、日、韓等國輸出的文化產品,在價值取向上大多以本國的意識形態為根基,內容多為當下本國的流行文化,如美國的“漫威”系列、韓國的K-pop、日本動漫等。這些文化產品娛樂性較高,不僅能迎合不同國家和地區受眾的審美趣味和審美需求,而且能展示本國文化先進、積極的一面,有利于對外構建正面、積極的國家形象。從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效果來看,近些年海外大眾接受度較高的文化產品,如小說《三體》、李子柒的短視頻、“無盡對決”手游等,創作者都在作品中表現出了強烈的主體意識。這些作品從當代中國流行的文化符號或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靈感,其價值選擇扎根于當代中國社會主流意識形態,把滿足國內受眾需求以及作者的自我表達作為創作的首要意圖。以上案例證明,創作者的主體意識是不同文化之間平等交流的必備條件,只有創作者堅持了文化自信,在文化交流中堅持自我,才能創作出真正被海內外大眾接納和喜愛的作品。
電影《流浪地球》在創作中把中國觀眾的觀影趣味和價值選擇放在首位,以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為根基,講述了一個中國人拯救世界的故事。導演郭帆甚至在花絮中直言:“影片首先服務于國內觀眾”,體現出主創們強烈的主體意識。影片以中國人為“地球代表”的敘事方式在科幻電影中實屬罕見,體現出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顯著提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不斷顯現,中國觀眾和文藝工作者的文化底氣和主體意識不斷增強。同時,主人公在片中不是唯一在行動的救援隊,而是所有人都在行動的“飽和式救援”,這就在意識形態上明顯區別于好萊塢電影中的個人主義。影片最后以英雄主義式的犧牲精神換來全人類生存的延續,洋溢著中華民族血液中“不屈不撓”的奮斗精神與“舍生取義”的犧牲奉獻精神,是對中華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生動詮釋。影片的核心創意是“帶著地球去流浪”,潛臺詞就是對家鄉的堅守與熱愛,是對“生于斯、長于斯、死于斯”的中國鄉土情懷的陌生化處理。影片一方面深深扎根于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另一方面利用了貼近大眾審美趣味的符號去表現中國當代主流文化和價值觀。影片的創作人員具有強烈的主體意識和責任意識,以自我、本國、本民族為中心,借助科幻的外衣表現民族精神,踐行文化自信,更容易獲得不同文化背景的受眾的尊重和認同。海外受眾需要的是真實、鮮活且與時俱進的中國文化符號,以滿足欣賞需求,而不是國內創作者基于西方文化背景中對中國文化的理解而創造的文化產品,這就對創作者的專業素養和主體意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尊重原著與大膽創新相結合——充分利用文學和影視兩種媒介的優勢
電影《流浪地球》改編自劉慈欣的同名小說,繼承了原著中的“故事世界”,并將小說中的經典場面視覺化,將原著中天馬行空的想象轉化為極具視覺沖擊和震撼力的逼真影像,但同時又講了一個幾乎不同于原著的故事,進一步豐富了人物關系,做到了尊重原著而不拘泥于原著,在“揚棄”的基礎上有所創新。
電影《流浪地球》的成功,與影片的改編策略密不可分。法國電影評論家安德烈·巴贊在其著作《電影是什么?》中曾說:“優秀的改編應當是展現原著的文字與精神實質。”電影《流浪地球》和原著小說雖然故事情節不同,但是電影在最核心的主題思想、價值取向上與原著保持了一致。在劉慈欣的小說作品中,人類往往是作為一個整體而存在的,他們需要面對共同的挑戰。電影《流浪地球》繼承了原著推崇人類集體意識、命運共同體的價值取向。影片中全世界各地的救援隊都投入到拯救地球的行動中,并在最后攜手戰勝危機,體現了對人類集體意識的呼喚。片中飽和式救援、各國救援隊支援主人公、劉培強犧牲等情節,都是以集體主義作為價值基礎。劉慈欣的作品以其嚴謹的設計被視為“硬科幻”的代表。電影《流浪地球》在美術設計上非常強調設計的“功能性”,比如地球發動機、領航員空間站、運輸車、防護服等。不同的設計都對應了不同的功能,觀眾看到造型就能直觀地理解其功能,優先突出“實用性”,因此極具工業美感。把小說中嚴謹的設計還原在了銀幕上,這種實用至上的設計理念是對原著小說“硬科幻”氣質的繼承。一般來說,能被改編成電影的科幻小說往往具備兩個突出特征,一是“高概念”,即整個小說和電影最核心的創意,整個敘事都建立在這一創意的基礎上;二是完整的時空設定,即文字中塑造一個完整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故事的發展具有無限的可能性。電影《流浪地球》完全套用了原著小說的核心創意和時空設定。原著中太陽氦閃對地球的威脅、各國組成聯合政府、地下城市、地球發動機等背景設定都被完整地運用到了電影里。小說中構建的“故事世界”被移植到了電影里,成為電影版主人公活動的舞臺。
電影《流浪地球》尊重原著,但是沒有拘泥于原著,而是進行了大膽的創新,適應了觀眾的審美需求和興趣。電影《流浪地球》節選了原著中地球和木星交會的緊張時刻,將其改編為地球即將撞擊木星的災難,講述了一個全新的故事,將原著中人類之間的斗爭,變成了人類攜手對抗天災的壯舉。影片參考了好萊塢類型片的敘事模式,圍繞如何化解木星危機展開敘事,情節發展跌宕起伏,主要人物個性鮮明,價值觀念貼近主旋律,符合大多數觀眾的欣賞趣味。在劉慈欣的筆下,角色往往是作為一個符號、一個工具,代表的是某個群體,人物的類型化痕跡非常明顯,這也成為讀者對其作品的一個爭議。而電影則力求展現鮮活生動的人物形象,劉啟、韓朵朵、劉培強等角色都有各自的人生軌跡和鮮明個性,給觀眾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影片在原著基礎上進一步豐富了人物關系,比如劉啟與劉培強父子間的羈絆與和解、劉啟與韓朵朵的兄妹情、救援隊隊員之間的戰友情等。這些人物情感的交織不僅能推動影片情節的發展,也能有效拉近觀眾與影片之間的情感距離。
三、以電影《流浪地球》為代表的中國科幻作品對中國文化對外傳播提供的啟示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文化作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顯現出日益重要的價值。加強對外文化傳播,增強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傳播中的話語權,是提升國家軟實力的重要保障。關于如何更好地進行對外文化傳播的問題,以電影《流浪地球》為代表的中國科幻作品在傳播內容、敘事視角、傳播形式等方面提供了啟示。
(一)傳播內容要彰顯文化自信,避免“自我東方化”
近代西方產生的“東方主義”是在“西方文明而東方野蠻”這一立場下,將西方作為標準來評判東方的一種意識形態,是殖民時代的產物。這里所指的“東方”并非地理意義上的東方,而是落后、野蠻的代名詞,是“探險”和“征服”的對象。例如,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就以“治水社會”的概念構造了一個想象中的東方世界圖式。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代史既是反帝反封建的斗爭史,也是模仿西方的學習史。在這個過程中,由于西方勢力的強大,國內的部分文藝工作者不加批判地接受了“東方主義”的相關理論,將西方價值觀立為標桿,導致了近現代的文藝作品中大量存在“自我東方化”的現象。進入21世紀以來,以《三體》三部曲、《北京折疊》為代表的中國本土科幻文學和以《流浪地球》為代表的中國科幻電影堅持了中國當代價值取向,并對意識形態等方面進行了求同存異的隱喻式處理,引發了海外受眾對中國和中國科幻的興趣,獲得了好評。將21世紀初的“國產大片”和新時代的中國科幻作品在海外的評價進行對比,可以發現創作者的主體意識和文化自覺意識的提升。文化交流的前提是平等。只有在平等的基礎上,不同文化間才能真正實現相互理解,欣賞對方的美好,實現有意義的傳播。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文藝創作者需要擔當新的歷史使命,堅定文化自信,在對外文化傳播中要避免“自我東方化”,向世界傳遞中華文化的魅力,讓海外受眾能真正了解中國,并熱愛中國。
(二)基于觀眾接受視野進行全球化敘事,引發不同文化背景受眾的共鳴
一部影片是否可以同時完成在海內外的成功傳播,關鍵在于它本質上是否能夠跨越民族文化差異與信仰差異,尋找到可以引起不同地區、種族、膚色和信仰的觀眾的共鳴的情感點⑦。以往在海外獲獎的國產影片,或是表現底層人物,或是和封建文化相關。這類影片雖然具有較高的藝術造詣,但是缺乏能引發海外普通觀眾興趣的形式和內容,其傳播影響十分有限。在對外文化傳播中,若想引發不同文化背景的觀眾的共鳴,首先要突破狹隘的自我定位,將“自我”定位于全人類的角度進行敘事。例如,《銀翼殺手》《2001太空漫游》《2012》等好萊塢科幻片、災難片大多將自我定位于人類的高度,利用超現實性的表現手段講述全人類共同關心的議題,能最大限度地突破文化差異對傳播造成的阻礙。以《流浪地球》為代表的中國本土科幻作品雖然在內容上深深植根于中國本土文化,但其探討的是全人類共同關心的話題,如戰爭的殘酷、對真理的追尋、對理性的推崇、對愛的頌揚等。創作者的“人類視角”使得作品中發生在中國的故事具有了引發其他文化背景受眾理解和共鳴的效果。進入新時代,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成為我國外交思想的重要內容。在中華文化對外傳播的過程中,我們也應認識到新的歷史時期人類社會的緊密聯系,將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貫徹于文藝創作中,注意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不同信仰的受眾所共同關心的話題,將人文關懷上升到全人類的高度,基于觀眾接受視野進行全球化敘事,不斷擴大傳播效果。
(三)充分挖掘時代特色與中華文化內涵,運用大眾喜聞樂見的形式進行傳播
要在讀圖時代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就要注意對傳播符號的選擇和運用,特別要重視對先進科技和傳播媒介的運用。電影《流浪地球》充分考慮觀眾的審美需求,深入挖掘中華文化內涵和時代特色,不僅在電影中充分運用了中國文化元素,而且利用現代高科技手段打造了一場視聽盛宴。在電影中期的拍攝過程中,創作團隊盡可能地進行實景拍攝,在后期則由MORE VFX、ORANGE FX等7家頂尖特效公司參與后期特效制作。在服化道、布景、特效上的大力投入,令影片既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又具有超現實性的視覺形象,極具視覺沖擊力和吸引力。同時,影片中所蘊含的當代中國價值觀中的集體主義、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思想能引發觀眾的共鳴。由此可見,在對外文化傳播中,只有創造性地將具有時代特色和地域特色的文化符號與超現實主義的表達方式相結合,深度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時代精神文化內涵,才能真正創作出大眾喜聞樂見的優秀作品,贏得國內外受眾的喜愛,促進新時代中華文化的對外傳播。
四、結語
《流浪地球》作為一部由科幻文學改編的電影,在敘事、特效、創意和思想內涵等層面都已相當成熟,整體品質并不亞于目前的好萊塢科幻電影。這不僅得益于中國電影工業的發展,還得益于本土科幻文學為電影改編提供的文學基礎。近年來,包括電影《流浪地球》在內的中國科幻作品之所以能在國際上引發廣泛關注,正是因為創作者將自我定位于全人類的視角,把當代中國意識形態與超現實的表現形式相結合,且講述的中國故事背后蘊含著全人類共同關注的議題。《流浪地球》在文化傳播方式上突破了以往“灌輸式”“迎合式”的輸出模式,為新時代中國文化對外傳播提供了積極的借鑒意義。
雖然《流浪地球》獲得了成功,但是從整體來看,我國的對外文化傳播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擁有較大的提升空間。面向未來,我們只有堅定文化自信,扎根于中國文化土壤,以新穎的形式講好中國故事,同時擴大對外交流與相互學習,才能真正迎來屬于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新紀元。
注釋:
①陳璐明.遷移·定位·發展——新世紀中國新主流電影話語的跨文化傳播[J].電影新作,2019(06):125-130.
②[美]艾瑞克·克萊默,劉楊.全球化語境下的跨文化傳播[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42.
③閔玲.跨文化傳播語境下的科幻影視創作探析[J].視聽,2019(03):26-27.
④[美]約書亞·梅羅維茨.消失的地域:電子媒介對社會行為的影響[M].肖志軍 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296.
⑤Hodkinson,A.Conceptions and misconceptions of in clusive education: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final year eacher trainees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in clusion[J].Research in Education,2005(73):15-29.
⑥陳璐明,曹越.并置·堅守·反思——全球視域下《流浪地球》國家形象跨文化傳播[J].發展,2020(05):64-66.
⑦曹靜雯.“叫好”與“叫座”:淺析新時期國產電影海外傳播遇冷現象[J].戲劇之家,2021(06):128-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