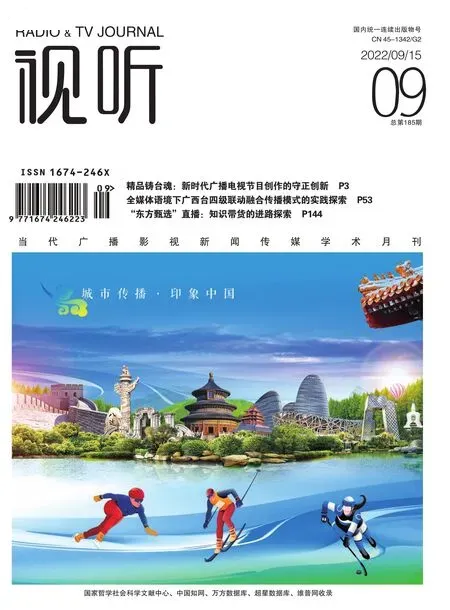表征與闡揚:《長津湖之水門橋》的敘事延展與審美情感研究
李軼天
1950年11月27日,作為抗美援朝戰爭中扭轉戰勢的重要一戰,長津湖戰役打響。中國人民志愿軍第9兵團3個軍在-40℃的嚴寒中,與以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苦斗20天,最終將他們全部逐出朝鮮東北部。在水門橋之戰中,志愿軍三炸水門橋,成功切斷美軍從長津湖撤退的通道,成為長津湖戰役的一個重要節點。電影《長津湖之水門橋》以此為背景,貫連《長津湖》,講述在結束新興里和下碣隅里的戰斗之后,七連戰士接到炸毀水門橋的艱巨任務的故事。《長津湖》引領2021年國慶檔電影,歷經三次延遲下線,最終以票房57.75億元登頂中國電影市場票房冠軍。2022年2月1日,《長津湖之水門橋》領跑春節檔,后又在中國澳門、中國香港上映。截至2022年7月29日,《長津湖之水門橋》收獲40.66億元票房。
戰爭史詩片《長津湖之水門橋》在氣勢恢弘之中,以多元敘事線、多重維度協同情節與情感的展現和刻畫,推動審美意象的再生,在武戲文拍之中將志愿軍的戰斗意志、生死之情和氣壯山河的抗美援朝精神表現得淋漓盡致。
一、復調與建構:三線并置的全景式敘事
美國著名文學批評家希利斯·米勒指出:“敘事就是沿著一根線條向前走,任何講述都是以不同的‘線條’對某件事的再度表現與重新講述。”①巴赫金將音樂學中的術語“復調”引用至文學創作中,以復調理論闡釋了文學創作中的“多聲部”。電影敘事學在文學敘事學的基礎上得以升華。以該視角觀此片,《長津湖之水門橋》在敘事線索上采用高層視點、基層連隊、美軍視角三線并置的全景式敘事,加以文獻式的“正史化”敘事方式,藝術再現了這場戰役的殘酷悲壯。
(一)高層視點:戰事視野,果敢決絕
水門橋的地理位置獨特,位于朝鮮古土里以南5.6公里,懸空連接兩座山體,就橋面而言,為單車道,橋的跨度為8.8米。其坐落處建有水力發電站,橋下有4根輸水管道。水門橋是美軍唯一可通過的路,對于敵我雙方來說至關重要。時任第9兵團司令員兼政委的宋時輪下令:“即便是有天大的困難,也要不惜一切代價把水門橋炸掉,將美陸戰一師阻隔在原地,予以全殲。”《長津湖之水門橋》在高度還原歷史的基礎上,以宋時輪的視角在開場便強調了水門橋之戰的重要性,這注定是一場充滿艱難及犧牲的硬仗。
據《宋時輪傳》及相關史料記載,1952年秋,司令員宋時輪在歸國前,面朝長津湖方向,脫帽彎腰并深鞠躬,待起身后戴帽行軍禮,隨行人員發現他在起身時早已淚流滿面。在《長津湖之水門橋》中,這個橋段也得到了還原。面對長津湖方向,宋時輪感慨萬千,緬懷保家衛國英勇犧牲的英雄們。那一瞬間,他的背影,宛若定格,深深印入受眾心田。今日的盛世繁華是無數英雄流血犧牲換取的,影片以此點燃了中華兒女潛意識中的那把火,致敬英雄,傳遞紅色精神。
(二)基層連隊:浴血奮戰,無畏犧牲
從敘事學角度看,敘事視角是指敘述者觀察與展開敘事的角度。基層連隊是《長津湖之水門橋》中的“集體主角”。伴隨著敘事的不斷推進,基層連隊逐步形成敘事話語,用以解釋及豐富劇情,讓受眾更有代入感。在大雪紛飛的惡劣天氣下,七連靠步行前進。冰雪伴隨著狂風肆意席卷著,雪渣飛濺進戰士們的眼中,讓人睜不開眼。在這個過程中,不斷有人掉進雪坑,被救出來后,大家相互攙扶著步履艱難地繼續前行。
除了惡劣的天氣之外,還有雙方軍事及工業力量的懸殊。在片方發布的英雄原型特輯中,志愿軍老兵郭榮熙表示:“美國人是機械化部隊,我們是土槍部隊。”在《長津湖之水門橋》中,還原了真實歷史的殘酷,志愿軍在無增援補給、無重器火力的情況下,不斷執行炸橋任務。當七連趕到水門橋時,發現九連已經實施了一次炸橋任務,但失敗了。帶領九連的談子為在山洞里與七連戰士共同商議對策,面對時下的處境,他堅定地說:“哪一場仗不難打?越難,就越要打!”身經百戰的談子為在負傷后犧牲,影片再次響起他的吶喊:“沒有凍不死的英雄,更沒有打不死的英雄,只有軍人的榮耀!”正是這樣英勇無畏的軍人們用鋼鐵意志頑強戰斗,為保家衛國視死如歸。
導演通過鏡頭營造氛圍及壓迫感。作為電影語言的組成部分,鏡頭、畫面在此功效顯著。影像符碼的能指和所指是同一的,每個影像能指直接指向一個具體的人、事、物,它們不是在相互對立中獲得意義,而是從直接的反應中獲得——所見即所得②。從戰士角度仰拍的水門橋十分險峻,無形之中增添了它的無可戰勝之感。美軍占據的制高點,F-80戰機用75加侖凝固汽油彈進行燒山,殺傷效果極大,手段極其殘忍。相比美軍的重機槍、迫擊炮、火箭炮等重武器,志愿軍的裝備不但少而且落后。在冰雪之中,志愿軍不僅忍受著酷寒,還時刻防備著敵機的轟炸。當槍林彈雨傾瀉而下時,無數戰士們的鮮血染紅了白雪。汽油彈和噴火器讓前一秒還處于戰斗中的志愿軍瞬間變成了火人,在熊熊烈火之中喪生。鏡頭所傳遞的既視感極具心理沖擊力。在冰寒火焰兩重天里,戰爭的殘酷、艱難以及志愿軍的無畏犧牲都盡顯無遺。
(三)美軍視角:裝備精良,工業發達
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一書中明確了“自我意識”的概念,并強調“他者”對于確定“自我意識”的重要性。“他者”是基于真實的文化差異而通過話語建構起來的,其重要功能便是以“他者”來強化對“自我”的認同③。在《長津湖之水門橋》中,將美軍的“他者視角”與“自我視角”相結合,全方位呈現水門橋之戰。
在水門橋戰役后期,志愿軍手里的武器僅剩1顆手雷、3把槍和幾十發子彈。而美軍方面,30挺機槍、105毫米榴彈炮彈、60毫米迫擊炮等武器均為嶄新配置且數量豐富。在朝鮮戰場中,美軍還投入了H-13、H-23、H-19直升機,與志愿軍的武器裝備形成了強烈對比。正因如此,美軍擺出了狂傲的姿態,認為“問題不大”。志愿軍受傷后吃的最好東西是從美軍那里繳獲的黃豆罐頭,且是已經凍成冰坨的;而美軍的指揮官喝著咖啡,聽著音樂。通過雙方懸殊的對比畫面,從側面描寫了志愿軍艱苦的作戰環境。面對志愿軍小分隊的炸橋行動,第一次,美軍及時整修完畢;第二次,美軍工兵部隊架設好一座鋼制車轍橋,可供坦克M26通行;第三次,美軍利用日本三菱重工制造了鋼材質的橋梁套件,僅用一天就恢復通行。面對美國的重工業與機械化,志愿軍不畏犧牲再次炸橋,浴血奮戰。美軍準備撤離前,匆匆將死亡戰士集體就地埋葬,在離開時指揮官致哀,并說道:“merry christmas(圣誕快樂)。”這與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先前的圣誕節計劃相呼應,是戰敗的預兆。
二、鏡像與延展:微觀敘事與多重維度
意大利歷史學家卡洛·金茲伯格等人提出微觀史學,這是一種“以縮小觀察規模、進行微觀分析和細致研究文獻資料”的歷史研究方法。把歷史看作無數個體交往活動的歷史,個體終于獲得了歷史敘事的合法性,個人化視角成為作家觀照歷史的普遍視角,最終導致元歷史敘事神話被顛覆,分裂為無數歷史個體的微觀敘事④。《長津湖之水門橋》打破了以往主流大片的宏觀敘事模式,采用宏觀敘事與微觀敘事相結合的方式,打破以往單個英雄塑造方式,將鏡頭對準多個士兵,用個人影像豐富敘事。微觀敘事用“大背景、小人物”的方式拉近影片與受眾之間的距離,加強貼近感和沉浸感,拓展影像藝術的創造空間和維度。與此同時,個體敘事所迸發的多元情愫更容易得到受眾群體的認同和共鳴。
(一)微觀影像:宏大歷史的具象解構
“解構”概念來自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一書中的“deconstruction”一詞,原意為分解、消解、拆解等,法國哲學家雅各·德里達在這個基礎上補充了“消除”“反積淀”“問題化”等意思⑤。《長津湖之水門橋》在把握宏大歷史精神內核的基礎上,將原有內容和影像元素進行拆解,以微觀視角予以連接,輔助敘事,以情節拓展電影藝術內涵空間,增強情感張力。
作為前作,《長津湖》的劇情及人物角色早已深入人心。在續作《長津湖之水門橋》的開場中,七連與炮兵營匯合,楊營長的一句“老雷呢?”讓原本還在調侃逗笑的伍千里瞬間沉默。戰爭的犧牲、隊友的離開,在開場便埋下了悲情。志愿軍在裝備不足的情況下,多數裝備均為繳獲美軍所得。當楊營長辛辛苦苦搶來的炮被美軍摧毀后,伍千里吆喝著要去幫他搶炮。在戰場上,楊營長右手被炸掉了四根手指,他單手拉響了炮彈,大聲喊著:“伍千里,你再給我搶四門炮來!”一根手指一門炮,他在充滿斗志的吼聲中繼續投入戰斗。關鍵時刻救了余從戎性命的鋼盔是在下碣隅里之戰結束后,從美軍手里繳獲的。就連伍千里使用的M1911A1手槍也是談子為在新興里戰斗結束后繳獲并送給他的。這些細節的描寫將志愿軍在武器極其短缺的情況下奮力抗敵的英勇充分展現出來,令人動容。
影片用特寫鏡頭將志愿軍凍得烏青的臉龐,眉毛、睫毛、胡子上掛滿的冰霜,負傷后凍傷的結痂一一予以呈現。在戰爭之中,他們首先面對的是惡劣氣候帶來的凍,當然還有饑餓。在饑寒交迫且露宿雪地時,戰士們仍然保持著昂揚的斗志,這種氣勢剛硬十足卻也令人心疼萬分。面對傷亡,他們一邊顫抖著雙手清理著可用的子彈,一邊用僅有的紗布對能活下去的戰友們施救。他們用血肉之軀,頂著槍林彈雨,在各方面都相對匱乏的情況下打贏了這場硬仗。
影片以微觀視角,細膩如絲地刻畫了鮮明立體的諸多“小我”形象。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這些個體平凡卻偉大,他們的命運及情感具有代表性。影片打破了以往戰爭片“千人千面”的人物塑造模式,以微觀敘事具體呈現了每個人身上的故事,其“個性”因歷史背景構建為“共性”,進而成為宏大敘事的組成部分。細節相對于整體而存在,亦具有整體宏觀上的意義。微觀敘事中的內心鏡像通過日常化、微觀化、內心化的敘事策略將武戲文拍,既有宏觀全景又有情感迸發。
(二)更唱迭和:相互呼應與伏延千里
《長津湖》伴隨著新興里戰斗而進入尾聲,《長津湖之水門橋》的開場情境便是下碣隅里機場,兩部影片在此處的銜接是導演用規定性情境將受眾代入戰場,更像是無聲的開場白,宣告水門橋之戰即將拉開帷幕。
《長津湖之水門橋》中,伍萬里在暴風雪中跟隨大部隊前行時戴了一個護目鏡,他俏皮地對著伍千里向上推了推護目鏡。在《長津湖》中,亦師亦父的雷公在犧牲前將自己的護目鏡送給了伍萬里,他全程佩戴,暗示雷公及其精神永遠與大家同行。同樣,作為雷公炮排的戰士,何長貴在水門橋之戰中表現得異常勇猛,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證明沒有給雷公和炮排丟臉。
關于伍萬里打水漂的鏡頭共出現兩次,同是在家鄉的河邊打水漂,卻早已物是人非。第一次打水漂出現于《長津湖》片頭,恰逢伍千里送伍百里骨灰返鄉,伍千里提及“哥說,讓我幫幫他”。第二次出現于《長津湖之水門橋》片尾處,伍萬里帶伍千里骨灰回家,在生死訣別之中,伍萬里與已經凍成冰人的伍千里相擁而坐。伍萬里完成了從毛頭小子到一名稱職的戰士的蛻變,兄弟三人從軍亦是賡續與傳承。
符號是攜帶意義的標記。物象符號是存在于畫面語言中的重要表達⑥。分析影片中的符號化影像能指,可得出其深層次的所指意義。紅圍巾作為兩部電影均出現的物象符號,透過影像的展面可透析其內涵意義。在《長津湖》中,紅圍巾是七連臨行前一名女醫護人員拋給伍萬里的。伍千里斥責伍萬里戴紅圍巾,理由是不能給敵人當靶子。伴隨著張小山的犧牲,伍萬里把紅圍巾深深地藏進了衣服里。可以說,紅圍巾對他意味著懵懂的情竇初開和剛剛結識便失去的友情。在《長津湖之水門橋》中,水門橋不遠處樹上飄揚的紅圍巾讓張營長發現了七連唯一的幸存者伍萬里。在一片白茫茫之中,那抹紅分外鮮明。此時的紅圍巾則背負著犧牲的戰友的囑托與遺愿,更是革命精神的延續。
(三)俠之大義:英雄史詩與家國同構
在抗美援朝戰場上,“血染沙場氣化虹,捐軀為國是英雄”正是對無數先烈最直白的表述。受中華傳統文化影響,電影中的“英雄”曾一度固化,形成了固定的形象范式,而《長津湖之水門橋》憑借敘事重新詮釋了何謂“英雄”,以小人物構建大歷史,促成“構建身份→個人認同→集體認同”的轉化。美國政治學家薩繆爾·亨廷頓將認同意識定義為“自我意識的產物,是一個人活在一個群體的自我認知”⑦。個人認同強調主體在自我認知與定位中明確身份,而集體認知指的是特定群體在特定文化語境、社會背景和意義建構中所構建的群體性身份認同⑧。影片對“英雄”的詮釋由個人認知延伸至精神內核:在部署完新的炸橋方案后倒地犧牲的談子為,在管道中拉開戰友卻用自己身體堵住手雷彈的戰士,為炸毀美軍坦克無畏犧牲的平河,已然被燒成火人卻因引開敵人火力而欣慰的余從戎,雙眼已近失明卻開車沖向敵人的梅生,面對敵軍環伺卻不屑一顧的伍千里……這些英雄以史詩般的豪邁構建了集體認知的精神譜系。
家國情懷是人對與自己密切相關的集體如家庭和國家眷念與愛戴的心境,以及對其包涵與寬容的胸懷,是個人對于家庭和國家的一種積極的思想意識、情感認同和自覺擔當的意愿,是一種道德評價和道德選擇⑨。《長津湖之水門橋》將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融合為偉大歷史的影像記憶,家國敘事中情節發展更為凝練、節奏緊湊,將普通人的情感與家國情懷融為一體,傳遞民族共同體意識,詮釋家國情懷的價值意蘊。
第一次炸橋結束后,連隊在清點戰士人數時,那些從未在影片中正面出現過的戰士犧牲了,只留下名字:梁有田、傅豐收、向春耕等等。從名字來看,不難猜想他們多來自農家,用先前伍千里的話來解釋就是,國家給我們分地分錢。新中國成立伊始,國家剛剛開始走向正軌和發展。在水門橋戰役中,志愿軍保家衛國,捍衛了新中國的尊嚴。在他們身上,“家”與“國”同體,不可分割。
在第三次炸橋時,梅生在已然負傷的情況下,為給伍千里吸引火力,開著裝滿炸彈的裝甲車從山坡上沖向美軍。他嘴里咬著女兒的照片,那是半張殘留照,承載的是他對家國的深厚思念。導演用閃回的方式呈現了臨行前梅生妻子送行的場景。梅生說:“等回來,一定要好好教教囡囡的數學。”這是一位父親對女兒最深情的告白,而回響在耳邊的那句話——“這場仗如果我們不打,就是我們的下一代要打。我們出生入死,就是為了讓他們不打仗”——將家與國同構,表現出烈士們舍小家為大家,用鮮血和生命捍衛家國平安的民族精神。
三、書寫與傳遞:情感迸發與賡續傳承
《長津湖之水門橋》通過敘事激發共情,使受眾產生情感認知體驗,通過敘事提升了情感張力。這種共情感是受眾與劇中情感形成同構而產生的,達成共情共力的審美效果。該片將全景與微觀敘事、情感驅動、戰爭影像奇觀和人文主義價值糅合互協,建構出商業類型片與主流價值觀并融的敘事范式。
(一)兄弟之情:生死與共,同仇敵愾
負責執行任務的七連戰士們長期一起訓練、作戰,彼此之間的融合度和情感是團結奮戰、勇猛頑強的寫照。如果說伍千里和伍萬里的兄弟情在影片中得到了升華,那么對整個七連的戰士們來說,部隊就是他們的家,他們勝似親兄弟,所呈現的是中華兒女團結起來的手足情。
伍千里與炮營的楊營長相遇時,調侃之余非常自然地奪過了他嘴里的煙,自己吸了幾口后又還給了對方,這個看似隨意且親和的細節凸顯了戰友并肩作戰的兄弟情。同樣是煙,還出現在一個小雪堆上,伍千里用它祭奠犧牲的戰士們。談子為犧牲時,伍千里強忍悲痛,將他嘴上尚未熄滅的煙取下,用手將它捻滅。有關“煙”的這些細節,承載了無言的兄弟情義,隱匿于敘事之中,把戰士們將悲痛化為力量繼續奮斗的精神表現得極其含蓄卻富有情感張力。
戰爭的磨煉讓伍萬里越發成熟。在第二次炸橋前,伍萬里對伍千里行軍禮并大聲稱呼“連長”。伍千里則以哥哥的身份關心地叮囑道:“以前不讓你亂跑是怕你惹事,今天你想怎么跑,你自己定。”這是兄弟情深,也是哥哥對弟弟的認可與鼓勵。在戰爭結束后,伍萬里返鄉時曾一度出現幻覺,伍千里微笑著站在他面前。當幻影結束后,他噙著淚說出的那句“哥,我特別想你”將兄弟情深推向了高潮。
在準備實施炸橋行動之前,平河告知伍萬里:“百里連長是為了掩護我才犧牲的。”平河一直心懷對伍千里和伍萬里的愧疚與自責,又或是,他怕此次不說便再無機會。影片對這個情節的刻畫,多采用近景或特寫,用以表達人物的復雜心情。伍萬里的回復是:“百里是我哥,你也是我哥,整個連都是我哥。”這種在炮火紛飛中攜手同行的兄弟情義令人感動。在之后的戰斗中,平河為了炸橋,抱著炸藥包沖到了敵軍的坦克之下,幾次試圖拉爆炸藥包均未成功。伍千里眼睜睜地看著平河被坦克拖拽且不斷被碾壓,卻無法營救。忍著劇痛的平河使出最后的力氣大吼:“開槍!”在伍千里開槍引爆炸藥包的那一瞬,特寫鏡頭在呈現其面部表情的同時,采用了定格,將人物內心的傷痛及五味雜陳的情緒表現無遺。
在眾人沉睡之時,余從戎獨自一人爬上了山頂,眺望著遠處被白雪覆蓋的高山,那是祖國的邊界。“永別了,七連的兄弟們。”在深情告別之后,他用機槍掃射吸引美軍的注意力,成功引開了火力。在被燃燒彈擊中后,余從戎仍堅持用最后的力氣努力向遠處奔跑,用生命保全了七連戰士們的安危。
(二)愛國之情:赴湯蹈火,舍身為國
“心系天下”是中華民族的歷史記憶,是儒學的文化基因和價值追求,是個體對國家認同感、歸屬感和使命感的系統表述⑩。從歷史層面看,心系天下的愛國意識由來已久,是“家國情懷”的表現方式。《長津湖之水門橋》通過敘事情感的外現,將愛國情懷作為精神力量予以傳承。
在敵我雙方經濟、軍事和工業化懸殊巨大的情況下,作為沒有出國作戰經驗的抗美援朝戰士們,他們有的只是一腔愛國熱血。這種高度的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相融,形成了獨特的民族精神。在這場戰爭中,無數烈士用鮮血贏得了最后的勝利,更給當時經濟相對落后的中國人上了一課。影片中,他們不知道如同膠一樣的東西叫口香糖,因為不懂英文而誤用了煙霧彈,他們難以想象美軍可以用如此之短的時間修復橋面。余從戎盯著直升機感慨地說:“我們多久也能有這樣的裝備?”伍千里的回答是:“遲早的事。”這是因愛國而脫口而出的答案,是伍千里對祖國未來繁榮昌盛的堅信不疑,也是愛國情懷激發的民族自信。
影片用詩意的鏡頭呈現了祖國的方向。當陽光灑在山間時,戰士們面朝祖國的方向行軍禮,高呼:“新中國萬歲!”這體現了無數戰士內心的愛國情懷和保家衛國的戰斗意志。伴隨著推鏡頭呈現出的戰士面部,是一個個夾雜著冰雪與血痂的混合體。為了祖國的和平,他們做好了向死而生的準備。《長津湖之水門橋》是以冷色調為主的影片,但片中多次出現戰士們凝望太陽升起的情景,這是該片少有的暖色調。廣大戰士內心深處對于此戰的意義非常明確,強烈的愛國之情是他們克服艱難、不畏犧牲的根基,這是每個有血有肉的個體靈魂深處的精神支柱。
(三)賡續傳承:精神歷史彌新與不朽
1950年是新中國的第一個虎年,志愿軍一邊唱著“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一邊踏上了抗美援朝的戰場。作為一線作戰的中國戰士,他們用生命完成了保家衛國的任務,換來了和平與安寧,保障了祖國的飛速發展。時隔72年,《長津湖之水門橋》選擇在2022年(虎年)上映,一方面是呼應了1950年的虎年,另一方面是觀照時下,不是歲月靜好,而是先烈們為我們負重前行。抗美援朝戰爭中志愿軍體現出的不畏強敵、團結一致、克服艱難、無畏犧牲的精神在新時代亦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在影片臨近尾聲時,第9兵團在火車站集結。在統計實到人數時,伍萬里孤身一人,但依舊用洪亮的嗓音報到:“第七穿插連,應到157人,實到1人。”一句簡短的匯報顯得萬般豪邁。此刻的他承載著156人的期盼與囑托,看似單薄的身軀見證了英雄烈士們的功勛與風范。這也令正準備離開的宋時輪轉身停下。當宋時輪問伍萬里有什么愿望時,他答:“恢復七連建制。”這個愿望是對七連精神延續的渴望,更是對用生命書寫悲壯之歌的烈士們的生動詮釋。
從傳播學來看,電影具有文化傳播的功能。對外而言,《長津湖之水門橋》成功探索出講好中國故事的范式,實現了中華文化與中國精神的跨域傳播,引導世界對中國形成正確的認知;對內而言,《長津湖之水門橋》用影像的方式再次重溫這段歷史,旨在感召時下的年輕一代,賡續紅色血脈。影片所折射出的愛國主義、革命英雄主義、革命樂觀主義和為和平奮斗的國際主義精神深深地感染了受眾。今天的祖國繁榮昌盛,山河無恙,這是紅色精神傳承的結果。吾輩須緊握接力棒,捍衛盛世之中華。
注釋:
①[美]J.希利斯·米勒.解讀敘事[M].申丹,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90.
②鄧尚,金妹.電影·語言·現實——再論麥茨第一電影符號學理論[J].文藝論壇,2020(01):100-108.
③劉文明.全球史研究中的“他者敘事”[J].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03):45-51.
④袁園.宏大歷史的碎片化解構——當代歷史小說的微觀敘事[J].當代文壇,2015(07):111-117.
⑤林隆強.演播廳研究——電視綜藝節目的一個角度[D].福州:福建師范大學,2017.
⑥李彬.傳播符號論[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87.
⑦[美]塞繆爾·亨廷頓.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M].北京:新華出版社,2005:34.
⑧李強,劉澤溪.主旋律儀式下的集體記憶建構[J].電影文學,2021(09):8-14.
⑨張軍.共同體意識下的家國情懷論[J].倫理學研究,2019(03):113-119.
⑩馬慧,梁向明.家國同構:儒學中“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化基因與話語體系[J].廣西民族研究,2021(05):77-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