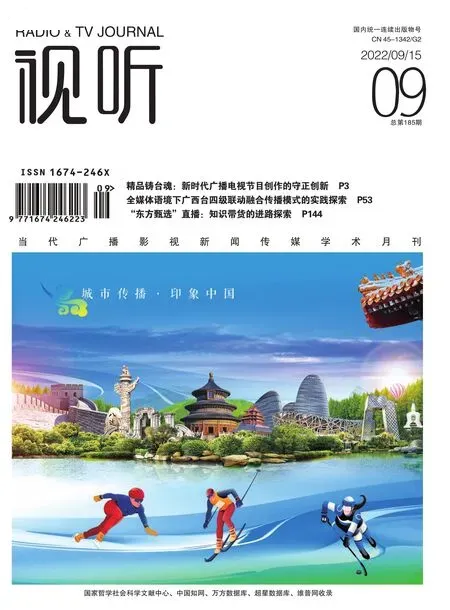文化自信視域下的中國主旋律電影敘事研究
王立斌
文化自信是一個民族的根與魂。當今中國立足于全球化背景下,在經濟、科技等外在實力引人矚目的同時,內在的文化根基的繼承與發展也不容忽視。“體現一個國家綜合實力最核心的、最高層的,還是文化軟實力,這事關一個民族精氣神的凝聚。我們要堅持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還有一個文化自信。”①在大力倡導文化自信的今天,影視以其自身獨特的表現形式和傳播特性,成為將中國文化進行海外輸出的最有力的媒介之一。
1987年,國家廣播電影電視部電影事業管理局提出“弘揚主旋律,堅持多樣化”的口號。在各種電影類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今天,主旋律電影的敘事策略也進行了改革和創新,拋棄了以往全面突出正面英雄人物的塑造范式以及展現正面戰場的敘事策略,以符合消費社會下受眾的審美興趣為主,在弘揚主流價值觀的同時對主旋律電影進行了敘事創新,從而擴大受眾群體。2019年的國慶獻禮片《我和我的祖國》延續了主旋律電影“弘揚主旋律,堅持多樣性”的創作方針,濃郁的愛國情懷盡收眼底。在主旋律電影發展道路中,改革和創新成為電影人在宣傳愛國主義精神時的一致目標。該片突破了以往主旋律電影塑造“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形象,運用獨特的敘事策略,實現了敘事空間和市場空間的雙贏。在2020年國慶檔上映的《我和我的家鄉》被認為是《我和我的祖國》的兄弟篇,兩者之間有相同之處,同時也體現出鮮明的進步傾向。兩部電影都成功地為觀眾傳達出中國精神和濃郁的愛國情懷。但從創作方面來說,相比于《我和我的祖國》,《我和我的家鄉》更加貼近觀眾的現實生活,既展現了真實的社會生活環境,又探討了存在于普通民眾身邊細小動人的事件。2021年的國慶獻禮電影《我和我的父輩》將主旋律思想與家庭內部的父子倫理相結合,在傳達時代精神的同時,具有現代性倫理思想的精神內核也得以突出呈現。本文以《我和我的祖國》《我和我的家鄉》和《我和我的父輩》三部主旋律電影為例,分析文化自信視域下主旋律電影的敘事策略。
一、從英雄人物到普通民眾的敘事主體嬗變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強調:“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生動活潑、活靈活現地體現在文藝創作之中……要把愛國主義作為文藝創作的主旋律。”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主旋律:“要牢牢把握正確輿論導向,唱響主旋律,壯大正能量。”②不論是20世紀90年代的《七七事變》《井岡山》,還是21世紀的《集結號》《湄公河行動》,均以革命英雄人物為核心展開宏大敘事,進而形成了英雄為國而戰并奪取勝利的創作范式。
近年來,《我和我的祖國》《我和我的家鄉》《我和我的父輩》等影片另辟蹊徑,摒棄了以英雄人物為主角的宏大敘事,更多地關照普通民眾,描繪他們身上的閃光點,以及他們對社會做出的貢獻。
管虎導演的《前夜》講述了開國大典升旗儀式前夜的故事。電動旗桿設計安裝者林治遠、護旗手老方等千千萬萬參與開國大典的工作人員和人民群眾齊心協力,攻克一個又一個難關,最終保障五星紅旗順利飄揚在天安門廣場上空。這段故事既沒有展現宏大的敘事背景,也沒有塑造高大的英雄形象,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個鮮活樸實的普通民眾。他們為了開國大典的順利進行,都在奉獻著自己的一份綿薄之力。影片通過修繕旗桿過程的生動演繹,展現出社會普通民眾的愛國之心。
張一白導演的《相遇》講述了普通工作人員為原子彈研發工作奉獻自身的故事。戰爭題材中的英雄形象在此段中不復存在,轉變為以在原子彈實驗中受傷的研發人員為主要描寫對象。影片將具有崇高性的英雄形象降格為現實生活中富有各種情感的普通階層進行刻畫,不僅拉近了與觀眾之間的心理距離,還喚起觀眾的情感共鳴。影片通過以小見大的敘事策略,從普通民眾的系列行動來體現社會的進程與祖國的發展,弘揚深厚的愛國主義精神。
《我和我的家鄉》則更進一步體現出此種創作傾向。影片塑造了“北京好人張北京”“偽科學家黃大寶”“癡呆教師范教授”“打腫臉充胖子的喬樹林”“放棄留學去扶貧的馬良”五個人物形象。在這五個故事片段之中,每一個人物形象都與以往主旋律電影中英雄模式化、完美主義化的人物形象截然相反。該片中的五個主要人物全部為普通人,影片將人物的弱點與缺點注入其中,以此塑造出五個“圓形”的人物形象。與此同時,觀眾跟著人物進入劇情時,能夠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每一個人物所傳達的真情實感。影片中既呈現出張北京與表舅在為了省手術費而騙取醫保的搞笑過程中所體現出的親情價值,也傳遞出村民黃大寶與村長等人為了家鄉發展而隱瞞“善意的謊言”過程中所展現出的友情價值,還蘊含著一批已長大成人的同學為了滿足范老師最后的愿望,克服困難,還原當年上課情景的師生情誼,同時也通過講述畫家馬亮放棄留學資格轉而下鄉扶貧,妻子秋霞由最初的反對到兩人達成共識,體現出愛情價值。與《我和我的祖國》中的國家重大歷史時刻,以及人物在重大歷史背景下付諸的行動相比,《我和我的家鄉》中的人物從現實生活的時間脈絡中主動行動,淡化了時代背景對人物的影響,強化了人物的自覺性與主動性,使人物形象擁有了現實生活中普通人物的性格特點,通過劇情發展體現出親情、愛情、友情、師生情的社會生活情感,使主旋律思想的傳達更加深刻與客觀,以真實人物的生活現實為觀眾傳遞出最為真切的思想價值。
《我和我的父輩》將主旋律思想與父子倫理思想相結合。在影片傳達主旋律精神的同時,中國的倫理思想也通過父子倫理關系的建構過程進行了表達,將中國文化植根于主旋律電影的創作之中。《乘風》中,馬仁興與馬乘風在父子倫理關系的基礎上被賦予了戰友的身份。馬仁興對兒子所說的“我不怕你死,我怕的是你不死”這句話,看似違背了傳統“父嚴子孝”的倫理思想,但這正是作為父親的馬仁興對兒子所追求的“舍生取義”倫理思想的鼓舞與激勵,從而對處于現代化作戰場景中的中國傳統倫理思想賦予了新的解讀方式。《詩》片段雖然以在制造人造衛星工作中鞠躬盡瘁的夫妻為主要人物,但影片并沒有著重描寫人造衛星的制造過程,而是把筆墨更多放在家庭倫理關系的表達上,并塑造了具有當代倫理思想的新女性形象。《鴨先知》和《少年行》通過戲謔的表達方式展現了兩對父子之間的故事,使受眾于笑鬧中體會到中國父子倫理思想的內在價值。總的來說,在文化自信的指導下,主旋律電影將創作主體轉向普通民眾,使主旋律思想與中國傳統倫理思想得到普遍表達。
二、以生活溫情接替戰場的宏大奇觀
文化自信是指要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保持自信心。這要求我們要善于把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和發展現實文化有機統一起來,緊密結合起來,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繼承③。電影《紅河谷》中穿插了大量的西藏人文景觀來增強影片的神秘氣氛和傳奇色彩;《大決戰》以鴻篇巨制的形式,全方位、立體化地展示了三大戰爭強大的視覺沖擊力,使影片具有恢弘的歷史感與文獻感。與之相反,在《我和我的祖國》中沒有宏大的奇觀化展現,而是將重點放在對社會生活溫情的細膩描繪上,以貼近受眾生活的敘事策略,將中國精神以生活化的方式加以傳播。陳凱歌導演的《白晝流星》以兩個叛逆青年為敘事主角,在老李的拯救下,他們完成對生命的認知體驗,并從迷惘落魄中重新找到了生活的目標。從老李的庇護與教導到哈扎布、沃德樂兩人的反叛與悔改,每一個生活細節中都體現出真實細膩的溫情存在,展現了“言傳身教”的中國文化與“知恩圖報”的倫理價值。
以往的主旋律電影大多反映中國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中的重大社會事件與歷史問題,與人們的現實生活有一定的差距。《我和我的祖國》同樣展現了中國發展中的重要轉折點,但是通過人物形象的平民化處理縮短了影片與觀眾之間的距離。《我和我的家鄉》不僅全面聚焦普通人,而且沒有繼續將中國發展進程中的重大社會歷史事件作為故事背景,影片體現的是發生在人們身邊的時事動態,因而使得主旋律電影更加具有現實主義風格,并以此獲得觀眾的認可與共鳴。在《回鄉之路》中,主人公閆飛燕被設置為帶貨主播。在網絡飛速發展的今天,賣貨網絡化已經成為普遍的現象,每一個網絡用戶皆可在日常生活中接觸到這一購物模式,因而閆飛燕這一人物形象能夠深入人心。直播帶貨為家鄉的農產品銷售提供了更為直接的渠道,不僅完成了影片的敘事使命,而且觀眾在閆飛燕回歸家鄉、造福家鄉的行動中體會到她回報家鄉的“故土難離”之情。《天上掉下個UFO》中,由于交通的封閉化,村長、黃大寶等人運用惡作劇的方式來緩解交通封閉所帶來的家鄉經濟停滯現象。看似無厘頭的種種行為實則表達著每一個人心中建設家鄉的美好愿望,而這一愿望實現的前提便是努力實現交通信息化。影片所展現的交通問題是每一個人生活中必須面對的問題,反映了某些地區的真實社會狀況,并得到受眾的深切共鳴。整部影片中沒有壯觀的戰爭場面,也沒有宏大的敘事視野,但以普通人的現實生活為主要講述內容,再通過真情實感與優缺點集于一身的“圓形人物”進行演繹,使得主旋律思想的傳達更加真切、客觀。
《我和我的父輩》中的《鴨先知》在展現趙平洋和兒子冬冬隱瞞妻子偷取家中存款用來拍攝藥酒廣告的系列行動中,傳達出“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的倫理價值,將中國文化中的傳統倫理思想進行了生活化的演繹。《少年行》講述了小小與假爸爸邢一浩之間的故事。在運動會中,兩人以假父子的身份亮相,并在機器人邢一浩的超能力加持下取得運動會冠軍,通過惡搞戲謔的表達方式將父子倫理思想進行了符合當代審美特征的現代化詮釋。在倡導文化自信的今天,主旋律電影將主旋律思想置于生活溫情之中加以展現,并以現實主義的創作方式在電影中注入了具有時代性的文化內涵與倫理價值,從而實現了主旋律思想與中國文化的融會貫通。
三、從突出塑造個體轉向深入表現集體
“從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從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從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三突出原則,曾經是中國所有文學藝術創作的唯一創作理論、標準和法則,對影視創作也帶來了影響。在三突出原則的影響下,電影中的主人公多處于被拯救、被幫助的地位,從而與觀影者產生距離感,使得影片中的主人公無法得到受眾的身份認同與情感認同。“不是說這個人物不可信,單調的人物的確存在,但是作為主角,他很乏味。”④在文化自信日益增強的今天,主旋律電影擺脫了單一化、絕對化的人物形象塑造,開始轉變為集體化的深入表現。
隨著市場化進程日益加快,文化自信視域下主旋律電影的改革與創新成為現代電影人最為關注的任務。以往主旋律電影中經常出現“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形象,驚心動魄的戰爭場面,宏偉壯闊的時代背景。而《我和我的祖國》打破了傳統的敘事范式,采用以小見大的新型策略,從普通人物的普通生活入手,細膩真實地展現了主流意識形態引導下普通民眾的生活變化,以及不同階層的民眾為國家發展所做出的積極貢獻,進而宣揚了愛國情懷。由寧浩導演的《北京你好》以一張門票為線索,通過塑造主人公張北京對奧運會門票從堅守到轉贈的變化,展現了普通出租車司機的溫暖情懷,并且通過汶川小男孩在開幕式上的采訪,傳遞出普通市民為祖國建設所做出的貢獻,體現出主流意識形態正確引導下的“心慈好善”與“恪盡職守”的中國倫理思想。
相對于《我和我的祖國》,《我和我的家鄉》中的人物以平凡的市民為主要描寫對象,傳達出與普通觀眾更為貼近的社會價值。例如,《北京好人》講述了張北京為了給表舅看病而兩人互換身份來騙醫保的搞笑過程。醫保在現實生活中關系到每一個人的就醫問題,因而通過兩個小人物的嬉笑怒罵以及貼切現實的故事情節,使觀眾在感受笑料之余,無形之中接收到影片所要傳達的“急人之難”的思想。電影中的每個人物形象都是現實生活中隨處可見的普通人,觀眾在進行審美接受時也會因人物形象的群像化而感到身份認同與情感認同。《我和我的父輩》更是著重描寫了具有普遍性的父子關系的建構過程,既塑造了作戰戰場上的戰友父子,又展現了現代社會中的家庭父子關系。影片通過父子群像的刻畫,向觀眾傳達了符合當代適應性的父子倫理思想。
總而言之,文化自信的合理性建構不僅需要文化主體的奮斗,還需要全體人民的共同努力。文化自信指導下的主旋律電影不僅將表現主體全面定位于普通人,而且在此基礎上轉向集體主義式的群像塑造,希冀以此來面向更廣泛的受眾群體,從而建構文化自信,獲得強有力的群眾支撐。
四、結語
“文化功能不再是被動適應轉型社會,而是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各種社會領域逐漸一體化的新階段中發揮文化的濡化功能。”⑤影視媒介因具有獨特的直觀表現力與高效的傳播特性,成為當代中國文化對外輸出的強有力工具之一。近年來,我國電影生態話語逐步由“娛樂至死”向“寓教于樂”回歸,具有國家意識形態載體和文化消費品雙重定位的主旋律電影借助主流文化機遇強勢崛起。主旋律電影是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建構的重要載體,也是中國從“電影大國”邁向“電影強國”的重要抓手⑥。在文化自信日益增強的背景下,中國主旋律電影成為弘揚主流價值觀和傳播中國文化的重要陣地。主旋律電影在以文化為內核的同時,還應注重外在的敘事策略。只有將良好的文化根基與符合當代審美特征的電影敘事策略相結合,才能將富有中國文化特色的電影作品傳播至海外,擴大受眾群體,獲得良好的傳播效果。
注釋:
①習近平.堅守發展和生態兩條底線 切實做到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同步提升[N].貴州日報,2014-03-10.
②邢香菊,李斌娟.新時代主旋律電影的文化自信及表達策略[J].大眾文藝,2020(11):163-164.
③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④[美]羅伯特·麥基.故事[M].周鐵東,譯.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1:118.
⑤張梧.文化自信的理論透視與當代建構[J].貴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05):1-9.
⑥周子琪.新型電影生態下新主流電影的范式創新:從“硬性宣教”到“軟性詢喚”[J].視聽,2022(07):2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