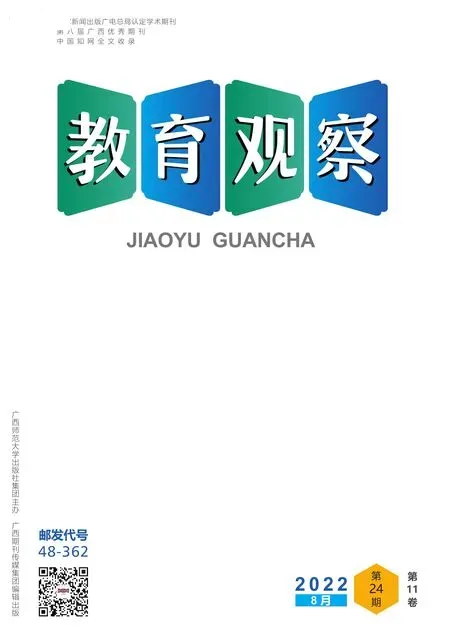大班科學活動中幼兒提問現狀的調查研究
——以A園科學活動中幼兒提問與教師回應為例
劉麗華
(南寧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廣西南寧,530299)
提問是幼兒對知識的渴求和好奇心的體現,是幼兒探索世界、主動學習的一種方式,也是幼兒解決矛盾的重要途徑。提問與反饋是常見的師幼互動方式。王英會認為,幼兒的提問行為是證明他們正在思考、感知事物和現象并且努力將新信息與原經驗聯系起來的重要證據,是其正在學習的表現,是體現他們學習主體性的現象。[1]在本研究中,大班幼兒提出問題的行為被記錄為獨立事件,研究者依據設計好的觀察量表,采用非參與式觀察法跟進大班科學活動,對A園大班科學活動進行觀察,記錄幼兒提問和教師回應的情況。本研究共收集到112次幼兒提問,研究者對其進行了編碼,并利用SPSS 22.0進行數據統計,分析大班科學活動中幼兒提問的問題類型、提問時機、提問質量,分析教師對幼兒提問的回應。本研究還使用了訪談法,主要訪談組織科學活動的教師,探究教師回應存在的問題。在梳理問題的基礎上,本研究提出了一些提升幼兒提問質量的建議,以期為教師提供教學參考。
一、大班科學活動中幼兒提問的現狀
(一)問題類型
何亞柳把幼兒的問題分為常識了解型、探究求知型、情感流露型三類。[2]常識了解型問題是關于活動材料和規則、實驗步驟等的問題,如在活動開始前幼兒看到新教具會問“這是什么東西”。探究求知型問題是幼兒為滿足自己的求知欲望而提出具有探究性的問題,如幼兒提出“為什么影子會跟著我”這一問題。情感流露型問題是幼兒為表達感受和需求而提出的問題,如幼兒問“為什么老師不請我”。此外,其他型問題包括被外界因素打斷的無效提問、與當時活動無關的提問等。
本研究發現,在科學活動中幼兒提出的常識了解型問題最多,占46.4%;其次是情感流露型問題,占36.6%;探究求知型問題占14.3%;其他型問題占2.7%。這說明幼兒會在科學活動中提出各種類型的問題。
(二)提問時機
本研究將幼兒提問的過程分為導入環節、活動環節和結束環節三部分。觀察發現,在科學活動過程中,幼兒提問數量較少,更多的是教師提問;幼兒在導入環節、活動環節、結束環節提問數量占比分別為31.3%、54.5%、14.2%。由此可知,幼兒在活動環節提問的數量遠高于導入環節和結束環節。這與張魯青的研究結論一致,即基本活動中幼兒提問數量多于導入環節和結束環節。[3]
為進一步研究不同時機幼兒提問的特點,研究者將提問時機與提問類型進行交叉分析檢驗,結果發現,在不同時機,幼兒提問的類型存在差異。在導入環節,幼兒最常提出常識理解型問題,占總數的48.6%;其次是探究求知型問題、情感流露型問題、其他型問題,依次占比42.9%、5.7%、2.8%。活動環節是幼兒提問總數最高的環節,常識了解型問題、情感流露問題、探究求知型問題分別占52.5%、45.9%、1.6%,沒有出現其他型問題。在結束環節,沒有出現探究求知型問題,提問數量也在減少,情感流露型問題、常識了解型問題、其他型問題分別占68.8%、18.8%、12.5%。卡方檢驗結果顯示,在大班科學活動中幼兒提問類型和提問時機是互相關聯的。
(三)問題質量
本研究借鑒蔣梅珠等人在研究大班幼兒提問水平中引用的三級量表:低水平問題涉及識記和回想的提問;中等水平問題是幼兒對活動材料的擺放、排序、功能等方面的提問;高水平問題涉及對信息進行的整理歸納、深度推理、分析、評價或元認知表征水平的問題。[4]另外,本研究補充0分為無水平問題,即無質量問題,包括被各種因素打斷的問題、未能完整表述的問題以及其他問題。
本研究基于觀察記錄,評定問題質量分數,對幼兒提問質量的基本情況進行分析,得出結果如下:幼兒主動提出的問題屬于低水平質量的占58.9%,屬于中等水平質量的占33.9%,屬于高等水平質量的占4.5%,屬于無水平質量的占2.7%。由此可以看出,幼兒在科學活動中提出問題的質量處于較低層次的占一半以上。
本研究基于以上數據進一步探究了幼兒問題質量水平是否存在提問時機差異。統計結果顯示:低水平問題出現數量的最高峰在活動環節,其次是在導入階段和結束階段;中水平問題在活動環節提出最多,較少在導入環節出現;高水平問題數量遠低于中水平和低水平問題數量,高水平問題在導入階段占40%,在活動環節占60%。中水平和高水平問題均未出現在結束環節。卡方檢驗顯示,幼兒在科學活動中提問的時機與提問問題的質量水平相互聯系。由此可知,大班幼兒在科學活動中提出的問題的質量基本能達到高水平,但總體問題質量水平較低,而且提問的活躍性明顯出現在導入環節和活動環節,在結束環節幼兒提問的興趣不高,質量也隨之下降。
(四)教師回應
1.教師對幼兒提問的回應情況
幼兒提出問題不僅是為了獲取知識,還是為了獲得注意和認可。在幼兒眼中,教師回答自己提出的問題是對自己表現的認可。宋志紅認為,教師回應是指教師對幼兒生成問題給予適人適時適宜適度的答應。[5]本研究將教師回答幼兒問題的態度分為正向回應、中性回應、負向回應。
正向回應表現為:對幼兒的提問及時回應但不會立馬給出答案;給予表揚、肯定和鼓勵;積極幫助、耐心指導幼兒探索問題答案。例如,在一次科學活動中,A幼兒問:“老師你今天為什么拿豆芽、蘿卜來教室呀?今天要做好吃的嗎?”Q教師答:“你好聰明,認識這是蘿卜。老師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認識植物寶寶的‘身體’,你們都認識這里的哪些植物?”在上述對話中,Q教師對幼兒問題的回應屬于正向回應,不僅夸贊和認同幼兒,還啟發幼兒對問題進行思考。
中性回應表現為:重復幼兒提問,以“過一會再討論”“下次再學習”等推辭回答;直接告訴幼兒問題答案,沒有共同思考的過程。例如,B幼兒問:“老師,植物也和我們一樣有小手小腳嗎?可它們和我們長得不一樣呀。”Q教師回應:“對呀,植物也有身體組成部分,但有另外的名字,不叫小手小腳。”Q教師的第二次答應是中性回應,直接給出問題答案,表現出不耐煩的態度。
負向回應表現為:教師對幼兒提問表現出嘲諷、無奈、厭煩甚至忽視的態度。例如,C幼兒問:“那它們的身體都叫什么?這些籃子是用來干嗎的呀?”Q教師:“小朋友們快來看看這株黃豆苗,你們知道這株黃豆苗的身體是哪些嗎?”Q教師的這次回應忽視了C幼兒的提問,開啟了活動環節,這是負向回應。
本研究觀察發現,在大班科學活動中,教師表現最多的是負向回應,占比50.46%;中性回應和正向回應分別占33.03%和16.51%。由此可見,教師更多給予的是負向回應,正向回應很少。
2.教師回應后幼兒繼續發問
幼兒第一次提問后,教師的回應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幼兒是否會提出下一個問題。觀察發現,得到教師的正向回應后幼兒繼續提問的數量最多,教師正向回應與幼兒繼續發問的數量比為3∶2,教師中性回應與幼兒繼續提問的數量比為9∶1,教師負向回應與幼兒繼續提問的數量比為55∶3。由此可知,教師的回應對幼兒繼續探索產生重要影響,教師正向回應更有利于激發幼兒繼續探索問題的欲望。
二、幼兒提問的問題
(一)幼兒提問處于較低水平
教師在導入環節介紹活動的主題、材料、內容,有助于幼兒聯系相關的前經驗,啟發幼兒思考。幼兒感興趣的是活動的材料、安排內容等,因此幼兒高頻提問的是常識理解型問題和探究求知型問題。在幼兒操作遇到難題時,會提出假設、不斷嘗試、主動詢問,此階段幼兒提問數量多。觀察發現,活動中教師常詢問幼兒的實驗進展,緊跟幼兒的操作步驟,這導致幼兒更專注材料問題,較少有幼兒就實驗原理或現象本身提出探究求知型問題。結束環節是收拾材料和分享的階段,幼兒逐漸減少思考,提問數量減少。因為教師在結束環節關注公布實驗結果并收拾實驗工具,此時的幼兒更關注自己作品與他人作品的異同,急于交流分享、尋求教師贊揚或期待下一環節,所以幼兒在結束環節提問的總數量減少,最常提出的是情感流露型問題,探究求知型問題極少。
從整個科學活動來看,教師主導活動,會帶領幼兒參與活動,教師擁有判斷和分配時間、材料的權利。因此,幼兒在活動期間更關注自己的操作是否正確,這導致幼兒較少有機會提出探究求知型問題。幼兒提出低水平和中等水平問題相對簡單,而提出高水平問題需要整合分析各種信息,需要具備一定表達能力,還需要教師的適當啟發。觀察發現,由于缺乏提出高水平問題的要素,幼兒整體提問質量處于較低水平。
(二)教師對幼兒提問的重視度較低
科學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科學活動中有幼兒熟悉的材料、環境,也有幼兒平時沒見過的現象,科學現象會給幼兒帶來感官刺激,促使幼兒主動提出疑問。觀察發現,在大班科學活動期間,教師作為主導者,掌控各環節的時間、進程、速度,教師向幼兒提問的次數遠遠高于幼兒主動提問的次數,這導致教師提問與幼兒提問比例失衡。由訪談可知,為了活動順利推進,教師并不想幼兒提出過多問題。科學活動比其他活動更自由靈活,幼兒會得到比其他活動更多的自由,因而教師認為自身應該掌控活動節奏。例如,在科學活動“淀粉遇到碘”中,教師常常提出封閉性問題,幼兒提問的頻率大幅度降低。教師是影響幼兒提問的關鍵因素,教師對提問的關注程度直接影響著幼兒提問的頻率。
(三)教師正向回應較少
教師的正向回應能促進幼兒繼續探索和提問,能較好地激發幼兒繼續探究的興趣和信心,有助于幼兒堅持研究。觀察發現,教師有時會直接講出問題答案,有時會草草回答,有時會以“下次再學”為由擱置處理,有時直接忽視不回答,甚至對于一些問題教師會表現出嘲諷、批評等態度。這些都是負向回應。教師的負向回應會嚴重影響幼兒科學探究的自信心和主動性,會將幼兒的奇思妙想扼殺在搖籃中。受打擊的幼兒會更膽怯,不再敢向教師提問。最終,幼兒發現問題的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都難以進一步發展。
三、提升幼兒提問質量的策略
(一)合理引導幼兒的提問
幼兒在觀察事物時,會關注某些現象而提出問題,并嘗試將這些現象與以前的經驗聯系起來,這些都是幼兒作為學習的主體開展學習的表現。因此,教師在開展科學活動時應注意:一方面尊重幼兒天性,善于捕捉幼兒問題的特殊性,培育幼兒的問題意識;另一方面以積極樂觀的正向回應鼓勵和啟發幼兒大膽思考和想象,以培育幼兒堅持不懈的科學精神。
例如,幼兒在科學活動“有趣的管子”結束階段的提問頻率有所降低,這時教師可以以幼兒正在分享彎管、三通管的連接作用為契機,拋出“怎樣將一個水壩的水同時引向三個水池”這一問題。這一問題啟發幼兒將“直管送水”的舊經驗與“彎管轉變方向”的新經驗聯系起來,構建連接管知識體系,促使幼兒發出疑問和假設。這樣,教師及時的提問可以引發幼兒思考,引導幼兒提出更多、更高水平的問題。
(二)轉變回應態度
為了使幼兒園教育對幼兒身心發展產生有益影響,教師要加強自身學習,擁有科學的教育觀,科學看待幼兒提問,明確科學活動的意義在于培養幼兒堅持不懈的科學研究精神。《3~6歲兒童學習與發展指南》在科學探究目標1中提出,5—6歲幼兒對自己感興趣的問題總是刨根問底。[6]教師應重視幼兒主動提出的問題,保護幼兒學習興趣和好奇心。反之,教師若制止幼兒的提問,不僅會打擊幼兒探索的自信心,也會降低幼兒對新事物的好奇心。幼兒提出問題是發現問題的表現,幼兒的提問是其獲得新知識的窗口,教師要理解每個幼兒都擁有提問的能力和權利,要特別注意幼兒提出的問題,及時、適當地進行指導,對幼兒的提問要正向回應。教師還要以整個科學活動的組織為落腳點,與幼兒平等交談,鼓勵和引導幼兒觀察科學現象,給幼兒時間思考與想象。此外,教師要深入學習教育學、心理學等專業知識,增強專業素養,提升幼兒提問的數量與質量。
(三)創設寬松的交流環境
人的心理活動是由心理生活空間引發的,這個空間決定了人的行為的發生,空間包含主體需求與其心理環境的關聯性。[7]教師有責任為幼兒創設寬松、和諧的交流環境,包括精神環境和物質環境。友好的師幼關系是幼兒安全精神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教師與幼兒的關系直接影響幼兒的提問。當教師與幼兒的關系融洽時,幼兒能夠生活在輕松和諧的氛圍中,他們就易于獲得主動提問的心理安全感,也就敢于與教師溝通,愿意提出更多問題,進而提出高水平問題。要建立友好的師幼關系,教師就要給予幼兒尊重和照顧,使幼兒園充滿平等和自由的氛圍。在這樣的環境中,幼兒不必擔心教師責怪自己,可以完全自由思考和提問。在活動中教師要給幼兒足夠的時間思考,足夠的空間動手操作,準備足夠豐富的材料,讓每名幼兒都有機會參與活動。教師要全面觀察幼兒,與幼兒多交流,挖掘幼兒的潛力,啟發幼兒提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