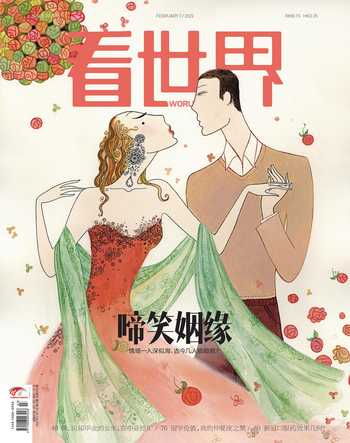“火焰之國”阿塞拜疆舊夢
樓學

阿塞拜疆首都巴庫老城
外高加索三國的總面積,加起來只有約18.5萬平方公里,和廣東省的面積相差無幾。然而,三國之間有著錯綜復雜的恩怨糾葛。自蘇聯解體以來,阿塞拜疆與亞美尼亞之間的領土紛爭幾乎從未停止過,飛地納戈爾諾-卡拉巴赫(簡稱為“納卡”)更是安置在南高加索地區的“火藥桶”。
盡管阿塞拜疆與亞美尼亞相鄰,但兩國之間的陸地邊境都已被關閉。想要一次性游玩高加索三國,只能以格魯吉亞為大本營,甚至還要面臨護照上有“敵國”簽證而被拒簽的風險。但幸運的是,我們在一個局勢相對穩定的時段抵達高加索,出入境官員似乎沒有必要刁難遠道而來的旅行者。
復雜的地緣政治,塑造了這段曲折的旅行路線:在抵達格魯吉亞首都第比利斯兩天之后,我們決定先坐火車去阿塞拜疆,幾天后折回第比利斯,轉車游覽亞美尼亞后再返回第比利斯,最后回到中國。
第比利斯每天都有一班夕發朝至的火車,前往鄰國阿塞拜疆的首都巴庫,全程需要約12小時。但即便是最昂貴的一等座,也只需91拉里(約合人民幣230元)。
一等座的車廂是雙人包間,上車時我們每位旅客拿到了一個封裝好的塑料包,里面有嶄新的床單、被套及枕套。設計簡約的床品上有藍色的“ADY”字樣,是阿塞拜疆國家鐵路公司的縮寫。
我不禁向旅伴感嘆,這套床品對鐵路迷真是太有吸引力了,如果ADY有自己的紀念品商店,我一定要去買一套。我內心希望這套床品的錢已經包含在車票之中,然而在抵達巴庫之前,列車員就將其收走了。
火車8時多從第比利斯發車,約一個半小時后就已從格國出境,但列車在邊境線上停留了約1小時,來完成兩個國家的出入境手續。列車員會收走我們的護照,各項手續都在車上完成,其中還有邊防警察上車檢查。每個人都拿到了一張海關申報表格,然而上面的一切內容都是俄文。正當我們面面相覷時,列車緩緩啟動,正式進入了阿塞拜疆。而那張俄文的海關申報表,后來成為了我的旅行紀念品。

跨國列車
想要一次性游玩高加索三國,只能以格魯吉亞為大本營。
清早我們醒來時,列車已在巴庫郊外。臨時停車時,我偶然瞥見窗外一棟流線型的現代建筑。這棟名為“蓋達爾·阿利耶夫文化中心”的新建筑,正是著名建筑師扎哈·哈迪德的作品。
2007年,阿塞拜疆政府委托扎哈設計一棟能夠代表全新國家精神的公共建筑,這座建筑被視為這個國家從蘇聯的規劃思想和建筑遺產中走出的重要嘗試。盡管試圖從蘇聯的歷史中脫身,但蘇聯的影響顯然無處不在—正如這棟建筑以蓋達爾·阿利耶夫命名,他是阿塞拜疆的總統,也曾是蘇聯時代的阿共中央第一書記。
蘇聯時代無疑形塑了外高加索地區的方方面面,如那張海關申報單所暗示的那樣,俄語曾是三國的官方語言。在蘇聯解體以后,俄語仍是阿國的通用語之一,但重要性已在不斷下降。
車窗外,蓋達爾文化中心的曲線,據說是從本地更久遠的伊斯蘭傳統藝術中獲得靈感,而其周邊的建筑似乎相形見絀,其中不乏國人熟悉的赫魯曉夫樓。在我們乘坐的這一趟國際列車上,列車員們仍說俄語,卻幾乎一句英文也不會—這列火車如同一個不愿醒來的舊夢。
蓋達爾文化中心只是蘇聯解體后,巴庫大規模投資公共設施建設的一個縮影。阿塞拜疆是里海沿岸重要的產油國,因此有源源不斷的財富支撐首都的更新,和外高加索的兩個鄰居相比,阿塞拜疆也確實更具現代魔幻感。
在巴庫的老城里,抬頭就能望見充滿魔幻色彩的火焰塔。這座高大的現代建筑由三棟火焰式的塔樓組成,這一設計來源于本地最悠久的文化傳統。火是阿塞拜疆古老的崇拜對象,是溝通人與自然的媒介,這里甚至被視為伊朗瑣羅亞斯德教的起源地之一—這個宗教更常見的名字是“拜火教”。

巴庫城外古老的火祠

巴庫老城內充滿魔幻色彩的火焰塔
早在公元前第一千紀的阿契美尼德時代,拜火教已成為阿塞拜疆一帶的重要信仰,就連國名本身也來源于中古時代的波斯語,意為“永火之地”。從地理上看,這一地區成為拜火教的圣地簡直毫不奇怪:地下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礦藏極易開采,一些天然氣的出氣口被意外點燃后經年不滅。巴庫的城市郊外就有一座燃燒了許多年的“Yarnadag”,已成為本地重要的旅游景點。
巴庫城外還有一座古老的火祠(Ateshgah),其名稱同樣來源于波斯語。火祠是拜火教的廟宇,但更早時曾是印度教徒祭祀毀滅之神濕婆的廟宇。在這座石構神廟的院落中心,有一座建造在天然氣出氣口上的神龕,這里的圣火直到1969年才最終熄滅;后來經過改造,由巴庫市政管道繼續提供天然氣,至今仍為遠道而來的各國游客熊熊燃燒。
拜火教、印度教的合流,恰好為我們展現了巴庫多元的文化背景。這座名城是古代絲綢之路上的重要一站。如今,阿塞拜疆的版圖如同一只朝向里海的飛鳥,而巴庫正處于鳥喙所在的阿普歇倫半島上,是橫跨里海最短的捷徑所在,也是連接伊朗高原與北方草原重要的陸地通道。
巴庫人引以為傲的老城,已經被列為世界遺產。這座城墻環繞的城市自古以來即是半島上最重要的定居點,其悠久的歷史甚至可以上溯至舊石器時代。中世紀以來,這里一直以發達的鹽業著稱,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為波斯、奧斯曼、沙俄等不同帝國互相競逐的前線—存留至今的高大城墻,就是12世紀時為了抵御連綿不斷的入侵者而修建的。

阿塞拜疆是里海沿岸重要的產油國
古城內有兩處重要的古跡。一座是始建于12世紀的少女塔,但“始建大法”將它的歷史上溯至2000多年前。由于其標志性的外觀,少女塔是阿國貨幣上的景點圖案。
另一座則是占據了老城制高點的希爾萬沙宮殿。這座宮殿的創始人是來自阿拉伯地區的移民,但受到強烈的波斯文化影響。9世紀中期,移民家族在今天的阿國境內創建了希爾萬沙王朝—盡管它在許多時段都是鄰國強權的附庸,但這個王朝延續了將近700年,是世界上最長命的伊斯蘭王朝。12世紀,王朝遷都巴庫,并下令修建了我們今天所見的城墻與少女塔。希爾萬沙宮殿反倒要年輕得多,大部分建筑是于15世紀修建的。
但我最喜歡的并非這兩處被列入世界遺產的地點。6月酷熱的午后,我們常常漫步于巴庫老城的石街上,懶散地循著空調涼風,走進一處精致的咖啡館坐下,慢慢消磨這炎炎的假期。待到太陽收起鋒芒,我們才從空調的庇護中走出,去偶遇山城中起伏的街巷,不時在轉角望見盡頭處深邃的里海,或是抬頭望見,高聳的火焰塔出現在古老城墻、寺院的背景中。
在高加索旅行的末尾,我們從亞美尼亞返回第比利斯。我們的班車出人意料地選擇了一條不怎么常見的路線,在途經風景秀麗的塞凡湖之后,竟然一路向東,拐向了亞阿兩國的邊境線。電子地圖顯示,兩國之間有著密集的“插花飛地”,我的定位也頻繁在兩國之間切換。
在離開阿塞拜疆幾天后,我竟然又意外地回到了這個國家,并且抵達了我最好奇、最想一探究竟的“敵國前線”。
但眼前的景象卻與我想象中截然不同,車窗外沒有森嚴的戰備工程,只有大片豐美的草原與潺潺的溪流,景色美麗至極。然而,不斷有古老或殘敗的修道院忽閃而過,其中的那些廢墟,提醒著這里并非太平之地。
在我們離開高加索一年之后,亞阿兩國的邊境線上戰爭又起。在新聞圖片上,我再次見到南高加索的連綿草原時,它卻已成為坦克殘骸的背景。阿塞拜疆,一個火焰的國度—有時是不同文明匯流的火焰,有時是現代建筑致敬的火焰,但也有時是戰爭的夢魘。
特約編輯姜雯 jw@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