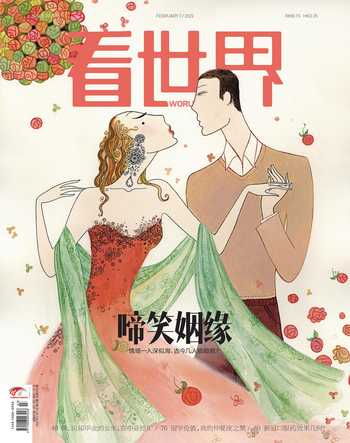里約折疊
米沙·格蘭尼

巴西,一個美麗的國度,卻有著這個世界上最糟糕的記錄:我們是世界上暴力兇殺案案發率最高的國家—世上每10個死于暴力兇殺的人中,就有一個是巴西人。這意味著巴西每年有超過5.6萬人在暴力中喪生,其中大多數是死在槍口下的年輕黑人男性。巴西同時也是這個世界上毒品消耗量最大的國家之一,禁毒戰爭給這個國家帶來了無盡的傷痛,在巴西街頭死于兇殺的人中,超過50%的人的死亡原因與此相關。
——伊洛娜·薩博·德卡瓦略,伊加拉佩智庫,2014年10月TED演講,里約熱內盧
葡萄牙語中的法維拉(favela),意指貧民區(slum)或非正式定居點,最早于19世紀末期在里約衍生出此義。這個詞也是從東北地區引進的。
1897年,剛在巴伊亞州擊敗卡努杜斯(Canudos)起義軍的士兵們,在里約市內的一個小山坡上安營扎寨,抗議政府拖欠工資。那時里約還是巴西的首都。
卡努杜斯農民起義與平定它的那一役,是這個年輕共和國的關鍵轉折點(那時君主制剛剛被廢除不到十年)。巴西的歷史總也離不開叛亂,一些是由分裂主義和地區競爭導致的,另一些則是因為社會不平等。
被鎮壓后五年內,卡努杜斯起義就被歐克利德斯·達庫尼亞(EuclidesdaCunha)寫進了他的小說《腹地叛亂》中,名傳后世。在這場戰爭中,巴西軍隊同一個身為千禧年信徒的牧師領袖和一群追隨他的烏合之眾開戰,這對那些沒經過訓練的共和國士兵來說是段艱苦的經歷。
然而當起義被平定后,政府卻忘記了自己對這些在熱帶草原上拼死戰斗的士兵負有的義務。士兵們被遣散了,他們來到里約,在小山坡上定居下來。今天,這座山上是一個名為普羅維登西亞(Providência)的貧民窟。
士兵們把小山命名為法維拉坡(FavelaHill),名字來自卡努杜斯起義軍曾經當作戰略基地的法維拉山。這一命名來源至今仍有爭議。一些人認為這個名字實際上源自一種適應能力極強的同名毒草,而法維拉山的名字就是這么來的。
他們的說法是這樣的:這些被遣散的士兵不屈不撓地討要自己的薪水,像極了在東北惡劣環境中頑強生存的法維拉草。士兵們在此扎下了根,此后政府不論怎樣努力,都無法將他們趕出這個第二故鄉。
第一批定居者來到此地時,法維拉坡不過是一處鄉村氣息濃厚的土堆,俯瞰著一座英國墓園,同今日沒什么差別。這里距當時的政府所在地和總統府也很近。
能夠擁有這片居住空間,很大程度上要感謝里約的地理風貌。市內各區被數不清的丘陵和山脈分隔開來,里約人因此非常依戀自己待的地盤和這座城市。19世紀到20世紀之交,市內通了幾條隧道,但直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才有隧道穿過最險峻的山脈,將整座城市連接起來。
這種獨特的地貌能幫里約人確定方位:假如小山坡在你身后,那海大概就在前面。除去這點作用外,這些小山坡很招人嫌棄。
自葡萄牙人最早在里約定居起,沒有幾個歐洲移民會爬上陡峭的山坡安家落戶。他們把家安在沙灘、海灣和港口旁的平地上,然后是開墾過的沼澤地上。
擊敗卡努杜斯起義的士兵們定居山坡數十年后,后來的打工者們也開始有樣學樣,在這些僅存的空地上支起了窩棚。對于保姆和傭人來說,從周邊地區穿過山脈到市里去太過麻煩,因此他們通常住在雇主家附近的小山坡上。
法維拉,這個貧民窟的通用稱呼就這樣叫開了。
全國上下都用起了這個詞。但在里約,人們又發明了一種更平淡的叫法,并且最終勝過了“法維拉”:omorro,意思是小山。在巴西其他地區,規模較大的貧民窟通常位于城市邊緣,遠離那些綠蔭如蓋、生活水準不亞于紐約或倫敦的中產階級住宅區。但里約的貧民區十分獨特,它遍布在市區的山坡上。
最早從東北部來的打工者們,往往把房子建在山的底部。
20世紀20年代,一些小農戶開始在圣康拉多區旁的一小塊土地上飼養牲畜,然后把農產品賣給當地人。到了40年代,隨著羅西尼亞—這個詞的字面意義是“小農場”—開始雇用越來越多的幫工,整個社區開始慢慢往山上擴展。沒多久,他們就可以通過“兩兄弟山”后的山口,把產品運往隔壁加維亞的富人區。
貧民窟在小山坡上成片出現,這帶來了兩個后果:首先,在南區,這些貧民窟緊挨著鄰近的富人區——伊帕內馬、萊伯倫、圣康拉多和加維亞。
貧民窟的臟亂同周邊的極度奢華混雜在一起,有時兩者相隔甚至不到九米。“瀝青區”,人們這樣稱呼鋪著瀝青路的中產階級聚居區,同貧民窟那布滿車轍的泥巴路堪稱天壤之別。總而言之,里約人要么住在瀝青路旁,要么住在小山坡上;要么在富人區,要么在貧民窟。
許多里約的中產之所以能過好自己的生活,是因為他們把貧民窟從意識中清了出去,這一心理機制只有在承認女傭和雜工也是活生生的人時才會被打破(這些人幾乎百分之百住在貧民窟)。
但也存在著一個很有影響力的游說團體,他們背靠房地產開發商的支持,希望把貧民窟從整個南區抹去。在他們眼中,鏟除這些難看的貧民窟不僅能促進旅游業發展,還能讓中產階級社區變得更安全—兩種愿景都是一廂情愿。
其次,里約各個山上的貧民窟就像被中產區分隔開來的小島。這里的貧民窟居民對社區的認同感要比其他城市的更強烈,特別是同圣保羅相比。
就像小說家和歌手希科·布阿爾克所說的那樣,在里約,“每一條溝壑都自成一國”。市內的每個貧民窟都有強大且清晰的自我認同,而這將影響毒品貿易的社會經濟發展進程,也能從根本上解釋為何同圣保羅相比,里約市區暴力事件的數量更多、性質更特殊。
(本文獲出版社授權,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