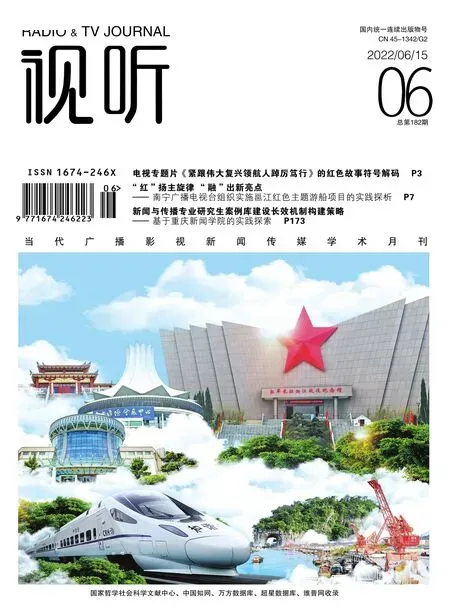抖音短視頻平臺上小鎮青年的形象建構
——基于框架理論
張玉玲
小鎮青年是與城市、鄉村青年具有本質差別的,處于城鄉結構之間的被標簽化的一類人群。新聞建構社會現實,在傳統媒體時代,由于小鎮青年的“失語”,其往往被貼以“精神小伙”“殺馬特”等非主流標簽,長期處于一種被“污名化”的狀態之中。隨著移動終端和短視頻平臺的興起,以及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長期處于城市邊緣地帶的小鎮青年在擁有更多話語空間的同時,也逐漸被人們關注。其中,抖音等短視頻平臺以其操作性強、短小碎片記錄以及娛樂性強等眾多優勢,成為小鎮青年表達自我、進行個人形象塑造的重要平臺,各種小鎮青年自媒體賬號也應運而生。他們在“自塑”的過程中,雖然仍舊避免不了與具有刻板印象的非主流標簽相關聯,“去污名化”道阻且長,但是可以看出小鎮青年的形象逐漸趨向正面,也獲得了大眾的認同,這在一定程度上與小鎮青年在自媒體發布內容時使用的框架有關。
一、研究理論及研究方法
“框架”作為考察人們的認知與傳播行為的學術概念,最早見于人類學家貝特森1955年發表的《一項關于玩耍和幻想的理論》論文。1974年,社會學家戈夫曼在《框架分析》一書中對其進行定義,認為框架是人們用來闡釋外在客觀世界的心理基模。框架使得人們能夠定位、感知、理解、歸納眾多具體信息。20世紀80年代,框架理論開始引進到新聞傳播領域,并由此誕生“媒介框架”與“新聞框架”這兩個學術概念。然而,隨著新媒體的不斷發展,消解了一部分傳統新聞框架的力量,新的新聞框架由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共同構成。
本研究主要采用框架理論的觀點,以抖音短視頻平臺上近兩年來小鎮青年的自媒體賬號為研究對象,對其發布的內容采用文本分析方法,分析小鎮青年在進行短視頻創作發布時運用的框架塑造了一種怎樣的形象,是否在刻意迎合大眾對他們認知的形象,是否能夠在眾媒時代為自己的形象正名,以及媒體和社會應當如何共同為其“去污名化”。
由于小鎮青年的范圍較為廣泛,本文選取的小鎮青年樣本主要是指出生在三四線及以下的城市或縣城小鎮并在大城市“漂泊”的青年,年齡在18至35歲。他們往往“融入不了大都市,也回不了小城鎮”,處于城鄉之間的邊緣地帶。在選取樣本時,除限制年齡以及賬號的活躍度之外,主要選取粉絲數在1000以上具有代表性的小鎮青年的自媒體賬號。其中,在定位于北京、上海、廣州三個一線城市的賬號中分別抽樣選取5個賬號,對其視頻內容進行文本分析,從議題、場景以及敘事三個框架分析小鎮青年在進行形象建構時呈現出的特點。
二、自媒體對小鎮青年的形象建構
(一)正向議題選擇:建構求知奮斗形象
與庸俗、膚淺、狂歡等負面取向的詞語不同,抖音短視頻平臺中自媒體賬號所塑造的小鎮青年形象更偏向正面。他們似乎在形象氣質上與一二線城市居民并沒有什么差別,甚至多了幾分“韌性”與“沖勁”,其實這與各個賬號在進行自我形象塑造時的議題選擇偏向有關。印象管理是指一個人通過一定的方式影響別人形成對自己的印象的過程,而其中,通過議題的正面偏向選擇可以限制其他負面信息的獲取,從而對自我形象進行美化。對北京、上海、廣州三個地區選取的15個有關小鎮青年的抖音賬號進行分析,學習、工作等提升自我類的議題是其設置的偏向議題。“滬漂女孩藝軒”初入社會,其議題主要垂直設置于提升大學生學習、生活方面,“10天沖刺四六級”“快速考證秘籍”以及“如何靠寫作賺錢”等相關議題,傳達出“學習改變生活”的價值偏向。隨著博主逐漸脫離學校,議題也逐漸轉向“租房”“打工人”等。“弄潮小四”發布的51條抖音視頻中,有80%以上以工作為主要議題,包括“最賺錢的行業”“面試不可忽視的寶藏問答”以及“工作賺錢買房”等議題。
簡言之,短視頻平臺為眾多小鎮青年提供了一個開放的舞臺,他們具有了自我呈現和建構的文化展演權利。學習以及工作等提升自我類的垂直議題設置,其固有的正向性議題偏向通過互聯網信息傳播,為受眾塑造了一個個愿意求知、積極奮斗的小鎮青年形象。他們愿意通過自我的提升和奮斗來改變城市“土著”對其的看法。對于這種淳樸觀點的傳達與呈現,受眾在接收之時,可以與以往刻板印象中固有的“殺馬特”等形象做出對抗。
(二)私人場景呈現:對悠然生活的認可
即便小鎮青年身在城市,經濟和生活方式也不斷城市化,但實際上他們自我感知在城市空間中的融入度很低。戈夫曼的場景決定論將人們在社會舞臺展示的不同自我行為分為“前臺的行為”和“后臺的行為”。如今,電子媒介的發展使得“前臺”與“后臺”相互交融,而“后臺”行為更能表現出真實自我。小鎮青年在抖音短視頻平臺上呈現的場景,也是“前臺”和“后臺”相互交融而形成的,所以不乏一些私人場景。這些私人場景往往與“復古”“民謠”等懷舊風和慢生活有關,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小鎮青年對小城鎮悠然生活的向往和認可。“小V一般般”的短視頻內容拼接以民謠風或慢節奏音樂為主,輕音樂配以“野餐”“一場音樂演出分享”以及“有意義的街道”等場景內容,再加上復古調濾鏡,都在反映比起城市的嘈雜和快節奏,其從心理上更為向往平靜悠然自得的生活。而“扎克的幸福生活”是在記錄旅行的意義,“西藏”“云南”等具有特色的旅行地點,“煙火”“街道”等具有煙火氣的場景呈現,也表達了其對自由生活的向往。
這些自媒體賬號基于日常生活場景的內容建構,能夠有效地拉近小鎮青年與受眾之間的感知距離,同時短視頻呈現出的“煙火氣”的生活狀態可以讓受眾從快節奏的生活之中抽離出來,撫平內心的焦慮和急躁之感,并且將自己的生活與小鎮青年展示的生活相對比和聯系。總而言之,小鎮青年通過這些“接地氣”的日常生活私人場景的呈現,不僅彌補了身處快節奏的大城市無法享受向往的悠然生活的遺憾,而且增加了受眾對其短視頻內容和小鎮青年身份的認同感。
(三)城鎮對比敘事:凸顯弱勢群體情感
比起圖文,短視頻的呈現方式更為多樣,文案、視頻、音樂、圖片等眾多單一元素都可融入其中。同時,可以采用各種敘事手法進行剪輯,倒敘、插敘、重復、對比等敘事手法的支持讓短視頻內容更為豐富。其中,對比敘事框架可以更為直觀地表達情感。在本文選取的15個抖音賬號中,這些小鎮青年的短視頻往往借用對比敘事框架表達城鎮之間的差異。一邊是城市,一邊是鄉鎮,讓受眾直觀感受到他們“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故鄉”的兩難心理。這些短視頻表現了眾多小鎮青年在地緣上的一種無奈,同時也突出了漂泊群體的情感。比如,“史別別”發布的短視頻對比了北京和老家,表現出“一個是繁華,一個是回憶”,在繁華的北京即便工資高也吃不起海鮮,雖對自己的老家掛念但是回去后卻生活不便。這些小鎮青年自媒體賬號借用平臺呈現出城鎮之間各種資源、階層的差異,即便在大城市艱苦奮斗,也可能買不起一套房或者擺脫不了成為“房奴”的宿命。短視頻對種種差異的呈現也是希望社會更為關注城鎮差異以及小城鎮青年本身,從真正意義上關心和縮小這種差異和差距,而非單單對其進行“丑化”和“污名化”。
小鎮青年為何會選擇漂泊在大城市之中?一是出于向往大城市,渴望走出小城鎮,“看看外面的世界”的內心需求。“王小娜”是由于在上海讀大學,后來成為“滬漂”。繁華的大都市讓“王小娜”目不暇接,內心渴望能夠留下來。二是城鎮之間的資源差異。除了就業、交通等資源,“明達”在敘述自己“為什么來北京時”,對比了北京和自己出生的小城鎮在銀行匯錢時的情況,表達出大城市生活更為便利以及高效率,而小城鎮卻遠遠沒有如此方便的資源。三是逃離小城鎮的強連接關系之下的觀念束縛。其中,“是昆哥呀”強調了小城鎮的居民持有“30歲不結婚就是怪物,女生不用太拼”等觀念。小城鎮的大量青年依舊在大城市流動,城鎮差異也依舊存在,留下還是回去的掙扎心理仍然存在于這個群體之中。如何真正關注小鎮青年這個群體,解決其實實在在的矛盾心理和問題所在,不單單需要自媒體的發聲與建構,還需要主流媒體及社會的共同關心與反思。
三、小鎮青年“去污名化”之策略
(一)自媒體人自我形象代表群體形象,應當提升媒介素養
在眾媒時代,自媒體的話語影響力有時會超越傳統主流媒體,但是自媒體發布的內容參差不齊。小鎮青年的自媒體也是如此,良莠不齊的內容常常會誤導受眾內心對其正面形象的形成。為了保證其在傳遞內容之時更具正向性,亟須自媒體人擁有其自我形象代表整個小鎮青年群體形象的觀念,同時提升自身的媒介素養。不僅僅是提升拍攝、剪輯和創作短視頻的專業素養,雖然這些專業素養的提升可以使得視頻呈現更為美觀,獲得受眾的點贊和評論,但是也要加強提升自身社會責任的意識。
不得不說,大量自媒體人為了追求流量及利益,由“審美”轉向“審丑”來博取受眾關注。比如被丑化的“殺馬特”“洗剪吹”等小鎮青年形象就是利用這一特點,通過病毒式的傳播,給受眾留下怪異印象。在互聯網時代,這種記憶難以磨滅,隨時會被網民翻找出來。這不僅給這個群體造成一定的傷害,而且時常超越底線的“審丑”內容也會污染網絡傳播的空間環境。所以為了避免給小鎮青年貼上負面標簽,其自媒體人的媒介素養亟須提升。
(二)主流媒體深度聚焦邊緣群體,適當進行輿論引導
小鎮青年這個群體長期處于城市邊緣地帶,缺乏社會各方面的關注和深度挖掘,“缺乏了解”也會促使小鎮青年形象“污名化”。所以,傳統主流媒體應當將弱勢轉為優勢,深度挖掘小鎮青年題材,聚焦這個群體,在快時代做慢報道。通過一系列的深度報道,讓受眾了解這個群體背后的故事,那么,以往受眾所無法理解的一些行為也能得到解釋,從而為這個群體形象進行正名。同時,傳統主流媒體也可以發揮其解釋說明和輿論引導的作用,反映小鎮青年行為背后的內心想法和成長背景,讓受眾能夠辨別惡意“污名化”小鎮青年的視頻內容,使網絡空間環境得以凈化,而不是讓“審丑”內容肆意傳播。
要對小鎮青年進行深度挖掘,傳統主流媒體可以深度融入各類小鎮青年的生活,不僅是大城市中“漂泊”的青年,也可以是回到小城鎮的青年等。譬如,媒體可以采訪報道不同形象的小鎮青年自媒體博主,或者在小鎮出生的名人明星,記錄其不同的生活狀態,用細化生活的方式讓受眾了解與接受這個群體。媒體也可以深入小城鎮去報道小鎮青年在家鄉的生活,細化幾代人的生活環境和文化背景,讓小城鎮的生活為人們真正接受,而不是被貼以各種“污名化”的標簽。
(三)各地區積極吸納返鄉創業青年,助力鄉村振興
雖然小鎮青年選擇“漂”于大都市,但是時常會處于不安、惶恐的心理狀態以及與城鄉之間的割裂感中。與此同時,三四線小城鎮各類高素質人才流失,不利于城鎮發展和鄉村振興。為了解決這種矛盾,為小鎮青年增加就業機會,助力國家的鄉村振興戰略,各個地區應當出臺相關政策和措施,積極吸納返鄉創業青年,建立人才庫。這些小鎮青年往往接受了高等教育,在所學專業上具備較強的專業素質和能力,各地區為其提供資金或者就業機會,可以大大增加小鎮青年與家鄉的黏性,從而帶動家鄉發展。
具體來看,首先,各城鎮應當積極發現、挖掘并培養當地的優秀青年,篩選形成人才庫,搭建成長和創業平臺,引導青年人才更好地服務城鎮經濟社會發展。其次,應積極吸納返鄉創業青年等,鼓勵他們成為助力鄉村振興的“領頭雁”。作為新農人的返鄉青年,在鄉村振興的過程中發揮著愈來愈重要的作用。掌握現代信息技術與關切家鄉發展的返鄉青年具有主體性與能動性,有利于鄉村文化傳播新生態建構。最后,各地區與企業形成聯動,開展直播培訓班與各類短視頻活動,吸納并培養當地短視頻直播達人,利用短視頻或直播宣傳當地特色旅游景點及文化,帶動當地農特產品的銷售。在帶動村民致富的同時,也可以實實在在地帶動當地經濟發展,助力鄉村振興。各地區可以通過各種措施,掀起小鎮青年返鄉就業的熱潮,弱化城鎮之間的資源差異,同時通過各種直播、短視頻培訓活動,為各個新生自媒體人樹立樣板和模范,從而讓小鎮青年的形象更趨正面。
四、結語
抖音短視頻以其短小碎片化以及易操作上手等特點,為小鎮青年自媒體人提供了一個展現自我的平臺。這些內容在短視頻平臺進行呈現之時,主要通過議題、場景以及敘事這三個框架進行建構,從而“自塑”了樂于求知奮斗,但是依舊向往悠然自得生活的小鎮青年群體形象。當然,單一自媒體的聲音遠遠不夠,還需要傳統主流媒體以及社會各主體從實際和根本出發,真正了解和解決這個群體背后的焦慮感,從而對其進行“共塑”,讓這個群體真正為大眾所認識。要想從認知上改變受眾對小鎮青年的刻板印象,依舊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返鄉創業青年等通過“自塑”實現了小鎮青年的“去污名化”,成功為自己正名,而傳統主流媒體等的“共塑”力量也不容小覷,未來將發揮出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