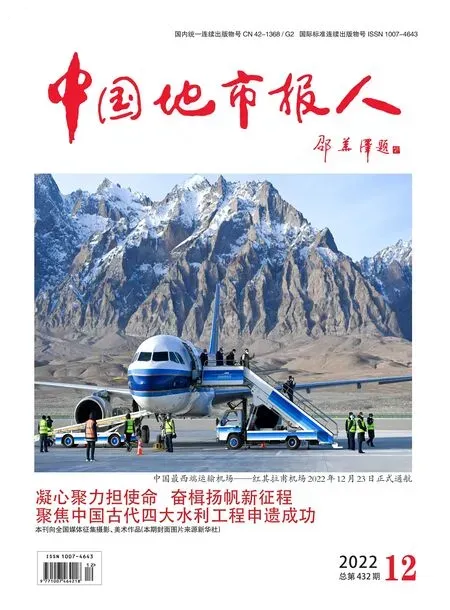助農中彰顯黨媒責任與擔當
徐賢禮
新聞工作者應主動深入基層、深入群眾,到群眾身邊去了解群眾、關心群眾、幫助群眾。關注民生是媒體的責任使然,而農村更是需要重點關注的領域之一。筆者在多年的采編工作中發現,一方面媒體對于農村的關注越來越多,另一方面,媒體助農這項工作在方式上還有創新空間。筆者試以江蘇鎮江日報社的一些做法談談媒體助農的方式。
主動和被動 效果大有不同
2017年,鎮江市丹徒區上黨鎮舉辦了一場黃桃節活動,幫助當地農戶銷售農產品。通過該活動,當地七成黃桃通過網上預售出去,剩下的則通過深加工生產線做成黃桃制品。當地媒體對這一事件進行了新聞報道。在這一助農行動中,媒體僅發揮了消息傳達的作用,參與度不高。
2021年夏,鎮江當地一位葡萄種植戶因葡萄滯銷向媒體求助,多家媒體對此進行了聯合報道,廣泛發布了種植戶的需求。消息發出后,熱心讀者紛紛響應,除了踴躍購買葡萄外,還幫忙提供場地、幫助運輸等。在這一次助農行動中,媒體是指揮中樞,供需雙方都由媒體聯系,每個助銷環節也由媒體來統籌推進安排,并通過一次次新聞報道將整個助農行動的進展一步步呈現在讀者眼前。
上述兩次助農行動,鎮江日報社都參與了,但是參與程度不同,效果也大不一樣。如果從讀者的反響來比較兩次行動,差別就更大了。后者所表現出來的互動性、讀者的參與程度,都是前者所不具備的。以上兩個例子對比可以反映傳統媒體在助農方面的進步空間。當然,對葡萄種植戶的這次援助畢竟是源于求助,媒體主動性發揮還有較大努力空間。
更好地助農 媒體有優勢和責任
從近幾年鎮江媒體報道的各種助農行動來看,農民對助農行動的效果還比較滿意。即使在這兩年受到疫情影響的情況下,他們也表示有信心渡過難關。
不過,筆者也發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一些小規模的種植戶容易處于政府部門大規模幫助行動的范圍之外而被忽略;農產品受時令影響很大,官方或者半官方性質的助農行動不可能應時舉辦;不同農戶遇到的具體情況不同,統一的助農行動解決不了全部問題等。基于這些情況,筆者認為,媒體在助農領域仍有發揮空間。媒體反應快速的特點正好對應助農行動的要求——新鮮農產品銷售需要的就是快速應對、速戰速決。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優先發展農業農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對于這“重中之重”,媒體的責任不言而喻。在媒體競爭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地市媒體在當地仍然有較強的公信力和影響力。面對農村發展的新需求,媒體的責任意識應當更強,自我要求應當更高,將更多精力投向廣大農村。
更好的效果 來自高效的行動
十余年前鎮江日報社就開始在助農工作方面進行了新的嘗試,一些經驗至今仍然有效。2008年冬天,鎮江日報社下屬媒體《京江晚報》率先嘗試將市民的年貨需求和本地的農產品聯系起來。首先報紙發布信息,征集群眾的農產品需求,同時調查了解本地農產品的情況。在信息不斷發布的過程中,一些單位拿出“采購單”,一些農民帶著農產品上門。在活動不斷推進的過程中,媒體對供求雙方的信息進行補充后對外發布,引起讀者持續關注。其次在對接活動“落地”的幾天里,供需雙方直接見面,各自需求得到滿足,活動取得了圓滿效果。在這次行動中,媒體不斷挖掘、補充、發布信息,服務農民和消費者的作用得到充分體現。
另一次助農活動嘗試體現了媒體的快速反應。當時,一個蔬菜種植基地遇到萵苣銷售難,情況很緊急:農產品還在田里,時間越久損失越大。得到消息之后,報社立刻組織記者趕往現場,很快就傳回了初步的信息。記者在前方不斷跟進,稿件連續刊登,形成了全城關注的熱點話題。大量的市民很快就行動起來,不但普通零散消費者參與購買,還有企業到田頭收購并簽訂長期購銷訂單。
這兩次助農行動都是媒體主導的,體現了媒體的優勢:快速掌握情況、信息傳遞順暢、解決問題有效。從這樣的行動可以看出,在自己掌控的助農行動當中,媒體更容易根據實際情況主導對接高效、直接的助農行動,這是其他力量難做到的。
深入基層 媒體受益多多
在助農行動中,媒體也收獲滿滿。在上文提及的萵苣銷售助農行動中,農民避免了損失,消費者獲得了優質優價的農產品,媒體收獲了優秀稿件。記者借這樣的機會前往農村最小的單元,了解一個個農村家庭真實的情況,離現場更近,更容易發現有價值的新聞。

2011年鎮江日報社《京江晚報》助農行動報道

報社在接到一位葡萄種植戶的求助后開展了助銷行動

農產品幫銷團相關報道
第一,更深的介入讓媒體能掌握實際情況,獲得好素材好稿件,在此基礎上獲得更多讀者關注。現場采訪核心當事人是核實新聞事實的最好方法,對于稿件的質量至關重要。對于媒體從業者而言,這更是增強“四力”的絕好機會。作為合格的媒體人,應當時時不忘深入基層、深入群眾。
第二,記者能真切感受農村、通過作品反映農村,媒體在關注農村的過程中彰顯社會責任。一篇深度稿件不僅要吸引農村讀者關注,還要能吸引廣大讀者對農村的關注。讀者通過媒體了解農村、吸引多層次讀者對農村的關注關心。另外,越來越多的特色村莊因媒體得到充分展示的機會。在鎮江,讀者通過媒體了解以葡萄著名的丁莊小鎮、以草莓出名的白兔鎮、盛產特色大米的戴莊村。讀者熟悉這些地方,認可它們的產品,從農產品銷售、旅游等途徑促進農村的發展。在鎮江,農村采摘經濟、旅游景點的發展,都離不開媒體的宣傳推介。
第三,深入基層,媒體可以借機獲得更多的報道資源。《新聞記者培訓教材》寫道:“隨著網絡、手機、移動終端等新媒體的出現,許多群眾已經扮演起‘報道者’的角色,尤其是在突發新聞現場,未趕到現場前,在場的目擊群眾就已經通過手機的拍照或錄像記錄下來……”作為媒體從業者,多建立聯系,也就多了新鮮信息獲取的渠道。
新技術助力 媒體助農更高效
媒體助農當然不是單打獨斗,其背后是全社會的力量。媒體所做的是統籌各種力量資源,獲得更高的辦事效率、更好的效果。正如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教授蔡雯所著《新聞報道策劃與新聞資源開發》所說,統籌利用“目的是使這些資源發揮整體效果大于部分之和的系統效應”。現在,鎮江日報社仍在通過旗下各類媒體平臺整合發布涉農信息、根據有價值的新鮮線索及時策劃助農行動。以前的經驗依舊有用武之地,加上現在的信息渠道更加多樣,助農效果比之前更好。
媒體要做好助農工作,還需要建立比以往更龐大的信息員隊伍,將更多人納入工作范圍,共同推進這項工作。幸運的是,新的技術手段可以幫助搭建暢通的渠道,讓媒體可以容易地掌握來自各方面的信息。
現在,這樣的隊伍已經建設并正在擴大。隊伍中,信息的提供者可以是通訊員、村干部、農民,作為信息源,他們都是助農行動“工作群”的重要成員。媒體還在相關政府部門、市場運營方、社區工作者、質量監管部門、消費維權部門之間搭建網絡,他們涉及與助農有關的方方面面,是做好這項工作的保證。以往媒體在助農過程中遇到過尷尬:受助方的農產品與施助方的期待不符。在一個完善的聯系人機制建立之后,問題會更容易被發現和解決。
鎮江日報社2021年夏天組織了“農產品幫銷團”。農產品信息通過微信及時發布。對接后,采摘運輸、質量問題反饋等都可以及時反映和處理,不管是效率還是質量,都更有保證。
新技術還給媒體做好報道增加了途徑,媒體的新媒體平臺已經在助農方面產生效果。鎮江日報社曾經通過視頻方式介紹當地的桃花集中地,短片不直接幫助農民出售桃子,但是在讀者被桃園風光吸引的背后是潛在的影響,對這一地產農產品的整體印象加深了。
綜上所述,在日益激烈的競爭之中,媒體可以在農村開發出更多的新聞資源、在競爭中獲取優勢,也能在這個過程中獲得農民的信任和關注,更能在廣大的農村履行好自身的社會責任。助農,媒體是不可缺少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