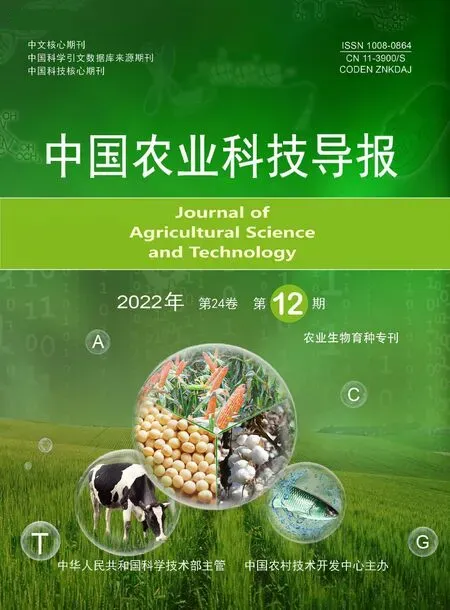畜禽重要性狀遺傳調控機制與分子設計育種
王文月, 米曉鈺, 孫康泰, 戴翊超, 姚志鵬, 高元鵬,劉軍, 葛毅強, 張松梅, 鄧小明*, 張涌*
(1.中國農村技術開發中心,北京 100045; 2.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動物醫學院,陜西 楊凌 712100;3.山東濱州國家農業科技園區管理服務中心,山東 濱州 256600)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下決心把民族種業搞上去,抓緊培育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優良品種”“基礎研究是整個科學體系的源頭”“深入實施種業振興行動,強化農業科技和裝備支撐,確保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當前,我國畜禽生物育種原始創新面臨巨大挑戰,分子設計育種原始創新不足、核心種源對外依存度較高、優質核心源被國外壟斷,嚴重影響我國畜禽種業安全。加快破解畜禽重要性狀形成的基礎,提升分子設計育種能力,對提升我國畜禽種業安全水平及保障畜牧業高質量發展和畜禽產品穩定供給具有重要意義。我國擁有豐富的畜禽遺傳資源,為畜禽生物育種原始創新與現代種業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近年來,我國積極開展種質資源表型與基因型精準鑒定評價,發掘了一批優異種質和重要基因,在轉基因和基因編輯育種方面取得多項突破。但是,與國際畜禽種業強國相比,我國畜禽遺傳育種原始理論創新缺乏,特別是重要經濟性狀形成機制和雜種優勢機理的解析不足。目前,已鑒定的具有重大育種價值的新基因及突變位點屈指可數,重要經濟性狀形成的分子機制及基因調控網絡仍不清楚。隨著高通量測序技術的快速發展,綜合多組學技術和基因編輯技術聯合分析,為解析畜禽重要經濟性狀的遺傳機制提供了技術支撐,為培育高產、優質、高效、抗病和環境友好型畜禽新品種奠定了重要基礎。本文重點闡述畜禽重要經濟性狀與分子育種的國內外研究進展,探討我國畜禽分子設計育種發展面臨的瓶頸和未來發展趨勢。
1 畜禽重要經濟性狀遺傳調控機制研究進展
1.1 家畜重要經濟性狀的遺傳基礎與分子調控機制
豬、牛、羊等大型家畜為人類提供豐富的肉、乳、絨、毛等畜產品。近30年來,國內外學者圍繞豬、牛、羊的產量、品質、繁殖和健康等性狀形成的分子機制開展了大量研究,鑒定了許多重要經濟性 狀 的 數 量 性 狀 基 因 座 (quantitative trait locus,QTLs)、插入缺失標記(insertion-deletion, inDel)、單核 苷 酸 多 態 性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基 因 拷 貝 數 變 異 (copy number variations,CNV)等,極大地推動了家畜重要經濟性狀主效基因和遺傳標記挖掘,加快了遺傳改良進程和新品種培育速度。
豬是最早被馴化的動物之一,在馴化和繁育過程中,其體型、生產性能、免疫功能和對環境的適應能力發生了許多變化,家豬的基因組中留下許多獨特的印記。國內外學者針對豬重要經濟性狀的遺傳機制開展了大量研究,產生了海量重測序、轉錄組等測序數據,但目前研究大多利用西方豬種‘杜洛克’的基因組(Sscrofa11.1)作為參考基因組,致使大量的亞洲豬特征位點和序列不能被準確捕獲,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對亞洲家豬的基因組學研究。Zhou等[1]成功繪制了我國地方品種‘梅山豬’的高質量基因組圖譜,contig N50達到48.05 Mb,是目前完整度最高、連續性最強的亞洲豬基因組圖譜。為突破單一線性基因組不同品種(類群)的個體的局限性,Tian等[2]使用12個基因組構建了豬的泛基因組,相較于杜洛克豬參考基因組共獲取了72.5 Mb的非冗余的新序列。對豬的各種經濟性狀進行全基因組關聯分析(genomewide association syudy, GWAS),鑒定出豐富的遺傳標記和候選基因。豬基因組中的SNPs非常豐富,Fu等[3]基于864頭豬的全基因組重測序數據鑒定出了 81 814 111 個 SNPs。在肉質和生長性狀方面,劉劍峰等[4]對97頭‘杜洛克’豬開展了GWAS分析,共確定了464個重要的候選區域,注釋了709個基因,包括600個候選蛋白質編碼基因和109個lncRNA,揭示‘杜洛克’豬在生長和肉質性狀上與其他品種的區別。Wang等[5]對中國土生豬品種香豬的重要經濟性狀開展了GWAS分析,通過與其他品種(包括西藏、梅山、杜洛克和長白)之間的比較基因組分析,分別鑒定了 3 062、1 228、907和1 519個選定區域,同時發現Wnt信號通路、組氨酸代謝、磷酸肌醇代謝、β-丙氨酸代謝、醚脂質代謝等與發育和代謝相關的重要途徑。此外,研究人員為了解雜交豬變異的潛在遺傳機制,對高密度變異品種的復雜性狀進行了高效定位,采用標準混合線性模型對57個品種的469頭豬SNPs、InDels、CNVs進行鑒定,并開展 GWAS分析,從中鑒定和分析了約1 900萬個SNPs、180萬個InDels和18 016個CNVs,這些變異可作為豬高效優質育種的重要資源[6]。產仔數是影響養豬業生產與經濟效益的重要因素,有研究對丹麥長白豬和約克郡仔豬的出生總數及第5天產仔數進行GWAS分析,確定6個區域與繁殖性狀相關,同時鑒定出位于11號染色體上影響總產仔數的候選基因ENOX1[7]。2022年,黃路生院士團隊在《Nature》上發表了重要研究成果,通過GWAS分析發現ABO血型基因通過調節N-乙酰半乳糖胺含量顯著影響豬腸道中丹毒絲菌科相關細菌的豐度,并系統闡明了其作用機理,這是畜禽領域首個利用GWAS鑒別到宿主基因組對腸道菌群組成影響因果變化關系的成果[8]。調控元件的功能注釋是解析表型變異及基因調控機制的重要基礎,Zhao等[9]利用ChIP-seq、ATAC-seq、RNA-seq和Hi-C等多種技術獲得了包含12種組織的199組表觀遺傳調控數據,解析了豬基因組的超級增強子、活性啟動子等調控元件特征,闡明了豬基因組調控元件的組織特異性及其三維空間結構對基因表達調控的影響。Yang等[10]系統繪制了妊娠前33 d至出生后180 d共27個生長發育時間點的骨骼肌全基因組甲基化和轉錄組圖譜,發現DNA甲基化通過影響轉錄因子SP1結合調節IGF2BP3的表達,從甲基化角度系統揭示了胰島素信號通路在肌肉發育過程中的重要調控機制。
在奶牛和肉牛領域,應用GWAS技術對產奶性狀[11]、繁殖性狀[12]、健康性狀[13]等進行了深入分析。肉質和生長性狀方面,Zheng等[14]在兩種中國本土肉牛中發現DMBT1基因中1個全新的CNV與生長性狀密切相關,證明DMBT1基因在早期成肌階段的骨骼肌發育中發揮重要作用,GAL3ST1[15]和MFN1[16]的CNV可作為肉牛選育的分子標記。韓國研究人員對2 110頭Hanwoo牛的表型和基因組數據進行GWAS分析,確定了位于14個選定染色體(BTA)上的107個支持牛肉質性狀的重要SNPs[17]。Liu等[18]利用綜合單倍型得分(integrated haplotype score, iHS)和 同 質 性 運 行 (runs of homozygosity, ROH)方法,全面分析了荷斯坦牛基因組中的選擇特征,識別與重要經濟性狀相關的基因,該研究成果有利于進一步了解家畜種群中持續不斷的自然或人工選擇對生物學過程和機制的影響。在產奶性狀方面,呂小青等[19]對1 596頭中國荷斯坦奶牛RPL23A、ACACB基因的3個SNPs進行檢測,發現RPL23A、ACACB基因多態性影響奶牛的乳脂或乳蛋白性狀,可作為中國荷斯坦奶牛產奶性狀的分子標記。在抗病方面,Johnston等[20]利用GWAS分析愛爾蘭商品牛的被動免疫和疾病性狀相關的SNP標記,發現1個SNP(ARSBFGL-BAC-27914)與血清IgG含量,以及結核、腹瀉等疾病性狀均密切關聯,為抗病育種工作提奠定了重要基礎。
Illumina公司先后推出綿羊50K SNP芯片、山羊52K SNP芯片、綿羊600K SNP芯片[21],使GWAS在綿羊和山羊生長發育性狀[22]、產仔數[23]、羊毛性狀[24]及抗病性[25]等研究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在高產性狀方面,Ladeira等[26]運用 Illumina OvineSNP 50K芯片研究CNV與綿羊生長、剩余采食量和飼料效率、胴體等性狀之間的關聯,在438只綿羊中鑒定了1 167個常染色體CNVs,發現包括SPAST、TGFA和ADGRL3在內的多個參與細胞分化和能量代謝的標志性基因。Rovadoscki等[27]對綿羊進行GWAS分析,發現27個染色體上差異顯著的基因組區域,并鑒定出DGAT2、TRHDE、TPH2等9個與綿羊脂肪組成遺傳機制相關的基因。在繁殖性狀方面,Bai等[28]利用GWAS分析發現,刪除山羊PPP3CA基因中的突變位點對產仔數有顯著影響。Grzegorz等[29]應用綿羊50K SNP芯片對3個品種的155只波蘭綿羊繁殖性狀進行GWAS分析,發現EPHA6基因與綿羊高繁殖率相關。在產奶性狀方面,藍賢勇等[30]發現產奶關鍵基因DGAT1與山羊中的一種新CNV重疊,為奶山羊育種提供重要輔助選擇標記。而在抗病性狀研究中,美國科學家Becker等[31]利用GWAS確定了與卡塔赫丁綿羊胃腸道線蟲耐藥性相關的遺傳位點,分析發現DIS3L2基因對卡塔赫丁綿羊胃腸道線蟲抗性具有一定作用。
目前,家畜重要經濟性狀遺傳分子基礎研究主要集中在基因結構和功能注釋,以及基因遺傳變異對表型的影響上。通過GWAS分析發現了大量與家畜經濟性狀和疾病關聯的分子標記,鑒定了一些重要的QTLs,但并不能確定這些通過GWAS發現的顯著SNPs是否影響蛋白質的形成,很難進行精確的致因變異研究,對關鍵功能基因和調控序列的研究不夠深入。GWAS分析的根本目的是尋找影響性狀的 QTN(quantitative trait nucleotides),對GWAS分析得到的分子標記和QTLs進行深度挖掘,才能鑒定出性狀決定QTN,從而闡明性狀變異的根本原因。我國畜牧業正處于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養殖業與資源環境、生物安全和動物福利的矛盾問題突出,同時自動記錄設備和各類傳感器在畜牧場的大規模應用給我國家畜養殖帶來了很多挑戰,應運而生的新性狀基礎理論研究與解析也是行業發展的必然趨勢。這些新性狀包括與生產效率(飼料效率、公畜繁殖力等)、應對環境挑戰(甲烷排放量、熱應激抗性等),健康和福利(免疫反應、后備牲畜存活力等)、產品和加工(傅里葉中紅外光譜、乳樣凝固性等)及管理等相關(牲畜性情等)方面[32]。
1.2 家禽重要經濟性狀的遺傳基礎與分子調控機制
家禽具有生長周期短、飼料報酬率高、繁殖力強等特點,是人類主要的蛋白質來源,也是脊椎動物發育生物學研究的重要模型[33]。2004年,雞基因組測序草圖發布,隨后雞、鴨、鵝等家禽的基因組參考序列相繼發布,禽類功能基因組時代也隨之到來,推動了家禽SNP芯片的廣泛應用[21]。目前,通過GWAS發現了與家禽羽色性狀、肉質性狀、生長性狀及抗病性狀等經濟性狀顯著相關的候選基因,并進行了驗證。
羽色性狀是禽類表型遺傳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主要由黑色素和類胡蘿卜素所決定[34]。目前雞羽毛顏色性狀遺傳調控機制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黑色素相關通路,其中,Wnt、KIT/KITL和EDN3/EDNRB等信號通路對黑色素細胞的生長發育、遷移和分化具有重要的調控作用,α-MSH/ASIP-MC1R信號通路負責調控黑色素的合成[35]。研究顯示,通過全基因組范圍內的遺傳變異檢測技術挖掘與羽色性狀相關的基因和變異位點,可以揭示黑羽、麻羽、顯性白羽、隱形白羽、常染色體白化、銀羽、性連鎖不完全白化、斑點羽和性連鎖橫斑羽(蘆花羽)等多種羽色性狀的遺傳調控機制[36]。肌肉是肉雞的重要經濟性狀,Zhang等[37]研究證明,miR-21-5p可以通過調控KLF3基因的表達影響雞骨骼肌的生長和發育。Liu等[38]對59只雞的55K SNP芯片數據和肌間脂肪表型數 據進行分析,發 現ACSL1、PPARα、ACADL、FABP7等與脂質代謝相關的基因可能與肌間脂肪合成有關。生長性能與生產效益密切相關,對家禽育種十分重要,Liao等[39]利用GGRS(genotyping by genome reducing and sequencing)檢測了252只白來航雞的基因型,發現RBPJ基因與體重密切相關,并進一步通過表達量分析探究了其參與表型調控的機制。Zhou等[40]分析1 024只鴨的重測序數據發現,一種遠程調控突變可能導致IGF2BP1基因在鴨出生后持續表達,使鴨的體尺增加15%,飼料效率提高6%。雞的抗病性直接影響家禽業生產力,也關系著食品安全,馬立克病毒(Marek’s disease, MDV)是目前應用全基因組學技術研究最多的病毒,Yan等[41]從具有MDV抗性的2個雞品系基因組中發現了許多CNVs,并從中篩選出了一些與MDV抗性有關的基因。同樣,Bai等[42]利用全基因組范圍內的CNVs掃描和分析,在2個MDV抗性有差異的自交系中發現IRF2基因與雞的MDV抗性有關。
在后基因組時代消費多元化和生物安全防控升級的時代背景下,家禽育種工作的重點是加強基因組選擇在家禽肉質、抗病和抗逆性等多性狀聯合的作用機制研究和解析中的應用。而目前各國育種學家運用基因組學技術的研究多集中在家禽外觀、生產、繁殖、肉質、抗病等單一性狀的機制,在復雜性狀聯合分析方面還比較缺乏。隨著高通量芯片和測序技術的不斷發展,多組學分析整合家禽各種性狀信息,如比較基因組信息、受選擇信息、基因表達信息、調控信息和變異信息等[43],將有助于更加精確地篩選與重要性狀相關的變異位點,加速育種進程。
2 畜禽分子設計育種技術的研究進展
分子設計育種已經成為未來種質資源創新、國際農業科技競爭和種業競爭的戰略核心。分子設計育種的概念源于2003年Peleman和Van der Voot提出的設計育種(breeding by design),主要技術環節包括基因定位,篩選優良等位基因,把分散在不同個體中的優良基因聚合在一起,從而實現設計育種的目標[44]。生物技術、信息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的融合發展為解析生物復雜性狀的遺傳調控網絡帶來了機遇,為分子設計育種技術奠定了理論基礎,為創制高產、優質、高效、高繁、抗病和環境友好型新品種提供了精準解決方案。以深度學習為代表的人工智能已成為挖掘多組學數據的高效工具。基于深度學習的多組學數據整合算法已在疾病調控網絡構建等領域取得了優異的預測性能[45]。利用人工智能分析工具深度挖掘畜禽多組學數據,將更加精確定位影響表型的關鍵功能基因及其變異[46]。整合多組學的育種價值評估已成為農業動物育種的新方向,基于基因組選擇的育種價值評估顯著提高了荷斯坦牛等商用品種的選育進程[18],但由于現階段基因組選擇依賴大規模參考群,因此地方品種中特有功能變異難以被有效評估。利用機器學習策略選擇最優預測模型提高了豬繁殖和牛肉質等性狀基因組預測的準確性[3,47],在部分性狀改良上優于傳統 GBLUP(genomic best linear unbiased prediction),但仍需添加地方品種的優異變異進行效應評估。與單純基于基因組變異數據的預測模型相比,多組學數據能補充基因組層面難以捕獲到的與表型相關的細微特征,提高基因組預測復雜性狀準確性,進一步引入機器學習算法調整地方品種中特有變異的權重值,可對地方品種育種價值有效評估。
基因編輯技術是對生物體內源基因精確修飾的一項新型技術,從出現到應用對農業科學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48],代表性基因編輯技術主要包括3種。一是鋅指核酸酶(zinc finger nuclease, ZFN)技術,它是第一代基因編輯技術,其基于具有獨特DNA序列識別的鋅指蛋白實現功能[49]。二是轉錄激活效應因子核酸酶(transcription activation-like effector nuclease,TALEN)技術,其是一類基因定點編輯技術,由特異性DNA結合結構域 TALE和DNA切割結構域Fok I核酸內切酶組成。與ZFN相比,TALEN技術的構建相對簡單、成本較低,在普通分子生物學實驗室即可完成操作;此外,TALEN技術基于重復單元和核苷酸堿基的一對一識別模式,具有更強的特異性和更高的目標編輯效率。因此,自2010年問世以來,TALEN迅速取代ZFNs成為新一代基因組編輯技術[50]。三是成簇的規律間隔短回文重 復 序 列/Cas關 聯 蛋 白 9(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CRISPR-associated protein 9,CRISPR/Cas9)技術,它是基于前兩種編輯技術的又一次飛躍,極大提升了精準基因編輯的效率和準確性,短短幾年內,CRISPR/Cas9成為現有基因編輯和基因修飾里面效率最高、最簡便、成本最低、最容易上手的技術之一,是當今最主流的基因編輯系統[51]。基因組編輯技術拓寬了相應的動物表型變異,在畜禽育種中迅速得到應用[52]。美國第一例利用基因編輯技術培育的豬(GalSafe)于2020年12月14日獲批上市,它不僅可以有效減少異種移植中的急性免疫排斥反應,還可為肉類過敏患者提供安全食品[53]。此外,研究者們還利用CRISPR/Cas9技術獲得了大批高產、抗病的牛[54]、山羊[55]和綿羊[56]。未來,基因編輯產品的產業化規模將越來越大,競爭將愈加激烈。
多基因聚合育種是畜禽分子育種的重要方法之一,其將分散在不同品種或品系中優良個體的優良基因聚合到同一個體的基因組中,從而獲得具備特定性狀的新品種(系)[57]。目前,實現多基因聚合的主要途徑是在確定與優異性狀相關的分子標記基礎上,通過雜交、回交和分子標記輔助選擇技術在后代中選擇多個優良基因聚合在一起的個體。分子標記輔助選擇所獲得的與目標數量性狀基因緊密連鎖的分子標記可靠性強,且不受等位基因顯隱性關系及環境的影響,在動物育種中的應用加快了遺傳進展,縮短了育種周期。但該方法選擇的個體后代中聚合的基因可能會重新分離,造成目標性狀不穩定[58]。近年來,隨著轉基因和基因編輯技術的不斷發展,多基因聚合已經成為畜禽育種的研究前沿。
3 我國畜禽分子設計育種面臨的瓶頸
畜禽很多重要經濟性狀都是復雜性狀,遺傳水平對性狀的貢獻率只有30%左右,其余來自遺傳與環境的互作[59]。多數研究還是聚焦在單個基因對于重要經濟性狀的影響,對于其復雜性、基因與基因間協同性、基因與環境間的互作模式研究不足。盡管有大量研究針對重要經濟性狀的遺傳水平,但是依然缺乏對畜禽個體表觀水平、環境水平的系統評價,以及3個水平間相互作用方式的探索。因此,必需加強遺傳、表觀、環境3個層次的研究并探索它們之間的作用機制,進一步精準定位具有廣適性或特殊適應性的、用于目標性狀改良的重要分子靶點,完善具有自主知識產權關鍵基因的育種體系,使遺傳研究與性狀改良實踐緊密結合、互相促進,推動我國畜禽分子設計育種技術體系建立。
除了復雜性狀的分子遺傳機制尚不清楚外,我國畜禽分子設計育種還存在種質資源保護和精準鑒定、基因組大數據平臺、智能表型組測定、育種價值評估技術和算法、基因編輯等關鍵育種技術原創性不足或應用滯后問題。雖然我國發布了一些動物跨物種多組學知識庫[60],但與美 國 國 家 生 物 技 術 信 息 中 心 (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 NCBI)擁有全球共享的生物信息相比,我國生物大數據平臺信息覆蓋程度還遠遠不夠。在基因編輯育種領域,我國雖然在畜禽基因編輯育種材料創制方面處于世界先進水平[61],但是技術原始創新的專利受控于國外。此外,多基因聚合育種存在多重技術難點,與畜禽重要性狀相關的功能基因沒有完全解析清楚,基因組操作的靶點仍不明確;在動物基因組中同時進行基因編輯的數量有限,難以實現同時編輯幾十上百個位點。隨著各種表型組和基因型數據庫不斷豐富,多種性狀相關的重要功能基因和調控序列挖掘不斷深入,以及基因編輯技術、干細胞育種技術的不斷突破,有望解決分子設計育種的技術難題。
4 畜禽重要性狀遺傳調控與分子設計育種的發展趨勢
未來,畜禽重要性狀基礎研究的方向主要包括畜禽優異種質資源形成與演化機制、畜禽重要性狀關鍵基因和調控網絡、高通量功能基因挖掘和鑒定技術等。其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構建畜禽核心種質全景組學特征,揭示農業動物從野生種到地方品種,再到現代品種的發展過程中重要性狀形成與演化規律,挖掘優異性狀形成的關鍵調控基因;建立我國畜禽品種標準樣品庫,研發表型高通量鑒定技術和基因型高通量鑒定技術;挖掘與鑒定親本和雜種間等位基因特異表達的功能基因和調控元件,解析基因互作與雜種優勢的關系及分子調控機制,闡明農業動物重要性狀雜種優勢形成的遺傳和分子機理;整合表型組、基因挖掘、功能解析、性狀選擇、新基因資源創制,系統解析性狀遺傳規律和形成機制,提升畜禽優良種質創制的關鍵理論和技術,突破分子設計育種的瓶頸。
組學技術和數據科學推動分子設計育種向高通量智能方向快速發展。基因組學、分子生物學、影像學、遙感信息學、數據科學尤其是人工智能的迅速發展,將推動育種科學向以高維數據收集挖掘為基礎、以數據建模預測為指導的智能化育種技術體系發展。在利用預測模型育種方面,國際研究呈現出單基因模型向多基因模型、線性模型向非線性模型、低維數據向高維數據轉變的特點。美國奶牛育種行業自2008年開始大規模使用全基因組選擇育種方法之后,產奶量、蛋白含量、脂肪含量等復雜性狀的育種選擇效率較之前20年的平均水平提高了2~3倍[62]。目前,國際上正在嘗試在全基因組選擇模型內加入其他多組學數據,并利用人工智能模型準確預測相關遺傳位點,為畜禽分子育種精準設計提供靶位點[63]。
綜合性狀的多維精準耦合是分子設計育種的新方向。復雜性狀首先受遺傳或基因控制,這種遺傳變異也被認為是第一層次的控制;然而,遺傳信息一致的生物也會因染色質修飾的不同表現出不同的性狀,這種表觀變異被認為是第二層次的控制。此外,同一個生物在遺傳和表觀修飾一致的情況下,仍然會在不同的環境中表現出不同的性狀,這種由生物與環境互作產生的環境變異被認為是第三層次的控制[64]。遺傳變異、表觀變異和環境變異3個層次的協同互作精準控制了復雜性狀的形成,決定了物種的不同表型,造就了生物的多樣性[65]。此外,不同性狀間存在一定關聯和相互影響[66],其根本原理是各個性狀決定中多維度控制之間的相互作用及耦合,譬如奶牛在突變DGAT1和GHR位點增加產奶量的同時,可能會降低脂肪和蛋白質含量占比[62],因此,發掘和解析控制畜禽復雜性狀形成的多維控制機制并將它們有效地耦合是實現畜禽復雜性狀精準改良的基礎,在實踐過程中形成的技術體系最終將成為品種分子設計理論的創新源頭。育種原始創新在由單一性狀的一維控制向綜合性狀的多維精準耦合轉變,深入研究復雜性狀的精準控制將為闡釋物種多樣性和精準育種奠定理論基礎。
5 結語
解析畜禽重要性狀的遺傳分子基礎是培育優良畜禽新品種的重要前提。綜合運用遺傳學、基因組學、生物信息學、分子生物學、生物化學、細胞生物學、動物育種學等方法破解畜禽基因組和基因圖譜,篩選畜禽重要性狀相關的基因定位和分子標記,挖掘關鍵功能基因、調控序列和調控網絡,揭示基因、表型與環境的互作規律,為動物高產優質育種提高分子遺傳學的選擇標記和操作目標。隨著各種動物全基因組測序完成和生物信息學技術的進步,基于分子標記和表型測定建立起來的全基因組選擇技術已經在動物育種中廣泛應用,大大縮短育種周期,提高了選擇的準確性。隨著基因編輯技術的突飛猛進,通過編輯功能基因和調控序列,開展多基因聚合育種,培育高產、優質和抗病動物新品種已成為動物育種的重要方向。解析畜禽產肉量和品質、產奶量和乳品質、產絨毛量和品質、產蛋量,以及生長、發育、繁殖、抗病、耐寒和耐低氧等重要經濟性狀的分子遺傳基礎,確定關鍵功能基因,從而提高性狀選擇的準確性,培育具有特定性狀的畜禽新品種,對落實國家種業振興行動方案,推動畜牧業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