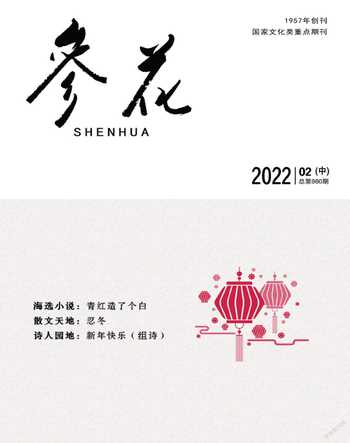試從影視藝術角度探析《福貴》的改編藝術
2005年,根據《活著》改編的電視劇《福貴》上映,引發巨大反響,本文試從影視藝術的角度探析《福貴》的改編藝術。
隨著大眾傳媒的發展,優質的小說文本作為文化IP被改編成影視作品已十分常見,如近些年由網絡文學改編的《慶余年》等。而在傳統、嚴肅文學領域,余華的長篇小說《活著》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
小說《活著》與據原著改編而成的電視連續劇《福貴》在各自領域及受眾群體中,都引起強烈的反響,并獲得成功。簡單而言,長篇小說《活著》為電視連續劇《福貴》提供了優秀的文本和素材,電視連續劇《福貴》也為長篇小說《活著》提供了多種宣傳渠道,使《活著》這一文化IP更加深入人心。
然而,由于小說和影視劇分屬不同的藝術類別,傳播媒介及原作者和影視編劇、導演在自身的審美價值觀、人生閱歷等方面的差異性,使影視改編作品的最終呈現效果與原著小說文本之間會存在部分差異,這通常是由于改編造成的。綜合來看,小說與影視劇有各自的局限性,也有各自的傾向性,但最終都在創造優質的文藝作品。
一、原著小說《活著》的藝術手法
長篇小說《活著》是作家余華的代表作品,其筆觸逐漸轉入溫情化。這篇小說最初發表于1992年的《收獲》雜志,一經發表,便在國內外引發巨大反響。小說《活著》延續余華傳統的表現手法,保留慣用的手段來展現故事。開篇采用倒敘手法,從第三人稱視角出發,以與老人的相遇為起點,講述主人公福貴40年來的風風雨雨,而身邊的親人朋友在這40年里一一離他遠去。
小說里本是大少爺的福貴,被人設計,嗜賭成性,在賭場敗光了自己的家產,這也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了其父母的離世。幸好還有溫婉善良的妻子對他一直不離不棄,而后子女雙全。本以為可以過上平淡美好的日子,可在十多年后,兒子、女兒、女婿、妻子、外孫卻都因為這樣、那樣的事故,不幸離世。到了最后,只剩福貴和老牛一人一牛共度余生。
“……我爹指望我光耀祖宗,他算是看錯人了,我啊,就是這樣的命。……做人還是平常點好,爭這個爭那個,爭來爭去賠了自己的命。像我這樣,說起來是越混越沒出息,可壽命長,我認識的人一個挨著一個死去,我還活著。”[1]
不得不說,福貴的一生是一部悲劇,在余華的筆下,這種人生的命運是與時代相結合產生的,也是個人性格所導致的一種必然。而這種認知,不可避免地為《活著》這部作品注入了悲觀色彩,這種悲觀是余華作品共有的特征,成為余華作品中極為明顯的表現手法和基調。
二、影視劇《福貴》的改編特色
影視劇《富貴》雖然源于小說,但是與原作相比又是一部完全獨立的新作品。
2005年,由《活著》改編的33集電視連續劇《福貴》登上熒屏,該劇由朱正導演,謝麗虹編劇,在社會上引發了熱烈反響。相較于小說而言,電視劇的表現形式更加豐富;而相對于另一種改編形式——電影來講,電視劇時間更長,受眾更廣,可展現的內容也更為豐富,所產生的社會影響也更加深遠。因此,電視連續劇《福貴》在忠于原著的基礎上對小說進行了二次加工和改編。
下面,本文通過對比來探析《福貴》中的特點與表現手法。
(一)感情戲刻畫更加細膩
在影視劇的改編過程中,為了增加看點,編劇往往會采用增加感情戲的做法吸引觀眾,《福貴》也不例外。
在原著中,由于作者余華的慣用手法是采用接近冷漠的口吻敘事,因此,對感情、故事人物的描寫,在情感刻畫中趨于理性,顯得冷靜而內斂。在《活著》中,福貴與妻子的婚姻描寫,放在電視劇中卻不能滿足觀眾的需求。因此,在《福貴》中,增加了男女主人公之間的感情交集,人物情感刻畫更加細膩,使劇中人物形象更加鮮活,也更具看點。劇中開頭,福貴前往陳記米行唱跳花鼓戲,陳記米行大小姐家珍放學歸來,家珍被花鼓戲吸引,福貴也對家珍的美貌十分著迷,心生愛慕,為兩人的婚姻打下了基礎,后來福貴要求上學,在學堂求婚,與情敵斗智斗勇,到婚禮現場搶婚,這部劇中男女主人公之間的感情戲十分精彩。他們的愛情貫穿全劇,雖歷經悲歡離合、滄海桑田,但始終不離不棄。
與描寫主人公之間的愛情一樣,原著對啞女鳳霞情感生活的刻畫也趨于平淡。因此,電視劇《福貴》在改編的過程中增加了胡老師、二喜、鳳霞三人的感情糾葛。該劇編劇謝麗虹在刻畫這一情節時,為了避免這一情節落入俗套,巧妙地安排了三人之間的情起情滅,從獨特的視角去審視這一感情變化,帶給觀眾更豐富、更獨特的情感體驗,描繪出普通人真摯美好的情感與現實之間的博弈與斗爭,刻畫了小人物在社會現實中卑微且無力抗拒的一面,也使這一影視劇沾上了一絲文學的意味。謝麗虹編劇將三人的情感糾葛植入在一個動蕩且復雜的社會背景里,這樣更容易打動人心,而文學的色彩也讓整部電視劇的悲劇性更加凸顯出來。
當然,如果只有愛情色彩,這部劇是無法成為經典的。劇中,人物之間的其他感情相較于原著而言,也進行了進一步的刻畫。福貴、家珍之間的不離不棄、情比金堅,他們與二喜、胡老師之間守望相助的真情,鳳霞和有慶真摯樸實的手足情,有慶和胡老師之間傳道授業的師生情,鄉親之間攜手共濟的友情,這些普羅大眾之間的情感,雖樸實但真摯,最能觸動人心,這些情感最終匯聚為一種精神力量,支撐著苦難的人們在生活中繼續前行。
(二)人物形象塑造更加鮮活
人物形象是否深入人心,是影視劇改編中的一大要點,好的人物形象塑造可以打造經典,例如王剛飾演的和珅,張國立飾演的紀曉嵐。這一點在電視劇《福貴》的改編中也得到了充分展現,對原著人物形象的塑造進行了增補,其中,比較典型的是胡老師與懶漢二愣。
胡老師是一名體育老師,在《活著》中其實沒有過多的筆墨描寫他,在《福貴》中卻增加了很多戲份,在劇中也很是搶眼。胡老師是有慶的貴人,他發現了有慶的運動天賦,成了有慶的老師,并將有慶帶入體校。后來,他又與鳳霞互生情愫,差一點成為福貴的女婿。如果用當下的視角審閱胡老師,那他一定是一個“老實人”,生性善良、懦弱、待人溫和。在后續的劇情發展中,盡管胡老師安分守己,卻依舊次次被推入浪潮。讓人意想不到的是,這樣的生活非但沒有打敗他,反而塑造了其堅韌不拔的品格,也有了后來胡老師為民請命的情節。編劇對胡老師的這種安排,是符合劇中與原著的精神內核的,這種內核也是后期支撐福貴活下去的精神動力,這也許是編劇想要傳達給觀眾的一種精神。
相較于對胡老師的補充,懶漢二愣的形象則是《福貴》一劇中進行的最徹底的人物形象改編。
二愣出生于一個貧困家庭,卻染上了好逸惡勞的壞習氣,是典型的地痞流氓形象。然而,他卻搖身一變,從一個令人不齒的地痞無賴成為令人畏懼的反派,倒讓人想起魯迅先生筆下的阿Q,只不過兩個人物的結局不同。二愣形象的變化也大大增加了福貴一家的悲劇色彩,無比牽動觀眾的心弦,也推動了整部電視劇的故事情節的發展,將劇中的矛盾沖突推上了一個新的高度:無辜的胡老師被抓走,間接造成了二喜的死亡。
其實,二愣的這種變化恰恰是悲劇的一種,他好逸惡勞的性格和品行,必然給他后續的發展帶來困擾,帶來災難,同時,這也給故事帶來了戲劇性,刻畫出一個經典的地痞流氓形象。因此,筆者認為,二愣是《福貴》改編過程中,塑造得最成功、最深刻的一個人物形象,其也成為電視劇《福貴》中的一大亮點。透過二愣,了解了社會的復雜性和人性本質的弱點。
(三)融入民間傳統藝術形式
從《福貴》一劇的影視手法中,不難看出,劇作者相較于原著而言,加入了一些民間傳統藝術,或者說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例如安徽省的花鼓戲。
劇中福貴與家珍緣起花鼓戲,同時,花鼓戲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這部劇的可看性和娛樂性,給福貴的內心帶來一絲慰藉,沖散了這部戲的悲劇色彩。為此,電視劇《福貴》的編劇將故事的發生地定位為安徽省。如此一來,花鼓戲這種源于安徽民間的傳統藝術便不再那么突兀。
與此同時,編劇還巧妙地將花鼓戲與時代相結合,讓其成為時代變遷的見證者,例如,劇中福貴前往農場看望岳父,告訴他鳳霞正在學跳花鼓戲,岳父心里一陣緊張,因為在過去,跳花鼓戲是災荒之年外出討飯的手段,老人在為自己的外孫女擔心。福貴趕緊向岳父解釋,現在都能吃飽飯,跳花鼓戲已經成為慶祝豐收的一種演繹形式,這也使花鼓戲這一安徽民間傳統藝術得到了進一步傳播。
除此之外,花鼓戲還成為貫穿整部劇中男女主人公一生的線索,起到推動故事情節發展的作用。正是因為福貴前去頂替頂班跳花鼓戲,才和家珍相遇,二人逐漸互生情愫。土地改革后,福貴分得了五畝好地,興高采烈地和家珍一起在田間跳起了花鼓舞。在家珍最后即將離開人世的時光里,福貴也是在強忍悲傷地跳花鼓戲將家珍送走的。在啞女鳳霞愛情失意的時候,她也將注意力轉移到花鼓戲上,兒子有慶不幸逝世之后,福貴來到有慶的墳前,在田間跳起了花鼓戲。其實可以理解為,跳花鼓戲是福貴與鳳霞的一種情感寄托,是他們宣泄內心情感的一種途徑,借此來排解心情,這一行為充斥著內心的滄桑與無奈。
三、《福貴》對影視劇改編的啟示
(一)做好觀眾貼心人
與詩歌、散文、小說等相比,以電影、電視劇為代表的大眾藝術,是講究效益的。
基于以上觀點,影視劇的改編應該慎重考慮觀眾的接受程度,切忌過于追求陽春白雪,從而影響觀眾,這一點,《福貴》一劇就做得很好。
相比小說,觀眾往往沒有充分的時間去觀看和了解福貴冗長的一生,不然難免會產生枯燥乏味的感覺,這就很考驗編劇的素養,能否做到合理轉化。
同時,在改編中也要慎重考慮觀眾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原著中,福貴的結局是帶著濃郁悲情色彩的,只剩他一人去面對這悠長的一生。而在電視劇中,結局卻帶上了一抹溫情色彩,有一頭老牛陪伴著福貴,不至于自己孤零零地走向生命的終點,這一敘事考慮到了觀眾的心理承受能力,也滿足了觀眾對于苦盡甘來的團圓結局的一種期盼,盡可能地保留了原著的精神內核,這種對觀眾心理的揣摩,值得其他影視劇學習。
(二)不斷打磨作品質量
文字化與圖像化是傳媒的兩個趨勢,影視劇改編則是將文字化的優質內容圖像化,因此,需要不斷打磨作品質量。
眾所周知,文字是小說文本的呈現方式,但文字往往又是抽象的,無法給人直觀的感受。因此,影視劇往往需要考慮觀眾充分的想象力與自身閱歷的影響,從而復刻出小說文本所敘述的世界。原著《活著》所敘述的世界處于幾十年前,許多讀者是沒有這個閱歷的,許多文本中呈現的場景可以調動想象力去理解,正因如此,小說文本可以通過文字表達更深場景或層次的深意。
而影視劇就大不一樣,它能夠經過鏡頭語言和聲音的處理帶給觀眾一種宏大的視聽盛宴。觀眾可以從這種營造出的圖像中直接獲得想要表達的內容,它是更加具體可見的,無須進行復雜的理解,因此,受眾更加廣泛。
通過影視劇中呈現的語言、神態、動作以及畫外音、背景音樂等元素,觀眾往往可以輕易了解影視劇想要表達的含義,但這種營造出來的場景往往是浮于表面的,較多觀眾也抱著消遣的心態去觀看,因此,容易忽略作品文本所表達出來的深層次含義。
四、結語
在將文本化轉變為圖像化的過程中,編劇需要進行不斷的取舍,由于容量、時長、技術等問題,部分原著文本所呈現的精彩之處,并沒有辦法在影視劇中進行復刻,只好進行省略。因此,劇作者在改編的過程中,需要充分地把握好兩者之間的差距,合理化地做好取舍,做好對原著內核的保留,這樣才能做好文本的圖像化,才能打造出一部優秀的影視作品。
參考文獻:
[1]余華.活著[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作者簡介:陳越擎,女,碩士研究生,吉林動畫學院,研究方向:影視藝術)
(責任編輯 于美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