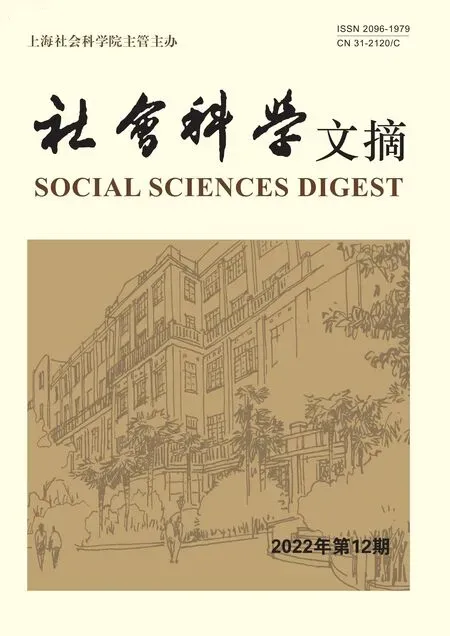身心一體與性命論主體的確立
文/吳飛
本文是對性命論主體建構的哲學探討。建構性命論主體的一個關鍵,是破除心物二元論。現代中國哲學接受唯物論,并非由于意識形態因素,而是因為以儒、道為主流的中國哲學本就有唯物論因素,即強大的氣論傳統。不過,正如熊十力和劉咸炘兩位先生意識到的,中國的性命論哲學傳統并非建立在心物二元基礎上,因而其唯物論亦非機械唯物論。若將傳統性命論哲學做一創造性轉化,以面對現代問題,我們首先需要破除二元論,在身心一體的基礎上建構性命論主體。
從心物二元到身心一體
主體性二元論哲學源于古代西方哲學傳統,經笛卡爾的心物二元論與主體性哲學而確立。前者奠定了現代人的世界觀并劃定了現代人文與科學研究的邊界,后者為現代自由主義奠定了哲學基礎。兩方面結合起來,便是一種以認知主體為出發點的現代哲學:我思故我在。笛卡爾將精神定義為思想,物質定義為廣延,而又認為,自我就是一個精神。
中國哲學和宗教傳統都沒有發展出這樣的二元對立,雖有諸如身心、陰陽、理氣之類的二分,但與西方式的二元論模式都有巨大差別。突破二元論傳統,理解身心一體,以建構性命主體,這是性命論哲學要做的工作。
嚴格說來,中國并不存在西方哲學意義上的“心物”問題,而只有身心問題。中西哲學皆以心為身之主宰,區別在于,西方哲學傳統中,這種關系被理解為精神性存在對物質性存在的優越和主宰。而在中國哲學中,心首先被當做臟腑器官當中的一個來看待,它和所有其他臟腑一樣,有自己的職分和功能,但它的功能比其他臟腑的功能更重要,因而作為君主之官,統領著身體中所有其他部分,但其又和所有臣民一樣,都是整體的成員。孟子說:“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告子上》)耳目為小體,心為大體。耳目沒有思的功能,所以會蔽于物;而思考正是心的功能,所以人要先用心來思考,這便是先立乎其大。
中國傳統之所以如此看待心與其他臟腑的關系,是因為身體當中的所有臟腑、器官都是維持與提升人的生命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心臟。心與其他臟腑之間的君臣關系,并不是精神對物質的關系。
《大學》中對八條目的次序安排尤其展現出這種身心關系: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中前四條都是修身的功夫,通過格物、致知、誠意做到正心,而正心是修身的關鍵,修身是齊家的關鍵,齊家是治國的關鍵,治國是平天下的關鍵。作為最要害的環節,所謂“修身”,并不是針對肉體性身體的鍛煉,而是以正心為最核心內容的自我修養。身即自我之總體,而心是這個自我的主宰,通過正心才能做到修身。以正心、修身建構起來的自我,與笛卡爾通過“我思—我在”構建起來的自我非常不同。中國哲學中這種身心結構,在《大學》中已經有一種倫理學和政治哲學的推擴,即由身而家,而國,而天下的推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正心以修身,被理解為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共同基礎。
性命論主體
性命論主體既非認知主體,亦非意志主體。我是一個以心御身的性命體,心雖為主,僅有心卻無法構成自我,因為身、心并非相互獨立的兩種存在物。身是自我生命之全部,心是生命之主宰與精華,理性的心對此一生命的反思、主宰與調整,即構成性命論主體。無論欲望、認知,對種種工具的使用,都是自我生命活動的一部分。這個主體,便是性命論哲學的出發點。我和其他生命體,乃至宇宙萬物之間的關系,首先是生、被生、共生的關系,認知、欲求、使用,都是其次的。
性者,生也,但“性命”不同于完全生物性的生命,而是對有生有滅之物的哲學理解。自我之性命,是我一切生命活動的出發點,但我僅僅是世界上眾多生命中的一個,我并沒有絕對的優先性。如何平衡文明與自然,是以二元論建構的主體性哲學的巨大困難,也是性命論哲學最大的優勢。以外物為認知對象、欲望對象或使用工具,最終都無法將他人當做和我一樣的主體看待,因為在自我面前,他人和所有其他物體一樣,也是被對象化的物,我無法將他當做和我一樣的精神主體。這也正是現象學之交互主體性試圖克服的難題。而在性命論的主體哲學中,各正性命的任何一個主體都處在相對的中位,但沒有一個中位是絕對的。
每個人只能以自己為中心觀察外部世界,無論是時空架構、聲音色彩氣味、茫茫太空,還是草木禽獸,乃至我的五臟六腑。但最重要的不是我這個靈魂對外物的認知,而在于我的生命與外部世界的交匯。我在世界中生活這個常識性的事實,是一個給定的前提,既然在生活,我就不是完全孤立的,因而必須從我所在的主體出發,與他人和萬物共同生活在這個世界當中。主體的尊嚴不是通過封閉自我、無視其他主體獲得的,而是通過反思自我、推己及人、觀照萬物、體察天地,盡可能從全局的視角看待我的生活世界而逐漸達成的。
我們由此可以確立性命論主體的哲學意涵。性命個體是因為生生而在天地之間有一席之地。他通過自己的智慧能力和理性思考,確立自己所處的這個中位,牢牢地立足于中位的主體,要認識自己周圍其他的性命體與萬物,把他們當做同樣的性命體來對待,理解自己所在的這個生生共同體。
氣論宇宙觀
氣構成天地萬物,是宋明理學各家,乃至整個中國傳統哲學的共識。對理、道、心的討論,只是在這一共識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通常所謂的氣論學派,并非不講其他概念,更不是機械之物質對精神實體的反抗或取消。而無論理學還是心學,也都不會在西方二元論的意義上講凌駕于物質世界之上的精神實體,而是在接受氣構成宇宙萬物的前提下,在確立性命主體與認識生生共同體之時,尤其強調理或心等概念。
性命論哲學并不假定能絕對客觀地理解整個世界及其構成。氣,是性命主體反思生命之成立與其生活之世界而形成的哲學概念,而非科學概念。氣的基本特點都是流動不居、生生不已。孟子已經將自己生命中的浩然之氣與塞于天地之氣聯系起來,莊子認為生死是氣之聚散。張載、王船山之氣論,實接續此一傳統而來:以構成我之生命的氣理解天地萬物;復以天地間氤氳之氣理解我之生命。氣聚而為生,并非氣體凝結為固體;氣散而為死,也不可理解為固體升華為氣體。我們必須拋開以哲學附會物理學的思路,才能真正理解性命論傳統中的氣論哲學。
從性命主體的角度觀察世界萬物,理解宇宙萬物與我之生命類似,有其聚散,有其生滅。我與萬物也是生、被生、共生的關系。這一態度并非否定有機物與無機物之間的差別,而是從哲學上,以流動不息、生生無窮的氣之聚散來理解有生有滅的萬物。沒有一種永恒的存在者,亦無絕對的創造者,更沒有完全超越于物質世界之上的精神實體。然而死生相繼,聚散無窮,各種生命體共同構成始終充滿生機、活潑潑的世界。
性命論的理解與現代科學對世界的基本理解可以協調,而不必設定一個永恒的存在者。傳統哲學中的“理”和“心”都不是精神實體。說理在氣中,就如同說心在身中。朱子一直堅持“理是紋理”的定義,將天理解釋為道理、規律和規則,雖然也會強調理相對于氣的優先性,但始終不會將理當做獨立存在的精神實體。正如心是身的主宰,也可以說天地之心或天理是天地萬物的主宰,然而這個主宰既非精神實體或神,亦非形式或樣式,而是內在于天地萬物之中的,生生之仁或是人。
人為天地心
在性命論主體與氣論宇宙觀的哲學圖景下,我們才可以嘗試理解《禮運》“人為天地之心”與張載“為天地立心”之語的宏闊哲學圖景。在這一哲學模式中,天地間的萬物是生生不息、變動不居的,萬物都有其存在之理與生生之道,也在相互影響中各正性命,組成一個永遠變動又維持大致平衡的生生共同體,而并沒有一個超越于萬物之上的絕對至善的精神實體,來制造、設計、安排。
作為有理性、有智慧的性命體,人類不僅像所有其他生命體一樣生生死死,而且可以反思、認識,從而有意識、有目的地改造自己的生命,乃至自己所在的這個生態系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可以參贊化育,也因而才能更自覺地成為《禮運》中所說的“天地之心”。
理性而智慧的人類,以自己的理性認知成果詮釋天地,這便是“為天地立心”。某種超出人類文明之上的超越性力量,都是對人類理性能力的放大,是人類文明的偉大創造。隨著人類文明的積累與發展,人類已經越來越不用借助于宗教性來源,來強化其理論的力量。我們并不否認有人類之上的自然規律和天地生生之德,但這種生生之德不會以人類理性和邏輯的方式表達出來,而只會呈現出一種自然而然、不可言說的整體。人類可以用自己的智慧不斷地去改造自然世界,但始終應該對這種自然而然的整體心存敬畏。這是“參贊化育”的智慧中的應有之義。
性命論的角度,展現出與二元論存在論傳統差別很大的問題域。善惡皆以性命為標準,我們并不把天地總體當做至善或超越性的神,天人關系不會呈現出善惡二元的形態,但仍會蘊含巨大的張力,這在先秦儒、道兩家的爭論中呈現得相當尖銳,也與當代人類面臨的大問題息息相關。
西方主體性哲學一直在真切地面對這一問題,但也在推動著天人張力走向越來越嚴重的境地。由于根深蒂固的二元論傳統,西方思想要么將希望寄托于人類文明之上那只看不見的手來調節和引導本質上自私的人類走向美好的天國,要么以善惡二元的尖銳對立來理解人類歷史的發展,將明明是人義的運動自我神化。
性命論哲學基于“參贊化育”的立場,認為人類仍然必須以文明創造來解決這一問題。這個角度有些類似于海德格爾批判技術化時代的態度:雖然深切意識到現代文明的種種問題,但必須接受這個文明處境,在內部對它做出修正。在這個意義上,性命論哲學雖深具古典思想氣息,卻也有十足的現代精神的歷史擔當。
在二元論架構之下,“不朽”就是精神實體的永遠存在。但性命論不朽觀的三種形態:立德、立功、立言,都不是字面上的永遠存在。性命論的哲學態度相信,身心一體,有生必有死,身體死去則沒有靈魂獨活的道理。不朽,要依靠歷史的忠實記載和永遠延續。中國的史學傳統高度發達,并不是基于一種先天的線性歷史和發展規律,而是人類制禮作樂與參贊化育的傳承不絕。
結論
性命論哲學試圖挖掘中國哲學傳統的基本精神,以面對現代性的種種問題,其要害是自然與文明之間的張力,它可以成為毀滅性力量,但也可能成為文明進步、創造歷史的動力。二元論傳統使這對張力呈現為激烈的心物、圣俗、神人之爭。
從性命論角度統合自然與文明兩個方面,方能更全面看待中國文明的精神。在人的性命中,心雖為身之主宰,但身為性命之全體,所以不能脫離身體,將精神當做性命的實質。將此智慧擴展到天地宇宙之間,是同樣的道理,理雖然是萬物之條理,把握了天理就可以把握物之根本,但物畢竟由氣組成,豈有脫離氣單論理的可能?要在自然與文明之間尋求中道,并不是刻意去放棄什么、勉強什么,而是應該始終著眼于性命本身,這是自然與文明的交匯點。人類文明的各種悲劇常常是,以生命中的一偏妨害生命之全體,以局部的生命妨害總體的生命。要突破這些偏見與狹隘,人類不應放棄文明的創造性活動,因為文明的創造也是內在于人之性命自然的。人類只有不斷擴大自己對天地自然的理解,由偏入全,由局部入全體,才可以在越來越大的整體范圍內,把握自然規律和生命走向,創造出更適宜生命及其延續的秩序。
性命主體應當深入認識自我,把握自己的心性結構與身心平衡,才能做到修身;再以性命主體為中心和出發點,去認識其所在的家庭,在主體和其他主體的辯證關系中思考和安排,使各方面盡可能各得其所,才能做到齊家;再進一步,能夠在國家的范圍內,在性命主體和其他主體之間,參酌遠為復雜的關系,不失自己的主體之位,卻又能懸置主體,盡可能客觀、辯證、平衡地處理各方面的關系,使其中的性命體各安其位,才能做到治國;而若是能更進一步,在各個國家之間的范圍內,乃至在不同文明體系、不同政治訴求的政治群體之間,做到更加多層次、更加多利益的辯證與平衡,使各個國家中的性命體都可以各正性命,才能做到平天下。
以此思路,我們還可以更大范圍、更多層次地推擴,抽象的“天下”概念可以無限推展出去,及于人類之外的各種生命體,乃至地球之外的廣闊宇宙。差序格局,是人類文明不斷認識自己、不斷為自己在世界中定位,同時也不斷承擔起參贊化育之責任的無限過程。文明拓展的范圍越大,對自然的認識就越全面,因而以文明毀壞自然的可能性就越小。在不斷推擴、不斷拓展知識的過程中,人類勇敢地面對和化解天人張力,不斷地實現自己作為天地之心的使命。從這個角度看,“天人合一”不僅僅是一個給定的事實,更是基于天人之間的哲學關系給出的文明理想。人類并不是任憑自然力量的擺布,就可以做到天人合一,反而是要在不斷拓展知識、擴大生活領域的過程中,通過“制天命而用之”,才能盡可能地天人合一。在追求天人合一的過程中,天人之間的張力始終存在,我們正是生活在這對張力當中,靠它的推動去認識世界,認識自然,乃至改造自然,從而創造人類的文明與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