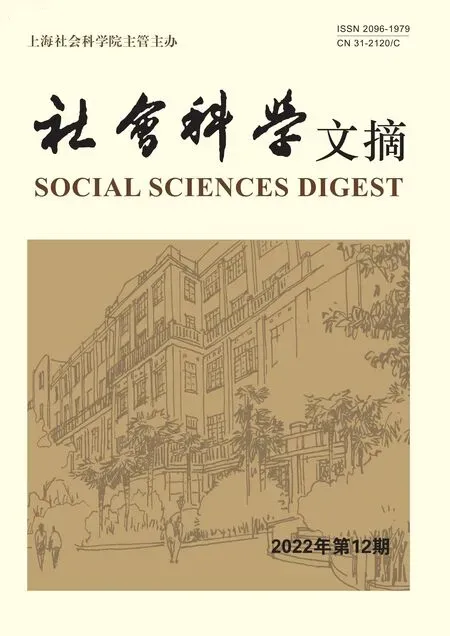西方國家調節財富分配的機制初探
文/周弘
當今世界各國都將財富的創造與分配放在治國理政的至關重要地位。各國也已經形成了許多類似或不同的財富構成,以及影響財富構成的機制。認識財富構成和分配的機制和方式之間的共性和特性,有利于我們尋找實現共同富裕的最佳途徑和最佳方式。
如何認識并衡量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的最初概念來源于社會主義理想。在社會主義者們追求共同富裕的各個歷史階段,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都是決定共同富裕水平的關鍵因素。發達國家的社會總體富裕程度遠遠高于欠發達國家,離開先進的生產力就不可能實現真正的共同富裕,而社會主義的要義也是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進而實現共同富裕。西方發達國家分配財富的機制和方式與社會主義有本質的區別,但是出于保護和發展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目的,這些國家里也出現了調節資本和勞動對立關系的機制,資本增值和利潤最大化受到了社會力量的制約。
為了便于跟蹤并衡量世界各國在財富分配領域里豐富多彩的實踐,很多機構和個人嘗試過多種計量方法,其中最為廣泛使用的是基尼系數和基于五等分的S80/S20指標。將基尼系數作為主要衡量指標,可以看到世界各國的社會均富(或共同富裕)與社會富裕水平(人均GDP)往往重合,但并不總是正相關。人均GDP在3萬美元以上的國家,基尼系數大多低于0.35,而一些欠發達國家的基尼系數高達0.5以上。
如果我們將實現“共同富裕”看作一個歷史進程的話,財富增長和財富分配都是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我們在這里要關注的是影響貧富差距的各種機制,以及它們在人類追求“共同富裕”道路上所起的作用。
市場機制與初次分配
(一)為什么說“市場本身就是社會的”
世界各國的市場規則所依據的社會公平尺度是不同的,而依據不同的社會目標制訂的市場規則會對社會財富的增長和社會收入的分配產生影響。世界上沒有不受社會因素影響的自由市場經濟。德國在二戰結束后重建自由市場經濟時即申明,所謂“自由的”市場經濟并非全然放任的自由,而是具有規范的市場秩序的經濟,德國人又將其稱為“社會市場經濟”。美國人將自由奉為市場經濟的圭臬,但是在美國的市場機制中也嵌入了大量的社會公平要素,例如美國對壟斷行業實施嚴厲打擊。幾乎所有發達的經濟體都采用了法律或行政的手段規范市場。市場經濟是包容在社會之內的。根據社會價值規范市場,防止市場無序競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社會快速滑向兩極化。市場規則保障了市場的平穩運行,而市場經濟的平穩運行是社會收入穩定增長的必要條件。
(二)干預勞動力市場的機制
西方發達國家另一個帶有共性的規范市場的機制是國家對于勞動力市場的干預,雖然干預的方式并不相同。美國的就業政策注重市場,實現了全國性、大面積、無障礙的勞動力自由流動,目的是使勞動力資源可以根據市場需求實現優化配置。歐盟/歐共體為了達到促進經濟增長和福利增加的目標,確定了“資本、商品、服務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簡稱“四大自由”)的原則,并通過各種法律和軟法的機制,為跨國勞動者提供公平的、均等的跨國工作環境和就業待遇。德國在歐債危機期間創造“短時工作制”,維持德國核心勞動力隊伍和勞動者收入的穩定。這種機制在新冠疫情期間得到了廣泛的應用,被歐盟作為“最佳實踐”加以推廣。北歐的勞動力市場規則也十分嚴格,個人所得稅費高達70%左右,用于各種“社會團結”計劃,不僅使社會福利服務能夠做到細致入微,而且大力投資于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幫助國民在競爭日益激烈的時代獲得競爭能力,被稱為“社會投資國家”。
(三)規范引導初次分配
初次分配是決定財富分配的關鍵環節,歐洲大陸國家在引導規范初次分配的領域里創造了一些成熟的機制。國家不僅干預薪資政策的制訂,而且通過特定程序保證勞動者的合理收益,同時確保勞動者依法納稅。這種對勞動力市場的社會性干預使得歐洲大陸國家的國民收入在初次分配后就達到了相對平均的水平。
在初次分配領域里,德國創造了被稱為“社會伙伴關系”的勞資集體談判機制,這種機制使勞動者在初次分配時占有參與決策的地位。“社會伙伴”由雇主、雇員和政府代表三方構成,分行業就工資水平及工作條件進行談判,達成一攬子協議,形成固定的、高度社會自治與社會自我管理的原則。經過集體談判后的雇員薪金和雇主利潤要達到合理均衡的水平。初次分配后,德國就業人員的可支配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從2010年的66.8%上升到2018年的69%。勞動報酬成為德國國民財富構成的主體,這種機制也體現了勞動相對于資本的價值,并保障了有效消費。
日本就業機制的特征是終身雇傭、工齡工資制和企業工會的核心作用,就業高度穩定,經濟危機造成的損失往往由企業主和高管承擔。每年步入職場的畢業生中和企業簽訂終身雇傭合同的比重超過90%。穩定的就業也使企業主更愿意投資員工的培訓和職業發展。結果是,日本在初次分配以后即呈現出收入高度均等化的特征。基尼系數長期穩定在0.35以下。
美國將對于初次分配的政府干預降到最低,薪酬談判多數情況下在個人和雇主之間進行。近年來,由于高端服務業和低端服務業之間鴻溝加大,資本快速擴張,所以美國的就業率雖較高,但是資本、土地和技術相對于勞動在分配中占比過高,初次分配后美國的貧富差距相當明顯,工資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自2000年以來快速下降,從63.3%降至2016年的56.7%,而1947年為65.4%。
社會保障——社會再分配機制
在保證市場運行的基礎上,各個國家根據不同的社會認同和政治制度,通過社會政策和社會立法及社會行政,干預社會分配,一則是防范工業市場經濟給社會帶來的風險,二則是平抑市場經濟體制下社會分配的不公,以彌補“市場缺失”。
社會再分配有很多機制,最為普及且制度化的機制是社會保險,此外還有專門用于扶貧的社會救助,為實現各種社會目標而制定的社會福利津貼等。2018年OECD成員國就業人員的基尼系數平均數是:稅前與轉移支付前為0.41,經過稅收和轉移支付等公共政策干預后,基尼系數降低到0.31。
(一)社會保險(社會保障)
社會保險(在英美等國家被稱為“社會保障”)制度是一種有一百多年歷史的社會再分配機制,起始于19世紀末的德國,普及于20世紀30年代世界性經濟危機之后,成熟于20世紀70年代。在不同的國家里,社會保險的制度設計不盡相同,但是涵蓋的保障內容卻高度一致,這說明了社會保險作為現代社會制度設計的合理性。
社會保險由于供款方式(雇主和雇員按特定比例分別繳費)和給付方式(根據年齡、失業、疾病等必要條件)的不同,在參保人中間(或參保人不同收入階段之間)產生收入轉移的現象和社會再分配的效果,因此也稱為“二次分配”。建立了社會保險制度并經過該制度的收入調劑后,國民的貧富差距一般顯著縮小。
社會保險在各個國家的“慷慨程度”相距甚遠。法國的公共養老金替代率高達60%~70%,與德國體制十分接近。西班牙養老、醫療、工傷、失業保險幾乎覆蓋了全部西班牙人口,對于維持基尼系數在0.35以下發揮了作用。有些歐洲發達國家的社會保險計劃甚至是均等的,例如法國和英國的醫療保障都無需患者額外支付費用。在新冠疫情大爆發時期,歐洲國家的醫療保障制度雖然承受了很大的壓力,但是作為一套社會平衡機制依然穩固。1989年日本政府出臺了一系列社會保險計劃的擴張性改革措施,強化了收入再分配功能,使20世紀90年代中期已經達到0.40的初次收入分配基尼系數回落到了0.30左右。南美有些國家的社會保險制度缺失,公共養老金采用“繳費確定型”(DC)方式,造成覆蓋面不足、社會再分配功能弱、強制性繳款率低和由此導致的老年貧困。此后經過向“待遇確定型”(DB)計劃或混合型計劃的改制,造成了改制代價和財政困難,基尼系數長期高于0.45。
(二)社會福利和社會救助
“社會救助”一般是防止落入絕對貧困的托底政策,在多數國家也是整體社會保障體系的組成部分。因為很多國家需要經過家計調查才予以有針對性的發放,因此其成為社會不平等和社會歧視的又一根源。
“社會福利”有不同的解釋。在一些國家里,“社會福利”泛指不包含在“五大險種”中的社會政策給付,其中包括社會救助等托底項目。但是在有些國家里,“社會福利”則代表高于社會保險的社會政策給付或社會津貼。這些津貼項目的實施不僅可以有針對性地提高需求者的收入水平,而且會兼顧人口政策、性別政策等其他國家政策,同時也可以用于進一步消弭貧富差距。
慈善組織與第三次分配
在經過了初次分配和社會再分配之后,有些國家(如美國)的資本利得仍然過高,貧富懸殊現象嚴重,社會動蕩不安。對于過高的收入,歐洲國家采取的是高額累進所得稅制,同時增加公共社會服務開支。在美國,資本受到了格外的庇護,平抑貧富就被作為一種自愿的行為。各級政府通過遺產稅、地產稅等多個稅種的減免或增加引導富人的取向,同時輔之以極其寬松的慈善法規,推動富人通過自愿的方式將多余的財富轉移他用。與美國相比,歐洲國家國內的貧富比較均等,因此除英國(每年約100億英鎊資金投給慈善事業)以外,投給慈善事業的捐款十分有限,且絕大多數投到國外的人道主義事業。
公共服務設施、區域政策及企業社會責任
在多數西方工業化國家里,社會對于政府介入公共設施建設、提供公共服務抱有期待,而公共設施亦能夠普惠不同人群。歐盟在經濟相對落后的南歐國家投放結構基金,初始目的雖是通過公共設施(如高速公路、地鐵等)的建設在歐盟內的欠發達地區創造就業,但在實現創造就業的社會目標的同時也形成了一種區域間均貧富的公共性投入。歐盟的結構基金和聚合基金就是歐盟內部不同地區之間的財政轉移支付,支持了落后地區中小企業的發展、促進了投資并改善了基礎設施,并為改進農業產業結構和發展非農產業提供資金支持,對平衡成員國之間的發展發揮了作用。
除了政府對公共設施的直接投入以外,很多國家通過減免稅的方式引導、推動、激勵、促進大企業參與社會基礎設施建設,鼓勵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支持公益活動。例如瑞典每年捐款2000克朗或一次性捐款200克朗即可享受25%的捐款免稅,每年最高可免1500克朗。西班牙政府推行地區之間的財政轉移,幫助較落后地區提高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縮小地區收入差距。歐盟利用法律法規、指導文件等軟實力工具倡導企業的社會責任,引導企業參與提供社會、環境等領域的公共產品,同時推動成員國出臺強化企業社會責任的政策、立法和監管措施。
結語
對西方發達國家的上述考察顯示,影響收入分配的政策和機制不僅限于一種或幾種政策,而是一整套社會系統。在這套系統中,市場規則、勞動力市場、初次分配、社會保障(二次分配)、慈善事業(三次分配),乃至特定的收入政策、公共服務設施的投入,以及區域發展政策等等都是重要的環節,在這些環節中,不同的國家選擇了不同的介入方式和政策重點。
幾乎所有國家都干預市場規則,借助市場的社會屬性尋求機會公平帶來的福利。絕大多數國家關注勞動力市場,盡管所使用的方式截然不同,但勞動力市場的合理配置可以帶來更多更好的就業和更多的財富。德國和法國大力干預第一次分配,創造了“社會伙伴關系”機制,在促進了生產力發展的同時促進了消費和公平。日本因終身就業、在職培訓、初次分配均等化等特點,基尼系數長期穩定在0.35以下。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市場規則、勞動力市場介入和初次分配這幾個環節解決不了的問題留給二次分配(社會再分配)。二次分配的目標主要是社會性的。社會保障制度作為成熟的社會再分配機制,有效地防范了社會風險,減少了老年貧困、因病因殘致貧,為更加公平的社會分配提供了機制性保障。
三次分配的社會背景是社會不公。在英國和美國,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力度都比較小,遺留了大量的社會問題,也積累了大量的社會財富。因此這些國家就通過稅收優惠并制訂法律法規,鼓勵慈善事業的發展,推動自愿基礎上的三次分配。西歐和北歐國家經過了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后,社會已經達到了較高的共同富裕程度,因此慈善事業并不發達。
除了三次分配以外,政府的減免稅、累進稅等機制對財富分配也產生一定的影響,有些政府甚至直接投資或由企業和私人投資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務事業,這些設施和服務只要是普惠性的,就會對國民的財富分布產生一定積極的影響。
綜上,現代社會發展出了很多影響財富分配的機制,形成了經濟、政治和社會相互融合滲透又相互制約的局面。當前,有些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狹隘的地方政治權力格局與全球化條件下的市場經濟發展不相匹配的現象,這將會制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必然面臨新的轉型,我們可以從中汲取正面或負面的經驗或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