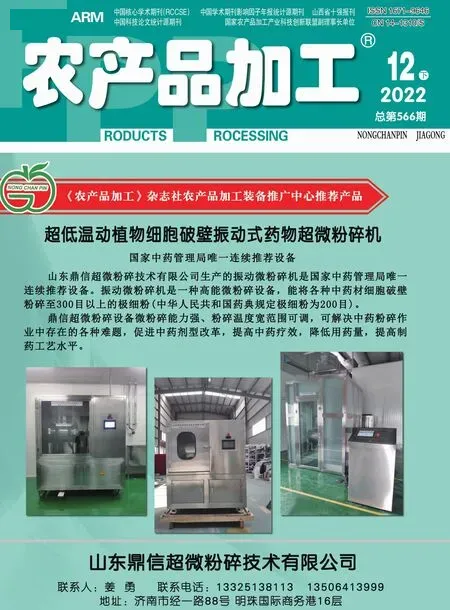芹菜素對機體免疫功能調節作用的研究進展
高國際,龍 玲,張海霞
(1.西北民族大學生物醫學研究中心生物工程與技術國家民委重點實驗室,甘肅 蘭州 730030;2.西北民族大學生命科學與工程學院,甘肅 蘭州 730030)
隨著社會的發展,越來越多疾病的致病病因被發現,醫學水平的巨大進步極大地提高了對疾病的治愈能力。盡管如此,人們仍舊“談癌色變”,這是由于癌癥仍然是致死率最高的疾病之一,目前已知能夠有效治療癌癥的藥物少之又少,且大部分都相當昂貴,所以尋找新的經濟實用的癌癥治療藥物迫在眉睫。
芹菜素(APG,4,5,7-三羥基黃酮)是一種生物活性植物類黃酮,屬于黃酮類化合物[1]。APG的結構于1900年首次被報道,并于1939年人工合成[2]。大約在20世紀60年代,當發現APG可以抑制嗜堿性粒細胞釋放組胺,并在肺部顯示支氣管擴張效應時,APG首次引起了科學家的關注[1]。關于APG抗癌活性的研究早在1980年就有報道[1],此后,許多研究人員較為深入地探究了APG在細胞培養和動物模型中的抗癌作用。
近年來,人們認識到APG具有廣泛的藥理活性,如抗氧化、抗炎、抗抑郁、抗突變、抗癌、抗病毒、抗細菌、抗血栓、心臟保護、保肝、免疫等[3]。大量研究表明,這種黃酮能夠延緩或阻止多種類型的惡性腫瘤細胞增殖,如胰腺、結直腸、肝、血、肺、宮頸、前列腺、乳腺、甲狀腺、皮膚、頭頸部等的腫瘤[4]。據報道,APG可以通過靶向多種途徑發揮抗腫瘤作用。此外,APG衍生物也具有抗癌活性[5]。對APG在預防和治療不同類型癌癥中的潛力進行了綜述,旨在為尋找新的抗癌藥物提供理論依據。
1 APG結構及分布
天然生物活性APG主要以苷元、糖苷和甲基化衍生物的形式存在。APG的基本碳骨架是一個黃烷核,由15個碳原子組成,其排列在2個芳環上(稱為環A和B),并通過3碳橋(雜環C)連接,形成二苯基丙烷結構(C6-C3-C6)[6]。
在植物學上,APG屬于傘形科植物[7]。其來源豐富,在洋甘菊、歐芹、芹菜、金橘等許多水果和蔬菜中均含有,其中歐芹中含量最豐富,高達45 035 μg/g,其次是洋甘菊(干花)為3 000~5 000 μg/g,芹菜籽為786.5 μg/g,蔓萍為622μg/g,芹菜為240.2 μg/g[8]。
2 APG誘導細胞程序性死亡的潛能
眾所周知,黃酮類代謝偶聯物的抗癌活性與母體化合物基本上不同,這些衍生物的結構及用于試驗細胞模型系統起著重要的作用[9]。例如,在HL60人白血病細胞中加入完全甲基化芹菜素后,在50 μmol/L濃度下誘導的細胞死亡率僅為10%,而同一劑量的未甲基化芹菜素誘導的細胞死亡率約為80%;這種差異是由于甲基芹菜素激活Caspase-3和誘導切割PARP(poly ADP-ribose polymerase)的能力有限[9]。然而,4'-甲基芹菜素或刺五加素和親本芹菜素均可抑制RAW264.7巨噬細胞表面TRAIL-R1死亡受體的表達[9]。
細胞凋亡是一種固有的防御癌癥發生的過程[10],而APG可以通過誘導細胞凋亡而發揮抗腫瘤活性[11]。對韓國乳腺癌患者進行的研究中,建議使用APG聯合5-氟尿嘧啶,通過下調ERB2表達和AKT信號通路從而抑制腫瘤生長并誘導細胞凋亡[12]。研究表明,轉錄因子NF-κB和絲氨酸(Ser)/蘇氨酸(Thr)激酶AKT通過增強癌細胞的存活能力和抑制細胞的凋亡過程而在腫瘤增殖中起作用[13]。抗凋亡蛋白(Bcl-2)和促凋亡蛋白(Bax)的比例決定了腫瘤細胞的凋亡過程,以此為依據,潘德特等人[14]對患有前列腺癌患者進行連續8周APG給藥,劑量為20~50 μg/d,結果顯示APG可有效提高Bax/Bcl-2的比例,從而使得前列腺癌細胞凋亡。此外,通過下調NF-κB/p65的組成性表達,誘導人前列腺癌細胞(LNCaP)的凋亡,顯示其具有前列腺癌預防劑的潛力。另有研究表明,APG通過顯著降低細胞活力和誘導凋亡來實現抗前列腺癌(PC-3和DU145細胞)的作用[14]。
在腫瘤細胞中,APG顯著誘導DR5的表達及其與外源性可溶性重組人TRAIL的結合,而在正常人外周血單個核細胞中則無該誘導過程[15]。研究表明,當神經母細胞瘤細胞(SK-N-DZ,SHSY5Y和IMR32細胞)用膳食APG和Bcl-2抑制劑HA14-12.5處理時,可以激活細胞凋亡途徑[16]。APG還可誘導乳腺癌細胞(T47D和MDA-MB-231)的凋亡和自噬水平的增加,自噬可保護癌細胞免受APG誘導的凋亡作用,因此APG和自噬抑制劑(3-MA)聯合治療有助于抑制腫瘤的發生和發展[17]。另有研究表明,用APG處理的HepG2細胞通過H2O2依賴性途徑誘導前列癌細胞(ND)的凋亡,從而降低谷胱甘肽(GSH)的過氧化氫酶活性和細胞內mRNA的表達,這可能與細胞抗氧化酶通過中和ROS而誘導腫瘤細胞活性有關,從而誘導細胞凋亡。因此,抗氧化劑作用的減少可使癌細胞對化療和放療敏感[18]。
此外,在人白血病細胞(U937)和異種移植物模型的研究中發現,APG的凋亡作用可能是通過AKT失活介導的,并伴隨著MCL-1,JNK的激活,以及Bcl-2與CYT下調,線粒體的釋放[19]。研究發現,通過使用小鼠巨噬細胞(ANA-1)的研究,表明不同濃度的APG通過增加細胞內Ros值和抑制Bcl-2表達來調節細胞的凋亡過程[20]。因此,APG可以刺激外源性和內源性相關信號通路的分子,使Survivin分子失活,具有新型抗癌藥物的潛力。
3 APG誘導的細胞周期阻滯
抗腫瘤藥物/分子誘導細胞周期阻滯是抑制癌癥的有效機制。已知APG調節細胞周期過程中的多個靶點,通過調節多個細胞周期組分可以引起細胞周期阻滯[21]。
Zheng P W等人[21]通過上調p53和p21腫瘤抑制蛋白,發現37~74 μmol/L濃度的APG在G1期宮頸癌(HeLa)細胞周期阻滯中發揮促進作用。已知腫瘤抑制因子可以通過阻斷CDK1細胞周期蛋白D/E復合物來控制細胞周期,而癌細胞則破壞這種抑制機制,從而繼續活躍的分裂[22],在針對口腔鱗癌細胞(SCC-25)、人結腸癌細胞系(HT-29和SW620)和人骨肉瘤細胞系(MG-63)的研究中發現,APG可以通過下調細胞周期蛋白,上調p21/WAF1和CDK1的表達,從而將腫瘤細胞周期阻滯在G0/G1和G2/M點[23]。另有研究發現,人前列腺癌細胞(LNCaP)和PC-3細胞的APG處理以劑量和時間依賴方式降低了總Rb蛋白及其磷酸化,增加了ERK1/2和JNK1/2的磷酸化,導致EKK-1磷酸化和c-fos表達降低,從而導致G0/G1期阻滯[24]。
此外,APG還降低了細胞周期蛋白D1表達及p38和PI3K/Akt的磷酸化,從而調節信號轉導過程[24]。在人類前列腺癌(CAHPV-10)細胞中,與正常人角質形成細胞相比,APG處理后呈現劑量依賴性G2/M細胞周期阻滯和細胞存活率降低,從而認為APG具有預防性植物化學物質的作用[25]。另有研究發現,濃度為22.8 μmol/L的APG通過阻滯G2/M細胞周期而抑制雌激素敏感性乳腺癌細胞MDA-MB-231的生長。相類似的情況,APG通過降低G2/M轉移所需的Cdc2和CDC 25的細胞周期蛋白A,B和其磷酸化形式,導致胰腺癌細胞系(ASPC-1,CD18,MIPACA2和S2-013)的G2/M期細胞周期阻滯[26]。利用小鼠大腸癌模型(APCMI+小鼠)進行的體內試驗證實,APG通過調節NAG-1,p53促凋亡蛋白和p21細胞周期抑制因子,從而對細胞周期具有阻滯作用[27]。諸多研究結果表明,APG可以調節致癌和腫瘤的抑制機制,從而用于治療或預防人類癌癥。
4 APG的抗轉移性效應
APG的抗轉移涉及癌細胞從原發部位到鄰近組織的遷移,隨后通過循環系統向遠處部位遷移。轉移是一個重要的腫瘤標志,并與癌癥相關的死亡顯著相關。這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涉及激活多個活性酶和細胞外基質(ECM)重塑所需的其他蛋白質,以促進癌細胞遷移。因此,這些蛋白質分子可能是抗癌的靶點,可用于治療癌癥,增加患者的總體存活率。幾十年來,包括APG在內的各種天然化合物都顯示出較好的抗轉移作用[28]。
Kim B R等人[29]研究發現,波形蛋白與APG誘導的細胞凋亡密切相關,并作為人肝癌細胞(HUH-7)遷移和血管生成的主要調節因子;尿激酶型纖溶酶原激活劑(uPA)等蛋白水解酶在腫瘤微環境中具有ECM重塑活性,在許多惡性腫瘤中被廣泛應用,因此針對uPA/uPAR的各種治療策略被探索用于癌癥預防和治療[30]。另有試驗表明,濃度為22.8 μmol/L的APG對胚胎干細胞(ES)有抑制作用,由于尿激酶(uPA)的部分減少和佛波醇、肉豆蔻酸誘導的MMP-9酶分泌的完全抑制,導致了TRAGN敏感的乳腺癌細胞系(MDA-MB-231)的遷移和侵襲[31]。針對人宮頸癌細胞(CASKI)的研究表明,APG通過抑制p38-MAPK信號通路來抑制MMP-9表達[32],從而抑制癌細胞的侵襲和遷移。
使用小鼠黑色素瘤(B16F10細胞)肺癌轉移小鼠研究中表明,APG不僅對STAT3磷酸化具有明顯的抑制作用,而且抑制其核轉運和轉錄活性[33]。此外,在人黑色素瘤APG治療后,細胞遷移和侵襲相關基因的表達也降低[33]。下調SNAI1和NF-κB(癌轉移生物標志物)可抑制人肝癌細胞中EMT標記,增加細胞黏附,調節肌動蛋白聚合,從而抑制腫瘤侵襲[34]。
現有數據表明,天然存在的APG可以有效針對癌細胞的遷移和侵襲,降低PLC細胞異種移植物的腫瘤生長,提高存活率。因此,APG等黃酮類化合物可作為一種有前途的抗癌化合物。
5 APG對抗癌藥物的增效作用
APG可以通過與各種化療藥物聯合使用,在治療不同類型的腫瘤中對化療藥物起增效作用[35]。事實上,在人胰腺癌細胞系MIPAPAC-2和ASPC-1中,吉西他濱和APG的聯合治療可以下調NF-κB活性,抑制AKT,因此與單一劑量藥物相比有更強的生長抑制反應[36]。此外,相同的組合可以抑制MIPAPAC-2異種移植模型體內的腫瘤生長[36]。
抗代謝藥物5-氟尿嘧啶(5-FU)廣泛用于治療結直腸癌和乳腺癌等多種癌癥,但由于耐藥性的發展,其療效受到限制[37]。在人乳腺癌細胞過度表達的乳腺癌細胞系中,5-FU聯合APG通過抑制ERB2表達和AKT信號串聯(CasACDE),協同誘導腫瘤細胞凋亡,降低腫瘤細胞對5-FU的耐藥性[38]。APG還可以通過增加ROS的產生和線粒體凋亡途徑的激活,增強5-FU對肝癌細胞的殺傷作用,抑制腫瘤異種移植物的生長[12]。同樣,在小鼠實體埃利希癌中,APG和5-FU聯合作用比單獨藥物的使用發揮更大的細胞毒作用[39]。
近年來的臨床研究發現,紫杉醇在某些癌細胞中有耐藥性的發展,從而產生非反應性[40]。在人宮頸癌HeLa細胞中,APG通過抑制SOD活性,從而增強紫杉醇的細胞毒性[41];Chan L P等人[42]研究表明,APG可上調腫瘤壞死因子受體(TNF-R)和腫瘤壞死因子相關凋亡誘導配體受體(TRAIL-R)信號通路,并與5-FU或順鉑顯示協同作用。用這種植物化學劑協同治療不同惡性細胞,通過促進順鉑誘導的細胞凋亡,從而促進順鉑的毒理作用[43]。
此外,聯合應用APG和另一種天然黃酮——白楊素協同抑制了人肝癌細胞和乳腺癌細胞的抗凋亡能力,降低了細胞活力[44]。與APG聯合治療后,姜黃素的抗癌活性也得到了提高[45]。盡管在臨床設置中有許多標準化的細胞毒性或靶向性的機制,但是由于腫瘤細胞對它們的敏感性較低,它們的功效暫時并未被發現。上述試驗數據證明了腫瘤細胞在APG存在下對治療的敏感性增強,顯示出其作為化療增敏劑的潛力。
6 結語
APG具有廣泛的藥理學活性,可用于預防和治療人類癌癥、心血管疾病和神經退行性疾病。通過在細胞、分子和基因水平上的研究表明,這種生物活性黃酮類化合物,可以調節癌細胞中的各種信號通路。然而,需要利用復雜的納米技術和QSAR方法進行進一步的研究來探索APG的多種生物功能,用納米顆粒靶向傳遞APG可能會提高其對癌癥治療的潛力。
隨著代謝組學、蛋白組學和基因組學等現代研究技術的發展,有利于促進APG黃酮類化合物在后期研究中的進一步開展。在我國,中西醫結合治療疑難雜癥是未來的發展方向,全面擴大中醫藥的應用將會為臨床醫療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