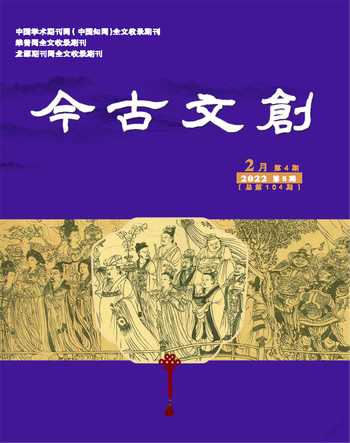清始祖神話所見(jiàn)滿族民族文化研究
【摘要】 清始祖神話中包含著諸多的滿族民族文化,諸如神鳥(niǎo)崇拜、柳崇拜、長(zhǎng)白山崇拜、弓矢文化,以及滿族神話特有的傳承方式。其或是來(lái)自滿族先民最原始的崇拜,抑或是來(lái)自清統(tǒng)治者對(duì)于清始祖神話的文化建構(gòu),但這些最終都成為滿族的民族文化,也成為中華民族的燦爛文化的一部分。
【關(guān)鍵詞】 清始祖神話;三仙女神話;滿族;民族文化
【中圖分類號(hào)】K289? ? ? ? ?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 ? ? ? 【文章編號(hào)】2096-8264(2022)08-0050-03
清始祖神話以三仙女神話傳說(shuō)為主要內(nèi)容,其早期作為族源神話流傳于民間,后被清初統(tǒng)治者重視,編入清史官修文獻(xiàn),將其收錄于《滿族實(shí)錄》開(kāi)篇,1986年中華書(shū)局將《清實(shí)錄》整理出版,《滿洲實(shí)錄》被收錄于《清實(shí)錄》的首卷。[1]以此可見(jiàn),清始祖神話的重要性。同時(shí)它為研究滿族的民族文化與信仰崇拜,提供了較為真實(shí)可靠的一手文本材料,具有較高研究?jī)r(jià)值。
根據(jù)日本學(xué)者松村潤(rùn)的研究,清始祖神話最早的版本出現(xiàn)于天聰九年的《舊滿洲檔》,這則神話實(shí)際上是皇太極征虎爾哈部后,由所降的“muksike”(穆克希克)帶來(lái)的。此后不久,皇太極頒布改定族稱為“滿洲”的諭旨,并在半年后的天聰十年改國(guó)號(hào)大清,年號(hào)為崇德。皇太極對(duì)于族稱和國(guó)號(hào)的改動(dòng)自然需要使用到清始祖神話來(lái)追溯“滿洲”的來(lái)源。所以此后在他的授意下,編纂清太祖努爾哈赤的實(shí)錄便將此神話改寫(xiě)潤(rùn)色后收錄進(jìn)去,代替了此前的金王朝后裔的說(shuō)法。
有學(xué)者指出,清始祖神話并非“古來(lái)傳說(shuō)”,它是清統(tǒng)治者為了統(tǒng)一女真族進(jìn)而實(shí)現(xiàn)帝業(yè),根據(jù)某些史事編造而成的“仿制品”。[2]筆者以為,該學(xué)者觀點(diǎn)可能忽視了這樣一點(diǎn),如果清始祖神話是所謂的“仿制品”,那它為什么會(huì)得到當(dāng)時(shí)新建立、還尚不穩(wěn)定的滿族政權(quán)認(rèn)同?皇太極改“諸申”為“滿洲”,實(shí)則是為了使遼沈地區(qū)所管轄范圍內(nèi)所有子民都融入“滿洲”,以此提高其政權(quán)民族凝聚力,與政治軍事實(shí)力。所以這一時(shí)期皇太極想構(gòu)建的始祖神話,實(shí)則是整個(gè)滿洲共同體的始祖神話。那么為了達(dá)到這種政治目的,它必然需要達(dá)到集體的認(rèn)同,也必然會(huì)對(duì)其無(wú)比認(rèn)真地對(duì)待。所以在對(duì)清始祖神話的創(chuàng)造過(guò)程中,并非只是簡(jiǎn)單地把降將講述的神話直接拿來(lái)用。改族稱為滿洲,改國(guó)號(hào)為清,如果只是貿(mào)然的改動(dòng),必然是會(huì)在其統(tǒng)治群體中產(chǎn)生反對(duì)的聲音。習(xí)慣了前一個(gè)國(guó)號(hào)、族稱的人,對(duì)于新稱號(hào)達(dá)不到認(rèn)同,那自然便不會(huì)支持。如果降將講述的神話只是他們的始祖神話,那對(duì)其進(jìn)行簡(jiǎn)單的改寫(xiě)便說(shuō)這是“滿洲”的始祖神話,這同樣無(wú)法獲得清所統(tǒng)轄下族群的認(rèn)同。所以絕不是這么簡(jiǎn)單的事情,改族稱、國(guó)號(hào)如是,改始祖神話亦如是。所以筆者以為,將清始祖神話看作“仿制品”,想來(lái)是不成立的。
筆者以為,清始祖神話能夠獲得當(dāng)時(shí)滿族人的認(rèn)同可能有以下幾點(diǎn)因素的影響。首先,這個(gè)神話本身出自東北地區(qū)民間的可能是非常之大的,其有著神話認(rèn)同的群眾基礎(chǔ)。其次,清始祖神話的后半部分有可能是來(lái)自于集體記憶的真實(shí)記錄,這是清統(tǒng)治者在原有版本的基礎(chǔ)上對(duì)神話進(jìn)行的政治建構(gòu),以此而形成的滿洲共同體自然會(huì)對(duì)其產(chǎn)生認(rèn)同。最后,清始祖神話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與皇太極改族稱為“滿洲”,改國(guó)號(hào)為“清”的兩項(xiàng)重大舉措同期出現(xiàn)的。
具體而論,清統(tǒng)治集團(tuán)對(duì)清始祖神話的政治建構(gòu)主要還是為了建立起一個(gè)名為“滿洲”的認(rèn)同歸屬感。作為早期的清統(tǒng)治者皇太極之所以建立清政權(quán),改族稱為滿,并創(chuàng)造自己的始祖神話,塑造自己的始祖形象,實(shí)則就是為了培養(yǎng)這種共同的歸屬感。這種歸屬感是凝聚滿洲共同體所有成員的核心要素。這種再生形式的“始祖神話”,在清代的社會(huì)中執(zhí)行了其政治意識(shí)形態(tài)的文化功能。正是在這種神話的影響之下,滿族的民族文化逐步建立。筆者將嘗試對(duì)其進(jìn)行以下的總結(jié)概述。
一、神鳥(niǎo)崇拜
神鳥(niǎo)是神話作品中十分常見(jiàn)的意象,清始祖神話中的“神鵲”便是神鳥(niǎo)意象的一種,而早在《山海經(jīng)》中就已經(jīng)大量的出現(xiàn)各類禽鳥(niǎo)。神鳥(niǎo)意象自“玄鳥(niǎo)生商”伊始,并逐漸開(kāi)始出現(xiàn)在各民族的始祖神話當(dāng)中,尤以東夷族系的始祖神話中的神鳥(niǎo)意象出現(xiàn)頻率較高,其反復(fù)出現(xiàn)在商、夫余、高句麗、鮮卑以及滿等東夷族系的始祖神話之中。除始祖神話外,東夷族系的古史傳說(shuō)和歷史文獻(xiàn)中神鳥(niǎo)意象也曾多次出現(xiàn),諸如以鳥(niǎo)命名的官職,以鳳凰作為其先祖,東夷又稱之為鳥(niǎo)夷等等。
筆者以為,在始祖神話之中,神鳥(niǎo)意象的反復(fù)出現(xiàn),是一種民族“集體記憶”的傳承,反映了該民族崇“鳥(niǎo)”的文化特質(zhì)。神鳥(niǎo)意象在神話中作為原始意象出現(xiàn),可能意味著“鳥(niǎo)”對(duì)于東夷族系而言,是十分古老而又原始的圖騰崇拜。滿族作為發(fā)源于東北地區(qū)的少數(shù)民族,其始祖神話亦同樣受其影響。
佛庫(kù)倫因吞食了神鵲所銜朱果而懷孕的,清始祖神話無(wú)疑是以感生神話作為其神話編撰格式的。而感生神話往往與圖騰崇拜聯(lián)系著,原始的民眾對(duì)人類發(fā)展繁衍的過(guò)程還不甚清楚,即使到了父系社會(huì)時(shí)期,也沒(méi)辦法精準(zhǔn)地確定父親是誰(shuí)。民眾會(huì)自然而然地將自然界中存在的事物——有可能是天體天象或是動(dòng)物植物,視為父親形象的存在,在神話中以此“感孕而生”,他們認(rèn)為感孕而生本族始祖的事物就應(yīng)該是本族的圖騰,進(jìn)而形成圖騰崇拜。并且這種圖騰崇拜并非只存在于神話之中,在清文官官服中的補(bǔ)子上就有繡有九種禽鳥(niǎo)。
關(guān)于補(bǔ)子紋樣的種種詳細(xì)規(guī)定,在《大清會(huì)典》《大清通禮》和《清實(shí)錄》等清代典籍文獻(xiàn)中也可以看到。從清朝對(duì)補(bǔ)子的重視程度,可見(jiàn)鳥(niǎo)圖騰崇拜對(duì)于清統(tǒng)治集團(tuán)都存在一定的影響。不過(guò),對(duì)清始祖神話中神鳥(niǎo)意象的分析也不能只單純觀其“圖騰崇拜”的部分。實(shí)際上,清始祖神話中神鳥(niǎo)意象的特殊之處,除了體現(xiàn)一定程度的鳥(niǎo)圖騰崇拜之外,對(duì)于滿洲先民來(lái)說(shuō),它實(shí)則代表著更多的文化內(nèi)涵,筆者將詳細(xì)對(duì)其進(jìn)行文化解讀。
首先,神鳥(niǎo)意象大量出現(xiàn)于東夷地區(qū)各類神話傳說(shuō),史料文獻(xiàn)與考古出土器物中,應(yīng)是與繁衍于東夷地區(qū)的滿洲先民以漁獵為生的生產(chǎn)生活方式有關(guān)。此前筆者曾分析過(guò)鳥(niǎo)的物候作用,滿族先民以此判斷季節(jié),觀察天象氣候,對(duì)于生產(chǎn)生活十分有幫助。不僅如此,鳥(niǎo)類中的猛禽逐漸被馴化成為漁獵時(shí)的得力助手。
其次,神鳥(niǎo)意象與薩滿文化信仰有著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以萬(wàn)物有靈論作為基礎(chǔ),產(chǎn)生的薩滿文化,對(duì)于動(dòng)物生靈產(chǎn)生崇拜是較為常見(jiàn)的情況。但對(duì)于神鳥(niǎo)的崇拜又是其中較為特殊的一種,鳥(niǎo)翱翔于天的特性,使得其在薩滿文化信仰中被賦予了與天或神相類似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薩滿文化對(duì)于鳥(niǎo)的信仰不止如此,它還代表著女性的生育能力,并經(jīng)常被賦予創(chuàng)世繁衍的寓意。諸如此前提及滿族起源神話中的鷹神,或是由鷹魂化為的女薩滿等等。而清始祖神話中的神鳥(niǎo)意象,也同樣承襲了這一點(diǎn),所以神話中的“神鵲銜朱果”的情節(jié)還有著“賦予生育”之意。
最后,綜上可知,神鳥(niǎo)意象對(duì)于滿洲先民來(lái)說(shuō)有著十分特殊的地位,這就不難想象“神鵲”在清始祖神話中是扮演何等角色的,它不只是作為簡(jiǎn)單的原始意象出現(xiàn)于神話之中,實(shí)則具有多重含義,是多元的信仰文化復(fù)合而成的產(chǎn)物。
二、柳崇拜
滿族人對(duì)于“柳”的崇拜實(shí)則由來(lái)已久。滿族的創(chuàng)世神話中,時(shí)常會(huì)將“柳”視為繁衍生育的意象。諸如,女始祖天神阿布卡赫赫“柳葉生人”的情節(jié),而后在進(jìn)入父系氏族社會(huì)后,出現(xiàn)了以男性始祖神阿布卡恩都里為主人公的創(chuàng)世神話,但神話中天神造人的情節(jié)仍然與柳意象一同出現(xiàn)。
在清統(tǒng)治時(shí)期,對(duì)于“佛多媽媽”的祭祀供奉也來(lái)自對(duì)“柳”的崇拜,滿語(yǔ)的佛多便是柳的意思。《大清會(huì)典》中記載:“若祈福,祈福所祭神,佛立佛多鄂謨錫瑪瑪。”根據(jù)《重訂滿洲祭神祭天典禮》中的解釋可知,“樹(shù)柳枝求福之神,稱為佛立佛多鄂謨錫瑪瑪者,知為保嬰而祀”。[3]所以佛多媽媽是由“崇柳”這一具體事物轉(zhuǎn)變?yōu)閷?duì)神靈的崇拜。其求福保佑?jì)雰旱膬?nèi)涵與創(chuàng)世神話中的柳意象有著類似的寓意。時(shí)至今日,“崇柳”仍是其民族文化之一,滿族人聚居的村落中,幾乎每家每戶都還保留著的“佛多媽媽”口袋。對(duì)她的祭祀,是滿族家祭中的必不可少的部分。
有學(xué)者認(rèn)為,滿族可能屬于圖騰崇拜[4]。與此觀點(diǎn)類似的還有富育光,他認(rèn)為,“崇柳”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氏族圖騰的意味。[5]又有學(xué)者將柳樹(shù)稱之為“氏族樹(shù)”[6]。筆者以為,滿族“崇柳”的民族文化可能來(lái)自歷史早期,人的生育能力較差,而柳樹(shù)幾乎可以適應(yīng)各種不同的生態(tài)環(huán)境,生命力極強(qiáng),同時(shí)柳葉的繁茂又較為容易產(chǎn)生聯(lián)想。滿族民族文化中的“崇柳”觀念,應(yīng)該就是來(lái)自這種繁殖思想的影響。創(chuàng)世神話中的柳意象與薩滿信仰中的“佛多媽媽”顯然是來(lái)源于對(duì)繁衍生育的崇拜。但無(wú)可否認(rèn)的是,清始祖神話中的柳意象則很難看出這一點(diǎn),但若觀之多個(gè)版本的清始祖神話,柳意象又確實(shí)存在每一個(gè)版本中。可見(jiàn)“柳”在這一時(shí)期,或許雖尚未達(dá)到圖騰崇拜的程度,但從某種程度上來(lái)看,也已經(jīng)成為神話中一個(gè)不可或缺的意象了。
三、長(zhǎng)白山崇拜
清統(tǒng)治集團(tuán)創(chuàng)造始祖神話,以此追溯祖先之外,清始祖神話體現(xiàn)出的政治意味是十分明顯的。清始祖神話中出現(xiàn)的長(zhǎng)白山,也逐漸成為滿族的民族文化。在皇太極的授意下,清始祖神話被收入實(shí)錄之中,自那時(shí)起直至現(xiàn)今,滿族以長(zhǎng)白山為始祖發(fā)祥地的意識(shí)一直非常濃烈。
在《滿洲實(shí)錄》中,對(duì)于長(zhǎng)白山的詳細(xì)介紹甚至放在了始祖神話的前面,清統(tǒng)治集團(tuán)對(duì)其的重視程度可見(jiàn)一斑。不僅如此,清統(tǒng)治者還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了許多措施,以保證長(zhǎng)白山始祖發(fā)祥地形成的民族思想文化傳統(tǒng)得以傳承。政治上,神話中出現(xiàn)的始祖誕生之地長(zhǎng)白山從此成了祭祀符號(hào)。望祭長(zhǎng)白山,是清代對(duì)長(zhǎng)白山進(jìn)行山祭的唯一形式。清朝祭祀長(zhǎng)白山,始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此后,每年交由寧古塔官員,在大烏喇地方望祭。康熙時(shí)期,正式將長(zhǎng)白山封為“長(zhǎng)白山之神”,模仿中原地區(qū)祭祀山神的模式,使其擁有如五岳一樣的歲時(shí)祭祀之禮。這一系列的舉措,是清統(tǒng)治者有意在構(gòu)建滿族民眾的清始祖發(fā)祥地意識(shí),也逐漸成為滿族自古以來(lái)對(duì)長(zhǎng)白山親切情感的延續(xù)。
此后的滿族人自然地將長(zhǎng)白山視為發(fā)源之地。康熙時(shí)期正式將長(zhǎng)白山封為“長(zhǎng)白山之神”,享受著五岳一樣的歲時(shí)祭祀之禮。神話確確實(shí)實(shí)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對(duì)于現(xiàn)實(shí)的影響,神話中的人物成了宗廟中的神像。它所呈現(xiàn)的不只是簡(jiǎn)單的一個(gè)故事,其背后暗含的政治意義才是創(chuàng)造始祖神話想要達(dá)到的目的。是為在其統(tǒng)治范圍內(nèi)形成一種政治導(dǎo)向,政權(quán)統(tǒng)治者是該民族始祖的后人,極大地加強(qiáng)了其統(tǒng)治影響力。神話成就了政權(quán),而政權(quán)也同時(shí)成就了神話。神話的發(fā)展脈絡(luò)其實(shí)十分有趣,它脫胎于原始的自然崇拜,來(lái)自民間最樸素原初的東西,在漢代神話被統(tǒng)治階級(jí)利用成為“造神”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雖居廟堂,但卻失去了神話最初的特色,而后統(tǒng)治階級(jí)不再依靠神話去施行其統(tǒng)治之時(shí),神話又回歸于民間,以新的形式植根于民間文學(xué)的沃土中繼續(xù)發(fā)展,從未斷絕。
四、滿族神話與薩滿文化
論及清始祖神話中所包含的民族文化,就不得不提滿族神話的獨(dú)特傳承方式。不論是滿族政權(quán)建立之前,還是之后,滿人都習(xí)慣使用神話來(lái)講述早期的人們對(duì)于自然界各種現(xiàn)象神秘主義的解讀。但這種原生態(tài)的神話在沒(méi)有書(shū)寫(xiě)文字之前,是較難留存下來(lái)的,清始祖神話如此的“出名”,一定程度上還是要仰賴被文字記錄下來(lái)的原因。所以滿族神話的傳承方式十分獨(dú)特,滿族說(shuō)部的口頭傳承文學(xué)就是其很重要的部分,滿族早期并沒(méi)有使用文字記錄事件的習(xí)慣,在滿文尚未形成以及其在并未在社會(huì)大眾之中普及之前,口耳相傳的傳承方式具有重大意義。同時(shí)滿族人也習(xí)慣于以此方式傳承,這種口耳相傳的方式是人與人之間交流思想、傳播信息的必要方法。口頭傳承活動(dòng),交流的雙方可以達(dá)到分享信息的目的。民間文學(xué)得以傳承,正仰賴于此。
滿族起源神話中有鷹神從大火中叼出一個(gè)石卵,生出了氏族女始祖,同時(shí)也是最初的女薩滿。亦有神話說(shuō)天地初開(kāi)之時(shí),大地全是冰雪,天神阿布卡赫命一只鷹從太陽(yáng)那里飛過(guò),把火收進(jìn)羽毛,再飛到天間,融化了冰雪,人和生靈才有吃飯、安歇和生兒育女的時(shí)候。可是母鷹飛得太累,打盹睡了,羽毛里的火掉出來(lái),將森林、石頭燒紅了,徹夜不熄。神鷹忙用巨翅扇滅火焰,用巨爪搬土蓋火,烈火中死于海里,鷹魂化成了女薩滿。在滿族神話史詩(shī)《尼桑薩滿》中,薩滿是由鷹神引路進(jìn)入陰府,靠神鷹將攔路的丈夫拋到酆都城,也同樣是靠神鷹將費(fèi)揚(yáng)古的靈魂救出,帶回人間。對(duì)于女真人來(lái)說(shuō)海東青不僅是作為圖騰,也同時(shí)是他們打獵的助手。遼金時(shí)期,海東青更成為北方地區(qū)兩個(gè)民族戰(zhàn)爭(zhēng)的導(dǎo)火索。
此外,神話的傳承還與原始宗教有密切的關(guān)系。在這種觀念的加持下,“萬(wàn)物有靈”的理論初具規(guī)模。這就是原始宗教——薩滿教產(chǎn)生的時(shí)代背景和理論基礎(chǔ)。薩滿教作為一種原始宗教,對(duì)于尚處于較為原始狀態(tài)的滿族先民影響頗大,薩滿文化自然會(huì)滲透進(jìn)滿族的民間文學(xué)之中,神話與薩滿教的結(jié)合就不難理解了。與此同時(shí),薩滿教還會(huì)一定程度的保存一些神話,實(shí)際上,除了滿族說(shuō)部這種口耳相傳的保存方式,滿族許多神話是由薩滿教以“神諭”的形式保存下來(lái)的。由此可見(jiàn),滿族神話由來(lái)已久,甚至在清始祖神話之前就已經(jīng)逐漸成形,同時(shí),滿族神話的傳承久遠(yuǎn),諸如滿洲說(shuō)部等講述方式已經(jīng)深深地扎根在滿族的歷史土壤之中,它毫無(wú)疑問(wèn)是其民族思想文化的體現(xiàn)。
五、結(jié)語(yǔ)
清始祖神話中包含著諸多的滿族民族文化,諸如柳崇拜、長(zhǎng)白山崇拜、弓矢文化,以及滿族神話等特有的傳承方式。其或是來(lái)自滿族先民最原始的崇拜,抑或是來(lái)自清統(tǒng)治者對(duì)于清始祖神話的文化建構(gòu),但這些最終都成為滿族的民族文化,也成為中華民族的燦爛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清始祖神話本身出自東北地區(qū)民間的可能是非常之大的,其有著神話認(rèn)同的群眾基礎(chǔ)。加之清始祖神話的后半部分有可能是來(lái)自于集體記憶的真實(shí)記錄,這是清統(tǒng)治者在原有版本的基礎(chǔ)上對(duì)神話進(jìn)行的政治建構(gòu)。并且,清始祖神話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與皇太極改族稱為“滿洲”,改國(guó)號(hào)為“清”的兩項(xiàng)重大舉措同期出現(xiàn)的。以此而形成的滿洲共同體自然會(huì)對(duì)其產(chǎn)生認(rèn)同。清統(tǒng)治者對(duì)于清始祖神話的政治建構(gòu),其目的是為了加強(qiáng)滿洲共同體的共同歸屬感與民族意識(shí)。而同時(shí),清統(tǒng)治者對(duì)于神話中發(fā)源之地長(zhǎng)白山的望祭則表明,神話中的長(zhǎng)白山確確實(shí)實(shí)已經(jīng)成為一種信仰符號(hào),并產(chǎn)生了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影響。
參考文獻(xiàn):
[1]清實(shí)錄[M].北京:中華書(shū)局,1986.
[2]程迅.《三仙女》是女真族的古老神話嗎[J].民族文學(xué)研究,1985,(04).
[3]金毓黻主編.遼海叢書(shū)[M].沈陽(yáng):遼海出版社,2009.
[3]尹郁山.吉林滿俗研究[M].長(zhǎng)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4]富育光.薩滿教與神話[M].沈陽(yáng):遼寧大學(xué)出版社,1990.
[5]劉小萌,定宜莊.薩滿教與東北民族[M].長(zhǎng)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
作者簡(jiǎn)介:
王悅,女,遼寧本溪人,渤海大學(xué)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獻(xiàn)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