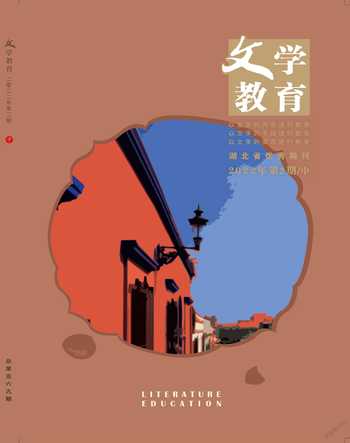魯迅改造國民性思想對蕭紅的影響
劉俊葳

內容摘要:在魯迅對蕭紅的文學影響中,最重要的是改造國民性思想。此影響體現在兩位作家都將人、神、鬼交織的城鎮作為刻畫國民靈魂的舞臺,并由此呈現出小說空間化的特點,讓看客的作用在公共空間得以發揮,產生一批非典型人物。在此基礎上,城鎮的空間化又滲透進人心,升華為喻示國民心理的“鐵屋子”。兩位作家既是“鐵屋子”的制造者,又是敘述者,蕭紅更是在這一過程中實現了不同于魯迅的獨特表達,延續了改造國民性思想。雖然不及魯迅深刻,卻帶有更日常,也更本能的生存意義。
關鍵詞:民俗 空間 國民性思想 文學影響
魯迅曾說做小說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要揭出病態社會中人們的痛苦,引起療救的注意,促使人進一步認識自己,發現與現實世界的聯結,讓人不再耽于歷史的幻想或“溫柔敦厚”藝術面紗下的種種“奇妙的逃路”,不再用“瞞”和“騙”的載道之具來自慰或欺騙世人。蕭紅受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并銜接了這一主題,在大時代的英雄史詩中仍不放棄對人道主義以及啟蒙的追求,認為“作家不是屬于某個階級的,作家是屬于人類的。現在或者過去,作家的寫作的出發點是對著人類的愚昧!”這是兩代作家在文學觀中最重要的聯系,而這一目的的達成是基于對鄉土中國的深刻認識,對世俗的生活畫面、人情關系及生活方式的描繪,魯迅有他的魯鎮,蕭紅有她的呼蘭河,他們在書寫個人情思的同時也在某種意義上建構了一座城的歷史,人的心的歷史。
一.人、神、鬼交織的城
民俗事象凝結著對人行為方式和文化特質的思考,敏感的作家便沿此深入到一種文化的內核之中,發掘其深層的歷史文化內涵,比如沈從文、老舍、廢名等,他們對于湘西或北平的習俗更多的是懷有一種身在其中的眷戀。而蕭紅由于童年經歷的不幸,與家庭決裂的意志,更接近于魯迅的深徹懷疑與批判,同時,他們對美的敏感又使民俗本身具有特別的蠱惑力,由此在審美的同時感受諸種民俗事象文化的悲劇性因素,揭示出鄉土中國的社會文化形態及其國民性特性。
魯迅與蕭紅筆下的民俗事象具備人、神、鬼交織的特點。祝福是為了“致敬盡禮,迎接福神,拜求來年一年中的好運氣”,《社戲》中描繪的目連戲是紹興地區流行的目連僧到地獄救母的故事,反映出儒、釋、道、巫等思想的融合,至于跳大神、放河燈、看野臺子戲、逛娘娘廟等盛舉,也都是為鬼而做的,并非為人而做的。人們創造了鬼神,又反過來心甘情愿地被鬼神吸引,受鬼神的支配,這種精神現象展示了人對鬼神的依附。于是魯鎮中的農民大多生活在人與鬼神的糾葛中,在“《藥》的結尾,善良的母親對兒子的冤魂‘顯靈的期待,于‘死一般的沉靜里透出陣陣陰冷的鬼氣。無知的單四嫂子徒勞地企盼在夢中會她死去了的寶兒,木偶人似的閏土對于神靈的偶像崇拜的麻木,阿Q‘過了二十年又是一個無師自通的‘豪言,以及人群中‘豺狼一般的嗥叫,驚心動魄地宣示著‘鬼神世界對‘人的精神世界的主宰與滲透。”而人被鬼神依附的主要原因在于生活的辛勞麻木和等級森然,更在于儒家倫理、佛教、道教等對人精神的枷鎖,由此形成自私、冷漠、愚昧、卑怯的性格。呼蘭城中的居民同樣受到薩滿、云游真人等的控制,甚至因此葬送了一個健康少女的生命,但他們的生活與魯迅筆下的絕望相比,顯得更加具有日常的麻木與惰性,表現出生存的無謂和貧瘠。
這些相信與崇拜固然會加重精神蒙昧,加重國民性愚惰,阻礙人的覺醒與解放,但,對于這些“辛苦而恣睢”的草民百姓而言,崇拜甚至迷狂未嘗不是他們苦難而沉重的人生的一種暫時解脫,雖然這種解脫是一種麻醉。五四及之后的作家對民風民俗的理解也并不僅止步于迷信,而是多了一點同理心和審美眼光,盡管也不乏強烈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心理。畢竟魯迅曾在《無常》《女吊》中表現出對鬼的癡迷,蕭紅更是在《呼蘭河傳》中對跳大神、放河燈等場景進行了如癡如醉的描寫。可以說,鬼神及其相關的民俗事象早已進入他們的生命,成為作家的一處精神棲息地,也成為其筆下人物的生活方式。所以,魯迅和蕭紅正是在這種又愛又恨的感情中,在鬼神氣息的籠罩中建構出了屬于自己的城,也表達了對改造國民性的理解。
二.國民群像與空間書寫
從改造民族病態的目的出發,魯迅把著眼點放在對人物精神病苦和社會思想狀況的剖析上,用場景或場景的組合突顯社會的某個側面,使小說形成空間化的結構。與蕭紅創作的《民族魂魯迅》第一幕相似,魯迅筆下的人物就像一個個演員,生活在“魯鎮”這一舞臺空間,描繪了單四嫂子、孔乙己、阿Q、祥林嫂等人的不幸與不爭,演繹著一場場生與死的悲劇。這種小說的空間結構形式也影響了蕭紅《呼蘭河傳》的創作,這里的一個個人物,一篇篇故事,就像一片片桔瓣互相緊挨著,具有同等的價值,共同趨向于中間,趨向于白色堅韌的莖。
如果說魯鎮是中國鄉土社會的濃縮與典型,趙府、四叔家、吉光屯等成為符號化的空間,捆綁著宗法制社會下的人,那么呼蘭城則更加具象,通過大量空鏡頭描寫城中的一條條街道,一間間鋪子,通過空間的構筑完成了對呼蘭城居民恒常且落后的生活的審視,表現出文明開化進程中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背離。碾磨坊、豆腐店、機房、染缸房、扎彩鋪等傳統空間指向永恒的勞作和生命的廉價,人們在其中“一天一天的,也就糊里糊涂的過去了,也就隨著春夏秋冬,脫下單衣去,穿起棉衣來的過去了。”這是對單調刻板的安之若素,對生老病死的無知無覺。與之形成對比的是人們對現代空間的強烈排斥:牙醫因掛了巨幅的牙齒招牌,讓人覺得害怕,而生意寥寥,最后做了接生婆;農業學校的校長被居民視為“天地人鬼神不分”,遭到龍王爺的報復;火磨在人們心中成為神圣而不得近身的所在,這種排斥到作品的后半段表現為對小團圓媳婦健康活力的扼殺,對王大姑娘和馮歪嘴子愛情的非議。對傳統空間及生存方式的認同與對現代空間及理念的排斥互為因果,說明人們精神的麻木與固守恒常。與此同時,人們在河沿、我家院子等空間中觀看跳大神、放河燈、野臺子戲等精神盛舉,空間氛圍也都從熱鬧走向凄涼、從繁華走向冷靜。而當人群散去后,敘述者仿佛從中現身,發出“人生為了什么,才有這樣凄涼的夜。”“那河燈,到底是要飄向哪里去呢?”的追問,寂寞的心境、形而上的思索與呼蘭城居民麻木而不自知的形而下的生活方式并存,讓兩種空間的背離擁有更加凄婉,更加深沉的格調,間接說明了改造國民性的艱難和啟蒙的悲哀。
在城鎮中最能夠呈現“國民”群像的地方莫過于公共空間。對魯鎮來說,便是如“民眾俱樂部”般處處可見的酒店茶館。在酒店茶館中喝酒、聊天是人們重要的休閑方式,是熟人社會中溝通人情世故,評論生活瑣事的中心。魯迅充分利用這一地域民俗特點,將筆下人物的活動空間多置于酒店茶館,所以也有人認為:“魯迅寫的‘魯鎮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酒店茶館文化。”周作人在《〈彷徨〉衍義》中講到《長明燈》時說:“《長明燈》也是一篇寫狂人的小說,但是我們的興趣卻是在茶館里和四爺的客房里那一群人身上。”雖然讀者的眼光一般會更為“狂人”式的典型人物吸引,但“狂人”之所以成為“狂人”的原因卻可能潛藏在酒店茶館之中。除了《長明燈》,《藥》《孔乙己》《阿Q正傳》等故事也都發生在公共空間,從人們的談論與笑聲中表現社會等級的威力和人精神的愚昧,比如華老栓經營的茶館成為康大叔、阿義耀武揚威的場所,成為花白胡子、駝背五少爺等鄉民討好上級,議論革命的平臺,而咸亨酒店也成為見證孔乙己一步步走向死亡的匯集點,讓孔乙己與酒客進行互動,形成詮釋國民劣根性的經典場面——看與被看。同樣,《呼蘭河傳》中也有大量看客的描寫,他們活動的公共空間自然也依據地域,從酒店變成院落,即“我家院子”。如果說出入酒店茶館的大多數人是成年男性,并呈現出明顯的等級之分,那么在家院中這一區分會被弱化,表現為家庭地位的不同。祖父、父親和“我”處于主人的地位,有二伯、老廚子等是仆人,馮歪嘴子、老胡家、開粉房的、養豬的等是幫工或者租戶,再加上東北有串門的風俗,注重鄰里關系,產生形形色色的看與被看者,導致所有的故事都和家院有所關聯卻又獨立成文,故而蕭紅筆下的“我家院子”更像是被并置的空間,像是一個濃縮的社會,成為刻畫國民靈魂的舞臺。
看客的作用在推動小團圓媳婦之死的過程中達到了高潮。從一開始百無聊賴的人們“從墻頭跳過來”爭前恐后的看這個初來乍到的外鄉人,之后因其健康活潑與人們對團圓媳婦的認知不同,于是開始飛短流長,“見人一點也不知道羞。”“那才不怕羞呢!頭一天來到婆家,吃飯就吃了三碗。”又在誤以為她被鬼附身之后想出種種“好主意”,吃全毛的雞、吃豬肉和黃連、跳大神、用開水洗澡,呼蘭城的居民對這些療法的效果深信不疑,于是進行一次次實踐,讓小團圓媳婦在一次次離奇而充滿神鬼色彩的折磨中逐漸失去活力,來到生命的終點。當小團圓媳婦去世后,看客們也只是循舊例幫忙安葬,心滿意足的吃了一頓酒席,又傳出故人變成大白兔的流言,但是這只大白兔不再具有童話故事中的美好與天真,而是拉過大耳朵為自己擦去眼淚,在無盡的流浪中發出一聲聲悲鳴。
在這一過程中對看客本身的描寫至多是一個姓名,“周三奶奶”“隔院的楊老太太”“東家的二姨”“西家的三嬸”……他們既是小團圓媳婦生命隕落的推手,也是被鬼神支配的,排斥現代空間及理念的普通人,并沒有太多惡意,只是因長期過著無聊而匱乏的日常生活,而失去了前進的意義。在蕭紅筆下,公共空間中的人,生活是庸常的,個性是麻木的,生活方式是相似的,所以他們之中不會出現“狂人”,有的只是蕓蕓眾生,有著共同的宿命。同樣,魯迅在書寫國民劣根性時,固然塑造了一批典型人物,比如阿Q、孔乙己、祥林嫂等,但同時也有像華老栓、七斤、小D、車夫這樣性格不太鮮明的人物,甚至還有更多類似《示眾》中沒有姓名的速寫人物,而蕭紅顯然繼承的是后者。如果從刻畫國民靈魂的角度看,這種塑造非典型人物的方法更能說明病態的普遍性和現實性,更能寫出最普通的人物,最一般的事件,達到對大多數人生活的真實書寫,揭露病態社會中的不幸。就像阿Q可以是阿貴,也可以是阿桂,給人像是在寫別人,也像是在寫自己之感,從而讓改造國民性的范圍變得更加廣闊,帶給人更多沒有限定性的思考。
三.“鐵屋子”的制造者與敘述者
魯鎮與呼蘭城是反映國民性的公共舞臺,其中的人不僅生活在城鎮中,也生活在心理空間“鐵屋子”中,預示著啟蒙的艱難。所以魯鎮不僅是一座城,也是著名譬喻“鐵屋子”的載體,存在著社會摧殘之下的底層群眾,對應著中國人性中的自大、卑怯、投機、自欺,喻示著心理思維的窒息和壓抑。也許,魯鎮中的人還會因死亡而恐懼,而呼蘭城中的人更像是生活在“鐵屋子”中,成為昏睡的人,“從昏死入死滅,并不感到死的悲哀。”正如《呼蘭河傳》中講的那樣,“生,老,病,死,都沒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長去,長大就長大,長不大就算了。老,老了也沒有什么關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聾了,就不聽;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動了,就癱著。這有什么辦法,誰老誰活該。假若有人問他們,人生是為了什么?他們并不會茫然無所對答的,他們會直截了當的不假思索的說了出來:‘人活著就是為了吃飯穿衣。再問他,人死了呢?他們會說:‘人死了就完了。”如果說魯迅刻畫國民靈魂的核心是書寫魯鎮的社會關系和歷史真相,那么蕭紅則更多是在慨嘆中營造悲涼的空間氛圍,書寫人在周而復始的日常生活中的枯萎,追問“人生是為了什么”,雖然不及魯迅的深刻,卻帶有更普遍,也更本能的生存意義。
“鐵屋子”是一個文學意象,其中作者是制造者,更是成功的敘述者。他們或者旁觀,或者扮演著無力改變他人,也很難說服自己的外鄉人角色,又或者類似隱含作者,發出如“女巫”般悲憤的預言,預言著小城人生的衰亡與毀滅。他們都帶著對人物的真誠,對人性的憂思進行創作,蕭紅曾說:“魯迅的小說的調子是很低沉的。那些人物,多是自在性的,甚至可說是動物性的,沒有人的自覺,他們不自覺的在那里受罪,而魯迅卻自覺地和他們一齊受罪。”她并不認為小說的調子低沉就不好,相反,正是對于人物自在性和動物性的描寫才真正達到了刻畫國民靈魂的效果,改造國民性的目的,其中充滿對生命價值的思考和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熱望,蕭紅也正是這樣創造出了呼蘭城中的人。
從《跋涉》到《生死場》,再到《呼蘭河傳》《馬伯樂》,蕭紅一直在進行國民靈魂的思索,東渡日本的經歷更是讓她對于鄉愁,對于民族的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認識。她在給蕭軍的信中就曾談到對“民族的病態”和“病態的靈魂”文化批判的歷史思考,旅日期間所寫的《家族以外的人》便是《呼蘭河傳》的雛形。在火熱斗爭的時代,蕭紅孤獨地在日本,在香港堅持自我,冷峻地面對一個民族靈魂的偉大孤寂,銜接了新文學以來的人道主題、個性意識,并進行更加現代和深邃的審美拓展。
參考文獻
[1]蕭紅.蕭紅全集[M].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1991.
[2]魯迅.魯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3]秦林芳.魯迅小說傳統與蕭紅的小說創作[J].魯迅研究月刊,2000(01):47-55.
[4]錢理群.心靈的探尋[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
[5]約瑟夫·弗蘭克等,秦林芳譯.現代小說中的空間形式[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
[6]徐曉杰.空間設置:蕭紅對魯迅的繼承與創新——以《阿Q正傳》《呼蘭河傳》為視角[J].北方論叢,2015(04):52-57.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