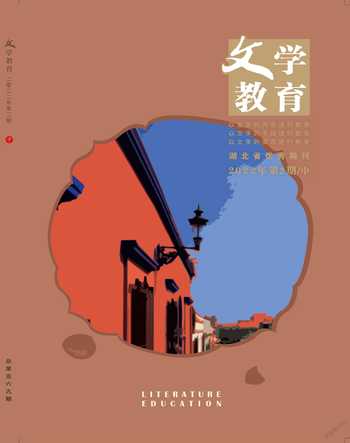試析柏拉圖《會飲篇》中愛與愛神的問題
羅文杰
內容摘要:《會飲篇》作為柏拉圖談論愛與愛神的代表性作品,歷來學者都以此為主要藍本討論柏拉圖的愛欲觀。但無人關注到,在柏拉圖的原文中,闡明了愛的本質,闡明了愛神的本質,卻獨獨沒有明確闡明愛與愛神間的相互關系,或許連柏拉圖本人也忽略了這一點。本文以愛與愛神的關系為切入點,嘗試著從新的角度理解柏拉圖的愛欲與倫理觀。
關鍵詞:《會飲篇》 柏拉圖 愛與愛神 多重關系 靈魂論
如果想要進入西方思想領域,繞不開的一位偉人便是柏拉圖(Plato),從公元前拜占庭亞歷山大圖書館館長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開始,到塞拉緒羅(Thrasyllus),再到古羅馬的第歐根尼·拉爾修(Diogenes Laertius),已經對柏拉圖著作進行了分類和真偽研究,更遑論時至今日,柏拉圖的重要地位只升不降。《會飲篇》(Symposium)確定是柏拉圖的真作,且是能完全體現柏拉圖本人思想,而不是單純轉述蘇格拉底的觀點的中期作品。[1]從文本內容本身出發,塞拉緒羅說它的主題是“論善”,就討論對象而言,通篇的主角實際是“愛”與“愛神”。[2]
一.基于文本的愛與愛神
全篇對話發生在阿伽通(Agathon)家的宴飲會上,共六人輪流對愛與愛神進行贊頌或論述,整個邏輯脈絡是相互連貫、層層深入的。最先發言的是斐德羅(Phaedrus),他開篇即點明愛神的重要地位,又強調愛的原則為惡丑、愛美,愛情的功用是有利于人美好品德的發展,成為保護家國的可貴力量。斐德羅的演講開啟了全篇的序幕,結論是愛神最能導致人類的品德與幸福。緊接著第二位演講人進一步區分愛神,認為共有兩位女愛神,分別屬于天上和凡間,這篇演講注意到了愛的區分和條件性,將愛與愛神都分別劃定為兩個種類,一種是肯定的、好的愛,一種是否定的、惡的愛,只有以增進品德為最終目的的愛情,才是好的愛情。從這個層面上看,愛的終極目標是通向柏拉圖所謂的“善”,塞拉緒羅的說法是很切題的。
第三位發言人是一位醫生,他從自然哲學的角度討論愛與愛神的本質,認為愛的本質就是創造和諧,使一切變得協調。醫生的發言不長,但他不再將愛或者是愛神當作一種純粹的、本身不變的存在物來看待,而是關注到了愛的“能動性”特征。愛與愛神成為了能使相互對立的各種因素,朝著和諧方面轉變的強大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原文說的是愛能“創造和諧”(Create harmony),使事物中原本具有的、但被惡的一面阻礙了的好的一面顯露出來,使之朝著好的方向發展。[3][4]如果說前兩位演講者還是在靜止的意義上對愛及愛神進行初步分析,醫生的措辭則直接把對話拉到動態層面,逐漸觸及到愛與愛神特殊性的根本。
詩人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是第四位對話者,他主要講述了關于原始人類時期愛的起源的故事,把愛看作是人本身追求完善自我的一種本能欲望,出發點和落腳點都在人類本體上。[4]對話進行至此處,柏拉圖借幾位演講人之口,對愛與愛神的歌頌,包括對兩者的功用、分類、淵源及地位等的討論,已完成了第一層闡釋。
有關古希臘神話及神的研究,中西方都有諸多論述,至十九世紀西方現代神話學建立,出現了眾多不同的學派觀點,例如人類學派愛德華·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的“萬物有靈”觀點、心理分析學派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無意識學說等。而古希臘神的最基本特征可概括為“神人同形同性”,一方面神與人外貌相似,另一方面神與人的性格、情感取向相似,甚至可以說“神的社會是人的社會的翻版”。這的確是事實,在早期的希臘神話文本中,如赫西俄德(Hesiod)的《神譜》對諸神的定義就同其特征及職能掛鉤,一方面諸神是該領域等的掌管者,一方面又是該領域或某種能力的神化物、指向物,兩者可以互相指代。[5]這幾乎是所有古希臘人、包括柏拉圖本人默認了的“常識”,例如主司文藝的繆斯(Muse)女神,柏拉圖認為正是繆斯的“恩賜”使詩人創作出偉大的作品,繆斯女神是詩人靈感的來源;有時又直接用繆斯指代這種源自神的靈感降臨狀態。[6]同樣的,這也極可能是后人認為該命題“不證自明”的原因。
從《會飲篇》中蘇格拉底(Socrates)發言之前的內容來看,柏拉圖顯然已經默認了愛與愛神間的關系:愛神是既是愛的掌管者、是源泉,天上與凡間的愛均由她統治和賦予;又可直接象征和代表愛,在不特意強調單論其中一者時,兩者可以相互置換。
但兩者間的關系并非止步于此,緊接著的蘇格拉底的演講帶來了一個大轉折。
二.愛為動詞:狄歐蒂瑪的發言
重頭戲就在蘇格拉底對自己與狄歐蒂瑪(Diotima)對話的轉述上。
蘇格拉底認為愛的是沒有得到的東西,是盼望擁有某物,愛有對象且其對象就是其所欠缺的部分。狄歐蒂瑪則認為蘇說愛神愛美,即美為愛神所欠缺,那么愛神實際缺乏美和好(適用于所有的神),這就違背了所有神都是美的這一認知——如果神即美好,那么愛神便不是神。她提到不美不等于丑,智慧(有正確意見而說出來)與無知間有中間狀態,即正確的意見。愛神介于美丑之間,是處于人神之間的精靈,是人神間的傳達者、連接者,本質是介于智慧者與無知徒之間的“愛智慧者”。女先知最后還討論了追求美(或者說是愛)的過程:從追尋個別的美到統一的美,再到美的知識,最后探求美之理念(Idea),最后一階段也是最有價值的階段。[7]
蘇格拉底看法的片面性不僅體現在被狄歐蒂瑪反駁的地方,還體現在將愛的對象定為“自己所欠缺的東西”上。這不單單指可視、可觸碰到的物質性欲望,更包括無形的、情感與心理狀態上的欲望,與其說愛的是所欠缺的部分,不如說愛的是沒有被滿足的部分,目的是得到欲望暫獲滿足時產生的快感。柏拉圖沒有明確點出愛的不滿足性的特質,但通篇文章,從第一位發言人對愛與愛神地位及功用的探討,到最后蘇格拉底的言論,都是以愛始終在追求某物、以期獲得完滿為核心的。這里就產生了另兩個問題:愛,究竟能不能獲得真正的完滿呢?假設獲得了完滿,愛是否還存在?柏拉圖同樣沒有明確解答,但就其原文分析,基本可確定兩個方向:
第一個是找到理想的、高尚的愛人,兩人始終不變地愛著對方的靈魂,或者兩個有缺陷卻上進的人相愛,最終都獲得“善”的德行與幸福,即獲得完滿。這樣的愛對應“天上的”愛神,既然柏拉圖認為天上的愛神是始終存在的,那么與之對應的完滿的愛也應是永恒存在的。
另一個則是不斷地追求美,從愛形體的、個別的美,到愛行動的、統一的美,最后發現美的理念自身,可看作達到完滿。因美自身是可發現的、永恒如一不變的,理論上完滿的愛也應存在。
問題的關鍵是,有誰真的獲得過完滿的愛?這要求愛者最終擁有最好、最善的品德,或者發現美理念本身,誰曾真正做到過?答案是未知的,甚至連愛神、哲學家、愛智慧者也還處在不斷地追尋完滿的過程中。矛盾就此產生:一方面,在思想上確信完滿的愛存在;另一方面,在現實中,尚無人真正得到過完滿的愛,愛是否有其最完滿的形式,可能將回到唯心主義自身的窠臼中。唯一能確定的是,無論是否有完滿形式,愛本身是不斷朝著完滿的方向前進的。這就導致了隱含的第三個方向:完滿的愛不是終點式的存在,而是一種理想和期待;比起最終目標和結果,更像是精神上的指引。愛或者愛神存在的根本意義是引導人向善,是否能在現世獲得完滿結果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追尋的過程和保持向上的狀態。蘇格拉底的演講正是這一層含義的體現。
實際上全篇的核心就是最后狄歐蒂瑪的論述,這旨在說明愛神或者說是愛,最本質的特征在其能動性,在其“變性”、“連接性”,能使有關物向好的方向演變:它是“動”的,而非靜止不變的。從這個角度延伸,可以說愛不僅能使愛的主體、愛的過程、愛的對象處在變化過程中,亦可以說愛自身是“動”的,永遠處在欲望中、不滿足中,以一種永不“知足”、永遠追尋某物的形式存在,或者本身即代表了永不完滿、但永遠渴求完滿的狀態。因此愛永遠是進行時,而沒有過去或完成時態,愛之一字,實為動詞,而非純粹的名詞或形容詞。
當愛為動詞時,與之對應的愛神概念也發生質的變化:愛神不是“神”,而是人神間的連接者,是不斷追求美好的“愛智慧者”;但如果說愛以不滿足作為其存在方式,推動人向善本身就是善的表現的話,愛神又是神,只是其他諸神所具有的特征大多為完滿的、不變的,而愛神因其代表的愛的特殊性,以不完滿、變動性作為其永恒之美與善的呈現形式。而愛一旦成為動詞,兩者間的關系隨之變動:首先,愛神可以成為愛的主體,也可愛某物,比如蘇格拉底說愛神“愛”美;愛神也可成為愛的對象,成為愛的接受者,如篇章中眾人對愛神的禮贊。或許正是愛的多義性,導致了愛與愛神間關系的多重性,從而使柏拉圖意識到兩者的特殊地位。
三.靈魂與世俗性內涵
有關愛及愛神定義的變化,傳達出一個訊息:“天上”與“凡間”并不是完全分離的兩個世界,而是可以通過連接者、某些介質相通。愛與愛神正是這種介質之一,于是柏拉圖的兩個世界延展開來,構成一個可“流動”的完整版圖,奠定了古希臘以來西方哲學宇宙世界觀的基礎。
愛與愛神的連接性內涵根源于柏拉圖的靈魂論。依據《裴德羅篇》(Phaedrus)中對愛的產生過程的闡述:神與人最初的靈魂都有羽翼,但由于人的理智無法保持激情和欲望的平衡,于是羽翼受損。羽翼的恢復依靠高尚品質的滋養,實現的方式只有兩種,一是實踐哲學,二是哲學地愛男孩。因此愛是根植于靈魂深處的本能,根本目的是為獲得善的品質,以此滋養靈魂的羽翼,即使是羽翼完整的神也需要其滋養。同時愛是一種“滋養”、“消耗”性質的存在,必須源源不斷地有新的供給,必須永不消散,這和前文論證的愛的過程性、始終處于進行時的觀點相通。從靈魂論出發,愛所扮演的角色是靈魂及其羽翼保持活力的源泉之一,于柏拉圖,或者古希臘人來說,“因愛,能生出羽翼”,將是天地間最動聽的情話,也是對天下有情人最美的祝福。[6]
連接性特質折射到世俗社會,亦形成一套與之對應的倫理、政治觀念。愛使有缺陷卻上進的人得以提升,意在強調萬物只要有向上的心或者潛力即可向高等級轉變。這實際是明確肯定了朝著正確的、善的目標前進的行為本身,且做出了向上的行為定會取得向上結果的承諾。與愛肯定人向上努力的行為相應,愛神肯定的是人向上跨越等級和階層的可能性。
柏拉圖構造的世界可劃分為永恒“理念世界”與可變的現實世界,西方學者已對此有諸多討論,其中以諾夫喬伊(Arthur Oncken Lovejoy)的見解較為精辟。他將柏拉圖理論中構建的兩個世界,歸納為希臘哲學中對立統一的兩種世界觀——來世觀與今世觀的碰撞。來世觀強調信仰的重要性,要發現、尋找永恒不變的、終極的善,其在今世不可得;今世觀則強調可變、偶然,要把握當下。但這兩個世界又是相連、共通的,柏拉圖的“理想國”追尋理念中永恒的國度,同時也是現世目的的工具。至中世紀,兩個世界的理論進一步演化為兩個上帝概念間的沖突。第一個上帝,是對一、自足性、不動心的神化,代表的是永恒不變的善的理念;第二個上帝是對多樣性、自我超越、生殖力的神化,代表善的行為。兩者一個在上,是有限靈魂上升到完滿性的目標,一個在下,是下降中的源泉,賦予生命向上的活力,兩者在邏輯上對立,思想上相互容許且必然,筆者更傾向將之稱為一個上帝的兩個方面。兩個上帝間的沖突,實際也是兩個世界的沖突,是靜止世界觀與變化世界觀的沖突。與靜止的世界觀推導出的,安于等級、抑制改革、逆來順受的倫理政治法則相反,變化的世界觀使人們意識到人只有不斷自我更新才能獲得幸福,要敢于否定現狀,勇敢地跨越階級。[8]這恰恰是柏拉圖在對愛與愛神的探討中體現出的傾向。
永遠趨向于完滿的愛與愛神構造的是一個非完滿的世界,兩者既是印證該世界成立的理論、哲學或者說精神性依據,又同時與處于其中的個體(尤指人)混合為一體。人人都能擁有愛,愛神的特性也代表著人性。在這樣一個過程化了的,隨著時間逐漸進化發展的大宇宙觀中,人的地位發生了根本改變:由完全依照設定好了的命運軌跡、只能安于天命的傀儡式存在,變為能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主宰自我命運的自由個體。
而這種主體性,正是處于世俗世界中的人,之所以為人的終極價值所在。
綜上所述,愛與愛神間的關系實質上承載了柏拉圖《會飲篇》最核心的思想,從原文出發,兩者間的關系可簡要概括為:愛神不等同于愛,但兩者在某些時候確實可以相互指代和置換,這主要取決于使用“愛”一詞時的詞性。當“愛”作名詞時,兩者概念可相互代換;為動詞時,愛神成為愛的主體和對象。兩者間的關系可同柏拉圖的靈魂論聯系起來,其根本是構造了一個非靜止僵化的、“可流動”的世界。愛與愛神的連接性、向上性特征,推動與之對應的世俗倫理觀的形成,使人能敢于挑戰現狀,自覺且更加審慎地不斷完善自我。
人能自主地主宰自我的命運,正是人自本的、終極世俗性價值的體現,亦是愛與愛神的定義和相互關系的真正內涵。
參考文獻
[1]范明生.柏拉圖哲學評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2](古希臘)第歐根尼·拉爾修.名哲言行錄(希漢對照本)[M].徐開來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
[3]Plato. 2008. The Symposium[M]. ed.by M. C. Howatson &Frisbee. C. C. Sheffield, translated by M. C. Howats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4]Plato.1961. The Collected Dialogues[M]. ed. byEdith Hamilton & Huntington Cairn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5](古希臘)赫西俄德.神譜[M].王紹輝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6]王曉朝.柏拉圖全集(增訂版)第五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7]Plato.1925. Lysis·Symposium·Gorgias[M]. LCL(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Vol.166.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8]Arthur O. Lovejoy.2001.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P.24-207.
(作者單位: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