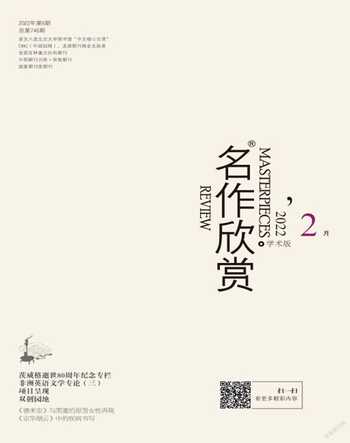彳亍徘徊還是砥礪前行
李天紫 洪春梅
摘 要:托尼·莫里森的《寵兒》史實般地再現了奴隸制下黑奴創傷的群譜圖。創傷具有侵入性、持久性和改變意識等特征。在后現代視域下,重新書寫黑奴創傷史對反思社會公正、爭取話語權和提升民族精神意義重大。非裔美國人當下應釋放創傷、治愈創傷,砥礪前行,勇敢擔當共同體的歷史命運。
關鍵詞:創傷 塞絲 公正
美國非裔女作家托尼·莫里森著名長篇小說《寵兒》(1987)中女奴塞絲的悲劇命運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焦點,奴隸暴政、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等被公認是造成悲劇的主因。莫里森本人則宣稱這是一部探究“自由”的小說,目的是“在高聲說話的鬼魂盤踞的墓地里搭一頂帳篷”,邀請讀者一起走進那段被“排斥的情景”,去體驗那“即將被遺忘、被隱蔽、被故意掩埋的絕地求生的記憶”(見《寵兒》序言)。“絕地”是因為殘暴和虐待挑戰了人類的極限,“求生”則意味著要將所有苦難都轉化為寶貴的財富,砥礪前行,更加樂觀自信地走向公正、文明、和諧的明天。因此,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背景下,非裔美國人,尤其是黑人女性,如何直面創傷,走出歷史,活在當下,爭取自身權利和幸福才是當務之急。當然,要治愈創傷,首先必須走近創傷,本文將分析女奴塞絲的創傷特征,審視后現代語境下黑人創傷書寫的現實意義。
一、創傷的緣由及特征
(一)創傷的緣由
1874年,辛辛那提郊外藍石路124號“充斥著一個嬰兒的怨毒”a,嬰兒的母親塞絲一個月之內接連遭受兩次重大打擊,先是被搶去奶水,打得皮開肉綻,后又親手殺死自己的女兒,從而被迫承擔由此引起的一切恥辱和創傷。塞絲生活在封閉的空間里,斷絕了所有社會交往,整日與鬼魂為伍,日子過得無比孤單寂寞。十八年后,塞絲依然無法忘懷身上的丑陋疤痕和奶水被搶的恥辱:
“他們用皮鞭抽你?”?
“還搶走了我的奶水。”
“你懷著孩子他們還打你?”
“還搶走了我的奶水。”
以上對話直截了當地反映出塞絲遭受的虐待和侮辱,同時指明了創傷的來源。搶走奶水損害和剝奪了塞絲的哺乳權。奶水是母親與孩子最直接的關聯,是母親的權利和責任的象征,搶奪奶水則意味著母權被剝奪,天職被褻瀆。塞絲攜帶著絕望和無助,逃離“甜蜜之家”以期過上幸福安寧的新生活。然而僅僅28天之后,莊園主追蹤而至,情急之下塞絲斷然割斷未滿周歲的女兒的喉嚨,制造了駭人聽聞的殺女慘劇。“為什么要在她的小下巴下面拉動鋸齒,要感覺嬰兒的鮮血在手中如油一般噴涌”呢?小說運用意識流和內心獨白等寫作手法,通過書中男女人物觀照和代際對比的方法,對此進行了不同視角的探討,但最直接的答案還是出自塞絲之口:“就算我沒殺了她她也會死的”,“可我不能容忍那樣的事情在她身上發生”,“沒有人,這個世界上再沒有人,敢在紙上把她的女兒的屬性列在動物一邊了”。為了不再重復做奴隸的悲慘命運,塞絲選擇了以生命的代價維護自己和女兒的神圣人格和尊嚴。塞絲的絕地反擊震懾了追捕者,對造成她命運悲劇的統治者和暴行制度發出了最強烈的抗議,但她并未得到公正和道德的寬恕,而是被關押起來,就連同是命運共同體的黑人鄰居們也孤立她,使她備受煎熬,整日生活在陰影之下。
(二)創傷記憶的表征
從表面上看,塞絲殘忍地殺死了女兒,但從心理學的角度看,殺嬰是搶奶事件應激機制作用的結果。當暴力事件嚴重沖擊受害者的心理和精神時,這種沖擊會潛伏在受害者內心的某個角落伺機歸來,對個體造成難以抹除的消極影響,沖垮其身份認同系統的堤壩,最終導致其精神崩潰。b下面逐一分析塞絲創傷的幾個特征。
1. 往事重現和影像侵入
塞絲長著“鐵的眼睛,鐵的脊梁”,但生活在罪惡的“甜蜜之家”,再堅強的意志品格也無法抵擋殘暴的侵害:“兩個長著青苔般牙齒的家伙,一個吮吸著我的乳房,另一個摁著我,他們那知書達理的老師一邊看著一邊做記錄”;當她試圖找回公道時,“一個家伙劃開了我的背,傷口愈合時就成了一棵樹”。在扭曲的意識形態以及強暴和壓迫體系之下,奴隸女性的身體常常遭到侵犯和褻瀆。莫里森以視覺化的語言創設了關于壓迫和虐待的創傷圖景,清晰而逼真地再現了難以言表的歷史創傷。作為生命力象征的樹的基本意象轉化為虐待圖景,既凸顯了受害者肉體所遭受的創傷,也隱喻著創傷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枝繁葉茂、根深蒂固。
朱迪斯·赫爾曼指出,創傷記憶是一種“抹不去的影像”,這種影像讓創傷經歷更顯清晰具體。如果記憶完全聚焦在這樣的感官片段和無前后因果的影像上,會更加放大創傷記憶的臨場感,變成“終極恐懼”c。“甜蜜之家”不斷跳躍式地閃現,對塞絲的生活構成極大困擾:“盡管那個農莊里沒有一草一木不會令她失聲尖叫,它仍然在她面前展開無恥的美麗。它看上去從來沒有實際上那樣恐怖,這令她懷疑,是否地獄也是個可愛的地方。”記憶不斷侵擾塞絲的生活,使她欲罷不能:“盡量不去記憶,因為只有這樣才是安全的,但她的腦子迂回曲折,難以琢磨”;她不能回想過去,“因為一提起過去就會喚起她的痛苦。過去的一切都是痛苦”;塞絲努力掙扎想讓“她的腦子里沒有任何別的東西”,想讓“那兩個家伙來吃她奶水時的景象已經同她的后背上的神經一樣沒有生命。腦子里也沒有哪怕最微弱的墨水氣味,或者用來造墨水的櫻桃樹膠和橡樹皮的氣味”。但與甜蜜之家有關的一切都歷歷在目:“學校老師把那繩子在我腦袋上纏來纏去,橫過我的鼻子,繞過我的屁股,數我的牙齒”;“學校老師四處夸耀,她做得一手好墨水,熬得一手好湯,按他喜歡的方式熨衣領,而且至少還剩十年能繁殖”;“‘把她的屬性放在左邊,她的動物屬性放在右邊,別忘了把它們排列好’”。用“繁殖”形容她的生育能力,像動物一樣對待她,就連墨水也成為痛苦的物理符號,這些記憶組合在一起構成的創傷圖景最終成為“終極恐懼”:“猛然間,‘甜蜜之家’到了,滾哪滾著展現在她眼前……她因而不能原諒自己的記憶。”
場域的真實性與創傷的永恒性之間的關聯成為標記種族主義話語意象的符號和承載歷史暴力的容器。甜蜜之家的圖景清晰地儲存在塞絲腦海中,“重現的記憶”在十八年后仍不消退。在和丹芙的對話中,塞絲詳細地描繪了時間、地點與創傷記憶的關系:“我在說時間。對于我來說,時間太難以信任了。有些東西去了,一去不回頭。有些東西卻偏偏留下來。我曾經覺得那是我重現的記憶。你聽著。有些東西你會忘記。有些東西你永遠了忘不了。可是不然。地點,地點始終存在。如果一座房子燒毀,它就沒了。但是那個地點——它的模樣——留下來,不僅留在重現的記憶里,而且就存在著,在這個世界上。我的記憶是幅畫,漂浮在我的腦海之外。我的意思是,即使我不去想它,即使我死了,關于我的所做、所知、所見的那幅畫還存在,還在它原來發生的地點。”
地理位置強化了視覺影像和虐待圖景之間的聯系,揭示了暴力與反抗的關聯性。原本賴以生存的場所“甜蜜之家”因此轉化為痛苦的容器,成為創傷的核心場域。這個場域長期占據塞絲的大腦,霸占思考空間,使創傷記憶牢牢控制她的思想意識并不斷強化過去記憶,導致她失了應有的思考能力,無法擺脫過去或設想未來。換句話說,影像創傷對塞絲創傷后恢復正常生活形成巨大障礙。
2. 耳鳴和回避
除視覺外,創傷還與聽覺、觸覺等多種生理感受相關聯。塞絲在面對創傷時,往往出現針刺、蜂蟄或鳥鳴等表征:“頭皮痛得像針扎似的……我的頭皮痛得要命,好像有人把針扎進了我的頭皮”;“有關他們的所有新聞都應該同她頭發里的小鳥一起停住”。當她看到“學校老師”的帽子時,耳畔出現了“小蜂鳥”的嗡鳴聲:
當她看見他們趕來,并且認出了“學校老師”的帽子時,她的耳邊響起了鼓翼聲。小蜂鳥將針啄一下子穿透她的頭巾,扎進頭發,扇動著翅膀。如果說她在想什么,那就是不。不。不不。不不不。很簡單,她就飛了起來。收拾起她創造出的每一個生命,她所寶貴、優秀和美麗的部分,拎著、推著、拽著他們穿過幔帳,出去,走開,到沒人能傷害他們的地方去。到那里去。遠離這個地方,去那個他們能獲得安全的地方。蜂鳥的翅膀扇個不停。
這是塞絲殺女時的生理反應,以上描述形象地再現了身體與事件之間的關聯,創建了創傷的可感知性。感知系統精確再現殺害女兒的可怕圖景,重演創傷個體身體上所遭受的煎熬可以使讀者深切體會奴隸反抗和抵制的誘因,加深人們對創傷的認知和記憶,建立創傷與歷史經驗的關聯。塞絲強烈地感知到自己和孩子都處于危險之中,以至于十八年后在面對保羅·D的詢問時,她還是采取回避策略:“回想起那件事,塞絲笑了。微笑戛然而止,變成猛的一抽氣,可她沒哆嗦也沒閉眼睛。她轉著圈子”;“轉啊,轉啊,現在她又嚼起了別的事情,就是不往點子上說”;“塞絲知道,她在房間、他和話題周圍兜的圈子會延續下去。她永遠不能圍攏來,為了哪個刨根問底的人將它按住。如果他們沒有馬上明白——她也永遠不會解釋”。塞絲對不愿觸及的內心傷痛采取規避行為以期痛苦的記憶隨著循環轉圈向其他方向遷移。“塞絲拾起一張床單,盡她胳膊的長度抻開來。然后對疊,再疊,再對疊。她拿起另一張。都還沒有完全晾干,可是對疊的感覺非常舒服,她不想停下來。她手里必須干點什么,因為她又記起了某些她已經忘記的事情。事關恥辱的隱私,就在臉上挨的耳光和圓圈、十字之后,早已滲入她頭腦的裂縫。”可見,母親身上的奴隸記號以及受辱吊死的畫面也是她精神崩潰的加速器,她不得不依靠重復動作來擺脫記憶的反復侵擾和傷害。
從心理學角度看,轉圈和對疊等行為都是心理創傷者用以緩解潛亢奮狀態的“回避行為”。回避是心理創傷的一種,在此狀態中,受傷者把自己的生活局限在不被激活的狀態中。d身體容納了過多的創傷記憶,亢奮長期受到壓抑無法釋放,從而形成一個持續的循環圈,使之成為創傷記憶的囚徒。回避表明塞絲缺乏把控和療愈傷痛的能力。
3. 麻木封閉與意識改變
心理學研究表明,當一個人意識到自己完全處于無能為力的境地時,就會進入屈服放棄的狀態,此時受害者會采用改變意識的方式逃離此種處境。e改變意識的主要特征有放棄自主行動,停止主動和必要的判斷功能、主觀梳理和平靜增強的知覺能力,感覺功能改變(包括麻木和無痛覺),現實的扭曲(包括人格解體和現實解體)和時間感的改變。f在《寵兒》中,莫里森強調“創傷會使人變盲、變聾、變啞”,塞絲自己也說“棚屋事件之后,我就不再看了”。寵兒的鮮血弱化了她的感知能力,某些感觀功能變得麻木乃至喪失:“故意的,她暗想,肯定是故意的,因為她女兒墓石上的粉紅顆粒是她記得的最后一樣顏色。……從那以后,她就變得像母雞一樣色盲了。……每個黎明她都看到曙光,卻從未辨認或留心過它的色彩。……色彩就到此為止了。”
意識改變反映了情緒上的疏離以及完全處于被動和不再抗拒的狀態,可以解釋為身體試圖化解恥辱和贖罪的企圖。漠視和規避緩解了內心的負疚和痛苦,減緩了潛意識中攜帶的恥辱感,再造了創傷者的情緒能量和價值體系,成為創始者反思創傷事件及其價值、重新構建自我認知和行為的基石。由于粉紅色墓石停留在意識層面,拒絕紅色成為塞絲疏離這個世界的標志。這種感知系統的改變在一定程度上重構了塞絲的價值體系。她主動放棄無為的掙扎,露出冷漠的表情,本能地自尋解脫。在《寵兒》中,發生意識改變的不止塞絲一人。婆婆薩格斯在周圍鄰居的譴責和譏笑之下選擇上床去“琢磨”色彩,她琢磨藍色、黃色,然后是綠色,就是不觸及紅色。對此,老黑奴斯坦普·沛德做出解釋:“藍色。它不傷害任何人,黃色也是。”塞絲也承認:“我知道為什么。因為我和寵兒已經用它做了空前絕后的表演。實際上,那個顏色和她的粉紅色墓石是我能記起的最后的顏色。”塞絲的意識本能地停留在與女兒相關的物體上,女兒的鮮血和粉紅色墓石成為承載痛苦的物理載體。而色彩的匱乏和缺失也凸顯了生命活力的衰竭和喪失,從側面說明了強烈的創傷痛苦錯綜復雜的特性。此外,七歲的丹芙被問到媽媽是否涉嫌謀殺時也關閉了自己的聽覺,“她問媽媽,她還沒聽到回答,耳朵就聾了”。流血事件之后,塞絲一家與外界斷絕聯系,可見放棄交際和話語權利也是創傷的顯著特征。
二、《寵兒》創傷敘事的后現代意義
消弭和療愈創傷是創傷敘事的重要責任,莫里森對此做出了積極的努力,如保羅的愛情、寵兒的回歸、宗教的召喚、鄰居的友情和集體的力量等都為治愈創傷提供了可能性。站在后現代的視角看,拯救塞絲揭示了關于歷史創傷的深刻洞見,創傷的危害持久而長遠,奴隸創傷不應該被遺忘、掩蓋或忽視,正視奴隸創傷的價值和教育意義,砥礪前行才是站在民族自立和文化融合交匯點上的美國非裔們和全人類應該面對的主題。所有創傷記憶碎片所期許的價值體系只有與集體的力量聯系在一起,才能更清晰、更完整地承擔認識自我的責任,因此療愈創傷離不開集體的團結和支持,共同分擔創傷歷史才能割破膿包,擠出膿汁,創造全新的自我。
創傷促使讀者思考生命的價值和意義。黑人的悲慘命運和無奈處境揭露了種族霸權在歷史上犯下的不可饒恕的罪行,彰顯了生命的尊嚴和意義。在《寵兒》中,塞絲的丈夫黑爾目睹妻子受辱失去理智;女兒丹芙失去聽覺;寵兒陰魂不散;婆婆不堪重負一命嗚呼;兩個兒子時時害怕受到媽媽的加害,不敢松開彼此緊拉著的雙手,這些都是無法規避的歷史創傷。塞絲一家的遭遇代表了奴隸制下全體黑人的命運走向。莫里森把故事背景設置在解放黑奴之后,就是要告誡人們,盡管奴隸制早已廢除,憲法也倡導平等自由,但不爭的事實是,現實并不樂觀。迄今為止,種族平等依然停留在意識形態的表面,那些無出訴說、無處安身的冤魂仍然沒有得到安慰和救贖。這些鬼魂高聲索要公道,而當權者卻編造黑人低級的霸權邏輯,使得黑人處境維艱,利益至今無法得到保障。作為少數族裔,每個黑人心里都承載著過去的創傷和痛苦,這些創傷延續至今,早已成為當權者頭上的虱子和黑人心中的刺,稍有不慎,就會引發流血和沖突。因此,托尼·莫里森借用老祖母貝比·薩格斯之口告誡讀者,仁慈不是法令,自由不是表面文章。“平等”不僅是制度問題,更是人心問題:“加納夫婦施行的是一種特殊的奴隸制。對待他們像雇工,聽他們說話,把他們想知道的事情教給他們,而且,他不用他的奴隸男孩子配種,從來不把他們帶進她的小屋,像卡羅萊納那幫人那樣命令他們‘和她躺下’,也不把他們的性出租給別的農莊。”但是“他會給他們挑女人嗎?這些男孩獸性爆發時會發生什么事呢?”虛偽的自由和奴隸制一樣可怕,賦予他們真正的平等自由,尊重人的發展才是種族平等中首要的問題。
親母殺女在任何社會都是會遭到譴責的極端行為,但在暴戾的奴隸制下,卻是母性的勝利。塞絲認為代價是值得的,她的態度是:“我一直都是對的。”所以,她能夠坦然面對和承擔惡行的后果,出賣自己,長期與女兒的鬼魂為伴,縱容寵兒的任性和過度索取,原因就在于,生命需要尊嚴:“我不能讓那一切都回到從前,我也不能讓她或者他們任何一個在‘學校老師’手底下活著,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為了獲取自由,“我把我的寶貝們帶到了安全的地方”。莫里森通過賦予殺嬰行為的合理性,告誡人們,與殘忍的塞絲相比,萬惡的奴隸制度才是元兇。從社會歷史的角度看,苦難記憶會作為民族象征發揮其作用。奴隸制是全體黑人共同的痛苦記憶,構成了全體美國黑人的集體創傷。相對于個體創傷者的自我苛責、自我貶低或自我放逐,集體創傷更具攻擊性,對其他文化也更具排他性和侵略性。這種創傷既是現實層面的,也是心理層面的,它會導致整個民族極度自卑或極度自戀,在這個意義上,《寵兒》的創傷敘事與社會公正和自由密切相關。
在《寵兒》的序言中,托尼·莫里森指出,現在自己感到幸福,享受著從來沒有過的自由,但她知道恐懼的滋味,因此她想去探究“自由”對女人意味著什么(見《寵兒》序言)。站在現代女性的立場,莫里森認為自由首先要保障女性的生育權、哺乳權、見面權等基本權利。可憐的塞絲無法保護自己和孩子,只能用絕地反擊的行為來保全孩子和尊嚴。事實上,在奴隸制度下,做母親、做家長、做夫妻的權利都是奢求,黑人“男男女女都像棋子一樣任人擺布”。《寵兒》中的每一位黑人被剝奪、被奴役、被販賣,都失去了這種“自由”,生存權受到嚴重威脅,話語權的缺失更不用說,因此值得一提的是,莫里森用內心獨白的方式為書中每一位人物賦予了話語權利,由他們多視角、多層次地敘述塞絲殺女的心理和動機,提供了敘事的內視角,由此建立了被隱藏者和沉默者的話語權。這對探究在黑奴制下黑人個人價值觀和心理狀態具有重要作用,其意義在于在重建自我的旅途中。整個黑人民族要清除心理創傷,加強個體之間的聯系和團結,把過去的苦難轉化為積極向上和砥礪前行的動力。
三、結語
莫里森的黑奴創傷敘事具有獨特的后現代魅力,莫里森在引領自己的同胞走出痛苦方面邁出了積極的一步。追憶創傷的價值不止在于再訪創傷,還原歷史,更在于站在歷史和倫理的高度為冤屈者發聲。莫里森以民族成員的身份為非裔美國人代言,控訴和批判蓄奴制度的暴行,發出了“不能回到過去,不能再那樣活著”的呼喊。塞絲的每一段回憶都是對奴隸制的控訴,她用行動編織了有力的語言,和書寫故事的托尼·莫里森一起擔當了黑人民族的代言人。塞絲的意義不僅在于顯示母愛的偉大,更在于呼喚生命的尊嚴。有別于傳統戰爭、暴力事件的受害者,塞絲是莫里森筆下的女英雄。這段黑人女奴創傷史上蕩氣回腸的悲歌,將永遠飄蕩在自詡“自由”的美國上空。
a 〔美〕托尼·莫里森:《寵兒》,潘越、雷格譯,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3頁。(本文有關該書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b 何衛華:《創傷敘事的可能、建構性和功用》,《文藝理論研究》2019年第2期,第172頁,第171頁。
cdf 〔美〕赫爾曼:《創傷與復原》,施宏達、陳文琪譯,機械工業出版社2015年版,第34頁,第38頁,第39頁。
e 〔美〕艾文·彼得、安·費雷德里克:《喚醒老虎:啟動療愈自我本能》,王俊蘭譯,機械工業出版社,2016年版,第128頁。
參考文獻:
[1] 托尼·莫里森.寵兒[M].潘越,雷格譯.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6.
[2] 何衛華. 創傷敘事的可能、建構性和功用[J].文藝理論研究,2019(2).
[3] 赫爾曼·朱迪斯.創傷與復原[M]. 施宏達,陳文琪譯.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5.
[4] 艾文·彼得,安·費雷德里克.喚醒老虎:啟動療愈自我本能[M].王俊蘭譯.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6.
基金項目: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以菲利普·羅斯為個案的后大屠殺時代猶太小說創傷敘事研究(2016年)”(項目編號:16BWWW066 )
作 者: 李天紫,寧夏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學;洪春梅,博士,寧夏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學。
編 輯:趙斌 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