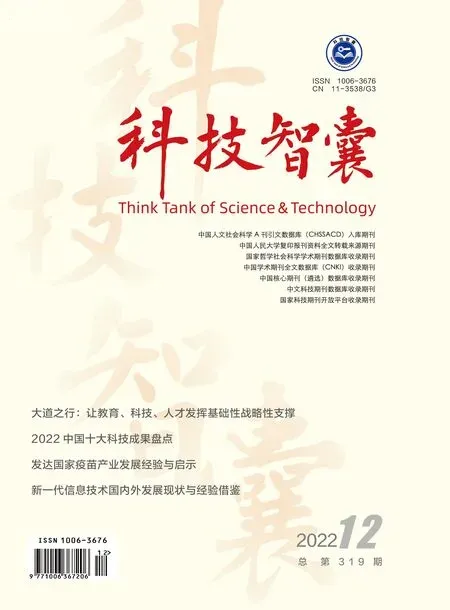近代民族危機背景下現代科學在中國的發展與啟示
焦鄭珊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北京,100190
在人類文明的發展歷程中,科學技術越來越成為現代生產力中最活躍的要素,科技創新決定著文明的發展與進步。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必須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通過梳理科技創新發展的歷史,深入理解實現科技創新的路徑與組織形式,探究影響科技創新的要素,對我國科技創新水平的提升有重要參考意義。
一、科技創新與強國之路緊密相關
現代科學技術自誕生以來就對人類社會和自然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科技是人類現代化的發動機,也是應對經濟危機的根本手段,特別是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國家和國家之間的聯系愈加廣泛而深入,各國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科學技術作為影響綜合國力的決定性因素之一,受到空前的重視,科技創新作為推動科技進步的根本動力,成為決定國家綜合國力、經濟發展趨勢和社會長期可持續發展能力的重中之重。21世紀以來,全球科技創新進入空前密集活躍時期,如何抓住機遇成為全球科技創新熱潮中的主力軍甚至領跑者,也成為我國所必須面對的問題。黨的十八大明確指出:“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必須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科學院視察工作時強調:“科技興則民族興,科技強則國家強,要結合實際堅持運用我國科技事業發展經驗,積極回應經濟社會發展對科技發展提出的新要求,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增強科技創新活力,集中力量推進科技創新,真正把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落到實處。”201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指出:“創新驅動是國家命運所系。國家力量的核心支撐是科技創新能力。”由此可見,科技創新對我國國家發展、人民生活、民族復興都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當今世界,國家間的競爭主要是綜合國力的競爭,其根本在于科技創新能力的競爭。歷史上,科技創新是大國崛起的重要基礎之一,英國、美國、德國、日本等國家都曾經抓住機遇、用符合國情的創新模式搶占科技創新的先機,綜合國力得到極大提升。當前,我國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處于“從創新型國家行列朝著創新型國家前列前進”這一2020—2035年科技強國建設周期的“轉折點”,亟須從多種角度探究科技創新的本質,為我國提升科技創新活力、實現科技自立自強提供支撐。
由此可見,科技創新與強國之路密切相關,提升科技創新水平、激發科技創新活力,是當代國家應對國際競爭、實現國家自立自強的必然選擇。列寧曾指出,科學分析問題最重要的是不忘記基本的歷史聯系,考察每個問題都要看某種現象在歷史上怎樣產生、在發展中經過了哪些主要階段,并根據它的這種發展去考察這一事物目前的發展狀態。圍繞“科技創新”這一主題,除了“科技創新”的內涵及重要價值外,更為重要的是系統分析科技創新的主體、環境和文化因素,剖析影響其發展的主要因素,探索科技創新的驅動力和運行機制,提煉和總結具有普適性的科技強國發展規律,積極尋找我國推進科技創新、實現科技自立自強的途徑。
筆者聚焦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彼時中國對外面臨著他國入侵、國家主權不保的危機,對內則處于政治經濟瀕臨全面崩潰的清王朝統治末期,可謂內憂外患。與此同時,西方的入侵與隨之打開的國際貿易,以及世界科技發展不可逆的潮流,共同推動著現代科技進入中國傳統文化的視野。在劇烈變革的社會背景與時代背景中,探討“科技創新在中國得以實現的路徑”這一具體的、動態的過程,涉及科技創新的主體、社會環境、文化背景、影響機制等問題,具有多重意義。在方法論維度,包括影響科技創新實現和成效的因素、產生影響的方式等;在認識論維度,涉及科技創新主體如何理解科技創新、社會公眾如理理解科技創新及科技創新與社會發展的關系等問題,即關乎時代的、整個社會的科學觀、技術觀、進步觀等諸多理念;在價值論維度,涉及科技創新路徑的選擇、科技創新成果的應用模式與成效、科技創新與科技自立自強的關系等。通過對這一時期科技創新的系統探討,探究影響科技自立自強的關鍵因素,為我國科技事業的發展提供經驗借鑒。
二、民族危機背景下中國的科技創新之路:學習與本土化
第一次工業革命推進了工業化的進程,歐洲首先實現了工業化,而后,工業革命的成果隨著貿易、戰爭等途徑傳播到世界其他地區,推動了這些地區的工業化進程。工業化在世界范圍內是不可逆的歷史潮流,在不同的地區卻以不同的方式開始并最終實現。中國工業化的過程與民族命運、人民抗爭和國家自立自強的努力交織在一起。自1840年英國發動第一次鴉片戰爭、用堅船利炮轟開中國的大門,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家之后,西方列強不僅在軍事上占領中國的土地、掠奪中國的資源,在文化和經濟上也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沖擊,西方科學技術、文化體制不斷涌入并瓦解著中國的傳統觀念和行為模式。在不斷地反抗中,中國被迫開始了解、學習西方科學技術,模仿、探索西方發展路徑,以“學習”為起點開啟了近代工業化進程。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中國被時代裹挾著開啟了學習、追趕、創新的過程,以“科學救國”為目標,以軍事科技為切入點和突破口,進而將學習的目標與工業化拓展至采礦、鋼鐵、交通等領域,以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為主要途徑,并且經歷了吸收與本土化的過程。探索這一時期中國科技創新的途徑及主要特征,對我國探索推動科技創新和實現科技自立自強的有效路徑有很大的啟發作用。
(一)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背景與動因:內憂外患與自強圖存
17世紀中葉,西方主要國家先后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接連不斷的科學革命、技術革命和工業革命的大潮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在西方世界的地位及西方主要國家在世界舞臺的中心地位。英國、法國、美國等國家隨著資本主義思想的傳播和科學技術的進步而不斷繁榮,“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1]。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快速發展的同時,世界的東方在傳統的封建統治下按部就班、緩慢前進,資本主義西方國家無疑開始主導世界的發展方向。一方面是急劇加大的實力差距,一方面是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而日益膨脹的野心和對市場、資源的追求,在這樣的背景下擴張與侵略似乎成為當時最自然不過的事情。
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都處于閉關鎖國的狀態,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不僅阻礙了急于擴張的西方資產階級賺取利潤的腳步,也隔絕了外界的信息與先進科技,讓中國沒有意識到世界環境的劇烈變化和發展的日新月異。英國為經濟利益而傾銷到中國的鴉片造成清政府經濟失衡、財政危機,進而加深了清政府的統治危機,中國正義的禁煙運動引發了第一次鴉片戰爭,而后英、法又在沙俄和美國的支持下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南京條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重創了中國主權與經濟,一批有識之士也逐漸意識到堅船利炮的威力。在外患頻發的同時,中國內憂不斷,大小武裝起義頻發,特別是1851年開始的太平天國運動動搖了清政府封建統治的根基。在這樣的背景下,風雨飄搖的中國迫切需要采取一些行動來緩解危機。外國先進科技的沖擊、中外文化的交流與碰撞、封建統治的日趨瓦解,動搖著中國的傳統觀念和行為模式。傳統的以閉關鎖國和自給自足為主要特征的中國,已難以抵御外來的武力入侵和西方文化的影響,中國必須找到救亡圖存的途徑,當時的一批中國人自然把目光投向了“戰勝”自己的“敵人”身上,力圖“師夷長技”。
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后,一批思想先進的中國人開始把眼光投向西方,把救國圖存和學習西方先進工業聯系起來,將中國的戰敗歸結于軍事技術不如西方,如林則徐首先提出要學習西方軍事技術,“制炮必求極利,造船必求極堅”[2]。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后,國人對西方科學技術的關注更甚、范圍更廣,如馮桂芬提出:“又如農具、織具,百工所需,多用機輪,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資以治生。”[3]同時,隨著國門的打開,西方商品涌入中國市場,對傳統中國工商業造成巨大沖擊。早期維新派看到了西方工商業繁榮所帶來的巨大財富和對社會發展的巨大推動作用,也感受到西方商品傾銷對中國造成的實質性危害,因而一方面主張開展正常的對外貿易,“封關禁海之策,一以絕諸夷之生計,一以杜鴉片之來源,雖若確有把握,然專斷一國貿易,與概斷各國貿易,揆理度勢,迥不相同”[4],另一方面開始重視工商業對國家發展、人民生活的作用。隨著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結束,中國被迫開放了十幾個通商口岸,西方商品對中國市場的沖擊愈發嚴重,中國的貿易逆差所引發的社會問題日益凸顯。根據鄭觀應的記載:“總計彼我出入,合中國之所得,尚未能敵其鴉片、洋布二宗,其他百孔千瘡,數千余萬金之虧耗胥歸無著,何怪乎中國之日憊哉!”[5]
在這樣的背景下,有識之士主張要通過技術進步、行業機械化來抵抗西方的經濟侵略,這為這一時期中國在科學技術領域的學習與創新奠定了社會文化基礎。總體上,“實業救國”可以從兩個維度來理解:其一,通過學習西方先進軍事科技、提升中國軍事實力來抵御外敵入侵;其二,通過學習民用工業技術來提升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以抵御外來經濟的沖擊。從歷史上看,中國“實業救國”的踐行也是自軍事始,逐漸拓展至民用工業、經濟等領域。在“實業救國”的過程中,近代中國的科學技術也經歷了從模仿學習到探索創新的過程。
(二)制器以自強:近代中國軍事科學技術的學習與發展
處于西方列強侵略下的中國,因無法抵御西方先進的堅船利炮的攻擊而任人欺凌,“自強”成為當時最為迫切的需求,從導致危機的直接原因切入解決問題成為很多人面對危機的“第一反應”,因而軍事科學技術成為當時很多中國人眼中科學技術的代表,槍械、火藥、大炮、輪船等領域首先受到關注。
對軍事科學技術的關注與學習始于開明知識分子的個人嘗試。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提出:“夷之長技有三: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龔振麟開創了中國造船技術與西方技術結合的先河,仿制火輪,還發明了鐵模鑄炮新工藝。潘仕成自費聘請美國海軍軍官研制水雷。丁拱辰在觀摩西洋火炮的基礎上寫出了中國第一部火炮制作專著《演炮圖說》,為中國引進西方技術奠定了基礎。然而這種個體的嘗試成效有限,難以產生較大的社會影響。
國家行為的中國近代軍事工業發端于1861年曾國藩創辦的安慶內軍械所,此后清政府陸續創辦了20余個軍工企業,這些軍工企業在近代中國引進、吸收、仿制、突破西方軍事科學技術的進程中發揮了主力作用。安慶內軍械所主要生產火藥、槍炮、蒸汽輪船等軍用設施,意欲擺脫西方的控制,其全部雇傭中國設計師和工匠。徐壽、華蘅芳等人研制成第一臺中國人自己制造的蒸汽機,并基于此于1862年開始試制蒸汽輪船。1866年,“黃鵠號”正式試航,這在某種意義上是中國獨立自主的初步嘗試。1865年,江南制造局成立,其建廠的基礎是收購的虹口美商的旗記鐵廠和容閎收購的樸得南公司(Putnam Machine Company)的機器,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國人對西方軍事科技態度的轉變。安慶內軍械所時期極力擺脫西方的影響謀求“獨立”,到江南制造局則更側重于全方位、高效率地學習西方,因而其中的洋匠、西式機器眾多。1866年創辦的福州船政局則致力于系統學習西方造船技術和管理理念,在學習的基礎上融會貫通、學以致用,以達到治海禍、提升海軍實力的目標。法國工匠德克碑(Neveue Paul Alexandre D’ Aiguebelle)和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guel)總領創辦福州船政局,還聘請大量西方技師在學堂和車間開展涵蓋理論與實踐的全流程教學,并制定了嚴格的考核標準力求培養出能夠獨當一面的海軍人才。盡管造船的關鍵部件如蒸汽機等并非我國原創性發明,但福州船政局的自主造船水平得到了顯著的提升,其自創建后所造的40艘艦船經歷了木船、鐵木合構、鐵船和鋼船3個階段,造船技藝逐漸接近當時世界先進水平。除了上述兵工廠之外,天津機器局、廣州機器局、山東機器局、吉林機器局、漢陽槍炮廠等不同規模的兵工廠相繼成立出現在中國沿海和內陸城市,基本形成近代中國軍工產業的格局。
(三)工業化以獨立:近代中國戰略性工業的學習與發展
在國際形勢壓力下近代中國軍事力量的需求有增無減,在諸多兵工廠投產后,有識之士日益意識到僅僅精準掌握槍炮、機械、輪船等技術是不能滿足軍事需求的,煤炭等燃料、鋼鐵等原料及運輸武器的道路等都是影響中國綜合國力的重要因素,因而在學習“堅船利炮”的同時,煤炭開采、鋼鐵冶煉、鐵路建設等具有戰略意義的工業也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這反映出當時的中國在軍事、工業、經濟等領域全方位擺脫西方侵略的愿景。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等軍工企業已經設有煉鋼廠、鑄鐵廠等相關機構,只是規模相對較小,不足以滿足當時的全部需求。
煤炭是重要的戰略資源。洋務運動后,軍工業的發展導致對煤炭的需求量驟增,當時的中國煤礦大多由私人經營,多采用傳統土法開采淺表層煤炭,遠遠無法滿足實際需求,而洋煤價格高昂。高漲的社會需求和高昂的洋煤價格,推動了中國近代煤礦的創辦,以擺脫外國的影響、實現資源自主。據統計,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洋務派創辦了15個近代煤礦,包括湖北廣濟興國煤礦、安徽池州煤礦、直隸開平煤礦、江西萍鄉煤礦等。相較于傳統煤礦,近代煤礦大多采取西方的勘探、開采技術和管理技術,有效提高了煤礦的開采率和產量。
鋼鐵工業同樣是重要的生產資源。與煤炭類似,洋鐵的傾銷不僅制約著中國軍事工業的自主發展,也對中國經濟產生嚴重沖擊。據統計,1867至1894年間,洋鐵年進口量翻了近10倍,給中國本土冶鐵業造成極大沖擊,“洋鐵、洋針、洋釘入中國,而業冶者多無事投閑”[6]。在這樣的背景下,鋼鐵工業受到當時政府一定程度的支持,貴州青溪鐵廠,湖北鋼藥廠、漢陽鐵廠、大冶鐵礦等鋼鐵廠相繼成立,成為我國鋼鐵工業的基礎。
以鐵路為代表的交通運輸業作為運輸路徑,對煤炭、鋼鐵、武器等物資的運輸至關重要,里程長、成本低、速度快則意味著可以在軍事對抗中快速補充消耗,可以降低成本以在貿易中取得優勢。作為鋼鐵工業的最大市場之一,鐵路建設的發展可以擴大鋼鐵的市場需求,進而推動鋼鐵工業的發展。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先后修筑了唐胥鐵路、津沽鐵路、關東鐵路、臺灣鐵路、淞滬鐵路等2000余公里的自辦鐵路,甲午中日戰爭后更是借外債以中外合辦的形式修筑了京奉鐵路、滬寧鐵路等3000余公里鐵路,這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交通運輸能力、擴大了鋼鐵需求市場,對我國整體實力的提升起到了推動作用。
(四)民族危機背景下中國科技創新之路的特征
回顧歷史發現,近代民族危機時期中國科學技術的萌芽與發展是在外在因素的推動下以被動學習為起點,進而催生主動創新的過程,是中國傳統的文化與社會制度不斷吸收現代科學文化并與之相互適應的過程。民族危機背景下的中國科技創新之路,最為主要的特征之一是“自我超越”,即從歷史發展的宏觀脈絡上看,中國一系列現代化實踐活動盡管推動了現代科學技術在中國的萌芽與傳播,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但在世界競爭中仍然不占優勢。
從科學技術自身發展的角度,中國在軍工、輪船、鋼鐵、礦業、鐵路、電信等領域開始了初步的工業化進程,這些產業或從無到有,或由現代工廠取代傳統手工作坊。同時,其采用的技術和裝備多來源于西方,西方的機器、西方的技師、西方的零部件在中國本土發揮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像是西方工廠的“翻版”。在模仿、學習的過程中,中國具有了一定的獨立技術能力,在某些領域有了一定的突破,如福州船政局能夠建造當時世界主流形式的戰艦,天津機器局生產的栗色火藥一度名聲響亮等。但依舊存在諸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一部中國近代史就足以說明這一系列的措施并沒有改變當時中國內憂外患的局面。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中國的工業化措施有很多是和本國社會需求和發展脫節的,科學技術的進步并不能直接應用于社會需求,從目的論的角度來講這些措施是不夠成功的。探究這一嘗試不夠徹底的原因,總結經驗教訓,對推動我國科技創新有重要啟示意義。
三、民族危機背景下中國科技創新嘗試的啟示
近代民族危機背景下,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歷程,是在外在因素的推動下,以吸收國外科學技術為起點,進而不斷開啟內部革新、追求科技創新、力圖實現科技自立自強,從而推動國家實現自主,筆者將之概括為“外生應激學習型創新模式”。從動因上來看,當時的中國并非主動發現世界的變化、并非主動探索學習,而是在外界壓力和世界歷史進程的裹挾下不得不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從方法上來看,當時中國的“外生應激學習型”科技創新聚焦在對西方先進技術的引進、學習與利用,通過購置機械設備、人才引進與人才培養、進口關鍵零部件、整體仿制等方式,實現西方工業化科技產品的制造本土化,同時嘗試將生產成果廣泛應用于軍事、工業生產和社會生活等領域。但由于技術引進與當時中國社會現實的“適配度”問題,以及純粹學習型的技術引進相對于技術前沿的滯后性,當時中國的“外生學習型”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僅實現了現代科學技術在中國的萌芽和傳播,縮小了傳統中國與西方強國的差距,培養了我國第一批具備科學思想的人才,但距自主科技創新尚存在較大的距離。
探究這一時期中國通過引進西方科學技術而開啟工業化之路的進程及成效,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科技創新。
第一,成功的學習與真正意義上科技創新的實現,需要對科學與技術的本質內涵有全面而深入的理解。近代中國對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的認識始于“師夷長技以制夷”,聚焦于“技”,引進的科學技術集中于先進機械等技術領域的成果,鮮有對其內在機理的探索,大多人對科學的理解也僅停留在經驗技術層面,是樸素而感性的、始于實踐并終于實踐的行為,缺乏理論升華,“科學”約等于“技術”,對支撐技術創新的理論突破、支持技術研發的政治經濟條件及技術創新的應用與產業化等問題鮮有了解。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社會對科學技術的理解深度和吸收、運用能力。只有同時探索科學理論、追求技術創新,才有可能推動真正意義上的科技創新。
第二,成功的學習與真正意義上科技創新的實現,需要全面而徹底的“科學化”的社會體系作為支撐。從目標上來看,引進科學技術是為了維護搖搖欲墜的清政府統治,當發現效果不甚顯著、不能從根本改變中國當時的困境時,中國的做法是轉而投向經濟領域的技術引進,是改變維護的“工具”而沒有思考自己維護的對象是否在“本質上”是不合理的,這是對科學技術與社會關系理解的錯位。同時,中國悠久而輝煌的古代文明自成體系,影響力大,這也對中國接受外國文化造成了一定的障礙。從實現路徑上來看,影響國家發展的科學技術創新勢必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統籌規劃才能夠達到各個環節、各個領域相互適配、協調發展。中國自洋務運動興起的改革活動往往缺乏強力有的領導,大多由疆臣自辦,這樣一方面各方觀點不一致,難以形成合力;另一方面,諸多決策多仰仗一人之力,難以周全、理性,弊端明顯。例如,張之洞的一系列做法,就受到了鐘天緯的質疑:“尚比之裁衣,先雇縫工滿堂,而布帛猶未具,先急于辦刀剪、針線之類”“一切用料、用人,皆未計及也”。[7]概而述之,缺乏系統社會機制體制和思想文化的支撐,科技創新難以有序發展并獲得良好成效。
第三,成功的學習與真正意義上科技創新的實現,需要強大的科學技術本土化能力作為支撐。科學技術本土化的過程,需要學習能力、持續的經濟投資、產業化運用等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才能真正實現。在通過購買機械、雇傭洋匠、自主培養人才等手段初步掌握技術后,當時的中國對西方的依賴程度依舊較高,這也付出了較大的代價,如蘇州炮局不僅購買的“西人汽爐”等機器每套就數萬金,雇傭的洋匠每月工資也在100~300元,而當時中國工匠每月的工資僅僅在7~30元。在付出如此高昂代價的情況下,由于機器不齊全,蘇州炮局也僅能鑄造炮彈,不能制造輪船長炸炮。不能自主掌握科學理論與技術關鍵,不能自主培養高水平人才,難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科技創新。
總之,成功的學習與真正意義上科技創新的實現,需要的是對科學技術全面而系統的理解,其中既包括對科學和技術本質內涵的理解,也包括對科學技術與社會文化、社會環境的關系,創新主體的類型及不同影響,影響科技創新的客觀條件等相關問題的理解,亦即將科學視作一個系統工程,建構合理的科學觀,才有可能實現科技創新與國家自立自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