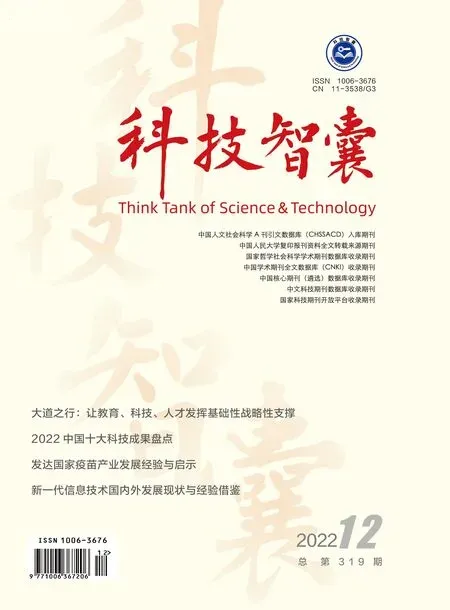智媒時代突發氣象災害的應急傳播機制研究
唐冰寒 劉 玥
成都理工大學傳播科學與藝術學院,四川,成都,610059
突發氣象災害的應急傳播是抗災救災工作的重要一環,是推動氣象科普活動進程的重要手段,也是新的歷史時期實現我國應急管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方式。互聯網的發展尤其是社交媒體時代的到來,加速了災害應急傳播機制的革新,使其內容體系逐步趨于完善、傳播渠道日漸暢通,對特殊時期的應急信息傳播和輿論引導工作具有重要意義。然而,在社交媒體時代,信息的碎片化和冗余使真正有效的信息愈發匱乏,受眾對有效信息需求的增加和信息獲取的不對稱性使新時期突發氣象災害的應急傳播難度進一步加大。
一、突發氣象災害應急傳播機制的現實圖景
我國氣象災害應急傳播機制的數字化建設雖然起步較晚,但是在互聯網、多媒體等技術的助推之下也取得了階段性的進展,形成了傳者、內容和渠道之間的良性互動。
(一)應急工作步入正軌:各組織聯動的災害信息傳播
新時期互聯網的高速發展對我國進一步提高信息傳播速率和災害防治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2015年,由中國氣象局承辦開發的國家突發事件預警信息發布系統正式啟動業務運行。[1]此后,該系統匯集了氣象、國土、水利等20個部門和組織的資源,并與預警信息發布系統進行對接,通過網站、社交媒體等信息發布平臺實現了國家、省、市、縣的四級信息傳輸,打通了氣象災害應急信息傳播的“最后一公里”。區別于傳統媒體時代的應急信息發布,新時期各組織聯動的災害信息傳播形成了全方位、高速率、精準化的傳播鏈條,為防災減災救災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
(二)內容體系趨于完善:用戶賦權的多元信息生產
互聯網的發展讓受眾有了更多選擇權,不同于傳統媒體時代單向接受信息,社交媒體時代的受眾可以與傳播主體進行雙向溝通,這種傳播—反饋的閉環完善了突發氣象災害的應急內容生產。此外,受眾可以通過社交媒體平臺進行相關應急信息的生產和發布,成為氣象災害信息的生產主體之一。例如,在2022年夏季重慶山火期間,當地居民利用手機等設備拍攝現場的山火視頻,通過微博、微信等社交平臺進行災區第一手信息的傳播;“@中國氣象愛好者”等氣象類自媒體依靠自身知識制作并發布相關氣象科普視頻、圖片和文章等,極大豐富了氣象災害應急傳播的內容體系。一方面,用戶生產的內容更貼合公眾接受習慣,通過社交平臺裂變式的傳播使氣象應急信息得到更大范圍的關注;另一方面,新媒體的包容性和短視頻的崛起使用戶徹底擺脫了文字媒介的束縛[2],降低了公眾進入信息傳播的門檻,人人都可以分享關于氣象災害的信息,使災區的受災情況得以及時傳播,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救災的進程。
(三)傳播渠道不斷暢通:新興媒體助力的傳播矩陣建設
依托互聯網技術,突發氣象災害的應急傳播呈現出多媒體的融合。區別于傳統媒體時代單一文本式的新聞報道模式,依靠社交媒體災害應急傳播形成了集文字、動畫和視頻等文本為一體的多元表現形式,并通過微博、微信、短視頻平臺和客戶端等新媒體渠道發布新聞內容,使應急信息以更加快速、高效的方式呈現,實現了突發氣象災害信息的快速有效傳播。例如,《人民日報》在關于2022年夏季重慶山火的相關報道中,首先通過現場拍攝的突發山火視頻在微博、微信公眾號和抖音等社交媒體平臺進行了災情報道[3],而后以圖文的形式對救災過程及結果進行及時跟蹤[4],并制作了溫情的救援視頻向公眾傳遞積極的價值觀念。
二、智媒時代突發氣象災害的應急傳播困境審視
隨著移動互聯網、數字化、云計算以及物聯網等新技術的快速更迭,數據以極快的速度和極大的規模充斥著我們所在的世界,人類社會已悄然邁進了智媒時代。在新興智能技術的加持下,信息傳播速率呈指數級增長,給突發氣象災害的應急傳播提出了新的挑戰。
(一)優質應急信息稀缺
突發性事件的發生總會產生信息差,尤其是在氣象災害這個與人民生命健康息息相關的公共衛生事件中,普通公眾所了解和掌握的有關災害的信息很少,而媒體作為社會公共資源的擁有者掌握著大量信息,尤其氣象災害所在地的媒體和相關部門是災害發生時公眾最主要、最直接的信息接收來源和渠道。然而,在突發事件中與公眾迫切的知情欲望不對稱是,在碎片化的社交媒體時代,實時的傳播速度和信息獲取訴求要求媒體要具備更快的事實核查速度,但是,這種短時間內產出的動態新聞很有可能是失實、不全面的[5]。這種失實、片面的信息極易導致媒體公信力下降。此外,各種假借災害謀取利益的假新聞和無效求救信息在社交媒體中形成了“病毒式”傳播,氣象災害預警和科普等應急信息卻極度同質化,具有針對性的優質內容生產不足。冗余的信息和優質資源的匱乏導致各種不確定性劇增,加劇了災害期間公眾的恐慌,繼而引發一系列輿情危機。
(二)謠言滋生,媒體應對滯后
“真相還在穿鞋,謠言已跑遍半個世界”,馬克·吐溫所言將社交媒體時代的謠言傳播體現得淋漓盡致。受“注意力經濟”驅使,部分媒體為第一時間搶占新聞,將時效性視作第一要素,在事實尚未核查清楚前便大肆報道,甚至將自己的主觀臆斷加入其中,致使謠言不斷滋生。尤其在突發性氣象災害期間,人人都可以是自媒體的社會環境給予了謠言更為廣闊的生存空間,部分別有用心的人士利用網民特殊的情緒不斷進行煽情,散布不實消息,缺乏網絡基本素養的網民在匿名的網絡空間中有可能失去自我社會責任意識,肆意宣泄自己的情緒,導致謠言進一步擴散。例如,在2022年夏季重慶突發山火期間,部分自媒體就山火的起因等散布無端謠言,甚至對山火的救援進行詆毀和抹黑。真相的傳播速度遠不及謠言,媒體的辟謠工作一直存在滯后性。在突發公共災害發生之際,大量不實言論的暴發使媒體對事實的核查和辟謠的速度無法滿足用戶對真相的迫切需求。尤其是突發氣象災害的發生伴隨著眾多不確定性因素,受極端惡劣天氣等的影響,新聞工作者長時間、不間斷地在現場進行信息的搜尋和報道,身體和心理上受到各種折磨。此外,在處理氣象類專業的消息時,由于知識障礙的存在,新聞工作者需要去咨詢專家核查確切的事實。因此,面對鋪天蓋地的謠言,他們經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在對突發信息進行把關和審核時存在一定的滯后性,而權威辟謠信息的缺失和滯后會導致公眾恐慌,致使謠言進一步滋生,形成惡性循環。
三、智能傳播:突發氣象災害應急傳播機制的破局之路
在智媒時代背景下,信息冗余和優質內容匱乏之間的固有矛盾突出,這阻礙了突發氣象災害期間應急信息的傳播,但智能算法等新技術在應急信息數據庫構建和傳播平臺化建設等方面的優勢漸趨突出。因此,政府部門、主流媒體等應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等現代技術,抓住機遇,積極進行突發氣象災害應急傳播機制的智能化轉型升級。
(一)建設智能應急隊伍:政府主導、部門聯動、公眾參與
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在各個領域的應用和不斷深入,給突發氣象災害的應急傳播隊伍建設提供了智能化融合協調的可能,對加快災害信息傳播和防災減災進程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應完善政府部門主導格局。就突發氣象災害事件的特殊性、急迫性和公共性而言,各級政府的組織協調至關重要,尤其對基層政府來說,應在完善防災基礎設施建設和氣象科普教育的同時,將氣象預警和應急信息傳播納入政府的重要工作當中,落實政府在氣象應急信息傳播中的主體責任,合理規劃并制定與本地相適宜的應急預案,不斷提升災害應急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逐步形成并完善由政府主導的氣象災害應急傳播機制新格局。
其次,應構建部門智能化聯動機制。突發氣象災害的防災減災不僅需要政府和氣象部門的協同共治,同時也需要國土、自然資源、水利、交通等部門的信息共享和聯動。因此,應建立智能化的各部門聯動機制,實現氣象信息和地域環境等資源信息的整合,繼而進行智能化數據處理和分析,并在第一時間完成相應氣象預警和應急信息發布,及時為公眾提供災害風險相關信息、防范措施等服務保障。
最后,應實現社會公眾能動參與。在突發氣象災害事件中,公眾往往是以受傳者的身份被給予預警信息和災害救助,并沒有面對未知風險的警惕和尋求自救的能力。因此,將公眾信息納入突發氣象災害應急傳播機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增強其風險意識,把公眾“要我安全”的思想轉變為“我要安全”,這樣才能夠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
(二)構建智能數據庫:災害監測、輿情探析、信息糾偏
在環境不確定性激增和信息不對稱的情境下,為緩解公眾緊張焦慮情緒,媒體應依托大數據等前沿技術進行輿情信息挖掘與整合,及時獲取并發布災害相關信息,更好地滿足公眾在突發性氣象災害期間的信息需求。
首先,通過智能檢測將公眾參與納入災害預警系統。作為防災減災工作的“第一道防線”,及時、高效的氣象預報和預警信息,可以在突發災害來臨之際警示公眾做好防護的同時為救災工作提供重要科學依據。例如,2022年夏季重慶山火的首發信息,是《人民日報》從重慶涪陵市民處獲悉而發布的,通過智能化的輿情監測,并由記者進行事實信息核實,實現了預警信息的實時發送。
其次,通過智能挖掘來把握瞬息萬變的輿情走勢。為應對信息的不對稱性而誘發公眾的極端情緒和集合行為,政府及主流媒體作為意識形態建設和傳播的重要陣地,應精準把握輿情,通過大數據技術實現對輿情的全方位、全覆蓋、全過程監測,深入挖掘并識別互聯網中經由點贊和轉發而形成傳播趨勢的文章與視頻,在獲取最新災情信息、救災互助信息、網絡輿情動態信息的同時分析用戶情緒和態度,構建相關輿情數據庫,繼而進行高效輿情分析。
最后,通過智能抓取用戶反饋來建構應急信息糾偏模式。雖然人人都有“麥克風”的信息環境使謠言不斷滋生,但同時這些手持“麥克風”的公眾也可以成為破除謠言的自生力量,從而實現謠言自凈。例如,在突發性氣象災害進行應急傳播的關鍵時期,某些網絡意見領袖和網民的發聲及辟謠信息的發布大大提升了抗擊災情的效率。因此,在突發性事件中,媒體和相關部門可利用智能算法技術對網絡中的相關優質類自媒體發布的信息進行綜合分析,同時通過抓取公眾瀏覽、評論等數據建立用戶反饋數據模型,將公眾的謠言自凈能力納入自身應急信息數據系統,完善應急傳播信息的糾偏體系,為公眾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三)搭建智能傳播平臺:精準推送、多元渠道、場景建構
傳統的突發氣象災害應急信息以報刊和電視等傳統媒體為主要傳播平臺,內容生產模式較為單一。智能媒體的發展催化出公眾多元的閱讀需求和媒介接觸習慣,災害應急信息的生產應當由單一的文本模式向多元化的表現形式轉變,為公眾提供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的信息,以便公眾更好地適應突發事件中周邊環境的變化。
首先,通過個性化算法推薦來滿足公眾差異化訴求。回顧傳統媒體時代,媒體應對突發氣象災害事件所發布的應急信息和科普相關內容等“千人一面”,在信息獲取不對稱的環境之下無法滿足不同受災情況和不同知識背景的多元用戶需求。因此,災害應急信息的制作應根據用戶的不同特征精準生產相應內容,而后將內容信息與用戶畫像實現精準匹配,并通過算法技術進行“點對點”推送,避免冗余的氣象預警等應急信息,滿足公眾個性化的信息獲取需求。
其次,通過全媒體渠道融合呈現應急信息全貌。在社交媒體時代,碎片化、過度冗余的信息充斥著網絡,造成有效信息的匱乏,使公眾在突發性氣象災害發生時無法高效、準確地知悉所需信息。媒體應改變內容生產方式,將災害應急信息按照各媒體平臺的不同特性進行差異化生產,利用智能算法技術進行全媒體渠道融合,實現不同形態碎片內容的精準投放。這種全媒體化的形式看似碎片化,實則通過不同的形式與受眾形成了直接交流互動,可以共同將“碎片”進行積累甚至共同再創造,逐步還原突發氣象災害事件的全貌,幫助公眾高效提取有用信息。
最后,通過多感官智能調動實現多元場景建構。因專業壁壘的限制,普通公眾無法理解氣象災害的各類專業術語,極易削弱應急信息的傳播效果。在氣象類災害預警和科普信息生產過程中,應針對其涵蓋的專業類知識進行智能簡化講解,通過智能算法分析用戶數據,在傳播內容中添加公眾易理解的聲音、動畫影像等新的媒體形式,調動公眾感官,將原本晦澀難懂的知識轉化為更易于接受和理解的信息。此外,還可合理利用增強現實技術(AR)、虛擬現實技術(VR)及智能定位系統LBS等新技術,基于用戶定位數據進行精準的可視化呈現,為公眾構建更加真實的信息獲取場景和實質性救災指引,消除環境的不確定性。
四、結語
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的迅猛發展使人類進入智媒時代,這導致在互聯網時代初有成效的突發氣象災害應急傳播體系遇到了新的挑戰,優質應急信息的稀缺和謠言的不斷滋生都在倒逼該體系向更加智能化的方向發展。因此,有必要借助大數據等技術,因勢利導組建智能化應急傳播隊伍、建設信息生產與發布的數據庫和多元化的傳播平臺,讓氣象災害的應急傳播機制趨于智能化以應對新時期數字化革新的挑戰,以期為公眾提供切實有效的信息和安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