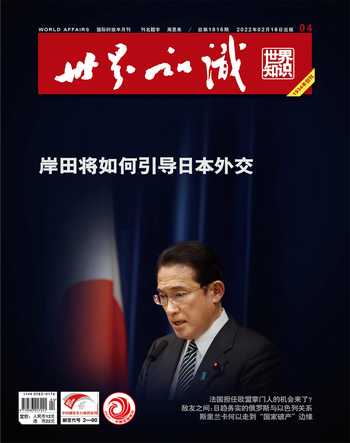能源困境或重塑歐洲能源格局
王曉光

2021年12月12日,德國外長貝爾伯克表示,“北溪-2號”管道無法以目前的形式獲批。次日,歐洲天然氣期貨價格飆升11%。圖為“北溪-2號”位于德國的管道設施。
從2021年秋天開始的歐洲能源危機并未隨公眾關注度緩和而消逝。相反,一些歐洲國家的冬天繼續被能源問題困擾,其中以英國、德國為甚。加上歐洲東部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緊張局勢不斷升級,歐盟能源困境持續引發深思,或許這個冬天將成為未來數年歐洲能源政策的轉折點。
如果說在這個冬天還有比新冠疫情更讓英國政府頭疼的議題,那么非能源問題莫屬。預計2022年春天來到時,英國每個家庭在過去一年的能源支出將超過2000英鎊,且預計2021~2022年冬天英國將有超過五分之一的家庭面臨燃料短缺的問題。能源價格暴漲已經使得英國多家能源經銷商倒閉,而這些經銷商承擔著數以百萬計消費者的能源供應。英國政府已經著手對部分能源公司施行政策上的救助,協調金融機構提供第三方的資金支持。英國的能源短缺問題已遠遠超過取暖等傳統的領域,很可能將通過產業鏈向制造業、化肥等領域蔓延。據多家民意調查機構的研究顯示,英國的能源危機程度之深已對政治產生明顯影響,不少選區的政治傾向很可能因為能源問題產生逆轉。目前,反對黨工黨要求約翰遜政府為家用能源削減增值稅,同時財政部長蘇納克則考慮對北海油氣生產商增加稅收,以此支援家用能源減稅計劃。但由于能源價格上漲過快,這些方式都收效甚微。當初約翰遜主張的脫歐條款中本就有減少國內能源增值稅的政見,不過僅為最貧困的家庭削減能源支出,而非全部的英國家庭。現在工黨就擴大該項稅收減免范圍向約翰遜政府施壓,令約翰遜政府感到進退維谷。
近期,是否向德國提供緊急天然氣供應問題引發德國、荷蘭兩國爭議。出于對地震風險和減排的考慮,荷蘭政府曾于2018年宣布將努力在2030年前關閉已有超過60年歷史的格羅寧根氣田,但由于2021~2022年冬季歐洲能源嚴重短缺,德國要求荷蘭格羅寧根氣田額外提供11億立方米的天然氣,這令荷蘭方面十分為難。1月13日,在與德國新任總理朔爾茨的會面中,荷蘭總理呂特委婉表示德國需減少并逐步放棄從格羅寧根氣田進口天然氣。從地緣政治上來說,圍繞烏克蘭問題不斷升級的俄羅斯和西方的緊張關系加劇了德國能源供應短缺的局面。從2021年秋季開始,俄羅斯就不再為歐洲市場提供長期合同之外的額外天然氣出口份額。俄羅斯原本意圖通過此舉推動歐盟快速通過對“北溪-2號”項目的審批,但是德國新政府組建后,綠黨籍的外交部長表示“北溪-2號”項目與歐盟法律相違背,因此德國一度延宕這一項目的審批。對于歐洲來說,“北溪-2號”每年能夠增加550億立方米天然氣供應,但目前俄羅斯和烏克蘭間的緊張局勢無疑使得“北溪-2號”項目前景充滿不確定性。
歐盟在能源危機背景下開始調整能源轉型的節奏。歐盟委員會計劃,將一些天然氣和核能項目納入歐盟的《可持續金融分類法》(該分類旨在幫助投資者實現低碳投資,公司實現低碳轉型,引導歐洲向低碳經濟轉型),在可持續金融投資的名錄上暫時為核能和天然氣保留一席之地,核能和天然氣能夠保持“過渡性”綠色能源身份分別至2045年和2030年。但是,由于核能會產生難以處理的核廢料,而天然氣仍屬于化石能源,因此這一舉動遭到一些成員國官員和環保組織的批評,稱這是赤裸裸地為核能和天然氣進行“洗綠”(Greenwashing)。有分析認為,歐盟委員會這一計劃受到了核能大國法國的影響,南歐和東歐國家也持支持態度。一直以核能為能源基石的法國在近幾年風雨飄搖的歐洲能源市場中是相對穩定的因素,這讓積極推動能源轉型的激進派頗為尷尬。
眾所周知,歐盟早期的合作起源于能源合作(比如建立歐洲煤鋼共同體和歐洲原子能機構),但歐盟的能源政策卻在發展中卻不斷扭曲,到今天成為最支離破碎的政策領域。這是一個長期困擾歐洲能源的政治謎題。實際上,歐洲戰后的煤鋼共同體無論是對于能源的定義還是能源涵蓋范圍,和今天相比都已大相徑庭。煤鋼共同體主要涉及的能源是煤炭,兼顧和煤炭密切相關的鋼鐵產業,與其說是一個能源機構,不如說是一個行業機構更為確切,最初的成員國也僅有西歐六國(法、西德、意、比、盧、荷)。當時石油已經悄然成為能源新貴,而天然氣和核能尚未嶄露頭角。應該說,歐洲煤鋼共同體誕生在一個能源大變局的前夜。
亞洲鋼鐵業崛起之后,歐洲煤鋼共同體的影響力和作用逐漸下降。后來世界能源格局發生變化,1973年發生石油危機,核能和天然氣登上歷史舞臺,然而在整個歐洲層面上并未就此在制度上給予回應,反而是各個成員國和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能源署在應對石油危機中發揮了主要作用。上個世紀80年代,德洛爾擔任歐委會主席期間,歐盟能源政策以能源市場自由化為引領。本世紀以來,歐盟能源政策則是以氣候變化和碳減排為引領。但試圖改變歐洲能源格局的努力非但沒有讓歐洲能源安全得到強化,反而讓歐盟對能源的供應和價格更為敏感,資源的來源變得更為緊張。此外,不斷擴大的歐盟成員國范圍也讓歐盟的整體能源規劃不得不面臨一次又一次調整,如在容克于2014年出任歐盟委員會主席后,其推出的“能源聯盟”計劃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解決新入盟的東歐國家的兩個能源問題,一是在能源來源上嚴重依賴俄羅斯,二是和西歐能源網絡在基礎設施上過于隔絕。雖然多位歐委會主席都立志于整合歐盟的能源政策,但是結果并不令人滿意。
這次歐洲所經歷的長時間能源危機很可能對未來歐洲的能源格局產生重大的影響。首先,經過這個冬天,俄羅斯能源在歐洲已被高度政治化,俄羅斯(包括蘇聯)超過70年穩定的對歐能源輸出很可能遭遇重大轉折,特別是如果俄羅斯和烏克蘭爆發武裝沖突,那么俄對歐能源輸出這條跨越了冷戰的經濟鏈接可能將逐步成為歷史。
第二,歐洲本土的傳統能源開發可能會迎來一個相對友好的時期,至少在短時間內核能和天然氣作為能源轉型的過渡方案會獲得認可,同時煤炭退出的速度也會被控制在一個合理的范圍內,在南歐和東歐國家更是如此。
第三,歐洲和美國在能源上的合作關系將進一步強化,除了美國未來可能在對歐能源輸出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一些比較受美國支持且帶有地緣政治色彩的能源開發項目將得到更多的關注,如東地中海天然氣、挪威極北地區天然氣開發等。